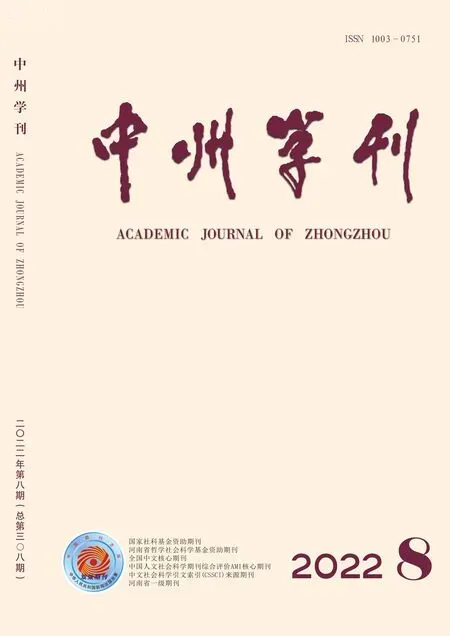論北宋科舉士人的身份建構與審美思想的轉變*
李 昌 舒
鑒于晚唐五代的武人之禍,北宋立國之初就確立了抑武崇文的基本國策。崇文的一個主要舉措就是將隋唐以來的科舉制發揚光大,這意味著在君主專政的封建體制中,政治的主導力量由魏晉以來的門閥士族轉為經由科舉選拔的庶族士人。這就是學界常說的唐宋轉型,其中的關鍵因素是科舉制。金錚說:“唐代科舉尚不夠成熟的表現,一是權貴豪門操縱的‘通榜’、‘公薦’辦法,意味著前期封建社會世族與庶族分離的狀況尚未打破;二是進士名額很少,科舉出身還不是入仕的最基本途徑,意味著后期封建社會典型的文官政治尚未建立。”“北宋科舉較之唐代科舉大大發展了一步,基本上脫棄了前期封建社會薦舉制的殘余,對后期封建社會整個社會結構、文化形態的最終形成發生了重大的作用。如果說科舉制度在歷史上經過長期孕育而在唐代脫胎成形的話,那么科舉制度的成熟定型則是在北宋……北宋科舉的一系列條規和立法,元、明、清三代都遞相承襲,即令有所變化,也不過是在北宋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擴展罷了。”在此意義上,研究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的政治、思想、文藝,需要重視北宋科舉制。本文嘗試探討科舉對北宋士人精神的影響,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審美流變。
一、北宋科舉對“道”“德”的推崇
學界對宋代文化有一個基本概括,即“宋學”或“宋型文化”,其奠定者是范仲淹、歐陽修等一批在仁宗慶歷年間主導政壇的士人。慶歷四年(1044年)的“慶歷新政”雖然持續時間短暫,但影響深遠,下面一段話頗具代表性:“即便說到唐宋變革,也還要提示一種見解的存在,就是在思想史上,宋代之為宋代,是從北宋慶歷年間開始的。也就是說,‘唐宋變革’這句話中的‘宋’,其內容體現在慶歷以后。”宋初三朝,主要是對科舉的機制和方式加以完善。從真宗開始,考試內容由之前的詩賦逐漸轉向儒家經典。在這種思想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士人到了仁宗慶歷年間,作為一個群體登上政治舞臺,他們普遍重視儒學以及與儒學相適應的古文。二者互為表里,以“文”為形式,以“道”為內核。
慶歷士人所推崇的“道”不僅僅是純粹的理論,更多的是強烈的濟世精神。范仲淹在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所作的《奏上時務書》成為“慶歷新政”的施政綱領。其中關于文學的思想是:“臣聞國之文章,應于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況我圣朝千載而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范仲淹的觀點很明確:復興古道,振作文章,從而改變風俗教化。在更為激進的石介那里,“斯文”與“斯道”是直接等同的,雖然歐陽修曾批評過石介的書法和文風,但就復興儒學、干時濟世的思想而言,二者是一致的。程杰說:“由于統一于社會政教、士人精神的建構過程,北宋詩文革新首先表現為文學禮樂教化、‘治教政令’功能的強化。隋唐以來士人沉溺個人情感,只知文章技藝余不知所向的‘才士’的、‘純文學’的心理性格受到普遍的反省和否定,文以載道、文章系乎治亂、文章關乎教化的傳統儒家文學思想得到確認與尊祟,為文立言越來越要求能‘左右名教,夾輔圣人’,服務政治,‘有補于世’。”因此,“文”與“道”的關系在北宋中期是緊密相融的,幾乎所有的士人,無論是后世所區分的道學家,還是文學家,都發表過關于“文”與“道”關系的言論,雖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幾乎都是以“道”作為“文”的內核,都以積極入世、有益教化為目的。
“道德”在今天是一個詞,但從詞義上講,二者是有區別的,“道”側重于社會的、政治的,“德”則更多是個人的、倫理的。二者又是緊密相連的,遵從社會的“道”必須完善個人的“德”,只有從個人之“德”出發,才能實現社會之“道”,換句話說,社會之“道”的實現要以個人之“德”的完善為前提。北宋士人大多并不強調二者的區分,而是對二者同等重視。就文學而言,為了傳播、宣揚“道”,就需要修養個人之“德”。作為“北宋五子”的第一人,周敦頤的這段話是論者經常引用的:“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作為北宋中期的文壇盟主、古文運動的旗幟,歐陽修《答祖擇之書》這段話可以視為北宋文學家的代表:“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于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于事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這兩段話經常被用來作為北宋道學家和文學家關于文學觀念的區別,其實二者的相似性大于相異性,都是強調文章必須以道德為根本,為內容。
隨著時代的發展,作為二人弟子的程顥、程頤兄弟和蘇軾、蘇轍兄弟分別將“道”與“文”發展到更高層次,“道”與“文”的矛盾凸顯出來,于是有了后世所說的“周程、歐蘇之裂”,也就是道學家與文學家的分裂。但回到歷史事實,這種分裂既有學術觀念的不同,更多的則是黨爭以及意氣用事的因素。程顥本人就有很多詩作,蘇軾兄弟又何嘗不重視道德修養?一個有趣的案例是,當有人將蘇軾視為純粹的文學家時,秦觀挺身而出為老師辯護:“蘇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于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美國漢學家包弼德的一段話可謂直探本源:“不論蘇氏父子和程氏兄弟后來變得多么不同,在1057年的時候,他們有許多共同的渴望。他們所感興趣的圣人是一個在做事之中保持道德的個人。他們在探求人們可以共同享有什么觀念,這些觀念可以在所有的環境中指導他們。他們試圖構想一種道德無瑕,同時又參與世務的學者。這就等于在為個人的道德自主尋找根據。這毫無疑問是早先古文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現在對那種根據的尋求已經成為一個嚴肅的思想目標。大概在1057年,他們對當時流行的觀念進行反思,即一個有道德追求的年輕人,什么樣的目標適合他。他們雙方無疑都繼承了歐陽修在成熟階段對個體的關心。”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士族并不過分突出道德修養的要求,因為一則九品中正制本身就包含了對道德的考察,二則士族有家族儀軌可以制約。科舉選拔的北宋士人則主要依靠自己,他們需要“為個人的道德自主尋找根據”。因為科舉制并不涉及對應舉者的道德考察,作為改造社會、移風易俗的主體,士人只能通過自己的努力以及共同體的輿論約束,實現道德的完善。于是,魏晉南北朝的通脫風流轉變為北宋慶歷以后的嚴謹自律。
陳寅恪先生指出,傳統士族具有“門風之優美”,而通過科舉躋身仕途的士人多有“逞才放浪之習氣”。在北宋,士族已經基本退出政治舞臺,科舉士人成為政治主體,如何約束這種習氣成為一個嚴峻而迫切的問題。余英時先生說:“知識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勢’更尊,所以根據‘道’的標準來批評政治、社會從此便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分內之事。……由于‘道’缺乏具體的形式,知識分子只有通過個人的自愛、自重才能尊顯他們所代表的‘道’,此外便別無可靠的保證。中國知識分子自始即注重個人的內心修養,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這段話對于科舉出身的北宋士人是特別適合的,正如歐陽修《朋黨論》所說:“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
從中唐到北宋,有一個顯著的“孟子的‘升格運動’”,這與慶歷士人密切相關。“孟子升格運動被重新喚起,那是在宋仁宗的慶歷之際。當時,伴隨著政治上求變呼聲的高漲和‘新政’的一度施行,學壇上出現了一股社會思潮,而‘尊孟’也成為這一思潮的取向之一……在慶歷思潮的有力推動下,‘尊孟’成為當時學者流行的學術取向。”孟子之所以獲得升格,既有文體的因素,更有思想的因素。從前者來看,議論為主的散文文體是古文的典范;從后者來看,孟子對集義與道于一身的浩然之氣的追求與新型士人的道德自律相契合。
這里引用一個有趣的案例以作說明。仁宗嘉祐六年,蘇轍與兄長蘇軾同時參加“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的制舉考試,蘇轍在答卷中認為當今皇帝好色懶政,勞民傷財,好邀虛名,將仁宗和執政大臣罵得體無完膚。他自己也認為言之太過,會因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為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仁宗堅持留用,并且在任命書中有這樣一段話:“而轍也指陳其微,甚直不阿。雖文采未極,條實未究,亦可謂知愛君矣。”這個事件對于那些準備應舉者和通過科舉出仕為官者的影響是意味深長的。在仁宗以及北宋大多數君主的寬仁統治下,士人從讀書伊始就以道德作為評判標準,甚至是在參加科舉考試中對君主直言不諱,并通過這種特殊的“愛君”方式獲得功名。我們翻檢宋人文集,可以發現,指摘君主、議論朝政可以說蔚然成風,這也就是學界常說的“宋人好議”。這既是君主“異論相攪”有意引導的結果,也是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表現,而推動這一現象的指揮棒則是科舉制。需要說明的是,蘇轍應制舉的文章中引起軒然大波的主要是對仁宗道德的批評,既然如此,則士人自己的道德更是要經得起考驗。一個反面的佐證是,歐陽修在攻訐對手時屢屢以私德作為證據,他自己也屢次因私德被對手攻擊,直至最后因此而退出政治舞臺,郁郁而終。這在此前魏晉隋唐時代是難以想象的,充分說明對道德完美的要求已經是北宋士人共同體的一種普遍共識。
二、道德與審美的沖突及消解
道德與審美,或者說善與美的關系是古今中外美學史的一個基本問題。對于北宋這些經由科舉而出仕的士人而言,對道德的重視必然影響到審美。蘇軾借用孔子的話評價范仲淹說:“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于口者也。”將道德視為文藝的根本,推崇文藝的教化作用,這是北宋士人的普遍觀點,這是學界已有充分探討的,此處需要展開討論的是,由“重道”而“輕技”的審美創作論。歐陽修《答吳充秀才書》:“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于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這是明顯的由“重道”而“輕技”。雖然作為古文運動的領袖,歐陽修的文學成就足以使其成為“文壇盟主”,但他對于技法的警惕意味著與六朝隋唐以來的文人有很大區別,這是北宋士人的一個突出特點。黃庭堅說:“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極當加意,養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后枝葉茂爾。”這是“重道”。他又說:“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于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這是“輕技”。“無意于文”可以說是大多數文學家的基本觀點,不僅如此,也可以說“無意于書”“無意于畫”,等等。類似的表述在北宋士人文集中不勝枚舉。南宋費袞的這段話是對北宋這一審美觀的總結:
書與畫皆一技耳,前輩多能之,特游戲其間,后之好事者爭譽其工,而未知所以取書畫之法也。夫論書當論氣節,論畫當論風味。凡其人持身之端方,立朝之剛正,下筆為書,得之者自應生敬,況其字畫之工哉?至于學問文章之余,寫出無聲之詩,玩其蕭然,筆墨間足以想見其為人,此乃可寶。而流俗不問何人,見用筆稍佳者則珍藏之,茍非其人,特一畫工,所能何足貴也?如崇寧大臣以書名者后人往往唾去,而東坡所作枯木竹石萬金爭售,顧非以其人而輕重哉!蓄書畫者當以予言而求之。
崇寧為徽宗年號,崇寧大臣當指蔡京等人。這段話可注意者有二:一是人品決定書品、畫品,道德是審美的根基;二是士人應該以游戲的態度對待書畫,不應沉迷技法。顯然,這是承續北宋士人的“重道”而“輕技”觀點。蘇軾的“枯木竹石”為后世所珍貴,顯然并非出于繪畫技法,而是道德人品的推崇。就技法而言,蘇軾的書、畫并非上乘,時人以及蘇軾自己對此都有清醒的認識,但后世卻將他作為宋人書法四大家(即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的第一人,這種評價也是著重于道德而非技法本身。
形成這一評價標準的原因很明確,對于這些出身平民卻能出入朝堂的北宋士人而言,社稷蒼生才是最重要的,其中的關鍵就是科舉制。科舉制使北宋士人處在一個中國古代歷史上空前絕后的政治地位最高的時代。左思身處門閥士族的西晉,悲鳴“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詠史》)。孟浩然身處盛唐,但科舉落第,布衣終身,只能感慨:“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望洞庭湖贈張丞相》)雖然孟浩然被李白視為“高山安可仰”(《贈孟浩然》)的高士,但正如聞一多先生所言,他的內心其實是矛盾的。
與前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因為科舉的普及,北宋士人滿懷理想和激情。范仲淹、歐陽修等人就是成功的典型,二人都是幼年喪父,由寡母投奔他人而得以生存,通過發憤讀書,科舉及第,出入將相。科舉使他們的命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最重視為社稷蒼生的獻身精神,以及與這種獻身精神直接相關的兼濟之道與獨善之德。一切文化、審美都必然要為“道”“德”服務,創作技法自然不被重視,甚至被有意排斥。
美國漢學家艾朗諾認為:“精英知識階層鄙視對文藝技巧所流露出的興趣,這一情況并不僅僅存在于古代的中國。但可以說,這種偏見在中國非常強大,在宋代的精英階層中尤為根深蒂固。11世紀,科舉考試的空前重要性很可能加劇了學者對留心寫作技巧行為的輕視。文章取士鼓勵人們潛心于寫作技巧,而精通文學的學者對這些技巧極為蔑視。對單純的寫作技巧感興趣,而不是把寫作當成與晉升無關的崇高事業,這樣的行為被定義為‘俗’。”“俗”會威脅到士人的身份,柳永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柳永在實踐這一新的言情方式時表現得格外大膽:他敢于做一個先行者。不過,他也為自己作為先行者革新詞壇的原創行為付出了沉重代價:他的社會身份遭到質疑,他本人為整個士大夫階層所不容。”在北宋士人看來,道德是士人的根本追求,如果沉迷于“藝”,會被視為玩物喪志,違背孔子所確立的“士志于道”的標準。但這并不妨礙北宋審美的繁榮,作為“文-官”雙重身份的士人,無論是作為官員的政治表達,還是作為文人的私人生活,“文”都是“不可須臾離”的基本途徑。例如蘇軾,給皇帝上萬言書,獻言建策,寫詩批評新法帶來的弊端,這是其作為“官”的表達;詩詞酬唱,以文會友,書畫著述,消愁解憂,這是其“文”的生活。“官”也許有得失窮通,“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文說》)。在此意義上,審美的繁榮是必然的。
正因為如此,北宋士人的謚號大多有“文”,這種意義上的“文”直接與儒家思想相關。例如,范仲淹和司馬光都是“文正”,王安石是“文”,歐陽修和蘇軾都是“文忠”,曾鞏和蘇轍都是“文定”。“文”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十分重要的范疇。孔子承續周公制定禮樂,其基本理念是:“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篇》)《周易》云:“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雖然作為治國方針的“文”與今天的文藝之“文”有很大差異,但可以說,經天緯地之“文”包含了各種文化、思想,也包含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文學、藝術。“在表達古典儒家關于自然秩序的概念時出現、與儒家的道相聯系、表示形的觀念是“文”,它的意思是‘描畫’、‘型式’和‘紋理’。就像天將它們的美麗表現為‘天文’,作為‘天地之心’的人類將他們的成就表現為‘文化’。‘文’是‘紋理’,它兼有美學的價值和意義。”艾朗諾面對北宋五彩紛呈、眼花繚亂的“文”,謹慎而敏銳地區分出“君子之文”和“文人之文”,即與“官”的身份相應的“載道之文”和與“文”的身份相應的“審美之文”。無論是哪一種“文”,實際的結果是北宋士人在內憂外患、紛爭不已的一百多年間創造出燦爛的文化。
三、科舉士人的審美思想:區分與融合
從上面論述可以看出,士人“文”與“官”的兩種身份之間既有區分,也有融合,在這種區分與融合中,形成北宋士人特有的審美趣味。
1.
北宋士人以天下為己任,憂患意識是貫穿于北宋中后期士人的一個基本思想,上到國家大事,小到個人修養,都是他們寤寐思之的問題。在宋人文集中,憂患與焦慮是基本主題。在此意義上,審美的一個重要功用就是緩解這種憂患與焦慮。孔子早就說過:(士)“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雖然孔子所說的“游”并非游戲,“藝”也不同于現代學科的藝術。但早在唐代,就已經出現有意的“誤讀”,將“游于藝”解讀為游憩于藝術。宋代審美繁榮,與士人“游于藝”的需要相關。郭熙道出了士人的心聲:“世之篤論:謂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畫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游、可居之為得。何者?觀今山川,地占數百里,可游、可居之處,十無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林泉者,正謂慕此處故也。故畫者當以此意造,而覽者又當以此意求之,此之謂不失其本意。”不僅是山水畫,其他各種文藝形態在宋代均得到重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們可以為士人營造可游、可居的精神游憩之地。北宋交游之發達,詩文酬唱之興盛,皆與此相關。在此意義上,審美成為士人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熊海英說:“活躍精妙的雅集創作不僅能見出北宋文人士大夫深厚的藝術修養、敏感的審美心靈和高超的藝術技巧,更顯示了其時詩歌、繪畫、書法等各種藝術門類的交融,和體現于其中的共同審美傾向。而藝術活動的多方面開展和創新表現,成為北宋士大夫生活形態、精神風貌的一個特點。”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文人之文”不能影響、損害士人的兼濟事業,換言之,“藝”不能妨礙“道”,借用程頤的話說,就是不能“作文害道”。茲以書法為例。作為基本的寫作方式,古人歷來對書法很重視,北宋士人同樣如此,但他們時刻不能忘記士人的社會責任。因此,一方面,他們不可避免地承襲前人慣性,喜愛書法;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反復強調練習書法只是“要于自適而已”。歐陽修說:“有暇即學書,非以求藝之精,直勝勞心于他事爾。以此知不寓心于物者,真所謂至人也;寓于有益者,君子也;寓于伐性汩情而為害者,愚惑之人也。學書不能不勞,獨不害情性耳,要得靜中之樂者惟此耳。”蘇軾說:“筆墨之際,托于有形,有形則有弊,茍不至于無,而自樂于一時,聊寓其心,忘憂晚歲。”這也是北宋大多數士人的態度。
“北宋的士大夫們在留心詩詞翰墨的同時,也對自己沉迷于‘藝’的行為表現出一些焦慮和不安。”我們可以米芾為例,從反面印證這一點。米芾在書畫方面成就很高,書法位居宋四家之列。曹寶麟說:“四人之中,蘇黃蔡皆以余事臨池,他們的精力和興趣,更多地放在立事和立言之上。只有米芾,似乎在現代觀念上才堪稱純粹的書家。”從米芾的人生態度看,他完全放棄了北宋士人的濟世情懷和憂患意識。他向往晉人風流,以“寶晉齋”為齋號,而晉代名士正是以不屑世事之“俗物”著稱,米芾推崇備至的王獻之就是一個典型。米芾處世以“癲”著稱,他對書法、繪畫等文藝作品的癡迷與對官員事務的懈怠,不僅意味著他是一位“純粹的書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他是北宋士人精神萎縮的典型。對米芾贊賞有加的徽宗是另一個典型,他對審美的癡迷已影響了其作為國君應該承擔的責任,越過了歐陽修、蘇軾等人刻意與審美保持的距離。如果說身兼“文-官”兩重身份的士人需要在“道”與“藝”之間維持一種平衡,以避免影響到作為“官”的責任,那么徽宗作為一個國君,因為“留意”于“文”而成為一個有“文”而無“道”之君。
2.
科舉出身的士人因為出身庶族,缺乏門閥士族的天然優勢,只能通過“文”來維持身份。因此,嚴格區分雅俗之辨是士人審美的一個基本特點。學界對此已有充分探討,連心達對此有精審的闡釋:
宋人孜孜于忌俗尚雅,事關能否保持其賴以生存的作為社會精英的自身特殊屬性。科舉制度在宋代的最終確立完善,使中下層人士向上流動成為常態,但這并未導致階級階層之間界限的消失……溫斯頓·羅在對宋代科舉及官制的研究中指出,除了在政府官僚系統中的作用之外,宋代士大夫還得扮演一個不可忽視的“形而上”的角色,即作為“國家民族智慧之積累的儲備力量”與“保證這個朝代的合法性、權威及穩定的偉大傳統的傳承者”。這個朝代需要“一個在性格氣質上能比之于前代門閥的文官人群”。士大夫因此被“授予”一種名望,一種“舍之其誰”的功能性特權。據此,士人對有損其氣質或可能破壞其道德文化權威的來自各方面的“俗”的高度警惕與自覺抵制,就很可以理解了。茲事體大,關系到其作為精英階層的存亡。
可見,雅俗之辨不僅是一種審美風格,其深層基礎是科舉制與士人身份建構。科舉一方面使得庶族士人得以自由流動,有機會進入社會上層;但另一方面,這種自由流動又意味著傳統門閥士族天然的身份保障已經消失,只能通過其他途徑來維持其精英身份的地位,而教育作為一種布爾迪厄所說的“符號暴力”,是維持社會再生產的必要工具。“教育系統實際上是一套圣化/排斥機制。通過文化專斷性的壟斷,它將一些特殊的文化賦予普遍意義,而對另一些特殊文化則大加鞭撻或視若無物。”無論是科舉及第進入仕途還是落第未仕者,北宋士人作為一個新型群體,在朝野上下,在官方和民間,共同構成一個重要而特殊的群體,雅俗之辨可以說是這種“圣化/排斥機制”在審美方面的典型體現。北宋士人關于雅俗之辨的表述不勝枚舉,最有代表性的是蘇軾的“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蘇軾《于潛僧綠筠軒》)與黃庭堅的“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書繒卷后》)。
值得注意的是,蘇軾和黃庭堅都是將“反俗”與士人身份的建構聯系在一起。一方面,宋代市民階層生活繁榮,與市民相關的文化藝術也相應發達;另一方面,精英階層大多出身庶族,如何在身份上維持自己與他者的“區分”,是士人在建構自己身份時需要面對的一個基本問題。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審美中的雅俗之辨是北宋士人對自己身份的一種維護。布爾迪厄說:“趣味進行分類,為實行分類的人分類:社會主體通過他們對美與丑、優雅與粗俗所做的區分而區分開來,他們在客觀分類中的位置便表達或體現在這些區分之中。”我們可以說,北宋士人從自己的身份出發,構建特定的審美趣味,當這種趣味一旦形成,又進一步強化、完善士人身份。
雅俗的區分并不是絕對的,我們從晏殊與柳永的不同遭遇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二人皆以詞聞名于世,遭遇卻是天壤之別:柳永前文已論,被士人階層摒棄;晏殊則是頗有成就的政治家,擔任過宰相、樞密使,達到士人在政治上的巔峰,成為士人仰望的對象。造成二人不同命運的關鍵也許就在于他們對待詞的不同態度:晏殊雖然填詞,但并不影響其作為“官”的責任,柳永則基本上以純粹的文人自居;寫作同樣的題材,晏殊能將其上升到一種人生體驗的層面,柳永則僅僅停留在男女之情的層面。借用王國維的觀點,也許可以說,晏殊之詞是“士大夫詞”,柳永之詞則是“伶工詞”。因此,區分雅俗的不是題材或內容,而是士人的態度。在此意義上,題材的雅與俗又是可以融合的。黃庭堅也有大量描寫男女私情的俚詞,但絲毫沒有影響其士人的地位,他“不僅成為柳永之后又一位發揚光大民間詞風格的重要作家,而且避去了前代部分艷詞的庸俗邪穢,并吸收弘揚了前代艷詞的淺理,進入了以故為新、以俗為雅、雅俗共賞的境界”。
3.
一方面,北宋士人將審美日常生活化,即將日常生活納入審美對象。正如蘇軾所說:“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镕化耳。”這個風氣肇始于中唐韓愈等人,就北宋而言,則由慶歷士人發起,在歐陽修、梅圣俞等人的筆下,日常瑣事、瑣物皆可入詩。這固然與宋代士人的出身有關,他們大多出身于普通家庭,在其科舉及第之前,對這些瑣碎事物司空見慣。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科舉及第之后的身份,即士人的態度。此時寫什么不再是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誰來寫,怎么寫。博學通識的北宋士人,可以憑借自己深厚的“文”的素養,即俗即雅,化俗為雅。
即便是在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北宋士人也能觀“理”悟“道”。蘇軾《觀棋》:“空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詩人在普通的對弈中體悟到深刻的官場和人生哲理。在日常飲酒中也能如此,蘇軾《濁醪有妙理賦》:“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北宋士人“文”的素養無處不在。蘇軾《書黃道輔品茶要錄后》:“物有畛而理無方,窮天下之辯,不足以盡一物之理。達者寓物以發其辯,則一物之變,可以盡南山之竹。學者觀物之極,而游于物之表,則何求而不得……今道輔無所發其辯,而寓之于茶,為世外淡泊之好,此以高韻輔精理者。”我們也可以接著蘇軾說:“無所發其辨,寓之于文、詩、書、畫,等等。”在北宋士人眼中,無論是什么“物”,皆可通過“一物之變”,盡萬物之“理”。換句話說,對理的認識即“辨”,若通過抽象的哲學演繹的方式,無窮無盡也不能完全表達,而寄寓于某一藝術門類即“物”,可以充分地闡釋“理”。其中最關鍵的是士人“文”的身份所形成的審美能力,通過它,士人可以從最普通的日常事物中發現“理”,享受審美的愉悅。
另一方面,宋代士人又努力使日常生活審美化,即將審美視為一種人生方式。歐陽修晚年在《六一居士傳》中,將“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和自己并稱為六個“一”。不同于市井之民,科舉出身的士人可以將自己的文化知識、審美素養轉化為一種能力,使自己的日常生活處處洋溢著文人雅趣。與歐陽修一起修《新唐書》的宋祁在《回李端明書》中說:“惟是平昔交游,以文史相樂者,每風月嘉踐,裴回念至,則怊然久不能平。”北宋時期出現的大量題畫詩,歐陽修等人首創的“金石學”,蘇軾、蘇轍與黃庭堅等人元祐時期的詩歌酬唱、賞畫題畫,等等,都意味著士人的日常生活逐漸趨向雅化。它既不同于魏晉士人醉生夢死、不問世事的風流,也不同于盛唐士人青春浪漫、熱烈奔放的激情,而是一種理性、內斂的優雅。
對于這些科舉出身的士人而言,優越的社會地位和雄厚的文化知識使得他們自覺建構一種與自己身份相關的“雅”的生活方式。經史子集、琴棋書畫、文房四寶、山水園林以及古代的石刻銘文,都成為士人公務之余或退老之后的欣賞對象。“文人階層從產生以來,其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就比普通百姓要更精致講究,而從詩歌、筆記和其它歷史文獻資料看來,到北宋,士大夫文人群體始自覺致力于日常生活的審美化,主要表現在有意識地營造詩意的生活環境,建立一種以人文活動為主要內容的休閑生活范式,和追求游心翰墨的人文旨趣、清雅脫俗的精神享受。”傳為李公麟所作的《西園雅集圖》充分表現了士人充滿審美趣味的日常生活方式,后世模仿者多不勝舉。衣若芬依照米芾的《圖記》,將《西園雅集》畫面布局加以分組:“人物的安排在畫面上大致被分為五組:第一組以蘇軾為中心,王詵、蔡肇、李之儀和蘇轍環繞在四周看蘇軾揮毫。第二組的主角李公麟執筆正畫著敘述陶淵明事跡的《歸去來圖》,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和鄭靖老在旁圍觀。第三組是秦觀坐在古檜下側聽道士陳景元彈阮。第四組有王欽臣仰觀米芾題石。第五組則畫了劉涇諦聽圓通大師高談無生論。”這是典型的日常生活審美化。繪畫中出現的主要是“文-官”士人,他們的生活方式由詩歌、書法、繪畫、音樂、賞石和佛法構成。誠如米芾在《西園雅集圖記》篇末所說:“人間清曠之樂,不過于此。嗟呼!洶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后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仿佛其人耳!”這是提醒觀畫者注意畫中人物“文”的身份,以及由此身份而形成的“清曠之樂”。
結 語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科舉給予了庶族士人躋身仕途、出將入相的機會,孔子的“學而優則仕”的理想在北宋成為現實。在此意義上,兼濟“道”與獨善之“德”成為士人關注的基本問題。與此相關的是“文”,“文”是科舉出身的士人的身份屬性,受道德的直接影響,由此又對審美產生影響,形成北宋審美的幾個重要特點。具體而言,即“道”與“藝”的區分與融合,“雅”與“俗”的區分與融合,日常生活和審美的融合。這種審美趣味在形成后,又成為建構士人身份的一個重要內容。
①陳植鍔:“所謂科舉,從形式上講……是政治制度之一種,但從內容上講,它自身又屬于文化的一部分。這里即側重后一方面講。分清科舉的這兩層意義十分重要,因為科舉作為一種取士制度,隋唐之際就已經開始了,為什么在北宋之前長達300多年的時間它就不能導致儒學的繁榮呢?即以有宋而論,建國伊始即已開科取士,緣何至仁宗初年才有宋學之勃起?可知作為一種制度的科舉取士和作為一種文化的科舉考試,在儒家傳統文化的發展史上所起作用的輕重大不相同。”參見陳植鍔:《北宋文化史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78頁。②參見歐陽修的《讀徂徠集》《重讀徂徠集》及《上杜中丞論舉官書》。③“所謂‘道’,其在物為客觀的‘理’,其在人為主體的‘德’。”參見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82頁。④類似的表述還有很多,如,歐陽修:“陋巷之士得以自高于王侯者,以道自貴也。”(《與焦千之書》)王安石:“士雖厄窮貧賤,而道不少屈于當世,其自信之篤、自待之重也如此。”(《與龔舍人書》)⑤參見聞一多《唐詩雜論·孟浩然》中的相關論述。⑥程杰認為,金石、藝文、山水、弈飲之類的習好與“復古明道”的思想尤其是儒家修身至善的道德信念有著潛在的矛盾。文化創造和生活享受、精神和物質的廣泛需求與“立德”至上的思想價值觀是否可以相互溝通,又如何調適一體,是宋代文化思想建設上的重要而又復雜的課題。這是更深一層面上的“文”“道”之爭。參見程杰:《北宋詩文革新研究》,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0頁。⑦蘇洵《謚法》卷一:“施而中理曰文”,“經緯天地曰文”,“敏而好學曰文”,“脩德來遠曰文”,“忠信接禮曰文”,“道德博聞曰文”,“剛柔相濟曰文”,“修治班制曰文”。⑧蘇軾的“君子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代表了北宋大多數文-官士人的審美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