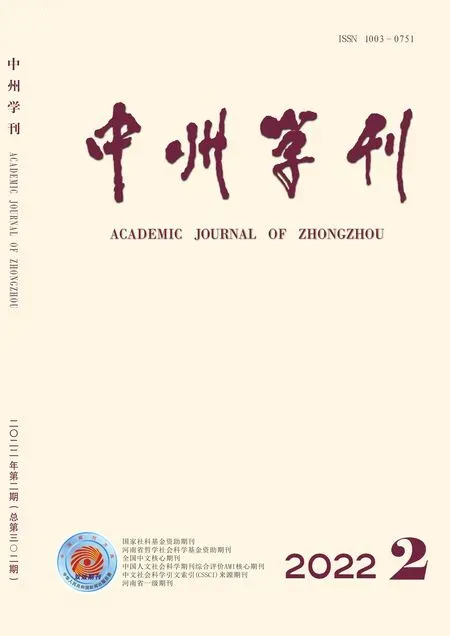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的理論重構及立法建議*
進入21世紀,我國加快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步伐。2007年原農業部發布《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在此基礎上,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集體產權改革意見》),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作了整體部署。目前,我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已經實現各省級單位全覆蓋,各地普遍成立了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組織振興是與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和生態振興相并列的五大核心目標之一。作為發展集體經濟的重要載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重要任務是通過內部治理機構的科學架構,奠定鄉村治理機制順暢運行的組織基礎。從實踐來看,各試點地方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的設置既有共性做法又有個性探索;在理論層面,學者們基于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不同認識,提出了關于其治理結構的不同改革思路。相關試點經驗和改革思路能否適用于全國各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文從實踐、理論、制度三個層面探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的設置,以期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立法提供參考。
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的模式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治理結構問題主要涉及其內部治理機構的功能定位和職權劃分,研究這一問題主要應考察兩個方面,即法律、政策中的制度設計和地方實踐中的具體操作。從制度設計來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治理結構存在一定的差異,出現差異的原因主要在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法律內涵泛化、法律定位不明確、各地經濟發展狀況不同等。從地方實踐來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存在照搬營利法人治理結構的傾向,形成這種傾向的原因主要在于人們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市場化的認識失之偏頗,相關法律、政策抽象化、模糊化,地方實踐經驗不足等。
(一)政策設計、法律規定的模式
基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律地位的變化,政策、法律上對其治理結構存在差異化設計。在《民法總則》頒布以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人地位并不明確,各地為了消除市場主體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律地位的疑問,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市場化發展,通過不同方式確認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人地位,如由地方政府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放法人證書,允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以農民專業合作社名義注冊登記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治理結構因法人資格取得路徑的不同而存在差異,如法人證書模式下的“政經合一”治理結構,傳統公司法人、合作社法人模式下偏向于營利法人的治理結構。此類治理結構的主要成因在于:第一,一些地方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法律內涵存在認識偏差,認為其包括農民專業合作社、集體企業等經濟組織,從而將此類經濟組織的治理結構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治理結構。第二,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律地位的立法缺失,由于缺乏統一的法律依據,不同地方政策指導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資格取得路徑不同,直接影響其治理結構存在差異。第三,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方實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村委會“政經合一”,而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方,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事務復雜化、專業化,有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村委會“政經分離”的需求和條件,隨著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獨立行使經營管理權,其治理結構偏向于營利法人。個別地方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已經改制為公司,其治理結構自然與營利法人的保持一致。《民法總則》頒布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特別法人地位得到法律確認,其以法人身份參與市場活動,因循市場化路徑,基本形成了“成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三會”)治理結構。
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是否具有開放性方面,相關政策、法律規定也存在差異。從國家有關政策的指導精神來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應保持適當的開放性。《集體產權改革意見》并未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治理結構,但強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當有別于一般工商企業。這為地方探索具有開放性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治理結構提供了空間,意味著各地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設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治理機構。農業農村部印發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示范章程(試行)》明確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大會、理事會和監事會為其治理機構,同時明確了成員代表大會設置的任意性,允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根據實際情況自行設置其他經營管理機構作為治理機構。該文件的規范層級和效力較低,其內容的開放性反映了地方實踐的復雜性及對適度開放性的要求。從地方性法規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示范章程來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治理結構呈現出有大量共同性兼具差異性的特點。2017年后一些省份出臺的地方性法規普遍規定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三會”治理結構,如《黑龍江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條例》第3章規定了“三會”的機構設置、職權范圍、會議制度,《四川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條例》第3章也有類似的內容。不同地方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各省份的地方性法規普遍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同時設置成員大會和成員代表大會,其中成員大會是必備的,是否設置成員代表大會由當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章程決定,依此,很多地方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示范章程都規定設置成員大會和成員代表大會,個別地方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示范章程規定僅設置成員代表大會而不設置成員大會;二是各地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大會與成員代表大會關系的界定主要有三類,即成員代表大會全面替代成員大會、成員大會與成員代表大會關系模糊、成員大會的地位高于成員代表大會;三是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治理機構的地方性立法模式主要有列舉式和“概括+列舉”式,通過文義解釋和體系解釋可知,前一模式下可以通過當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章程的兜底性條款調整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治理機構,從而使治理機構的設置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后一模式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治理機構的類型限定于概括性法條規定的類型,使得治理結構呈現出一定的僵化性。
綜上所述,在《民法總則》頒布以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人地位處于模糊狀態,相關政策規定只是特定法律環境下的權宜之計,難以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特別法人治理結構的設置提供有力的支撐依據。同時,由于相關政策指導和法律設計的差異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法律內涵、治理結構等問題復雜化,不利于建構統一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制度。《民法總則》頒布后,以“三會”為主、其他經營管理機構為輔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成為相關改革實踐中的主流模式。
(二)地方實踐中的共性模式與個性探索
《民法總則》頒布后,各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基本模式相同,即普遍直接照搬公司、農民專業合作社等經濟組織的治理結構;二是具體模式有差異,即一些地方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有獨特的治理結構,或者說設置了比較獨特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機構。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各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基本按照相關政策設計和法律規定,采取“權力機構—執行機構—監督機構”的治理結構,只在具體治理機構的設置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如有的同時設置權力機構和執行機構,有的僅設置權力機構而不設置執行機構;第二,各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的設置沿用既有經濟組織治理結構的設置路徑,未能擺脫公司、農民專業合作社等經濟組織治理結構的影響,難以體現改革的階段性要求和漸進性特征,不利于呼應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治理的需求。
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的理論爭議
地方實踐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制度完善提供了現實基礎,相關實踐經驗能不能、如何通過統一的立法予以妥當的體現,對此需進行充分的論證。理論界關于通過立法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進行表達的爭議點在于,如何實現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特別性與一般法人治理結構之間的平衡,換言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特別性是否會直接影響其治理結構制度設計?圍繞這一問題,學者們主要有以下兩種觀點。
(一)公司構造論:模仿現代公司的治理結構




(二)國企模仿論:突出黨組織的領導作用
在公有制框架內構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以國有企業的黨組織嵌入國有企業治理為模型,強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集體所有制經濟載體的主體地位和主體構造,本文將這種觀點稱為“國企模仿論”。


“國企模仿論”的兩種觀點對村黨組織參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內部治理的方式也存在不同認識。“黨組織嵌入論”認為村級組織只有一個黨組織,即村黨支部,其可以作為治理機構直接參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內部治理;“黨組織領導論”則認為村黨組織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內部的黨支部是兩個黨組織,村黨組織應當通過意識形態領導等方式間接參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內部治理。
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理論的反思與重構
理論界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的分歧體現了相關理論的路徑依賴和固有偏頗。路徑依賴是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的理論探討依賴于模仿既有法人治理結構和國有企業改革模式;固有偏頗是指既有法人治理結構和國有企業改革模式有其特定歷史背景和適用對象,難以直接適用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對“公司構造論”和“國企模仿論”進行反思,實質上就是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理論的路徑依賴和固有偏頗進行反思。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的理性認識應當是:堅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特別性,厘清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發展的階段性,賦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選擇治理結構的自治權。
(一)“公司構造論”的反思
“公司構造論”直面鄉村治理的困境,試圖通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公司化改造,還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經濟組織”屬性,使其沖破承擔過多社會功能的制度藩籬。這種富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構造論無法回避三個重要的問題:在法律性質方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營利法人定位如何與《民法典》規定的特別法人定位相協調?在鄉村治理方面,全面公司化改造的主張是否符合農民意愿,是否適合所有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城鄉均衡發展方面,政府通過財政支持等措施尚難以消除城鄉差距,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純粹的經濟組織又怎能實現農村經濟社會穩定發展?這些問題在“公司構造論”框架內找不到圓滿的答案。

實際上,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進行公司化改造或者將其定位為營利法人,這種主張的目的主要在于賦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市場主體地位和獨立法人地位,而在《民法總則》確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特別法人地位之后,仍然討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性質已無太大實際意義。理性的認識路徑應當是,肯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特別法人地位,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特別法人的特別性對其治理結構的影響,結合既有經濟組織治理結構的基本模式,構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特別法人的治理結構。
(二)“國企模仿論”的反思
“國企模仿論”認識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不能簡單照搬公司治理結構,而應當體現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特別法人的特別性。但是,該觀點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治理結構的構造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未區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發展階段,無法適用于所有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另一方面,以國有企業為模型,限縮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治理結構的多種可能性,難以體現集體資產與國有資產在功能定位、經營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差異。
從村黨組織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治理結構中的地位來看,“國企模仿論”的兩種觀點都肯定村黨組織在基層治理體系中的特殊地位,并認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基層治理的重要主體,進而通過不同方式明確村黨組織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治理路徑。但是,兩種觀點并未證成村黨組織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治理及其治理地位的正當性、妥當性,也未厘清村黨組織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治理與國有企業黨組織對國有企業治理之間的差異。“黨組織嵌入論”認為村黨組織應當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對嵌入治理的方式和范圍并未明確。“黨組織領導論”認為村黨組織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治理方式應是間接的,但間接治理并不直接影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對集體資產的經營管理,難以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集體資產形成有效的監督。


(三)“自治階段論”的提出
“公司構造論”與“國企模仿論”或忽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特別性對其治理結構的影響,或僅關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一個方面,因而都無法完成構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的任務。鑒于此,筆者提出構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的“自治階段論”,即厘清城鄉融合和集體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肯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發展的階段性,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自行決定其治理結構。




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的立法選擇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的地方探索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立法提供了現實基礎,相關學術爭議則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立法提供了理論參考。在此基礎上,我國制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時,其中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的設置可以參考如下建議:在立法技術方面,以倡導性規范為主,使用“可以”等倡導性詞語以表明立法對該治理結構的適度開放性態度,并認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采取“政經合一”模式的做法,為相關改革提供一定的制度空間;在立法內容方面,側重于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各治理機構的功能定位、職權范圍等事宜,并允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章程對此作出例外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