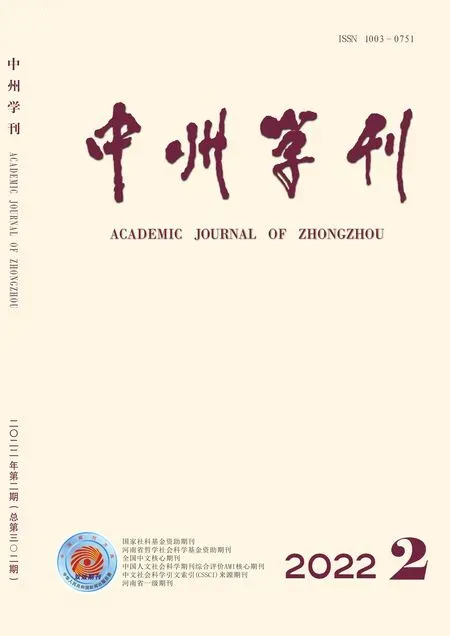西方環境美學對框架理論的反思與重構*
西方當代自然審美的復興由羅納德·赫伯恩的文章《當代美學與自然美的忽視》開啟。赫伯恩在對比藝術審美與自然審美的基礎上,反思了藝術美學傳統對自然審美的錯誤引導,并將“非框架性”視為自然對象與藝術作品的重要區別,由此也開啟了西方環境美學對自然審美中框架的反思。環境美學在發展的過程中一直在探求跳脫于藝術模式之外的適當自然審美方式,但也在對比和采用藝術審美路徑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建構,對于框架的態度顯得矛盾且曖昧。包括赫伯恩在內的西方環境美學家反思藝術審美傳統對自然審美的侵襲,將框架視作藝術審美方式對自然審美的不合理移用,主張無框的自然審美;但也有學者肯定框架在自然審美中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或在顛覆藝術框架理念的同時為自然審美的適當框架尋求根基。由此,框架既被視作藝術模式誤用于自然審美的代表而被批判,又被視作自然審美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而被重新構建,環境美學內部針對框架問題出現了分歧與爭論。那么,自然審美中的框架究竟具有怎樣的內涵?適當的自然審美中的框架將何去何從?
解決上述問題需要我們對環境美學中的框架內涵進行深入分析,探求環境美學對框架問題的多重反思,從而在多維理論的交織下探索更為適當的自然審美方式。這不僅有助于驅散縈繞于框架之上的各種爭論與質疑,同時能夠在更為廣闊的語境下理解自然審美的特性,從而對框架理念做出適當的調整與重構。
一、顛覆:藝術審美反思下的框架批判
西方環境美學對框架的反思與其自身的興起同步展開。西方現代美學更加重視藝術審美,黑格爾更是將美學等同于藝術哲學,此后,分析美學進一步將藝術作品視為美學研究的關鍵對象。在這一過程中,自然美學處于被美學界忽視的邊緣地位,即使有所發展,也受到主流藝術審美傳統的侵染與規訓。這一情況在20世紀60年代迎來轉機,赫伯恩的開創性文章《當代美學與自然美的忽視》深刻反思了現代西方美學對自然美的忽視,并在對比藝術審美與自然審美的基礎上論述自然對象的廣闊審美前景。在赫伯恩看來,“非框架性”是自然對象區別于藝術作品的重要特性之一,同時也給自然對象帶來更為豐富的審美可能。此后,西方環境美學在繼承赫伯恩思路的基礎上逐步發展,也由此開啟了對框架理念的反思與批判。
相比于自然對象,框架在藝術作品中更為普遍。畫作中的畫框,戲劇中舞臺與觀眾的分隔,文學作品中內容與標題、頁碼之間的空白等,都是藝術作品中框架的常見表現形式。但審美實踐中的框架并不僅僅局限于物性、可見的形式,更是指審美對象與其所處環境、欣賞主體之間的邊界和區分。因此,藝術作品中的框架不僅能將主體的注意力快速集中于審美內容之上,避免審美對象的混淆與誤認;同時也能維護審美對象的完整性與穩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規避外部環境對審美特性的干擾。由此可見,藝術作品中的框架有助于提升審美的確定性、完整性與穩定性,逐漸成為藝術審美的常規思維模式。
但與藝術作品不同,作為非人造物的自然對象并不天然就具有明確的框架,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自然對象的不穩定性與開放性,因而也成為現代美學傳統認為自然對象不具有審美價值的重要理由。但藝術審美傳統下的框架思維仍然深刻地影響了現代自然審美模式的形成,審美主體更多地將藝術欣賞方式挪用至自然對象之上,更為關注自然對象的形式特征,人為地給自然對象設定框架,興起于17世紀的“克勞德鏡”便是人為添加的自然框架的代表。通過這種隨身攜帶的有色凹凸鏡,人們可以將難以把握的自然對象“移到一個適當的距離,用柔和的自然色彩與最尋常的視角將它們展現出來”,將散亂、無界、多樣的自然對象重新選擇、組合形成類藝術作品,進行審美欣賞,從而可以更為便捷地關注自然對象的如畫性特征。這一框架在發展過程中逐步衍生出景觀游覽中的特定視點、人為設置的風景名勝等形式,藝術模式也在自然審美中深入拓展。
西方環境美學以顛覆藝術傳統下的審美欣賞模式為基礎反思自然審美,將推動自然審美由“膚淺、碎屑”走向“嚴肅、認真”,構建適當的自然審美方式作為理論研究的目標。因此,在環境美學看來,框架理念是藝術審美傳統對自然對象審美本性的錯誤規訓。環境美學認為,作為自然本性的“非框架性”實則是自然對象審美特性的來源之一。在赫伯恩看來,“非框架性”非但不是自然對象的缺點,反而能給自然審美帶來額外的體驗,“如果‘框架’的缺失排除了自然審美對象全部的確定性和穩定性,作為回報,它至少提供了一種不可預測的感知驚奇;僅僅它們的可能性就為自然的靜觀賦予一種具有冒險性的開放意義”。這種開放意義源于自然的整體性與連續性。與藝術作品相比,自然對象不是獨立自持的穩定整體,其與所處的環境天然地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展現不同的面貌。但在藝術審美傳統為自然對象加上框架時,自然對象或被從其密切相關的環境中孤立出來,或被框架分割成斷裂的形式畫面,如同畫廊中的靜默作品一般被人凝神靜觀,以藝術作品的方式展現自身。
環境美學認為,作為藝術審美輔助工具的框架并未如其本然地對自然進行審美聚焦,反而在這一過程中扼殺了自然審美的多樣面貌和無限可能。藝術作品的審美特性并不會因其從環境中移出而有所改變,但“自然對象卻與創造它們的環境有著我們可以稱之為有機統一的東西:這些對象是它們所處環境的一部分,并通過環境的作用力而從元素中發展而來”,因此,當我們將一塊巖石從其所生成的環境中移出,將其作為獨立完整的藝術對象進行審美靜觀時,我們雖然能夠獲得形式上的審美體驗,但忽視了自然更為豐富的審美特征。由此可見,自然對象在具有色彩、線條等形式特征之外,交織在它上面的復雜關系所體現的生態內涵更是其審美價值的重要來源。在現代美學中占據主流地位的藝術審美傳統忽視了自然對象的特殊性,將專注于形式的框架強加給自然對象。
此外,環境美學批判了藝術審美框架所帶有的鮮明人類中心主義傾向,認為這不僅違背了自然對象的審美本性,而且不利于自然審美走向自然保護實踐,缺乏對自然的倫理關懷。在框架的協助下,人類主體按照自身的偏好將符合藝術審美原則的統一、對稱、和諧等特質的自然對象框選出來,在加深如畫欣賞模式的同時,也將自然審美引向了主體性泛濫的方向。正如景觀地理學家羅納爾多·瑞斯所言,如畫審美理論“表明自然的存在只是為了取悅和服務我們,只為確保我們的人類中心論”。艾倫·卡爾森將這一模式總結為自然審美欣賞的景觀模式,在這一模式下,人們會“尋找和欣賞的主要是風景優美、有趣的自然環境。因此,那些缺乏有效繪畫構圖、刺激感或娛樂性(即那些不值得展示在畫上)的自然環境就被視為缺乏美學價值”,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對自然審美價值的忽視與貶低。同時,偏好如畫性的框架理念也通過審美活動影響到人們的具體實踐行為,“有人心甘情愿地被人帶領著成群結隊地走過‘景’區;認為大山里只要有瀑布、懸崖與湖泊,他們就覺得大山很偉大。而諸如堪薩斯平原則被認為是單調乏味”。當這種審美實踐進一步拓展為生態實踐時,美學觀念上的如畫性框架也將轉化為具體生態保護中的行動界限,諸如沼澤、濕地、沙漠等缺乏如畫性特征的自然環境可能會被忽視。例如,美國國家公園最初便是“為了保留美國西部那些賞心悅目、意義久遠的壯麗景觀”,而將佛羅里達沼澤地排除在外。由此可見,如畫性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使審美維度削弱了生態維度,在背離適當自然審美的同時,也阻礙了生態保護的道路。

由此可見,自然審美中的藝術性框架并不局限于物性框架的簡單套用,更是自然審美中人類中心主義與主客二元分離傾向的集中體現。因此,環境美學對框架進行反思,實則是反思藝術審美模式對自然審美的誤用與規訓,其目的在于恢復自然的本然面貌,從而達成適當的自然審美。但隨著西方環境美學的深入發展,學者們對自然審美中框架的反思從藝術傳統的制約延伸至更為廣闊的層面,也引發了針對自然非框架性的質疑。自然審美是否真的不具有框架?框架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框架反思所具有的自反性并未瓦解適當自然審美的基礎,反而在更廣闊的層面上推動了框架的天然內涵實現回歸。
二、回歸:根植于主客體特性中的審美框架
正如上文所述,西方環境美學在發展之初主要以對比自然審美與藝術審美為基礎構建理論,因此更多在藝術欣賞語境下理解自然審美中的框架。這種框架實則是藝術審美模式對自然審美領域的越界規訓,因此也引起環境美學理論的反思與批判。但隨著對自然審美適當性的深入探索,環境美學也開始在更廣泛的視域中思考自然審美中框架的內涵,從而逐步認識到框架的合理性與必然性。這種對于框架合理性的肯定與辯護看似與非框架理論形成了分歧,但在實質上拓展了環境美學對框架的狹義理解,從而對藝術審美中的框架內涵進行了補充。對于框架不同層面的反思所產生的理論張力,不僅溝通了藝術審美與自然審美的相通性,也在尊重主客體本然特性的基礎上回歸了框架的原生內涵。




由此可見,框架主義并不是對非框架主義的攻擊,而是對它的補充與拓展。環境美學在不同層面對框架的反思看似矛盾,實則相互補充,殊途同歸,共同指向對自然本性的尊重。但是,體驗層面的焦點式框架在具有普遍性的同時,也意味著它可能過于寬泛而缺乏審美引導作用。自然審美僅僅依從原生的開放框架,是否就適合自然本性?如果說藝術模式的有限框架是對基礎性體驗框架的錯誤提煉,那么,如何推動框架內涵朝著適當性自然審美的方向發展成為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正因為如此,西方環境美學對框架的反思并未止步,而是進一步在語境維度上拓展了框架的內涵,重構符合自然審美特性的框架理念。
三、重構:多元語境支撐下的框架拓展


那么在生態化地重構自然審美框架的過程中,人類如何分辨是否尊重了自然的客體性?對于這一問題,卡爾森主張的科學認知主義為重構提供了更加具體的原則。在科學認知主義看來,適當的自然審美體現為將自然當作自然進行欣賞,即“如其本然地”欣賞自然,這本身就包含了一種倫理維度。一個道德的人本身就意味著他能夠對自然對象的客體性加以尊重,而不是對其強行加上主體的幻象。因而,如何正確、公正地認識自然的客體性就成為需要解決的問題。對此,卡爾森借助了藝術鑒賞的思路。在卡爾森看來,正如藝術審美欣賞需要有藝術史、藝術鑒賞等相關知識作為支撐,自然審美知識同樣需要有諸如生態學、地質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知識進行引導,從而使主體在正確的認知基礎上展開適當的自然審美。這一方面能夠避免審美方式的誤用,尊重自然對象的客體性與多樣性;另一方面也能以自然客體性平衡人類審美主體性,推動自然審美中審美維度與生態維度的融合。由此,科學認知主義為生態化地重構自然審美框架提供了客體性的基礎,在語境層面進一步拓展了自然審美框架的內涵。

由此可見,在對焦點式框架的進一步反思中,環境美學以科學知識、文化敘事、審美語境等因素重構了自然審美框架,從而平衡了自然審美中的主體性體驗與客體性特性。這種語境性的重構使自然審美框架具有有限性與無限性的雙重特質:自然審美的框架雖然以主體體驗為基礎,但對體驗有所約束,從而使主體審美在生態環境有序發展的框架內進行;與此同時,這種有限性框架又具有開放的語境維度,以包容的姿態接納多樣的自然審美要素。在有限與無限的張力作用中,自然審美框架有助于推動自然欣賞中審美性與倫理性的融合統一。
四、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無論在自然審美還是藝術審美之中都存在框架意識,這種焦點式的框架有助于主體對審美對象進行選擇、組合和聚焦,從而推動審美過程的實現。但這種焦點式的審美主要受人類主體觀念、喜好、經驗所影響,因而容易將審美引向過度主體性的方向,不利于尊重與保有自然的客體特性。因此,需要對這種生發于審美體驗中的焦點式框架進行必要的補充和規約。現代美學在藝術審美傳統的影響下,以藝術審美模式規范自然審美框架,將原本開放包容的框架壓縮為對形式特征的專注。這雖然為焦點式的框架進行了規約,但仍是主體性對自然對象的規訓,并未尊重自然的客體特性,反而使框架理念在主體性的道路上愈行愈遠。
在對以上兩種框架的反思之中,環境美學不斷拓展框架的闡發語境,從自然科學、文化敘事、藝術經驗等多種維度尋找框架的支撐理論,提出了平衡自然審美主體性與客體性的多重方案,拓展和重構了框架的內涵。框架從有形走向無形,從有限拓展為無限,這種變化本身就體現了西方環境美學的后現代多元取向。而這也啟發生態美學的中國話語建構需要采取多元探索路徑,從而實現生態文明建設所要求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學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