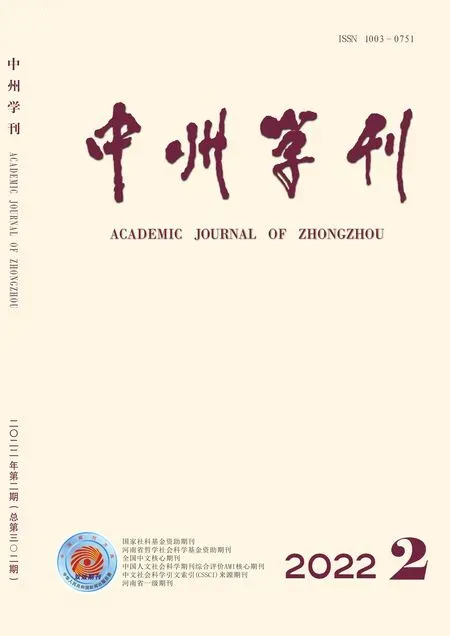論虛擬現實中電影與游戲的邊界*
虛擬現實技術(Virtual Reality,簡稱VR)是一種帶有全方位顛覆性和融合性的信息傳播與記錄介質。原本概念清晰明確的電影、游戲、動畫、多媒體藝術等媒介形態,在VR牽引下產生深度跨界融合,表現為生產、存儲、呈現、傳播和接受等方式的趨同,不同媒介之間的邊界逐漸變得模糊。在理想狀態的VR電影中,除了4π個球面度全景沉浸影像外,觀眾還可以與影片內容形成互動,由單純的被動觀看變為主動參與,這似乎很像是帶有故事性的VR游戲。VR電影和VR游戲兼具沉浸性、交互性和想象性,敘事性又進一步消解了二者的差異,使它們成為非常接近的兩種形態。更有一些電影直接選擇使用游戲引擎去生成實時畫面,以減少視頻素材量,實現與交互性更有效的結合。因此,單純從沉浸性影像、故事元素、交互等要素構成和制作技術方面看,兩者已無明顯區分。直觀現象和特征的相似使VR電影和VR游戲的邊界逐漸變得模糊,使人產生原本作為獨立藝術形態的電影會不會在虛擬現實中不再獨立,甚至可能消亡的憂慮。
一、虛擬現實中電影的身份及其與游戲的關系問題
關于“邊界”勘定,如果以電影為論述主體,以游戲為參照系,它代表的是電影作為獨立藝術形式不同于游戲的獨特性和區分性,在不同構成要素和維度層面不可越過的差異。它既有初始本體概念在新媒介形態下的延續保留,也有新媒介浸潤下獨特性和區分性的延展。
1.VR電影的“電影身份”
目前的研究多數是直接將VR電影默認為電影在VR技術條件下的一種形態,但也指出傳統電影技法和語言在VR中不再適用。有學者認為,這類帶有交互性的VR影像作品,可能結合生成一種被稱為“VR游戲電影”的新藝術形式,并做出了“當VR電影不再被認為是電影時,VR電影才真的能成為VR電影”這樣相對含混的論斷。另有學者認為,電影強調的是觀賞,不具有交互性和操控性,VR作品則更強調交互性和操控性的體驗,電影的觀賞和VR的體認在行為的主體價值方面已經發生顯著變化,從而得出“VR不是電影藝術的未來”這一結論。但交互性并非僅存在于VR媒介形態下,在二維影像中同樣存在。理查德·格魯辛將這些帶有交互性的影片定義為“交互式電影”,但同時也主張對傳統電影理論話語進行更新。克里斯汀·戴利認為,這種交互式影像是一種“用戶電影”,已從德勒茲“時間—影像”的“Cinema 2”進入賦予觀影者權力的“Cinema 3.0”。不過,他們討論的核心點并未脫離“Cinema”,即帶有交互性的電影仍被視為“電影”,同時比較側重電影在新媒介浸潤下獨特性和區分性的延展。
自2012年VR作品首次進入圣丹斯電影節以來,全球已有不少于33個電影節開辟了VR單元或VR展映。威尼斯電影節設立獨立的VR競賽單元,《肉與沙》在戛納電影節展映,榮獲奧斯卡特殊成就獎。這“不僅體現了電影節從電影藝術的角度對VR藝術形式的接納,也反映了電影形式與VR形式的密切關系”。從電影節在電影史上所起的作用來看,它既是一個窗口,也是一個帶有前瞻性的引擎,推動著電影藝術向它可能的方向探索與發展。
2.電影與游戲的融合與分化
一部分學者認為,在新媒介形態下,電影與游戲有走向融合的趨勢。他們或者通過具體游戲和電影作品的例證描述某些融合的現象,或者從IP轉換角度探討游戲和電影的相互改編,或者從推導互動電影的特征及身份歸屬入手,認為互動電影將會融合電影和游戲的優點,成為極具感染力的敘事新載體。這些論述多數是在泛新媒體語境下進行的探討,其中聚焦于VR的大多是對其表面特征的描述與總結。


二、視覺邊界:奇觀消退后的功能、目的差異
在視覺層面,為什么當前VR電影和VR游戲會讓人感覺非常相似呢?主要原因是二者兼具全景影像產生的相似奇觀化感受。但影像的奇觀化會隨著視覺經驗的增長而經歷“創造—接受—消退”的過程。1895年《火車進站》上演時,巴黎大咖啡館里的人們面對銀幕中迎面開來的火車驚慌地四散奔逃的情形,就來自于活動影像所創造的奇觀。自那之后,人們開始愛上這種視覺體驗,湯姆·甘寧將這種訴諸奇觀快感的影像稱為“吸引力電影”。隨著電影的發展和視覺經驗的積累,早期電影的奇觀功能所帶來的視覺沖擊力逐步被人們接受并成為視覺習慣,縱深運動的活動影像不再引起銀幕前觀眾的慌亂。這既是奇觀的接受過程,也是奇觀的消退過程。
就像《火車進站》的二維動態影像是為了記錄火車開進站臺的現實情景一樣,3D電影是為了拓展二維影像相較于人眼現實觀感所不具備的Z軸立體感,120fps-4K-HDR-3D影像又是在3D基礎上提高分辨率和幀率,使影像的清晰度、流暢度和明暗層次更接近人眼見的現實世界。它們的共同目的都是為了通過影像逼近人眼的現實所見。只是在這些影像誕生初期,因為超越了當時人們的視覺經驗,形成了奇觀化。同理,VR在走進大眾視野之初,階段性奇觀驚嘆來自不曾被體驗過的全景影像。與之前類似,VR的本意是對現實的虛擬,當目前畫面畸變、眩暈等一些技術問題解決后,理想化的VR影像所呈現的就是模擬人眼所觀的現實感世界。隨著早期新奇感的消退和視覺習慣的形成,奇觀便會消失。同“火車效應”一樣,VR影像的奇觀化也會經歷“創造—接受—消退”的過程。
因此,當VR電影和VR游戲都具有4π個球面度全景可交互影像,甚至畫面都依賴游戲引擎生成時,二者的表層(直觀)視覺已無差別,但相似的奇觀感受并不能成為影響視覺邊界劃分的因素。若要探求視覺邊界,則需要尋找表層之下視覺功能和目的所潛藏的深層差異。VR電影與VR游戲這種直觀視覺畫面無差異、視覺的功能和目的存在差異的關系,可近似地類比為二者能指相同,所指存在區分。剝離表面的奇觀,隱藏在視覺感知背后的視覺本質得以凸顯——電影傾向于敘事和審美,游戲則更偏愛替換現實的參與式體驗,這是二者的視覺邊界所在。需要說明的是,敘事、審美和參與式體驗在VR電影和VR游戲的視覺功能和目的中都存在,但各有側重,我們關注的是功能和目的的最終指向。探討視覺本質,其實是在探討視覺畫面在這一媒介形態下所承載的最終且最核心的功能與目的。



至于游戲,無論是否在VR條件下,其視覺畫面的功能和目的都最終指向替換現實的參與式體驗。游戲畫面的功能在于建立玩家與游戲進程間的視覺連接,使玩家從視覺這一感官路徑介入到任務沖突之中,體驗到進程完成的快感。游戲畫面強烈依附于互動,在人機互動中起到傳遞信號的作用。評價游戲畫面好壞的根本標準在于是否順暢傳遞了視覺信號,增強了信號傳遞效果,達到使玩家獲得更好進程體驗的目的。VR游戲《遙遠星際》(2017)在這方面做得不夠好,即便它擁有完善的背景故事和建模,更具仿真手感的槍械形控制器,但較為荒涼的地圖使得玩家在不同區域間移動時,看到的都是大片荒地或廢墟,影響了游戲進程的體驗感和代入感。

制作愈加精良的游戲畫面雖然很有美感,但不是以審美為最終目的,美感的功能是為了增加玩家的官能愉悅度或沉浸性,增強游戲體驗。因此,游戲的畫面敘事和視覺美感更多是為了完成游戲功能,是實現最終目的的中介或過程。玩家通過視覺接口,將現實中的自我和游戲中的化身融為一體,取得化身認同,獲得替換現實的參與式體驗,才是游戲視覺的根本性目的與功能。
三、表達邊界:語言性與表意空間



但在VR游戲中,這些語言性的表達方式不是必需的。游戲比電影要直接許多,在表達上可以淡化甚至不需要語法規則,只要將玩家帶入空間中直接體驗即可,視聽和交互體驗越擬真、越沉浸就越好。游戲官能性感知的核心指向是規則、進程、沖突和結果,而不是一個“大影像師”在背后發揮控制權。在《生化危機7》(2017)VR版中,即便游戲整體是Ethan解救妻子Mia并對抗E階段成品Eveline的故事,但游戲架構的核心仍舊是讓玩家扮演成Ethan,在游戲空間中感受驚恐的氛圍,面對沖突,完成通關,并在關鍵任務節點通過選擇救Mia還是Zoe,得到不同的游戲結果。這其中,不需要向玩家講故事的表達主體,故事和視聽的交互體驗只是構建一個沉浸性虛擬空間,對玩家關注點的引導也只是暗示他們如何推進游戲進程,如前行方向指引、獲得道具等。又如,VR游戲《頂樓》(2016)改編自同名短片,電影原作講述了一個陷入失敗窘境的基金經理狼狽蝸居于一棟大樓頂層的故事,導演通過多樣化的視聽語言,呈現了主人公的落寞和與兒子相處的快樂,使二者形成反差對比。而改編者僅使用原作作為故事背景,將其改編成了墜樓體驗型游戲,核心著力點放在了電影中并不存在的高空墜落。無論是乘坐觀景電梯升到樓頂,走在樓頂懸空木板上低頭俯瞰,還是玩家腳綁定位器踩在地面凸起的現實木板上,這些電影中沒有的內容都無關語言性表達,只是為了增加擬真和沉浸性,強化高空驚險的空間體驗,以便在最后墜落時釋放最強烈的感官沖擊。



觀眾同樣能在VR電影中發揮能動性,主動參與意義建構。我們仍以蔡明亮的電影為例,他以往的二維電影充滿著沉悶的固定長鏡頭,對于很多觀眾而言非常枯燥乏味。在他的VR電影《家在蘭若寺》中,雖然保留了固定長鏡頭的個人風格,但觀看的感受卻并不沉悶。觀眾可以在固定長鏡頭空間中自由找尋自己想看的,一些觀眾甚至在電影敘事之外,獲得對畫面意義的自我理解。VR使觀眾獲得視覺自由度,可以主動去探索導演所提供的空間和故事,進而超越這一敘事空間形成意義的主動建構。未來交互性的完善更能發揮這一主動性的優勢,觀眾從被動接受意義傳遞轉變為主動參與,甚至成為意義的生產者之一。

四、本體邊界:原動力驅動下的分別
在本體論層面,VR電影是關于人和人的精神的敘事藝術,其原動力是再現“世界原貌”的欲望,“世界原貌”既包括物質世界,也包括精神世界。傳統電影的本體在VR中并沒有根本改變,在疊加VR媒介特質后,電影反而更接近“世界原貌”本質,更貼近巴贊現實/超現實主義理論中現實的“真實”。VR游戲是關于規則與交互結果的虛擬空間體驗,原動力是玩家在賽伯空間中的官能性狂歡,更強調玩家作為角色化身的沉浸度。精神維度蘊含在背景主題之內,居于輔助或次要位置,其目的側重指向可以更好娛樂的有用性,而非超越性。


VR電影并沒有根本改變傳統電影的本質,它仍舊是關于人和人的精神的敘事藝術。“人的精神”是一個語義相對寬泛的概念,指代存在于人類精神世界的非物質的存在,既包括情感、夢境、幻覺,也包括更為宏觀的審美、認知等。電影不僅能制造精神敘事,還能喚起觀眾的精神意識。相比傳統電影,VR電影的沉浸性和交互性在表現精神方面有獨特優勢。例如《肉與沙》的沉浸交互體驗,讓觀眾身臨其境般體會到穿越美墨邊境的難民在沙漠中的痛苦與恐懼,形成更強烈的心靈沖擊;《涉足荒野》(2014)VR版中,毫無徒步經驗的女主角深陷荒野,在疲憊和恐懼中產生了見到去世母親的幻覺,沉浸影像使觀眾看到了主人公的幻覺景象,產生了強烈共情。沉浸性和交互性對觀眾的感官刺激更為擬真和直接。這種對人類精神世界表現的通透度,是傳統電影所無法達到的。
從本體論角度看,VR游戲的本質是關于規則與交互結果的虛擬空間體驗,其核心要素是任務、進程和結果。VR技術強化了視覺、聽覺、觸覺的沉浸感和擬真感,并通過故事性外殼將三要素包裹在虛擬的角色世界中,給玩家呈現出一個高度仿真情況下擁有自我化身的景觀帝國。這些官能性體驗都來自程序化和系統化的合成,用物質化方式展現單一層次、直觀感受的仿真幻境。在VR游戲《半衰期:愛莉克斯》(2020)中,除了空中穿梭的直升機、掛滿鋼索的巨型城堡等超逼真建模營造的極強視覺刺激的仿真幻境,其最大突破在于遵循常識的交互設計。通過重力手套,玩家幾乎可以和一切可看到的物體進行交互,例如用筆隨意涂鴉,喂老鼠抽煙,甚至給槍換子彈都要把手伸到背后做出掏彈夾的動作,仿佛一切都是真實的物質存在。游戲通過孤獨營救父親的故事外殼,將所有沉浸體驗、玩法訓練、關卡設計包裹其中,玩家置身于強烈官能性體驗的空間內,完全感覺自己成了愛莉克斯,與這一空間進行現實性行為互動,打通一系列關卡完成任務。

五、結語
上述對VR電影和VR游戲邊界的考察,實際上是以游戲為參照系,探討電影在VR中能否繼續保持其作為獨立藝術形態的身份。由于二者外在特征的相似性,我們嘗試從構成要素和多重維度入手,尋找表層之下最終指向的區分。

我們現在看到的VR不會是VR的最終形態。就像攝影術的出現并沒有讓繪畫消亡,反而讓其發展出更高的人文價值。即便未來技術走向元宇宙的方向,在人類再現“世界原貌”的終極目標下,VR電影作為藝術仍能散發著感動、思考與人性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