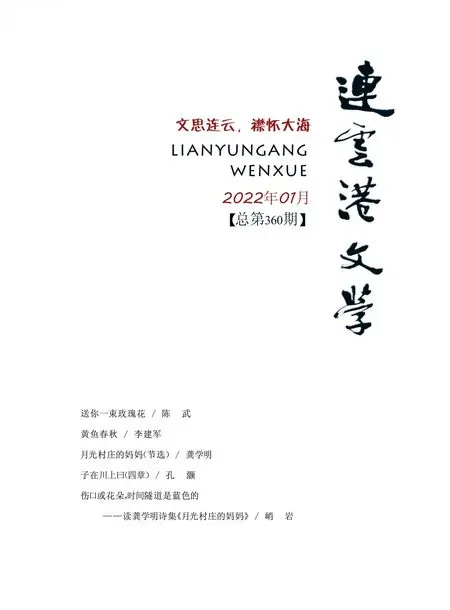純粹的玉米
山 女
再沒有哪一種植物像玉米一樣,和我如此血脈相連、休戚與共。玉米糊糊喂養了我,當我從玉米堆上站起,一股濃郁的玉米馨香把我浸沒,把我掩埋。
年年歲歲跟在玉米后面,和它哭和它笑,和它妥協,和它爭吵。玉米以不可違逆的宿命植入我的內在,我精神的特質和性格的基因冒出玉米的味道。春來了,雞糞,化肥或者草木灰,統統跟著我的簸箕或糞筐顛簸到南坪的地塊,隨著我手臂悠揚起落,它們溶于黃土,漸化為玉米的苗床,成為玉米到來的鋪墊。犁鏵是真正迎接玉米的前奏,一場飄逸的春雨落下,玉米地酥軟了骨架,它一夜間展露多情的容顏,等待春風通透地揉捏。
一粒優質的玉米種,在我手里捻了又捻,然后順著我指縫的通道落到褐色的土壤。它有發芽開花結果的歷程,也帶著我希冀它穗大粒飽的祈愿。玉米苗迎風破土了,開始了穿越季節的涅槃。寒流是它第一個考驗,跨過倒春寒的門檻,然后就是抵御外敵入侵。土蠶最喜歡咬斷它的根莖,從土里一寸寸地翻尋過去,像一個專門滋事的搗蛋鬼,玉米一株株敗在它貪婪的唾液里。后來是野雞的肆虐,它們以沖鋒的姿勢盤旋在玉米的頭頂,把蓄積一冬的力氣和餓極了的狂躁,發泄在嬌弱的幼苗上。一爪子就刨起一棵,全然不顧包裹種子的毒液,它們對毒液已然有了免疫。
玉米搖搖晃晃地蔥蘢于初夏的陽光,寫意出一片濃淡不一的綠。間雜其間的灰灰菜,打碗花從除草劑那里漏網,它們的加盟讓玉米們更加惺惺相惜。吸納了養料和雨水的玉米挺拔了腰身,模樣一天天苗條俊秀,漸進孕育佳期。暗夜里低頭含羞的玉米花一絲絲張開,承接愛澤的浸潤。每一絲花蕊都連接著一粒種子,等無數個種子匯集,一穗玉米就獲得母體的完整。我時而抬頭仰望,時而低頭傾聽玉米波瀾壯闊地交媾,對大自然的神奇充滿深深的敬仰。
初秋的雨夜,玉米把拔節和吐穗張揚得有聲有色。一棵和一棵交談,一棵和一棵耳語,彼此傾訴生長的疼痛和快感。玉米林蛻身為收集秘密的專屬地,一只南瓜在玉米葉下悄悄坐胎了;幾只蜘蛛在玉米林里秘密織網了;野兔出門覓食時有了掩體了;蝴蝶路過時有處歇腳了;無限生機在玉米地里蓬蓬勃勃。而我,最鐘情那鮮亮潔凈絲線一樣的玉米花。大自然配好的顏色,隨便抽出一根,繡出的都是無與倫比、獨一無二的畫。
歷經春夏秋,品嘗酸辣苦的玉米在田野上挺立持重的身姿。旱來了,榨干自己也要把保命的水分留給后代;風來了,靠本能緊緊抓住腳下的土地。這小小的草木,以自己獨有的方式,高舉綠色的火焰,在韻味十足的風姿里,傾訴關于生長的欣悅。等待秋,等待一種心滿意足的交付,等待歷經滄桑后的歡顏,等待顆粒歸倉的圓滿。
那天的陽光細篩子篩過一樣均勻,我拿出被老鼠啃破的舊袋子縫補,收拾好袋子要去裝田野上快要成熟的玉米。公路邊的玉米地里側翻了一輛大貨車,我家的玉米被碾倒一大片。貨車司機顫抖著從車里爬出來,他的顫抖堪比冬天最蕭瑟的葉子:茫然、無助、惶恐。
山路彎多,他在轉彎的時候,一只奔跑的黑狗在前面誤導了他,他把車開進浩浩蕩蕩的玉米林。地堰上一片果實累累的豆角被卷進車輪,各種植物的藤蔓把輪胎染綠。在等待吊車救援的時間,司機在我家的小圓桌上狼吞虎咽地往肚里倒下兩碗菜餃子。小村太小,沒有飯鋪,而他跑了半天,渾身癱軟,已經聞不得人家飯香。我家的韭菜餃子緩解了他的哆嗦,他看起來穩健許多。說到賠償事宜,他說他會給我家那些被撲到碾碎的玉米一個說法,我和丈夫相視一笑。他說得最多的是他外省的那個家,家里有賢惠的媳婦,調皮的孩子。孩子讓他眼里升起亮晶晶的云彩,徹底消散翻車的陰霾。他說為了妻子的大衣,孩子上個好學校,他才千里迢迢跑車。這個理由有著相當的普遍性,沒有哪個男人的流汗不為這些,丈夫很快和他有了許多共鳴的話題。天色黑下來,丈夫不僅為他準備了閑屋里碎花被子的床鋪,還和他共賞了月色,月色下品咂了我藏在柜底的一瓶玉米酒。第二天,他啟程了,對著丈夫揮揮手,對著被壓碎的一片玉米林揮揮手,路邊沒有一個人提醒他該對那片凌亂的玉米負責。
在秋陽滑爽的撫摸里,我欣欣然掰著自家的玉米。從我開始追溯到母親,從母親到祖先們,他們統統和玉米有著最親密的糾結。層層剝開的玉米泛著太陽的色澤。院門口、屋檐下、房頂上,一串串玉米被下鄉采風的人定格,被畫筆臨摹,被詩歌吟誦。農人們不知道,玉米除了實用價值外,還有如此質樸厚重的藝術價值。
玉米是女兒下學期的寄宿費。收玉米的三輪車突突開進院,我和丈夫正費力地一顆顆掰著被雨水淋濕有點發霉的玉米尖。秋陽一覽無余地灑在平房頂上,炙烤著我,先是外套后是毛衣,逐件脫去的衣服頂在頭頂,翻飛的衣袖下的一點陰涼擋不住紫外線的侵襲,我的臉接納了很多的太陽變得黑紅油亮,這樣的膚色決定城里時裝店服務員對我的態度,然而,我對自身沒有一點不滿,相反我樂于和陽光打交道。它博大無私地普照玉米、麥子、大豆,灰灰菜、芨芨草。它從墻壁、煙囪、豆角蔓和洋槐樹梢上掠過,給我足夠的踏實和安定的溫暖。
無數玉米堆疊鋪陳,在平房頂匯聚成一方金色的織錦。組成這團錦繡的每一個色塊都從手里過了幾遍:首先從玉米稈上擰下來,然后從玉米皮里剝出來,它們在粗糙的手掌里起落,一穗穗裝進蛇皮袋,又經過肩膀一袋袋扛到房頂,嗵的一聲傾倒進陽光里。
七八畝玉米,從地里出發,就被丈夫的肩頭扛起。雞腸子一樣狹長的地塊,磕磕絆絆的山間路,不斷掄起的蛇皮袋,玉米歇腳到房頂,他的肩頭磨出繭子。厚繭子在夜晚的燈光下,被我層層揭起。不止肩頭,還有指肚。指肚上的老繭在指甲刀上打滑,我建議他溫水泡泡,用小刀刮刮,他揮舞著手掌要撓我,說留著這雙橡皮手套可是鐵砂掌,要我小心。
今年玉米快收了,凄凄瀝瀝的連陰雨漚爛了玉米尖。我說往玉米機里一塞,什么好賴全混淆。現在玉米是給大工廠造乙醇,這一點點霉爛別說在大工廠,就是在玉米販子這里都是滄海一粟。他是個死腦筋,非要一穗穗過手,每個玉米擰一下尖,無數個玉米擰無數遍。迂腐到這地步,也非他莫屬。驕陽在房頂曬得人渾身冒油,我剝了幾下終被太陽趕跑。他邱少云一樣紋絲不動,一穗,兩穗,千百穗,剝過的玉米在他眼前堆疊,層層摞起,每一穗都像是收拾清爽的佳人。
玉米販子的三輪車打開車廂候在廊檐下,打成籽粒的玉米一袋袋順屋頂的高梯子滾落到他的三輪車上。裝好車后,他連帶著買走丈夫剝下倒在屋角的爛玉米。好玉米八毛,爛玉米兩毛。過秤后,販子解開好玉米袋子,一袋袋往內添爛玉米。赤橙紅綠青藍紫,丈夫的臉瞬間變了幾個色,他奔過去抓住人家的袋口。販子笑道,我買來的玉米我想咋整咋整。丈夫說,那是我一顆顆剝下來的。販子說,你都賣給我了,管得著嗎?丈夫說,早知道是這結局我也會這樣干,哪能輪到你,昧良心賺這差價回家睡得著嗎?一粒老鼠屎壞一鍋湯,萬一人家買回去是磨面,做食品,想想,要禍害多少人呢,嗯!伙計?我上前拉他,他死扯住人家口袋不丟。
三輪車突突開走,我說,人家不當咱面,回到家不會繼續往里摻?他一拍腦袋說,咋沒想起這茬,我得攆上給他說說。
丈夫在攆人的過程中迎面碰到了二憨媳婦。她披頭散發一路奔突,掩面號啕。再三問詢之下才知,她家有剛咽氣的老人,她被突如其來的事打擊得不知所措。丈夫在她家廂房昏暗的光線里,看到了數不清的塵土,飛揚的塵土落了一鍋蓋,一桌子,還有老人的臉上。他的臉扭到一邊,烏青漲紫。丈夫拿起炕邊的壽衣,和地上站著的幾個鄰居把他衣服換上。老人兒子在外打工,生活起居憑兒媳照應。二憨媳婦腦子不清,根本不知道喪葬之事從何下手。丈夫拿起手機給二憨打電話,信號在院子里追蹤了幾個回合,還是沒連上網。丈夫把手機甩到窗臺,一個人扛起蒸饃的大鐵鍋,把它穩穩當當落在臨時支起的大灶臺上。從報喪,買菜,到打墓和下葬,他像陀螺一樣在她家運轉起來。村人外出打工,留守的是老人和孩子,體力活拿錢也尋不到人。出殯時下著雨,土路濕滑,抬棺材的丈夫在地頭一個趔趄,被杠頭的糙皮擦破了腰。我拿紅藥水給他涂抹,他的嘴巴朝一邊咧去,一直咧到想要啃住什么東西。二憨來家坐了半晌,拿條香煙給他,他和他在堂屋里推來讓去。
丈夫經營著犁地的拖拉機,我們明年還有十幾畝玉米要種。收獲玉米后空蕩蕩的田野上,丈夫開著拖拉機來來回回一尺尺掘進,拖拉機的嗒嗒聲打破田間寂寥。新翻的泥土在陽光下晾曬,晾曬相當于增強肥力。黑黝黝的膚色是它今日的陷落,明年又會被綠油油的禾苗扶起。玉米被陽光和汗水凝練成不含雜質的純粹,信手抓一把泥土,玉米的味道,彌漫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