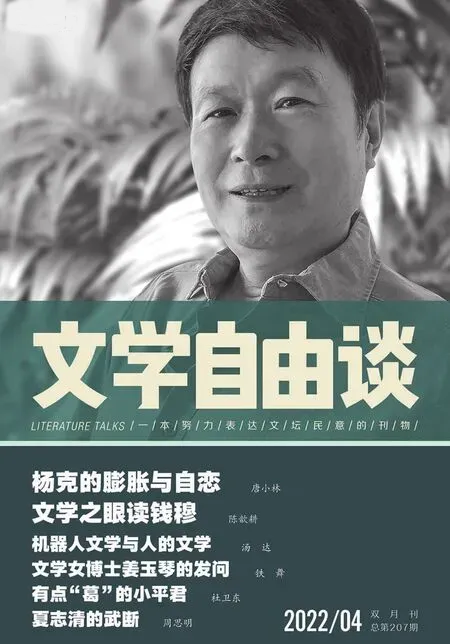文人年譜編修的三種疏誤
□劉 陽
已不知幾回,每逢新生導學場合,我推薦給學子們的第一種入門讀物,總是文人學者的年譜。因為這等于起先就拿金針度人,趁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滿懷理想朝氣時,樹起高大上旌旗,引導其少走彎路。我自己就是這么摸索過來的。記得昔年讀《夏承燾年譜》,不但領略了一代詞宗既博且專、又不立崖岸的治學心路,而且從年譜中不少有意思的細節,比如徐朔方、吳戰壘等晚一輩杰出學者勸夏公“專力為學,勿寫小文章”、“作提高科研,勿分心于普及工作”中,驀然有所悟,慢慢開始明白了“螣蛇無足而飛,鼫鼠五技而窮”的道理,從此提醒自己小心別掉進“多歧亡羊”的窠臼。這種經驗想必很多讀書人也都有過。
當然,以上感受的前提,是須面對一部除了基本史實不出錯,還能做到不留白、不簡化和不滯悶的年譜。這做起來非一日之寒,可遇不可求。《夏承燾年譜》之所以一上手便讓人不忍釋卷,畢竟是由于有先生數十年寸累銖積的《天風閣學詞日記》為底本依據,整理鋪排成年譜,相對容易措手。饒是如此,倚重現成的文獻,不意味著畢其功于一役。近讀到雪克《湖山感舊錄》,當中以親歷者身份栩栩載錄夏翁未入儒林傳之逸事,舉凡“撰作這類普及性讀物的事,心叔(任銘善)先生并不認同,數次進言勸止,云從(蔣禮鴻)先生也不以為然,這是可以理解的,可夏公自有主張,以普及詞學為己任,一直不為所動”云云,便又開我眼。在看到了譜主的鮮活反應之余,也悟到年譜永遠有可補的材料遺珍,不能不九蒸九釀,火候越久才越上佳。果真要臻于不簡化、不滯悶之境,難矣哉。
但不簡化和不滯悶,都立足于作為前提的一個“有”字,取決于放長線釣大魚的時間或者說機遇,花功夫深耕細作,總能一遍遍完善。它們是年譜成敗的充分條件。比起充分條件來,不留白則是必要條件。假如做年譜避難就易,遇到某些年份時忽略不計一溜而過,骎骎然以“無”出之,則難免失之于粗疏。同樣是評上面的書,盧敦基《雪克老師側記》記有次詢問《辭源》如何,師答:“《辭源》嘛,我懂的它都有;我不懂的,它都沒有。”——我每每感到遺憾的,是目下行世的文人年譜,懂得這個類似于注書的道理者似乎不多。表現為,在讀者能推知究竟、可憑一己之力尋檢到相關脈絡、也不乏文獻支撐處洋洋灑灑極盡鋪陳,而對歷來難注、缺注而讀者迫切盼注處,乃至被公認為懸念與難點的空白地帶,卻概付闕如。這恐怕多多少少是此類年譜行而難遠之故?
歸結起來有三點:應敘之處從眾回避而留白;所敘尚需明顯補充而簡化;敘中本可穿插細節而滯悶。促使我油然產生這些想法的,是年來又讀到的一種渴慕已極的文人——恰好是夏翁傳人——年譜:《吳熊和學術年譜》。對于吳先生,雖曾有幸就學于他多年設帳的學府,卻生也晚而未有親炙之機,只能仰之彌高。焚香沐手急急拜讀之下,便感到了上述三種疏誤。
先談回避應注之處而造成的留白問題。吳先生身為“30后”文人,在三四十歲時遭逢各種運動,固然屬于時代風會,然而若僅滿足于將《天風閣學詞日記》中所載的活動反過來載入吳氏年譜,卻在許多年份下以“在杭州大學任教”七個字籠統打發,是否便解決了問題?余期期以為不夠。深入的勾稽表明,這時的譜主不輟讀寫,并沒有閑散,否則又如何解釋他“文革”甫一結束便蓄勢沖頂,很快享譽于學林?像下面這些故實,我覺得因而就不該被跳過:
(1)從《杭州日報》1957年4月26日三版鉤沉出吳先生弱冠詩作《迎》:“仁愛胸懷百戰身,和平勛業創基人。……今朝試上湖船看,西子新妝百態生。”不僅應補入年譜,而且讓人看到了年未及而立的精神狀態以及早期詩藝。
(2)周育德《戲外尋夢》載,“1957年冬天,中共中央發出了知識分子勞動化,干部參加體力勞動的動員。這是‘反右派’以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重大措施。各個大學里都有下放農村勞動的指標,由校而落實到系,動員教職員報名。徐朔方先生和呂漠野、蔣風、吳熊和、蔡義江等先生都報了名,而且都得到批準,成了第一批下放的勞動者。留校的先生作詩送行,下放的先生也作詩唱和,搞得有聲有色。”并附吳先生詩作,可謂洋溢現場感的珍貴史料,應徑錄而未著錄,或也可補入1958年紀事。
(3)陸昭徽、陸昭懷合著的《書如其人:回憶父親陸維釗》,和白砥編的《陸維釗文獻集》,都指出1959年陸先生“與邵海清、吳熊和、平慧善合編教材《晚清詩文專題綱要》,供中文系進修生使用”。這又是條堪稱珍貴的翔實材料,提供了任青年助教時編撰教材的情況。年譜若不載,知情恐難再。
(4)方厚樞《中國當代出版史料文叢》詳細介紹了1962年吳先生與夏翁合著(實以吳為主執筆)的《讀詞常識》作為“知識叢書”之一種,如何受中華書局約請而出版的背景情況,作為稀缺史料,當在年譜1962年部分作必要的補充交代。
(5)徐元《味耕園詩話·詩文集續》敘及1963—1964年間吳先生曾參加浙江古籍出版社策劃、供知識青年自學參考的“古代文學作品選講”(共五冊)的編寫工作,本已寫好編好,卻因《關于當前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驟至而不得不終止。立此存照,慨乎一代國運民瘼。
(6)蔡義江《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初版“后記”說,“一九七四年杭州大學中文系編了一本《〈紅樓夢〉研究問題資料續編》,……當時中國古代文學教研組吳熊和、陸堅同志和我都參加了這項工作。”以旁證形式坐實了“文革”期間譜主的重要行跡,拈出后有益于展示譜主學養的構成。
(7)1999年出版的《吳熊和詞學論集》,“后記”稱“然明刻陳子龍、李雯、宋微輿三人合集《幽蘭草》,于國內各大圖書館訪求殆遍,皆無藏本,意謂不復尚存于天壤間。不久前幾經輾轉,從滬上一位前輩藏書家處得到原刻本的復印本,不禁驚喜不已”。此處提及的“滬上一位前輩藏書家”,疑為詞學大纛施蟄存先生。黃裳《憶施蟄存》有“記得有清初刻《幽蘭草》,康熙刻《羅裙草》,都是精本。第二天跑去看時,三書已為蟄存買去,懊悔無已”的敘描。云間詞派的重要文獻《幽蘭草》如何歷艱辛而訪得,是頗不妨從細部上詳考一番的。
僅據上面七例可以看出,它們中有本證,更多則來自鮮活的旁證,匯聚在一起后,首度勾勒出了譜主前四十余年人生中的不少事況。運用這樣的方法,當還可陸續復原出一幕幕更豐沛的歷史場景,而避免取材過于單一而造成的年譜敘述上的逼仄。似這般努力填空,才能從各個角度滿足讀者之所需。
再談所注尚需補充而造成的簡化問題。人們希望看到的文人年譜,究竟是微言大義還是收羅詳細?答案總該是后者。信息量越準確詳盡,越會有意想不到的參考價值,保不準會在研究者習焉不察之處,提供火花和幫助。事實上,一位學人的著(特別是佚文)、編、譯、序跋和訪談、學術與社會活動、成就反響、教書育人乃至生平軼聞,都應為編者悉心采擇,左抽右取,一一安置于恰切的人生部位。以此來觀照,眼前這部年譜能提供何種經驗教訓呢?
不得不說有遺珠之憾。這又包括著述敘錄之全璧、參編成果之搜討、零散文字之打撈、治學影響之述評、學術活動之檢閱和培桃栽李之剪影等不一而足。
(1)對于吳先生豐入吝出的著述情況的敘錄,存在著缺口。比如1977—1982年陸續發表于《語文戰線》上的《杜甫的〈石壕吏〉》《韓愈七古三首》《杜牧為什么寫〈阿房宮賦〉》《豪放派和婉約派的來由》《〈菩薩蠻〉、〈水調歌頭〉等詞調的調名有什么意義》《〈永遇樂〉的“否”字》這六篇早期論文,便都被漏了。至于1986年為《人民政協報》所撰《悼念夏承燾老師》,作為不可或缺的集外文,補入可窺吳承夏學的具體軌跡。而收入2003年《文史新瀾》中的《〈石湖詞〉編年》,不見于公開梓行的著作而彌足珍貴。像這些,便都屬于有價值的補筆。
(2)參編文字亦復不少,若有心將分散八方的它們串聯成珍珠船,自可發揮余熱。如1989年擔任副主編的《古文鑒賞大辭典》中,那特色鮮明的“集評”,實出吳先生倡議。證據是《杭州日報》1988年6月6日第四版《既博且精 深中肯綮》報道的吳氏原話:“還有一個特色是集評,搜集前人有關評論,分條列在鑒賞文字之后。……搜輯這部分資料需要化費大量精力,要有多年積累才能匯輯成編。但這也是讀者和研究者久所企盼的。”言者無心而聽者應有意,這足以啟示后學在編篡看似通俗的鑒賞辭典時,如何匠心獨運而使之生命長青。
(3)還有大量散布于各出版物的鑒賞文字,它們能為今天的讀者提供門徑指示。如為唐圭璋先生主編的《唐宋詞鑒賞辭典》和《宋詞鑒賞辭典》,精心執筆趙鼎、劉克莊等詞人詞作,又在《唐宋元小令鑒賞辭典》中對劉禹錫的《瀟湘神》、在《元曲鑒賞辭典》中就朱庭玉的《行香子》《天凈沙》等的一一指授,使我們不經意間,看到了詞學專家對曲學的同樣熟稔,而深深服膺其“要打通視野,才能取其一點”的治學咳唾。余如1984年為《大學語文選講》賞解《明妃曲》,以及為《電大教學》縷述《〈詩經〉與音樂》《李煜詞的抒情特色》《關于初唐詩與初唐四杰》、1993年為《毛澤東詩詞畫意》評析《賀新郎·讀史》、1999年為《吳文英詞欣賞》導讀《鶯啼序》等,珠璣遍地,例不勝舉而指不勝屈,皆之前聞所未聞,而復失收于年譜。還要提及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推出的一套六冊《高中古代詩文助讀》。那絕非一般教輔讀物,以學術的高質量廣受青睞。吳先生是其中多種的署名作者,不但不應漏略,錄之于年譜,正可讓今人瞧瞧一流教輔書該是何等風貌。
或曰:做年譜得拿譜主已系統行世的成果為依據。這不能說完全沒道理。只是著作也好,論文集也罷,都是學者帶上了價值評判色彩的、去取之后的產物,年譜則應如實交代事實,以全面還原著述為本色,不宜輕言“有選擇”,嘗鼎一臠反倒不好看了。在大數據技術深入人心的當今,要求年譜編者盡可能竭澤而漁,乃至不放過一副出自譜主之手的挽聯(如傅杰《前輩寫真》記吳先生1989年挽郭在貽教授聯:“母老家貧子幼,空有才名驚耆宿;雨冷燈昏夢斷,又為斯民哭健兒。”吳敢《吳溪流澤長》記吳先生2005年挽吳戰壘先生聯:“百身莫贖,天其喪予!八表同昏,吾將與誰?”),看起來就不是過分的期待。
(4)有關治學影響的述評,也需辟出空間來詳加觀照,因為這具有學術史定位的深遠意義。其中既需要充分體現1990年入載張高寬等主編的《宋詞大辭典》這樣的肯定,以及曹辛華《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詞學卷》對吳氏領銜的杭州詞學群體成就的大篇幅論述,還有《宋代文學研究年鑒》等大量評價,包括在《浙江通志》和《浙江年鑒》中也能找到的相關評議。也應適當容納進一步的申論或商榷意見,如黃世中《中國古典詩詞:考證與解讀》嘉許吳先生有關《釵頭鳳》非陸游、唐琬本事的著名考證之余,也追問“如果沈園題壁不是《釵頭風》詞,那么陳鵠關于唐琬和詞有‘世情薄,人情惡’之句,又當屬什么詞牌呢”,不失時機地一并附入,讓文人年譜產生“學記”的索引和參考價值,有什么不好?
(5)至于對學術、社會活動與育人情況關注的不夠,也留下填充空間。譬如1990年3月主講海峽兩岸蘇杭詩詞研修會,授“唐宋杭州的城市與詩人”課等等不煩枚舉。這方面的情況,總以做到齊全為宜。特別是1991年以來,吳先生應邀以主要專家身份開展“唐詩之路”論證,著古代文學地理學之先鞭,在年譜中著墨欠豐。又《杭州日報》1982年2月25日第三版《青年女工汪維爾考上研究生》說,“她還到杭州大學中文系向吳熊和副教授求教。吳老師開始對這個姑娘攻讀古典文學有否前途持懷疑態度。經過一段時間接觸,吳老師發現在小汪身上有一股鍥而不舍的精神,使他深深感動,從而悉心輔導。”這樣有教無類的育人事跡,踏破鐵鞋難覓,豈有閑置之理?
最后談敘中匱缺細節穿插而造成的滯悶問題。縫合以上缺憾之余,如何讓譜主血肉豐滿?尤其是對吳先生這樣精氣內斂、自覺遠離媒體采訪等浮世喧囂的純粹文人,更需要留心輯錄。我的經驗和建議是,用繁而密的注釋形式,充分調動譜主各種生活細節,包括富于靈氣的、事件化的例外狀態,來支持正文中的事項排列,恍似交響樂中主音和復調相得益彰,又仿佛編年體與紀傳體互補。可別小看一條生活化材料在年譜中的作用。比如胡可先訪談《甘愿坐冷板凳的人》記吳先生尊尊教誨:“搞學術研究,文獻功底及考據都極為重要,但往往識見難高。一定要以考據為基礎上升到理論研究,必須要有異端思想和獨立精神。決不許隨便濫發文章。”張仲謀《懺悔與自贖:貳臣人格》的“后記”,以吳先生1997年一次談話點睛:“現在有些年輕人,一天到晚忙著寫書,卻沒有時間看書,那怎么行。”寥寥數語而一針見血,足可為后學誡。由于是在注釋中處理這類內容,盡可放開手腳,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隨物賦形而一任大珠小珠落玉盤。
聊舉一隅以三反:
(1)不乏能于小細節中看出大境界的珍聞。《浙江日報》1988年3月22日第四版配照片刊發何燕芬的特寫《學無涯,思亦無涯》,當入年譜而未入。其中的重要材料,如引吳先生語“寫文章是件苦差事,我這輩子還沒與人板過一次面孔,卻也老是高興不起來”,以及“他說:‘晚上是必看電視的。這幾天在播放的《假若明天來臨》等電視劇,我看不錯。呶,基本上就是根據這書改編的。’他拿起桌上放著的已閱了一半的謝爾頓著的《有朝一日》。又講到魔幻現實主義作品《百年孤獨》的兩個譯本,還有《文匯報》上新近發表的謝晉導演關于電影發展問題的探討文章”,詼諧還原文人多面手的生活原色,再度讓人領略卓犖之士在攻書為學上的博通。這于今似已成空谷傳響,實值得移為年譜之注。
(2)論其性情氣質,陳白夜、徐琰合著的《天使陽光行》鄭重拾撿出“大學時期詞學大家吳熊和先生讓自命不凡的我們這一代警醒的驚世名言‘一代不如一代’”的史實。《杭州日報》1991年12月7日第三版《送禮》一文,娓娓道出了“有好多同學欣賞吳熊和先生的板書,便上門求字。吳先生生就菩薩心腸,一一滿足,大家的心里好像樹林里下來的陽光,好美。先生題的最多的是那句‘歸來笑拈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的實事。蔚然而深秀,大抵是讀到年譜中這兩節注的人會有的感受。仍以頁下注形式和正文敘述并轡,整部年譜是否頓然立體起來了呢?
出色的文人年譜,常常帶給編修者一種偵探般的快感。從紛繁的枝葉鱗爪里,經由思維的縝密勞動而爬梳、排比、推演,漸漸理出頭緒,甚至妙手有偶得,那一刻的快慰真是不足為外人道。這在我自己出于某種機緣而有幸編修某種文人年譜的過程中,確乎得到了共鳴。查考比勘之際,情不自禁地寫出上面的真實閱讀觀感,或許有在博學君子面前班門弄斧之嫌?但我執著地以為,隨著觀念的解放,過去被認為逝者才享有的年譜編修資格,儼然正把許多健在的名人也涵容進來,對象的擴展會不會帶來門檻的下降,是出版界面臨的新挑戰。本文為此提出的問題,對有興趣的同道來說想必不至于全然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