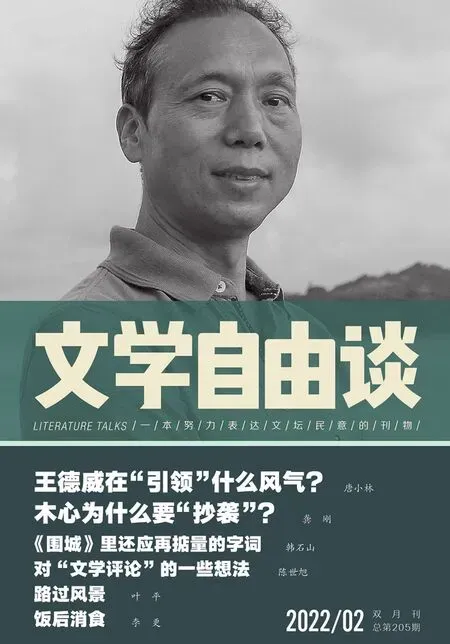短章一束
□郭建勛
一只貓的誄
有一年,我寫過一個《賦得貓》,扯到西方關(guān)于貓是邪靈的傳說。自以為寫得好。這是作家的通病,總以為自己寫的最好,別人的是狗屎。就得這樣,沒這么點(diǎn)自我激勵,這作還沒法兒寫。那么個苦差事。
過了些年,到今天重讀《賦得貓》,我卻覺得沒什么好,但也沒什么不好。過去的文章就像過往的人和事,好不好,都在那里。知道這一點(diǎn)并非易事。
寫文章,原本是記錄,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事,或那點(diǎn)兒心情,如此而已。好不好,皆是附麗。
一切沒那么重要,如一只死去的貓。
我說死去的貓是有天晚上散步時碰到的。那是一只小貓,在草叢里,很絕望地呼號,聲音卻大得像頭牛。一只很小很小的貓,估計出生也就半個月的樣子,一掌可握。是這樣的,它在我的掌中蜷伏而憩,鼻息均勻。
我動了惻隱之心。好像也不是動了惻隱之心,覺得不救它,它就死了。——其實(shí),就是動了惻隱之心。
我?guī)Щ貋砹耍€買了瓶純牛奶給它喝。我平時很少喝純牛奶。可見我真動了惻隱之心。發(fā)現(xiàn)自己這一點(diǎn)還是有點(diǎn)小殘酷的,有些人有些事我均視之如煙云,卻會對只貓動惻隱之心。
這似乎是我們,不,是我的病。
我把貓放在工作室,還囑咐保安,請他給貓喂奶。保安很愿意的樣子。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對我很客氣。我走了幾步又回過頭,看見他蹲下去服侍小貓。天地一片惻隱,像彌漫著郁金香。
回家的路上,我還想,把它喂大,在以后的日子里,也許是個伴,可以放到車上,哪去跟哪。我懷疑自己瘋了。我曾是那么討厭貓的人。
第二天去,貓痙攣不止。我找注射器給它嘴里注了水。沒用。幾分鐘后,它就死了,縮成一團(tuán),像個握緊的拳頭。
我估計昨晚那年輕的保安沒給它喂奶,他的惻隱之態(tài)一如我的惻隱之心,很有表演的成份。但我又為我的估計羞愧,或許他真的用了心,只是貓沒能挺過來。而且,我不該讓那個年輕人搭進(jìn)這個事里來。貓或有辜,他肯定是無辜的。
這樣想的時候,我就抽了一支煙,忙別的去了。
我要總結(jié)的是,別讓你廉價的惻隱之心綁架別人。當(dāng)然,這樣的總結(jié)是沒意思的,比說自己的《賦得貓》寫得好更沒意思。
貓未必是邪靈,人真的是。
鏡 子
有一年,我說要寫個短篇小說《鏡子》。想寫一個色衰的女人,老拿鏡子出氣,不斷打碎,又不斷買。
好在沒寫,寫了更沒女人歡喜我。
從年輕仔開始,我有好多事情都開了頭沒結(jié)果,包括一個爛小說。這些年,我想過開煙筍面館、寫一本“甘蔗理論”輔助孩子寫作文的書、買個皮卡車等等,連頭都沒開,直接不干了。
寫《鏡子》其實(shí)是由《空鏡子》引起的。好多年前一個蠻好的小說。一句話說,青春愛情留不住,就鏡子里五分鐘的“歡顏”。這有點(diǎn)小厲害,把佛的那點(diǎn)小東西埋里面了。
一些作家喜歡弄點(diǎn)佛呀道呀的搭頭,賈平凹尤甚。但都露在外面,很淺。說佛就是“菩提本非樹”,說道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貌似奧古,其實(shí)淺薄。卻有效。像現(xiàn)在的互聯(lián)網(wǎng)黑話,發(fā)朋友圈不說發(fā)朋友圈,說鞏固私域流量,但就能把到妹,簡直能氣死你。
好像王安憶說過,《肉蒲團(tuán)》有種天真的無恥,寫性勝過《金瓶梅》。我對她頓時肅然起敬。“天真的無恥”其實(shí)就近乎——不是近乎,就是佛。禪宗的那幾個人把“天真的無恥”玩到了極致。清的那些人玩不了了,就寫,曲里拐彎,用現(xiàn)在的話說,叫“高級黑”。
《空鏡子》大抵只能叫“低級紅”,但也不簡單。
我近年有個“鏡子理論”。“甘蔗理論”是方法論,“鏡子理論”那是純哲學(xué)。
人和人之間,像塊鏡子,你覺得他對你好,那是因為你對他好;你對他齟齬了,八百年前他就對你如此了。
即 然
很多年前,我寫過一個小品文《聯(lián)是酒家》。說——,打住一下,我的寫作有個小原則:凡小說,寫假的;凡散文,寫真的。我謂之誠實(shí)寫作。我知道,不少人反過來:凡小說,寫真的;凡散文,寫假的。當(dāng)然,這不重要。個人喜惡而已。
《聯(lián)是酒家》里說,年輕的時候,我“聯(lián)”“朕”不分,“酒家”和“灑家”不分。鬧了點(diǎn)笑話。現(xiàn)在想起來,其實(shí)這也不重要。我分清楚了這么多年,也未見有多厲害。
所以,當(dāng)有個校長說“鴻浩之志”,一些人罵得傷筋傷骨,我覺得過了。我通透了。
通透的意思是,凡事就這樣,該“鴻浩”的“鴻浩”,該“鴻鵠”的“鴻鵠”,別覺得念對了“鴻鵠之志”就可以問鼎北大,別說你念對了,就算你真?zhèn)€有“鴻鵠之志”,也問鼎不了。
既鴻且浩,總算扯到“既”字上來了。是的,很多年,我把“既然”寫成了“即然”。發(fā)現(xiàn)這個事時,我都做了編輯了。我那時還沒有現(xiàn)在這么通透,很害羞了一段時間,喝啤酒時少喝一杯,以示懲戒。
世事總那么吊詭,有一天,汪曾祺告訴我,寫文章少用或不用關(guān)聯(lián)字。從此,我?guī)缀鯖]用過“既然”,像空谷里練就武藝的高手,出來尋仇,仇家早得花柳病死了。
既然“既然”錯成了“即然”,那么,“即然”當(dāng)“既然”使,也是沒所謂的,不妨礙我把蔥花煎蛋煎得那么好。
當(dāng)然,如果想吃寫作這碗飯,那就既不把“鴻鵠”寫成“鴻浩”,把“既然”寫成“即然”,也不要把“朕”寫成“聯(lián)”,把“灑家”寫成“酒家”。因為“既然”就是“既然”,你寫成了“即然”就錯了。即使你蔥花煎蛋煎得再好,也不行,人家會笑話你的。
漆 畫
那一年,我認(rèn)真地看過一個人畫漆畫。在我家的火柜上。那個人十七八歲的樣子。我那時十二三歲。
他畫得不好。很笨拙地捏著筆,蘸黑油漆在干了的紅油漆上畫。喜鵲畫得像烏鴉。甚至可以說,連烏鴉都不像,不知道他畫的什么。
但我娘說他畫得好,還要把我一個親戚作媒給他。不知道她真說了還是哄他的,反正沒下文;或許說了,可我那個親戚不同意吧。也難說是他不同意。
他后來做生意有一套,就開了加油站。
我到他的油站加過油。有一年回去,油站撤了。我停了車兀自想了一會兒,想起他當(dāng)年在我家火柜上畫漆畫的情形,那只烏鴉就飛了起來。
不知道前年還是去年,我在朋友圈看一個人發(fā)過漆畫。說是他家鄉(xiāng)祖?zhèn)鞯钠峤常嬈岙嫼苡忻N业诙握J(rèn)真地看了那些漆畫,覺得一般。主要是畫的內(nèi)容一般。梅、蘭、喜鵲登枝等等,俗不可耐的東西。
說起來,這是中國的油畫,但畫的東西襲舊,紙上畫的如此,瓷上畫的如此,木板上畫的亦如此。都在一個套套里。
我們很多東西都在套套里,字、畫、做家具、看病,都在套套里轉(zhuǎn)。剛開始是得鉆進(jìn)套子的,但得出來,破,才有意思。
一代代老那幾枝枯荷那一樹臘梅,不過是從早到晚吃八刀湯,你非得說你吃不厭,我不信。
說起來,我倒歡喜那個把喜鵲畫成烏鴉的漆匠,他至少有兩點(diǎn)是可敬的:一,他敢畫,喜鵲畫成了烏鴉,或什么都不像,還繼續(xù)畫;二,他敢不畫,突然擲了筆,開加油站了。
我娘就覺得他畫得好,我也覺得他的油不錯,哪怕有人說有點(diǎn)缺斤少兩。
竊以為,較之缺斤少兩,缺意思更沒意思。
寧波床
為什么叫寧波床?好像當(dāng)年我也問過我的舅舅。他們說不知道。當(dāng)然不知道。我四個舅舅,三個比我大一丁點(diǎn),小舅比我還小。
那張寧波床是我外公外婆家最厲害的家具。是從地主家分來的。紅油漆有點(diǎn)斑駁,但氣勢還在。層層疊疊的檐抻出來,雕了花鳥,還嵌有琺瑯,琺瑯上也嵌了花鳥。左右兩個柜。柜的抽屜銅鼻兒呈魚狀,劃了細(xì)細(xì)的鱗,掰一下,叮當(dāng)作響,魚在跳。連左右兩柜的床前是踏板,板面上磨得起了木褶子。
床很大。我們幾個舅甥睡一起,翻筋斗,打架,不敘長幼。那時候,外公外婆家又蓋了五間新房子,木柱木椽木門木窗,一溜白,窗子上糊了米紙,也白,好漂亮。那是外公外婆家的黃金時代。
花開到極艷,就要枯敗了。凡人凡事,極盛必衰。我的外婆死了,這個家就呼啦啦一點(diǎn)點(diǎn)歇?dú)狻?/p>
二舅去當(dāng)兵了,大舅倒插門了,小姨出嫁了,外公死了,三舅武漢打工了,小舅又倒插了。
反正,那些年,傳到我耳里的關(guān)乎舅家的事,都是壞消息。壞消息也得聽。前前后后一二十年。其間,我客居深圳,偶爾回趟家,又更偶爾地去趟大舅的家。
那個老宅子,聽說要塌了。
塌了就塌了,我也懶得去看。幾個舅舅,零散各方,也很少見面。
有一年,大概七八年前吧,也許五六年前,去給大舅拜年,忽動了興,就信步到了那個老宅。剩了兩間還是一間半,半塌在那,衰草連橫。搜尋間,我看到了一塊彩色的碎琺瑯,上面半幅梅鵲圖。是那張寧波床上的物件。偌大偌美的那張寧波床就剩了這么片碎琺瑯。分來的,又分了去。我有點(diǎn)想撿起來,留個念想,到底也懶得撿。
原址蓋了房。我去的時候,還沒裝修,一個還不錯的平房。我有點(diǎn)為他們高興。又跟著一大群表弟表妹去給小舅拜年,滿滿一屋人,個個門高樹大。
塌了那么些年,這個家族好像又抻起腰來了。
聽說,小舅的閨女去年出嫁了。小舅比我小一歲,在天津一個家具廠上班。
過年的時候,我問他回去過年不?他說不回。我也說不回。沒聊別的。其實(shí)我本想聊點(diǎn)別的,比如那張寧波床。到底也沒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