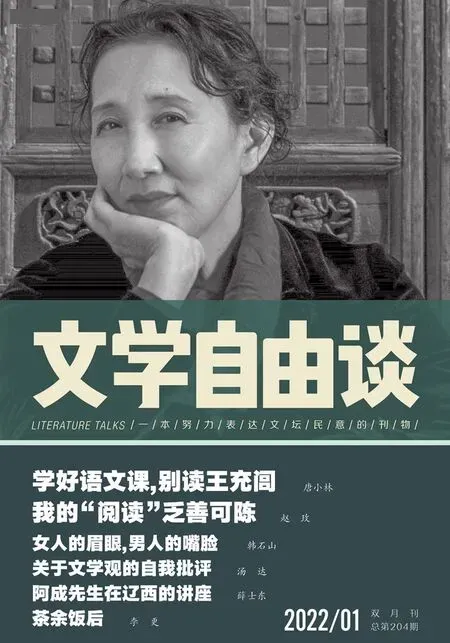阿成先生在遼西的講座
□薛士東
無功利的讀書
窗外是“三燕古都”遼寧朝陽的千年老街“慕容街”。沒有風,時令已進晚秋,但暖暖的陽光透過玻璃窗,投射在“龍翔書院”的大講堂里。作家阿成先生是這場講座的主講人。面對我們幾十個聽眾 ,阿成先生娓娓道來,用通俗易懂的民間俗話講述他的人生經歷、讀書心得和小說創作的體會。只是時間太短了,僅一個半小時。好在我錄了音,可以反復聆聽,認真體悟。
阿成先生說:“我認為讀書最好的方式,是無功利的讀書。不是為了考試,不是為了這個那個,就是喜歡看。我喜歡看書到什么程度呢?年輕的時候我是無軌電車的駕駛員,開車的時候衣兜里常備著一本袖珍版的古典詩詞,唐詩、宋詞、元曲什么的,都是小薄冊子,很便宜,一兩毛錢一本。到一站了,拿出來看一下:‘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乘客都上車了,乘務員大聲說,關門!我就繼續往前開。到了下一站,掏出來繼續看:‘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你說讀這些東西背誦這些東西,干什么呢?當時就是空虛,就是喜歡。僅此而已 。”
阿成先生說,這些無功利的讀書,想不到日后還真是起了點作用。早年他考黑龍江大學比較文學碩士研究生的時候,考試遲到了十五分鐘,而且那時還沒有任何復習材料,也沒上過什么補習班,考試的時候還真的是第一個交卷兒。沒想到順利通過了。總結起來,就是仰仗于當年的無功利的讀書。
自信與修改
阿成先生講,其實就讀書而言,選什么書很重要。他認為應該選擇自己喜好的書讀。“我才不管你是多大的作家,也不管你多么有名,我看好就好,我看不好,對不起,即使是獲過什么什么大獎我也棄之不讀。這才是正確的讀書方法。我們老是講讀書讀書,讀什么書啊?告訴你,讀你喜歡看的書,讀你能夠看下去的書。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對寫作者來說利莫大焉。不要硬看那些你看不進去的、質量可疑的書。”
阿成先生說,我剛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一是初涉此道,二是又年輕氣盛,非常自負,感覺自己是懷才不遇,覺得自己寫的挺好啊,為什么這個刊物不選,那個刊物也不用啊?不僅如此,稿子投出去還不斷地遭遇退稿。這些編輯是不是有眼無珠啊?是不是咱沒有關系,沒給人家送禮啊?后來,他終于明白了一個非常淺顯,也容易做到的真理,那就是要學會佩服別人。這不僅是一種聰明,更是一種智慧。這與個人境界無關。
阿成先生說,“中國人有一個有趣的習慣,只要是印成鉛字的文章、文字就深信不疑。我覺得這種認知方式并不可取。我經常把報紙上的某段新聞或者小故事改一改,如果我要寫這段該怎么寫該怎么改?當然得是值得一改的。如此行徑我覺得挺有意思。我要說,一篇好小說一定是改出來的,是反復修改出來的。法國有位女評論家說過這樣一句話,我一直奉為座右銘。她說(大意),無論你這篇作品改了多少遍,最后成稿的時候,要給讀者的印象,是你‘隨隨便便’把它寫出來的,很自然,很流暢,很親切,也很幽默、優美。這句話非常有道理。我們修改作品的目的,就是把作品變得輕靈、輕逸、自然,像水一樣往前流淌。”
閱讀與節點
阿成先生說,中國是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如果你的小說能被中國人認可,就已經相當了不起了,還想什么外國呀?自古以來,比如唐詩、宋詞、司馬遷的《史記》等等,先人們的這些優秀作品并沒有受到外國的影響啊,但絲毫沒有泯滅它們智慧的光芒和藝術的魅力。所以,經歷過種種的挫折之后,他就想用中國的情感,中國的表達方式,中國人的審美觀點和價值觀來寫小說。這應該是一條正確的道路。當然阿成先生并不反對欣賞和借鑒外國的優秀文學作品。他說:“只是從此之后,我想作為一名中國作家,有必要改變洋腔洋調的寫作方式、敘述方式,用中國的氣派來創作自己的作品,抒發自己的情感,只有這樣才能鮮活地、有效地、豐富地凸顯自己的創作價值。”當然,這種改變還是仰仗于之前的無功利閱讀,使得他寫作方向和路徑的改變得以順利進行,成為了其個人創作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節點。
寫作,一個人的宿命
回顧寫作生涯,阿成先生好像是在說著別人的故事,“那個時候只要是禮拜天,我就騎個破自行車去編輯部寫作。帶什么飯呢?就是家里的剩飯剩菜。孩子說,老爸,咱家還不至于到這種程度吧?又是咸菜又是剩飯的。走苦行僧的道路哇?我說,老爹沒寫好小說,不配也沒資格吃好吃的東西。到編輯部后開始寫。記得有一次有一段我不會寫了,就站在那兒看著窗外。那是個冬天,窗外大雪紛飛。自己感覺也挺悲愴的。”阿成心里在想,這是圖什么呢?盡管如此,還是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寫作步伐。
阿成先生說,當初寫稿子用的稿紙多。朋友知道他愛寫東西,就給他送來十幾本稿紙。但很快就用完了。朋友說,你吃稿紙啊?過了兩天,朋友提了整整一捆五十本稿紙說,這回夠你寫的了吧?當時他也覺得自己中了邪。有人問,阿成先生,如果有來世你還想當作家嗎?阿成先生這樣說:“如果真的有來世,打死我也不當作家。太難受,太煎熬了,這是拿自己的生命賭一生啊!如果寫不出來,寫出來的東西又沒人愿意看,情何以堪?如何見龍江父老和家人呢?你一輩子正事兒不干,天天寫,除了大年三十和初一不寫,所有的節假日都在寫,是不是對自己和家人太不負責任了?”這大概就是一個人的宿命吧。
阿成先生的創作生涯
怎么能把小說寫好呢?
阿成先生說,那個時候他已經認識了王倜老師,舊社會王老師曾是哈爾濱東陲商報館出版的《小說月報》主筆,哈爾濱被揪出的第一個右派。當時他是一中的老師。阿成經常拿自己的小說向他請教。王老師沒兒沒女,住在一間只有六七平米的小屋子里,一進門就到床邊了。加上王老師又是高度近視,兩個人幾乎是頭碰頭才認出他來,“哎呦,阿成。”要命的是,兩個人都不善于和不太熟悉的人交談,尷尬地坐了一會兒,阿成把小說放到他那兒就走了。過兩天再去取的時候,發現稿子上面紅彤彤的改了一大片,都是文中的錯字,看了以后汗水順著腦袋往下淌。這才是貨真價實的汗顏,真丟人吶。從那以后開始認認真真地寫稿子。可是,無論怎么認真,投出去的一篇小說能退十次。因為不甘心不服氣呀,這個編輯部不行,再給另外一個編輯部。阿成說:“那個時候不像現在用電腦打字,就是用鋼筆,我寫得像鋼楷一樣,標點符號都非常標準,錯一個字,絞成一個小方塊兒貼上,再補寫上。編輯的那些退稿信我都會反復讀。我這人有個優點,也算缺點,越退稿越不服氣,我就不信了,還寫。我把單位那個大瓶子的紅色鋼筆水順回家(紅鋼筆水單位人幾乎不用)。所以那些年寫草稿我一直都是用紅筆寫。記得年輕的時候買了一個金筆,寫得連筆尖上的小金疙瘩頭兒都磨沒了,就剩后面已經被磨成斜面的鐵片兒。我打算留給女兒勵志,女兒笑了,說,拉倒吧老王同志,勵啥志呀。當年,我家里點爐子全都用我的廢稿,卷一卷兒,灑點煤油點著引火。當時賣出去的廢稿差不多有一手推車。”
阿成先生在隨筆《江邊囈語》中寫到:
每搬一次家,我總要扔掉一些手稿。這些手稿或機智或拙劣,或真誠或自欺欺人地,真實地記錄著我的那一段生活。天可憐見,我每次扔掉的手稿都不少。這使我感到汗顏與自卑。畢竟這些手稿當中有三分之二是真正的廢稿。眼下,將他們做廢紙賣了,賣給了一個從浙江到東北走街串戶收廢品的老人,他說,字寫的好多哇。我冷眼看了看他,沒吱聲(從這以后我也明白了,并不是所有人的冷眼都含有惡意)。他給了三十塊錢。我知道,這三十塊錢除了能證明我絕對的愚蠢之外,還能說明什么呢?
汪曾祺曾經這樣寫道:“湖南的何立偉,哈爾濱的阿成,山西的曹乃謙和我的創作思想一致,走的是平實的路子,評論界稱他們受我的影響,為抒情現實主義和風俗畫筆致,他們都正寂寞地寫著……”
“踏踏實實地寫中國氣派的小說”,這是在阿成先生的講座上讓我銘記于心的一句話。值得一提的是,在聽阿成先生講座時,講桌上放的那一摞書,是我多年來收藏的十二本阿成先生的作品集(據說他已經出版了四十多本書),這次帶到座談會上,就是想告訴阿成先生,在遼西有一個他的讀者,或春或秋,或晨或午,或晴或雨,平心靜氣,摒棄功利,用一顆欣賞的心閱讀著他的作品。
(本文根據錄音整理,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