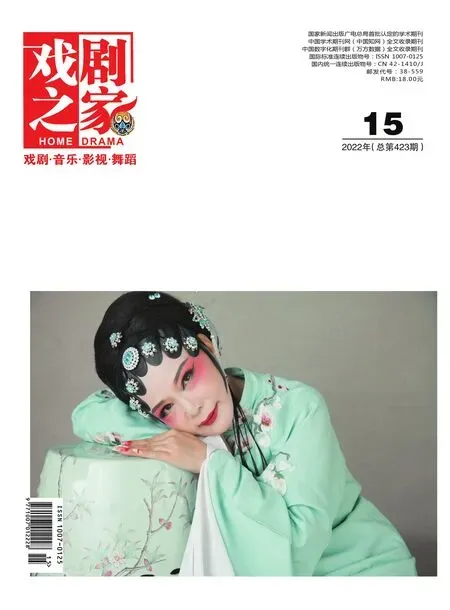論荒誕派戲劇的非邏輯性與錯亂性
——以《禿頭歌女》與《等待戈多》為例
鄧力嘉
(成都理工大學 傳播科學與藝術學院,四川 成都 610059)
縱觀西方戲劇的流變歷程,無數藝術才子致力于通過戲劇化的情節內容,表征出個人或集體所進行的獨特社會思索與精神探求,由此涌現了大批獨具特色的戲劇流派,如寫實主義戲劇、荒誕主義戲劇、象征主義戲劇、表現主義戲劇等。作為20 世紀50 年代興起于法國的荒誕派戲劇,其受到半個世紀內兩次世界大戰的毒害,以至戰爭的挫敗與生活的無望日益僵化著人心,異化著精神。加之各國將恢復經濟放在首位,選擇性忽視戰后精神文明的重建工作,從而讓本就陌生的人際關系變得愈加疏離,游走在可有可無的社會邊緣。在此背景下,荒誕派劇作家們逐漸喪失了對于民生的關注、社會的體恤以及國家的信任,轉而投向如何用荒誕、非邏輯性的戲劇形式展現人類存活于世的價值、一生等待的目的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虛無縹緲的依附關系。《禿頭歌女》與《等待戈多》作為尤涅斯庫和貝克特兩位荒誕主義大師的扛鼎之作,充分展示出人與人之間情感的缺失、靈魂的空虛與精神的異化,讓本就充斥著非邏輯性與錯亂性的荒誕主義,顯得愈發怪誕、引人深思。
一、非邏輯性的語言是機器般的循環往復
荒誕派以劇本情節的非常規化推進,人物語言的顛三倒四,主題要義的破碎拼湊、循環往復作為戲劇的具體表現形式,以此區別于眾多西方戲劇流派。其中,非邏輯性的戲劇語言是荒誕派戲劇的一大特色,馬丁·埃斯林在《荒誕派戲劇》中談及“荒誕派戲劇傾向于徹底地貶低語言,語言本身在這一概念中仍然起著重要作用,但是在舞臺上發生的事情優于人物說出的詞語,有時甚至與其矛盾”。究其原因,于現實層面而言,荒誕派劇作家通過戲劇舞臺中人物對話的非邏輯性,以此映襯市民階級的乏味生活與社會秩序的崩塌;于精神層面而言,由紊亂思維與顛倒語言所建構的劇作本身,實際上便是荒誕派劇作家們所處時代的縮影,直指矛盾、荒誕的時代主題。劇作《禿頭歌女》《等待戈多》通過劇中人物的語言對話將此種非邏輯性的概念不斷傳遞,深化著劇作家們所強烈抨擊的世界之虛無、怪誕。
在《禿頭歌女》中,情節、矛盾、人物沖突等戲劇所需的關鍵要素皆為人物語言“讓道”,荒誕的“對話”成為了戲劇的主體。尤涅斯庫將人物的單調語言、生硬交流與可有可無的人際關系相融匯,樹立起第一個荒誕派劇本的語言標桿。《禿頭歌女》以一對平庸且普通的史密斯夫婦在晚飯后的閑談對話拉開序幕,作為中產階級的史密斯夫婦擁有屬于自己的房屋與女傭人瑪麗,但二人卻并未表現出中產階級所特有的情致與愛好。相反,二人冗雜無味的閑談始終圍繞著家庭的日常食物,如魚、肉、湯、英國茶等不能再普通的食物。不難發現,史密斯夫婦實則是劇作家所精心設計的諷刺性人物,即使二人的語言符合基本邏輯,但無疑也只是如“機器”般不斷重復相同的生理行為。尤涅斯庫將此種語言方式延續于本劇的所有出場人物中,隨著女傭人瑪麗、前來拜訪史密斯夫婦的馬丁夫婦以及消防隊長等人物的不斷登場,觀者會驚愕地發現這不斷重復的人物對話已然成為了劇本的主要組成部分,但人物的語言卻依然顯現出矛盾、毫無意義的特點。誠然,此荒誕的戲劇效果無疑是尤涅斯庫有意為之,而其真正的意圖便是將劇中頻繁登場的諸多人物塑造成種種單調的語言機器,通過空洞地說出匪夷所思、不合時宜的錯亂語言以及在毫不相關的環境中,提出一些自相矛盾、非邏輯性的個人觀點等行為,表明尤涅斯庫所處時代下人們積極活躍、條理明晰的思維方式的喪失。從一定程度上而言,荒誕派戲劇中的人物對話已不再是能夠以豐富的思想內涵展現人物性格特點的戲劇表達途徑,而僅僅是一個人類所能體現出具備語言能力的生理行為。
此外,《禿頭歌女》戲劇語言的非邏輯性還體現在幾處看似可有可無,實則至關重要的細節之中。例如,當史密斯先生談及自己認識多年的好友波比·華特森時,先是訴說他已于兩年前死去,又自認為參加波比的葬禮是在一年半之前,而當旁人談及波比的死亡時間時,卻又已隔三年之久。乃至到最后,史密斯更加驚訝地發現“波比·華特森”居然是他一家族人所共用的姓名,而推銷員的職業則是這一家族所共同從事著的唯一工作……如此荒唐,思維邏輯上絕無可能發生的事,卻有理有據、理所當然般在主人公身上一一靈驗。以至于在結尾,馬丁夫婦取代了史密斯夫婦,再次開始了同本劇開頭如出一轍的生活閑扯與無聊對話。在眾多循環往復的非理性、機器化的人物語言下,《禿頭歌女》在戲劇精神上的荒誕化意蘊也愈加濃郁,而史密斯夫婦、馬丁夫婦等諷刺性人物的塑造不僅僅表征著冷漠社會下人際交往之間的隔絕與背離,更寓意著畸形的資本主義發展對人物語言、精神的禁錮,人與人之間的漠視與毫無靈魂交流的主題精神也隨之顯現。
二、錯亂性的情節是混沌人生的無望等待
顛倒錯亂,折疊重復的情節設置是荒誕派戲劇的另一重要特征。在這前因后果被倒置的情節中,人物日復一日重復著已然發生的行為動作,談論著答案已然明了的困惑與抉擇,希冀著明知絕無可能出現的轉折與未來,呈現著一個“什么也沒有發生,誰也沒有來,誰也沒有去”的悲劇。直到在千篇一律、重復錯亂的無望等待中,主人公的虛無人生同時間一道,徹底消散于天地之間。
塞繆爾·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包含了眾多錯亂、荒謬的情節,其中可以分為因果倒置產生的混亂和不知目的、不明方向、不曉事因而造成的錯亂。劇中簡明地采用了兩幕劇的演出形式,將戲劇的發生背景設立在黃昏時分的鄉間小路,直白敘述了兩個流浪漢愛斯特拉岡和弗拉基米爾,在鄉間小路的路口等待著一個名為“戈多”的外來人,二人說不清等候的原因,更道不明直至何時才能見到“戈多”本人。在這乏味的等待過程中,兩人通過脫靴子、抖帽子等方式消磨著時間,直至自稱“信使”的小男孩上場,并勸誡二人“今天戈多不會來了,明天再來等他。”于是次日,愛斯特拉岡同弗拉基米爾又回到原地,重復著前一天的行為與動作,二人的人物關系也不斷從相識,到忘卻、互不相識,再至重新認識的錯亂過程。其中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劇中從未出場的“戈多”神秘且虛幻,但實際卻貫穿著愛斯特拉岡與弗拉基米爾的錯亂行為始終,主導著情節不斷走向紊亂、重復的發展歷程,而相似的情節、動作也在劇本中無限地輪回,致使本應簡潔明了的兩幕戲劇給予觀者內心一種深不可測、無法望及盡頭的空虛感。
正因戲劇角色在言行舉止上表現出的重復、錯亂,才不斷使荒誕的戲劇情節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二人反復脫鞋子、摘帽子、模仿著波卓和幸運兒的奇怪動作、在每天等不到“戈多”后嘗試著上吊自殺……在某種意義上,劇中的人物始終未能觸及人生在世的實質意義與至高真諦,既沒有長遠的目標也不知為何而活,于是便只能在錯亂的人生中依托重復的動作、循環的語言暫求到一個共同的、能夠寄予個人希望的“庇護所”,那便是——等待戈多。在塞繆爾·貝克特的荒誕化視角下,“等待”的這一本應無意義的行為也漸漸具備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因為這不僅是愛斯特拉岡與弗拉基米爾二人所能夠做出的唯一選擇,更是在映射無數身處貝克特同時代下普通群眾所能遵循的、唯一的存活于世的“生活方式”,而無盡的人生等待、混沌的人生命運以及幻滅的人生希望早已成為了二戰后人類所共同面臨的精神創傷,亟待著世人的反思。
三、荒誕性的題材是破碎世界的虛無重現
英國作家馬丁指出,荒誕派戲劇的主題是“人類在荒誕處境中所感到的抽象的心理苦悶。”縱觀眾多荒誕派戲劇作品,不難發現其所選擇的題材類型具有高度相似性,荒誕派劇作家們借怪誕、荒謬、令人費解的戲劇內核,展現著當代下層群眾的真實生存狀態:大眾群體與休戚相關的社會所脫節,人際交往的真情實意為金錢與利益所代替,以至人類逐漸喪失了原有的鮮活本質,進而麻木屈服于虛無的社會。但同時不難發現,不同戲劇作家對于此戲劇內核的展現有著各自獨特的表達方式,《禿頭歌女》與《等待戈多》雖都為荒誕派戲劇的扛鼎之作,但二者在關于荒誕性戲劇題材的具體呈現方式上卻依然存在著差異。
尤涅斯庫筆下《禿頭歌女》的題材核心意指于市民生活的苦悶與冷漠社會的虛無。為了達到凸顯冷漠、虛無的戲劇目的,尤涅斯庫不僅將僵硬、枯燥的人物語言作為推動荒誕戲劇發展的重要手段,更從史密斯夫婦、馬丁夫婦等人對于生活日常的陳詞濫調出發,展現出一幅生活無趣、人生無味、世界毫無生機的傳奇名場面。墻壁掛鐘的無規律敲打、波比·華特森眾說紛紜的死亡時間、馬丁夫婦無止境的夫妻猜疑、消防隊長別離時的時間疑惑……在尤涅斯庫的戲劇世界中,“反傳統”“反邏輯”已然成為社會生活的代名詞,本應多姿多彩的世間萬物都喪失了各自的鮮活本色、存在于世的價值意義,唯剩下如史密斯夫婦二人空殼般的肉體延續著毫無意義的人生,詮釋著現實世界的虛無。
反觀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其對于荒誕題材的表現形式可以概括為“語言的匱乏,動作的枯燥,時間的重復,等待的無盡”,其中劇中人物對“戈多”這一所謂“希望”形象的虛無等待占據著戲劇的重要部分。愛斯特拉岡和弗拉基米爾在關于“戈多”的無盡等待中,不斷遺忘著社會中的人際關系,忘卻著已然做過的事、說過的話,在“戈多”必經的鄉間小道上向大眾無窮復述著輪回般荒誕的故事。戲劇《等待戈多》鮮明區別于《禿頭歌女》枯燥且死板的人物對話的題材表現方式,其將荒誕性的戲劇內核通過愛斯特拉岡和弗拉基米爾兩人的消遣行為、心理過程、錯亂關系來展現,將“戈多”這一起決定作用的人物,描繪得朦朧且虛幻,意指二戰后廣大法國人民的生活希望的迷失、對于虛無世界的無盡惶恐、對于人生的無望。至此,荒誕派劇作大師貝克特的創作意圖也逐漸明了,其旨在通過戲劇作品中世人對于“戈多”這一希望形象的等待,揭示所處社會的虛無與世界的荒誕。一如劇中“將說未說,欲現未現”的潛臺詞一般——如果“戈多”永遠不會到來,那么愛斯特拉岡與弗拉基米爾的重復等待便毫無意義;而即使“戈多”最終來了,那么它所帶來的無限失望感也同樣會讓眾人先前的等待成為“無意義”。貝克特用以此種戲弄般的戲劇方式,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給每一個普通人所帶來的精神挫敗感外化于對未來的無意義“等待”、對破碎世界的虛無與絕望。
四、結語
正如“荒誕派作家看重人生的荒誕性,認為人的存在與不存在都是荒謬的,人活著就是一場夢,人的努力既無意義也無用處。”毋庸置疑,荒誕派戲劇家們在經歷了世界大戰的精神性創傷與毀滅性洗禮后,又繼續面對突飛猛進的工業化變革與資本主義經濟急速膨脹的冷漠社會,表現出極度的懷疑、恐慌、畏懼。他們將全部身心寄托于荒誕劇本的創作中,試圖對非邏輯性、錯亂、異化的破碎世界重新進行拼湊,嘗試重建已然被摧毀的信仰根基。但希望與現實的巨大落差,讓劇作家們在虛無的時間與空間的雙重失落中,只得靜默等候著永遠不會到來的“明天”,不停地期盼又不斷地失望,循環往復,周而復始。
當身處21 世紀的現代學者們再次回首荒誕派戲劇時,卻也在異化、荒誕世界的戲劇表象下,探尋出縷縷具有積極意味的時代發展軌跡。因為“荒誕的存在并不是人的存在本身荒誕,而是人在荒誕世界對理想無限的沖擊和超越。”荒誕的戲劇是無數劇作家們正視生活落差的勇敢嘗試,更是向落魄、無望的人生困境尋求解脫與超越的堅定信心。正因如此,荒誕派戲劇才得以從眾多西方戲劇的流變中脫穎而出,開創一片嶄新的戲劇天地,并傳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