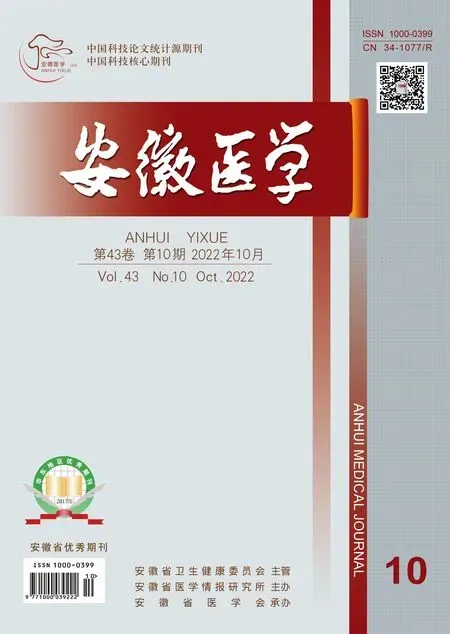急性丘腦梗死后認知功能及抑郁狀態與事件相關電位P300的相關性分析
李春芳 徐蘇林 苗 青 胡林壯 張 干
據WHO統計數據顯示,至2019年卒中已是我國疾病致死和傷殘的第一大病因,2019年卒中患病數2 876.02萬人(1 468.87/10萬),死亡數218.92萬人(127.25/10萬)[1]。近年一項大型國際隊列研究提示卒中后認知障礙的發病率為24.0%~53.4%[2],認知障礙及抑郁情緒會直接影響卒中患者肢體功能恢復,增加患者死亡率及致殘率[3],嚴重影響預后,早期干預認知障礙及抑郁情緒可能作為腦梗死二級預防的策略之一[4]。額葉、角回、丘腦等腦內關鍵部位梗死患者常出現認知障礙[5]。丘腦是聯系額葉皮層及腦干的中繼站,丘腦損傷后不僅會出現肢體麻木、無力等臨床癥狀,還會合并廣泛的認知障礙及情緒異常。但丘腦梗死多為腔隙性梗死或穿支動脈梗死,臨床癥狀多樣,不少患者因癥狀輕微,自身重視度不夠,治療依從性不高,但其引發的認知及情感障礙及導致的遠期不良預后卻不容小覷。本研究采用病例對照的研究方法,分析丘腦梗死后認知功能、抑郁狀態及其與事件相關電位P300的相關性,探討事件相關電位P300對丘腦梗死后認知功能障礙及抑郁的診斷價值,為早期識別丘腦梗死后的認知功能障礙及抑郁并及時采取干預措施提供科學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20年5月至2021年7月在蚌埠市第三人民醫院神經內科住院治療的患者為研究對象,其中觀察組(丘腦梗死組)為在我科住院治療的30例急性丘腦梗死患者,對照組為同期為30例門診就診且無腦血管病史患者,兩組對象性別、年齡、受教育年限及合并癥等基本資料均衡、可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參加本研究入組對象均簽署知情同意書。本研究經過蚌埠市第三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倫科批字[2020]第47號)。
觀察組納入標準:①符合急性腦梗死診斷標準[6],所有患者均經頭顱MRI檢查證實存在丘腦梗死;②能夠配合電生理檢查及量表評估。排除標準:①有嚴重認知障礙、失語等不能配合者;②有精神疾病史者;③既往有器質性疾病如額顳葉及島葉等大面積腦梗死、腫瘤、感染及代謝性腦病等導致認知功能障礙的患者;④合并嚴重的基礎疾病如心功能衰竭、肺功能衰竭及惡性腫瘤者。對照組納入標準:無腦血管病史;能夠配合檢查及量表評估。排除標準:同觀察組。

表1 兩組研究對象一般資料比較
1.2 方法
1.2.1 臨床資料 所有入選患者完善一般臨床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水平、既往基礎疾病史,吸煙及飲酒史等。丘腦梗死組患者完善如血常規、凝血功能、生化等化驗,完善如心電圖、頸動脈彩超及頭顱CT檢查,并在一周內完成頭顱核磁及血管檢查。
1.2.2 事件相關電位P300檢查 受試者在試驗前清洗頭皮降低阻抗,要求檢查環境安靜,室內溫度適宜。本檢查均在單獨的神經電生理室由神經電生理醫師完成。使用丹麥MEDTRANIC肌電誘發電位儀,按國際腦電圖10-20系統法安放標記電極,記錄電極安放于Cz點,參考電極安置于左右側耳垂,接地電極置于FPz。采用聽覺Oddball范式,靶刺激為概率20%、頻率2 kHz、聲強80 dB的純短音,記錄受試者P300的波幅和潛伏期。
1.2.3 量表評估 受試者在安靜的神經心理室,由神經內科接受過神經心理量表培訓合格的主治醫師測評。認知評估量表采用簡易精神狀態評價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蒙特利爾認知評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scale,MoCA)、抑郁評估量表采用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24項。其中MMSE量表判定標準為:最高得分為30分,分數≥27為正常;MoCA量表判定標準:最高30分,分數≥26分為正常,如果受教育年限≤12年則加1分;HAMD量表判定標準,總分<8分:正常,總分8~19分:可能有抑郁,總分20~34分:肯定有抑郁,總分≥35分:嚴重抑郁癥。

2 結果
2.1 兩組研究對象認知障礙發生率比較 觀察組認知障礙發生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研究對象認知障礙發生率比較[例(%)]
2.2 兩組研究對象認知功能及抑郁相關量表得分比較 觀察組MMSE總分及計算力、回憶子領域得分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差異(P<0.05);觀察組MoCA總分及視空間、注意、語言、抽象、延遲回憶子領域得分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可能有抑郁癥患者比例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5。

表3 兩組研究對象MMSE總分及各子項得分比較(分)

表4 兩組研究對象MoCA總分及各子項得分比較[M(P25,P75),分]

表5 兩組研究對象抑郁狀態比較[例(%)]
2.3 兩組研究對象事件相關電位P300潛伏期及波幅的比較 觀察組事件相關電位P300潛伏期長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6。

表6 兩組研究對象事件相關電位P300潛伏期與波幅比較
2.4 P300潛伏期和MMSE總分、MoCA總分及HAMD得分的相關性分析 采用Spearman秩相關檢驗分析研究對象P300潛伏期與MMSE總分、MoCA總分及HAMD總分的相關性,結果示P300潛伏期與MMSE總分呈負相關(r=-0.827,P<0.001),與MOCA總分呈負相關(r=-0.886,P<0.001),與HAMD總分呈正相關(r=0.873,P<0.001)。見圖1~3。

圖1 P300潛伏期與MMSE總分的相關性

圖2 P300潛伏期與MoCA總分的相關性

圖3 P300潛伏期與HAMD量表得分的相關性
2.5 P300潛伏期對丘腦梗死后認知障礙及抑郁的診斷價值分析 MoCA總分<26分者為存在認知障礙,賦值為“1”,MoCA總分≥26分者為正常,賦值為“0”;HAMD得分≥8分者為可能有抑郁,賦值為“1”,HAMD得分<8分者為正常,賦值為“0”。以P300潛伏期為檢驗變量,以是否為認知障礙及可能抑郁為狀態變量,繪制ROC曲線。結果顯示:P300潛伏期診斷丘腦梗死后認知障礙曲線下面積為0.940(95%CI:0.883~0.997),臨界值為363.5 ms,靈敏度為85.71%,特異度為92.85%。P300潛伏期診斷丘腦梗死后抑郁曲線下面積為0.961(95%CI:0.910~1.000),臨界值為392.5 ms,靈敏度為100.00%,特異度為83.33%。見圖4~5。

圖4 P300潛伏期診斷丘腦梗死后認知障礙的ROC曲線

圖5 P300潛伏期診斷丘腦梗死后抑郁的ROC曲線
3 討論
本研究發現急性丘腦梗死后認知障礙的發生率為70.00%,首先考慮丘腦位置關鍵,對認知的影響是復雜且多維度的,丘腦損害后出現認知障礙的高發與其關鍵解剖位置密切相關,丘腦與額葉皮層通過復雜的神經環路聯系,并對額葉皮層的信號有維持及放大作用[7],而該環路與認知、情緒及意識水平相關,因此環路中的結構損害勢必會出現認知障礙如語言障礙、記憶力減退、執行功能下降及學習障礙[8-9]。其次本研究樣本量相對偏少,可能存在一定的統計學偏倚。此外本研究證實,急性丘腦梗死后出現的認知障礙并非單一領域,而是廣泛的、多領域的異常,尤其表現在執行及延遲回憶方面,這與既往研究[10-11]基本一致。另外本研究僅通過MoCA量表發現在語言流暢性方面丘腦梗死患者表現較差,提示丘腦對語言的影響不易被察覺。丘腦對語言的影響主要區域為在腹前核及其投射纖維,該部位對Broca區及Wernicke區有調節作用,丘腦投射功能不足可出現找詞困難、命名障礙及理解障礙,本研究中丘腦梗死患者語言障礙不典型,考慮與未能區分優勢半球與非優勢半球病變相關,后期可增加樣本量進一步分析。
本研究發現丘腦梗死不僅會導致全領域的認知障礙,而且卒中后抑郁的風險也大大增加,部分患者自我表述存在情緒低落、恐懼后遺癥及睡眠障礙。丘腦卒中后引發的感覺異常甚至丘腦痛及認知障礙導致患者生活質量下降,從而使患者更易出現情緒障礙。同時丘腦也參與睡眠調節環路,丘腦梗死后出現的睡眠障礙,如日間嗜睡、入睡困難及早醒,也一定程度上會導致抑郁。本研究提示丘腦梗死后可能有抑郁約30%,這與既往研究[12]結果相似。不容忽視的是,卒中后抑郁會影響卒中后認知障礙及肢體功能的恢復,增加致殘率及死亡率[13],因此需要早期識別及干預。
事件相關電位P300是中樞神經系統在接收外界信息時產生的生物電活動,而P300的潛伏期反映了大腦對外部目標刺激處理速度,是反映認知功能效率的1個指標。Howe等[14]認為P300潛伏期可篩查出處于前驅階段的癡呆,有學者[15-16]認為P300是可識別認知功能變化的指標。本研究發現丘腦梗死后認知障礙越重、抑郁量表評分越高則P300潛伏期越長,這與孫函林等[17]研究一致。且本研究發現P300潛伏期對丘腦梗死后認知障礙及抑郁均具有較佳的診斷效能,故P300檢查具有很大的臨床使用價值。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丘腦梗死患者更易出現認知障礙及抑郁傾向,P300潛伏期可作為評估丘腦梗死患者認知功能及抑郁狀態客觀指標。據此,筆者認為對于關鍵部位腦梗死患者進行P300檢查及神經心理學量表評估,將有助于早期識別患者卒中后認知障礙及抑郁狀態。本研究仍有一些不足之處,首先樣本量偏少,其次,本研究設計的對照人群為同期非腦血管病者,并未將同期非關鍵部位急性腦梗死患者納入研究,分析關鍵部位腦梗死患者與非關鍵部位腦梗死患者在認知、情緒及事件相關電位P300方面的差異,后續擬增加研究寬度進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