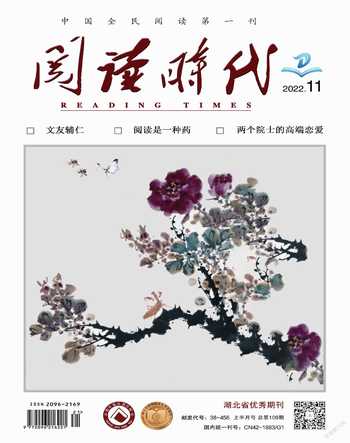為核酸檢測立下汗馬功勞的細菌
Yab
1964年,38歲的托馬斯·布洛克開車途經美國黃石國家公園時,決定下來參觀一番。作為地標性景點的彩色溫泉,當然是他必看的景觀之一。
對其他人來說,可能拍兩張照片,和家人、朋友分享一下,參觀黃石國家公園這件事就結束了。可巧就巧在,布洛克當時是印第安納大學的一位細菌學教授,作為內行人,他一眼就看出了門道:溫泉中的色彩多半是由帶色素的微生物造成的。但究竟是什么樣的微生物有這種“魔力”?它們又是怎么在約70℃的水中生存的呢?
沒有人知道答案。于是第二年夏天,布洛克帶著這些問題再次回到這里。這一次,他申請了項目資金,還帶著一個本科生哈德森·弗里茲。
“探究黃石國家公園溫泉中的生物”這種暑期項目,現在聽起來像一個簡單的假期活動。而當時,托馬斯·布洛克和他的學生絕不會想到,他們真的發現了一種新細菌,這種細菌在20世紀80年代末就已經開啟了現代分子生物學的新篇章,并且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的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PCR(聚合酶鏈式反應)核酸檢測,也少不了它的身影。
耐高溫的細菌
在黃石國家公園水溫70℃的“蘑菇泉”泉水中,托馬斯·布洛克和哈德森·弗里茲分離出一種粉橙色的細菌,并把它命名為“水生嗜熱菌”。這種細菌生活在水里,故為“水生”;能在高溫中生存,因此稱作“嗜熱”。
接下來的10年,他們師生二人主要的研究都集中在“為什么”:在當時“細菌能夠承受的最高溫度是55℃左右”的普遍認知下,為什么水生嗜熱菌如此特別?生物都有它自身最適宜生存的溫度范圍,而一般決定這個范圍的是該生物體內的酶。作為蛋白質,超過一定的溫度,酶就會失活,因而,布洛克和弗里茲假設,水生嗜熱菌帶有的酶都有高于其他生物酶的溫度范圍,所以它才能耐住高溫。
事實也是這樣。1970年,布洛克和弗里茲在《細菌學雜志》上發表了他們對水生嗜熱菌的醛縮酶的研究成果——這種酶竟然在水溫95℃時活性最高,也就意味著它平常生活的70℃的溫泉,對它來說,并不算太好的生活場所。
他們的發現逐漸引起了科學界的興趣。隨后,DNA連接酶、轉錄酶等生物體內比較重要的酶也從水生嗜熱菌里被提取出來。在其他酶都會支離破碎的高溫條件下,這些耐高溫的酶大放異彩,首次為科學家展示了很多反應的其他可能性。
開啟PCR時代
1976年,中國臺灣科學家錢嘉韻教授的團隊分離出一種DNA聚合酶,它最適宜的生存環境的溫度是70℃以上,在95℃時仍然不失去活性。他們將水生嗜熱菌的拉丁文學名簡化后,將其命名為“TaqD? NA聚合酶”。
然而,研究人員在短暫的興奮之后,感到的卻是無盡的空虛。在解答了“為什么”之后,那個年代的科技水平限制了他們提出下一個問題:“我們能用它嗎?”接下來,是十多年的沉寂,直到1988年,真正屬于水生嗜熱菌的機會才終于到來。
這一切離不開一個叫作凱利·穆利斯的人。今天他為人熟知的身份,是PCR項目的開發者。
當時,穆利斯是生物醫藥巨頭賽圖斯公司的一名研發人員,懂得商機的他知道,這種復制擴增生物核酸的技術需要做到規模化、自動化、快捷化,才能體現出真正的價值。而這條道路上的阻礙,恰巧就在于PCR的核心——聚合酶的選用上。
讓我們先復習一些基礎的知識:PCR的原理是用高溫將初始樣本DNA的雙鏈分開,再用聚合酶引導DNA復制,形成新鏈;重復幾十輪后,原來微末的DNA被成億萬計地擴增,從而可以被可視化地分析。比如在新冠病毒的核酸檢測中,專業人員是怎樣判斷樣本呈陰性還是陽性呢?就是通過PCR,擴增可能在鼻咽拭子中存在的病毒核酸,當病毒核酸達到一定數值,即判定為陽性。
初期的PCR使用大腸桿菌的DNA聚合酶,這種酶雖然已經是人類的老朋友了,但無奈它在最開始的高溫解鏈的環節就會失活,導致加入的大腸桿菌聚合酶只能用一輪,而后面的幾十輪中的每一輪都需要手動加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還只能使用這種酶的話,核酸檢測耗費的人力、財力和時間恐怕都會成倍增長。
穆利斯曾經說:“我開發PCR,并不是我真的創造了什么新的東西,而是只有我把那些已經存在的東西正確地組合運用起來了。”正是他在賽圖斯公司的團隊重新“挖掘”了已知的、非常耐熱的Taq聚合酶的研究,也有如神助,這種酶的耐熱性、反應活性和準確性等性質,完全符合他們當時對PCR聚合酶的所有期待——它簡直就像為PCR而生的。
在Taq聚合酶商業化后的第二年,它就登上了《科學》雜志。它的應用,再加上之后發明的可以自動變換溫度的熱循環儀,標志著PCR技術的成熟。這種技術今天幾乎成了生物醫藥領域研究和研發的必備工具,而穆利斯也在1993年憑此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
嗜熱菌的未來
回到水生嗜熱菌本身:在各大搜索引擎、書籍文章中搜尋它的身影,你會發現PCR相關的故事占據了絕大多數的篇幅。這樣的“光環”反倒遮蓋了這種細菌其他可能的閃光點。
除了耐熱的酶之外,水生嗜熱菌的代謝方式與周圍細菌的交互等等,是否也有利于它在這樣極端嚴苛環境下的存活?目前已知的包括水生嗜熱菌只有兩種嗜熱菌會形成的“圓小體”,是一種通過肽聚糖細胞壁將周邊細菌連接起來的球狀構造,它是否像科學家假設的那樣能夠起到保護和耐熱的作用,還可以幫助嗜熱菌在貧瘠的熱泉中儲存營養?和親緣關系較近的非嗜熱菌相比,又有怎樣的進化故事讓它們適應了現在的生活方式?
這一切都還是未知。
解答這些看起來足夠基礎、冷門的問題,只是滿足生物學家的求知欲,還是將來也能造就Taq聚合酶那樣的奇跡呢?今天的我們尚且不知,而基礎研究的魅力正在于此。
(源自“物種日歷”)責編: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