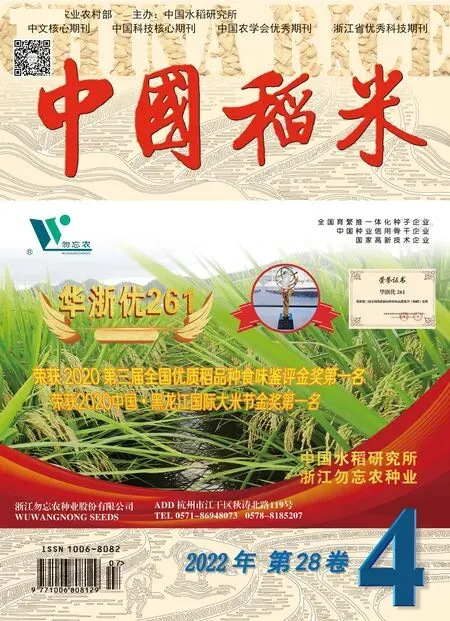稻文化和浙江稻作文化漫談
楊雨菲
(紹興文理學院,浙江 紹興 312000;作者:yufei010710@163.com)
浙江自古以來山靈水秀、人文蔚興,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數千年以來,浙江人民創造了千姿百態、光輝燦爛的文化成果,為豐富和繁榮中華文化做出了重要貢獻,絲綢文化、茶文化、詩路文化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良渚文化時期就已出現蠶桑紡織業,并發現了世界最古老的絲織品;唐宋時浙江茶文化頻繁傳至國外,南宋時期成為世界茶文化中心;浙江詩路文化帶文化底蘊豐厚,李白、孟浩然、陸游等歷代文人在浙江游歷論學,留下了《夢游天姥吟留別》《舟中曉望天臺》等大量詩詞名篇[1-2]。浙江還擁有上萬年稻作文化歷史,留下了許多光輝燦爛的稻作文化遺存習俗,如上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青田稻魚共生、杭州南宋八卦田等遺跡遺存、農耕景觀[3]。稻作文化一般是指水稻耕作民族在長期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中創造和約定俗成的民俗文化,包括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4]。這些文化是各族人民血汗的結晶,是人類寶貴的文化遺產,至今深刻影響著全球半數人的生活。
1 關于稻文化的古今記憶
從世界農耕發展史看,大約在1 萬年前,在生存環境變化等因素促進下,新石器時代的古人類即開始對野生動植物進行馴化,使得人類祖先的生活方式發生了由狩獵采集向農耕養殖的轉變,也是人類文明起源的里程碑事件。據統計,約有250個物種進行了完全馴化,其中水稻、小麥和玉米等成為世界主糧作物,為全人類提供了50%以上的能量。現在,世界水稻90%以上種植在亞洲國家,稻米一直是亞洲人餐桌上的主食,卻少有人清楚其從田間到餐桌的全過程。
太湖平原地勢平坦、土壤肥沃、水網密布,適合發展種植業和漁業,構成了江浙地區經濟發展的自然優勢。東晉在建康(今南京)建立政權后,北方士族大量南遷進一步繁榮了江浙一帶的經濟文化水平。“魚米之鄉”一詞,顧名思義,就是指盛產魚和米的地方,當然這只是狹義之說,廣義上應指富饒之地。其文最早出自唐代王脧的《清移突厥降人于南中安置疏》:“諂以繒帛之利,示以麋鹿之饒,說其魚米之鄉,陳其畜牧之地”。隋煬帝下令修建京杭大運河,除貫通南北加強統治外,將江南富余的糧食布帛等北運也是其主要目的之一。
既是“魚米之鄉”,自然與稻田脫不了干系,在我國源遠流長的農耕文明時代里,稻田便是隨處可見的人類生活記憶。《詩經》中早有記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是為西周時期河水灌溉公侯稻田的生動寫照。唐宋時期中國的經濟中心開始不斷往南遷移,水稻逐步取代小麥成為最主要的糧食作物[5]。宋朝王應麟所作《三字經》已將“稻”置于首位:“稻粱菽,麥黍稷。此六谷,人所食。”宋朝詩人蘇軾、陸游曾在詩詞里如此描述過“插秧”,那正是“分秧及初夏,漸喜風葉舉”“陂塘處處分秧遍,村落家家煮繭忙”;董嗣杲、連文鳳、戴復古也如此描述過“稻花”,說它們“四海張頤望歲豐,此花不與萬花同”“紛紛兒女花,為人作顏色”“雨過山村六月涼,田田流水稻花香”。而于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宋朝辛棄疾的《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辛棄疾本是宋代名將,一生金戈鐵馬,既寫下了豪邁熱血的《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也寫下了豪壯悲涼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然而他在貶官閑居江西上饒時,也能寫下一首吟詠田園風光的《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足見只有鄉村的清風明月、稻香蟬鳴才能帶給詩人這樣的愉悅之境,才能寫下如此清新安逸的田園詞作。
我的家鄉在紹興諸暨,屬于浙東南和浙西北丘陵的交接地帶,四周群山環抱,境內丘陵山地居多,但在那山水之間,總還是錯落分布著一塊塊整齊而金黃色的稻田,襯映著山水,美不勝收。那還是在我特別小的時候,大約剛開始記事吧,夏日的傍晚總喜歡跟在外公后面,搬一張小板凳靜靜地坐在稻田邊上,聽風吟、聽蛙鳴。外公總會指著夏日里剛栽下去不久的小禾苗對我說,農民伯伯們插秧之后,五至七日,這些秧苗便可返青,之后便經過分蘗、拔節、揚花、灌漿、結實等一系列生長,直到立秋時節谷子成熟,向著大地彎下腰身,便是一年中最為喜悅、忙碌的秋收景象。隨著慢慢長大,這樣美好的場景卻越來越少,鋼筋水泥混合的城市越來越大,稻田卻離我們越來越遠。外出求學后,更是遠離了老家,只在暑期返鄉偶爾經過時,還會遠遠地望一下那些孤單、落寂的稻田,卻很難再有童年時的心境了。聽外公說起,每到秋收時候,村子里就是一臺臺轟鳴的收割機在作業,只是它們似乎不再對稻子懷有敬意,純粹在展示沒有靈魂之美的喧騰。誠然,從刀耕火種到鐵犁牛耕,再到全程機械化,這無疑是時代在不斷進步,但似乎總有些東西在漸行漸遠。
2 浙江稻作文化漫談
“十月獲稻,為此春酒”“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這些我們從孩童時期就耳熟能詳的古詩,在一代又一代的流傳中已經蘊藏了豐富的稻作文化密碼,只待我們層層揭開。
一直只知道浙江是“魚米之鄉”“絲綢之府”,殊不知浙江還是世界栽培水稻的馴化起源地。直到大二暑假,我先后去了杭州良渚古城遺址、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和浦江上山考古遺址公園,方才對源于我國長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有了更深入了解。北京大學的嚴文明先生曾經有一個很有趣的比喻,他說浙江的遺址名很有內涵,從美麗的小洲(良渚)出發,過一個渡口(河姆渡),跨一座橋(跨湖橋),最后上了山(上山)。這是一條通向遠古的詩意之路,也是中華文明的探源之路。
良渚文化距今5 300~4 300 年,良渚文化的中心為良渚遺址。“渚”,意為水中間的小塊陸地;“良渚”,其字面含義即為美麗的小洲。相傳古時這里多“渚”,后墾為良田。良渚坐落于杭州市區西北部,屬于典型的江南水鄉,此說自有淵源。從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浙江博物館前身)的施昕更1936 年首次發現良渚遺址,到2007年發現良渚古城,再到2015 年確認了設計合理、規模浩大的良渚遺址群水利系統,最后到2019 年良渚古城遺址正式成為中國第55 處世界遺產,實證了5 000 年前的古老中國與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以及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在同時期進入了國家文明社會階段。在良渚古城遺址,考古學家們先后發現了水稻從耕種到收獲使用的成套的石制工具、大范圍的稻田耕作區、配套的灌溉水渠和超過10 萬kg 的炭化稻谷,直觀展示了良渚時期逐步成熟的稻作農業,為良渚文明的早期國家形態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6-7]。
從良渚到河姆渡,再到跨湖橋,長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歷史再次向前推進了2 000~3 000 年。1973 年,河姆渡遺址被發現發掘,造型別致的象牙雕刻藝術品、精美的漆木器和連片的桿欄式木構建筑遺跡等令人耳目一新。當然最為重要的是,在河姆渡遺址第4 文化層較大范圍內,普遍發現有稻谷、谷殼、稻稈、稻葉等遺留痕跡,出土了大量的炭化稻米;農史學家游修齡先生鑒定后認為河姆渡出土的水稻遺存屬于栽培稻,同時伴隨出土的大量農具——骨耜,表明河姆渡先民的稻作農業已經進入“耜耕農業”階段[8-9]。跨湖橋遺址的發現則將浙江的人類文明史提到了8 000 年前,同時也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骨器、木器、石器,以及人工栽培水稻等文物,還發現了距今約8 000 年、人類歷史最早的獨木舟。
這條漫長的中華文明之路、稻米之路,部分始于金華市浦江縣一個被當地人稱為“上山”的小土坡。2000年,一個完全陌生的文化遺存逐漸被考古學家們揭開了神秘的面紗,大口盆、夾炭陶片、圓石球、石磨盤等古老的事物被逐一發現,迥然不同于已知的新石器時代器物,后被命名為“上山文化”,距今約11 000~8 500年。在上山文化考古工作中,陸續發現了10 000 年前屬性明確的栽培水稻、迄今最早的定居村落遺跡和大量彩陶遺存。當然,其中最耀眼的自然是那一粒跨越萬年之久才得以與世人相見的炭化稻米,上山遺址發現了包括水稻收割、加工和食用的較為完整的證據鏈,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農業遺存。10 000 多年前,上山先民從洞穴走向曠野,邁出了人類走向文明的一大步[10-11]。
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盡管上述幾種文化在發現的住所、石器、陶器及其他代表性器具方面所呈現的面貌各具特色,但僅從稻作農業發展的不同階段看,上山、跨湖橋、河姆渡和良渚等四種文化實際上分別代表了我國稻作農業發展的起源、發展、演進和成型等不同時期;水稻栽培歷史演變就像一根繩索一樣,緊緊地將不同文化牽在一起,稻作農業的不斷發展最終也推動我國農業社會由上山文化“最早的村落”走向良渚文化“最早的國家”,完成了中華文明的初步演進。
3 尾聲
原來一片稻田的時光是沒有盡頭的,只是翻來覆去的稻谷青了又黃,黃了又青。我們所閱的每一株稻穗的風姿,所食的每一碗米飯的能量,都是一部綿延萬年的史詩。如今,我們的世界正變得越來越多姿多彩,城市里閃爍的霓虹燈照耀著川流不息的車水馬龍,白天和夜晚,喧囂和寧靜,常常讓人忘卻了曾經我們一路走來,那些最樸素、最尋常的美好。原來那些漸行漸遠的,正是漸漸丟失的農耕記憶和稻作文化。這也許便是發展的代價吧,如今我們要做的不正是尋找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之間的平衡么。當然,我們也欣喜地看到,文化正在回歸,城里的人們正重拾對稻田的敬意,試著放慢自己的腳步,在周末去赴一場稻田的盛大約會,只因那時,稻花開過,稻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