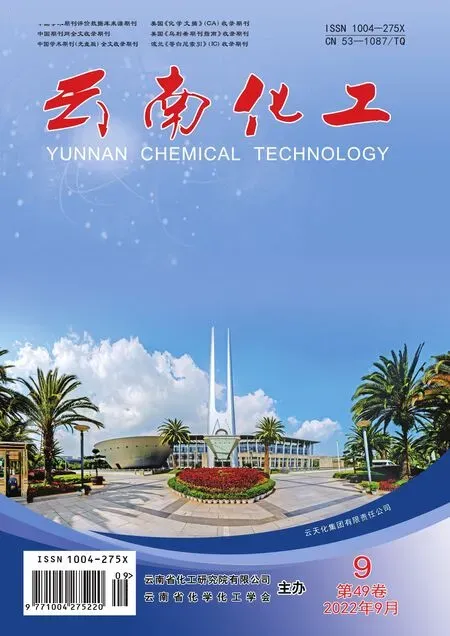課程思政在《藥用植物學》教學改革中的發掘與探索*
段黎娟,李 雅,王 麗
(黃河科技學院,河南 鄭州 450063)
《藥用植物學》是藥學專業的一門主干專業基礎課,包括藥用植物的形態學、解剖學、分類學、種質資源、化學成分、藥用價值和臨床應用等基本理論知識和操作技能。它是一門理論性、實踐性、直觀性強的學科門類,其理論教學內容龐雜,枯燥難懂,容易混淆[1],也是《藥用植物學實驗》《生藥野外采集》的先行基礎,是《生藥學》《天然藥物化學》最直接、最重要的專業基礎課程。在教育教學過程中實施 “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教學模式,以專業知識、技能教學為基礎,以專業知識、實操訓練相融合為支撐,以知識—能力—綜合素養的全面提升為目標,以藥學專業的人才培養方案為指導,以高等院校專業課的課程教學標準為依據,進行課程思政頂層設計,整體把握課程體系,挖掘、提煉思政元素[2]。該門課程在教學上為《中藥鑒定學》《生藥學》等課程奠定基礎,在生產上有助于保證中藥材采收階段品種的準確性,從源頭上保證中藥質量[3]。
課堂講授植物的細胞、組織、器官和植物分類學基本理論知識的同時,融入當下普遍關心的社會熱點問題(如新冠疫情下中藥方劑的臨床使用以及青蒿素與諾貝爾獎)和科研中常遇到的疑難問題,培養學生對所學知識的綜合運用能力;通過了解藥用植物學的研究前沿和研究熱點,把握學科的發展動態,拓展學生視野。從多側面挖掘探討專業基礎課程的思政要素,挖掘思政元素是“課程思政”教學改革的基礎和重點項目,緊密結合藥學專業特色,將思政教育與藥用植物學專業知識交互融合,最終實現立德樹人的教學目標。
1 課程思政的教學目標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刻領會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確立價值塑造。
1.1 專業知識與技能目標
課程主要以藥用植物為研究對象和研究重點,應了解藥用植物學的發展、主要內容、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以及以后的發展方向。能正確理解、掌握藥用植物的形態結構特征,以此能進行準確的植物分類。掌握重點科的特征及重點藥用植物的來源、形態特征等。熟悉植物的生長環境和分布特征。
1.2 能力目標
通過本課程的學習,學生在獨立學習能力和深度思考能力,對相關研究方向資料的搜集、整理和綜合分析的能力,解決現實問題的研究能力等方面有所提高。
1.3 素質目標
小植物,大道理,每一株簡單的植物都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
1)藥用植物作為中醫藥文化的一部分,通過課程系統的學習,理解中醫藥理念的“天人合一,陰陽平衡”,展現中華傳統文化“道法自然”和“和合致中”的哲學智慧。通過自然界植物與人類的和諧關系,理解除現代西方科學的思維方式之外還有中醫文化的思維方式,增強學生適應社會的能力。
2)通過對社會熱點問題探究,讓學生運用所學知識對典型案例具有科學的判斷,增強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從中領略科學研究的真諦,養成不斷探索、求真務實、批判思維的習慣。培養學生具有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科學素養和科學思維能力。《藥用植物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植物的種植、加工等都需要實踐操作,通過課程學習,培養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品德。同時,在野外實踐過程中可培養師—生互助,生—生互助,學會傾聽,懂得包容,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和集體榮譽感。
1.4 思政育人目標
以中醫藥文化為基本,緊密結合思政要素,創建集理想信念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專業認同感教育、職業素養教育以及生態保護教育為主的《藥用植物學》課程思政教學體系。
2 課程研讀要求
中醫藥歷經千年,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記錄著我國發明和發展醫藥學的智慧創造和卓越貢獻。《藥用植物學》是全國高等院校中醫藥各專業的基礎、核心課程之一,對學生后續的課程學習和研究工作具有重要作用。通過貫穿《藥用植物學》課程與德育主線的有機結合,培養學生中醫藥思維與科研創新思維,增強學生對傳統中醫藥文化的認同,樹立文化自信。
《藥用植物學》內容冗雜,從植物細胞到植物個體或全株形態特征,內容環環相扣,層層遞進。因此,教學過程應突出專業特色,按照價值引導、能力達成、知識授受的目標,理論與實踐達到功能互補,應掌握藥用植物從微觀到宏觀的結構特征、植物分類方法及各類、各科植物的特征及其重要藥用植物,能正確鑒別其種類。
通過教學中融入德育元素,增強學生對專業知識的理解,促進中藥認知體系的形成和思維方式的培養,實現教書育人的目標,培養德才兼備、傳承創新的藥學專業人才。
3 課程思政教學案例
菌物藥資源開發應成為國家戰略,加快開發。例如:新冠肺炎中藥治療方劑“清肺排毒湯”中的茯苓、豬苓;“知了頭上長蘑菇”的蟬花,漢代就已記載;譽為“仙草”的靈芝及其提取物靈芝多糖、靈芝三萜等;“森林黃金”抗癌藥桑黃等,都是菌物藥中的佼佼者。
我國植物資源種類繁多,且很多藥用植物已實現人工栽培,需要精心培育幾年乃至數十年之久,達到規定采收年限后,才能采收入藥,如人參(園參約5~8年,林下參約10年以上)、肉桂(約5~40年)等。其次由于加工炮制的技術差異,如附子、半夏等新鮮藥材通過多道加工流程,從而達到降低藥材毒副作用、增強藥效的目的。另外,個別藥材需要貯存到一定年限才能體現其價值,譬如陳艾、陳皮等。通過嚴格遵守中藥材種植、加工、生產儲存等原則保證中藥材品質的技術向學生展示日積月累、持之以恒的“工匠精神”[3]。
學習中國蕨類植物學奠基人秦仁昌對植物分類潛心研究;被國際藥用植物界稱為“藥界大熊貓”的鐵皮石斛;活血化瘀的“紅色黃金”藏紅花等,體現了我國藥用植物資源豐富,截止2019年底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全國中藥資源普查工作中發現約百個新物種,近六成或有潛在藥用價值。
普及傳統中藥文化,例如新冠疫情期間治療新冠肺炎的藥用植物金銀花、黃芩、黃連等;傳統中藥蒲公英;以及抗瘧藥青蒿素的原植物黃花蒿的特征和功效等。被稱為“黃連之圣”的徐錦堂堅持不懈的研究,改變傳統的毀林栽培黃連的技術,既保護當地的生態環境,又提高黃連栽培的經濟效益。種種事例契合了藥用植物栽培技術的榜樣,引導學生討論和思考。教學過程中對傳統的毀壞松林栽培茯苓的案例進行深入淺出的分析;又對木犀科中藥女貞子多種加工方法針對不同需求進行市場行情的調研,并積極申報省級大學生創新創業項目。
4 課程思政的教學成效
4.1 愛國主義教育
緊密結合全國第四次中藥資源普查情況以及我國豐富的天然植物資源,如利用植物類群之間的親緣關系發現降血壓植物資源蘿芙木及同屬多種植物的國內代用藥,節省大筆外匯資金,使學生對國家產生強烈的自豪感。介紹近代在我國肆意采挖植物標本、掠奪我國植物資源的外國“植物獵人”,激起學生強烈的愛國熱情。
如藥用植物各論部分講解的銀杏科-銀杏(ginkgo biloba L.),屬落葉大喬木,又稱公孫樹、白果樹,特產我國,是現存種子植物中最古老的孑遺植物,有“活化石”之稱,目前僅浙江天目山、重慶金佛山、廣東南雄等少數地方有野生狀態的樹木[4]。遍布全球的銀杏樹種幾乎都來源以浙江天目山為代表的中國東部種群。銀杏延綿至今,造福于人類,可用于藥用、食用、材用三種方式。
4.2 專業認同感教育
通過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國醫學科學院屠呦呦從東晉時期葛洪所著的《肘后備急方》中受到啟發,改進提取方法,從而獲得青蒿素的知識講解,又經歷創新研究在青蒿素基礎上發現了雙氫青蒿素,讓學生對于藥學專業有新認識,愿意學習并鉆研創新,從而產生強烈的專業認同感。
4.3 職業素養教育
復旦大學的鐘揚教授援藏十六年,堅持考察青藏高原的植被狀況,潛心研究并收集種質資源,在西藏大學教學工作之余奔赴野外收集4000萬顆植物種子,填補了世界種質資源庫沒有西藏種子的空白,被譽為“將畢生獻給高原的植物學家”[5];又將西藏大學的生態學學科建設成一流學科的事跡對學生進行核心價值觀教育,讓學生形成初步的職業素養,為今后的醫藥相關行業打下堅定的工作基礎。
神農氏嘗百草,發明了醫術,是醫藥之祖。《史記·補三皇本紀》中載:“神農氏作蠟祭,以赭鞭鞭草木,嘗百草,始有醫藥。”《淮南子·修務訓》載到:“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6]。神農嘗百草的神話流傳久遠,至今不衰。神農氏大公無私,以天下蒼生為己任,勇于嘗試,大膽創新,發明了醫藥業與耕種業,為子孫后代傳承優秀的人文精神。
4.4 生態保護教育
2005年8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在湖州安吉考察時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深刻揭示了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
學習冬蟲夏草、人參、雪蓮等藥用植物時可以結合過度采挖利用的后果,對學生進行生態保護的教育;在生藥野外采集實習時,教育引導學生采集植物標本適度、適量,杜絕濫采濫挖,破壞植物資源以及生態環境。
5 結語
植物資源是藥品原料的一個巨大寶庫,我國藥用植物資源的開發利用淵遠流長,從神農嘗百草的傳說至今,中醫藥在我國的醫藥衛生體系中發揮著巨大作用,其根本是中草藥資源。現今,中草藥資源仍然和西藥并存,為人民的衛生健康作出貢獻,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生機。在當前新型冠狀病毒肆虐的情況下,各國都在努力尋找有效防治新冠特效藥,我國在防疫以及治療新冠肺炎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中醫藥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連花清瘟膠囊、清肺排毒湯等。在此背景下,本課程不僅能幫助學生學好藥用植物學相關知識,還能回歸對傳統中醫藥文化的認識;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整個教學過程,激發學生對中醫藥文化的熱愛之情,積極配合為高等院校的課程體系教學改革營造良好的教學環境,增強愛國主義情懷,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