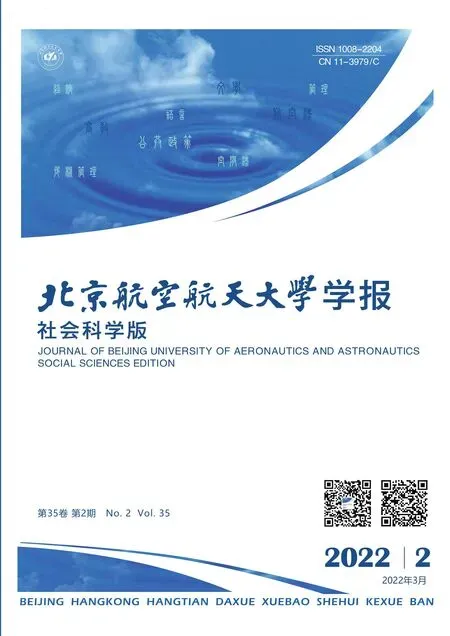加強國際執法司法合作,打擊嚴重跨國網絡犯罪
張曉鳴
(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 國際合作局, 北京 100006)
司法部作為一線的司法實踐部門,其國際合作局代表司法部與中央和地方的調查機關、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和刑罰執行機關共同合作,履行中國政府開展國際執法和司法合作的職責。司法部國際合作局代表司法部,也就是代表中國政府,與世界上凡是與中國締結有刑事司法協助類國際條約的合作伙伴國加強合作,共同打擊各類犯罪,包括嚴重的網絡犯罪。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與國際社會進行了高度的交流與融合。與此同時,嚴重的跨國網絡犯罪不斷侵害世界各國,中國也難以獨善其身。從筆者自身的工作實踐來觀察,中國有時也會成為包括網絡犯罪在內的嚴重跨國犯罪的發源地、過境地和目的地。此三地疊加對打擊和預防包括網絡犯罪在內的嚴重的跨國犯罪提出了空前高的要求。可以說,當前嚴重的網絡犯罪,多是跨國跨境的,因而,國際合作的議題也被前所未有地提上了議事日程。開展國際執法司法合作,必須按照習近平法治思想和外交思想來推進國際合作;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國際合作,這是根本遵循;國際條約和國內法律是開展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國際法基礎和國內法基礎,兩個基礎應當配套實施,一體推進。
第一,當前嚴重的跨國網絡犯罪中主犯的追逃,多離不開國際條約和國際法的一體適用。進行過刑事調查起訴審判的人士應該知道:嚴重的跨國刑事犯罪調查,最重要的就是要被告人到庭,當然,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對被告人不到庭情況也有特別的程序。通常情況下,刑事被告人的到庭是主權國家行使司法管轄權的基礎,要追逃就離不開國際合作,也離不開國際條約和國內法的一體適用。例如,一起嚴重的跨國網絡犯罪,主犯在肯尼亞,從犯在西班牙,被害人是中國境內的退休人員,這時,既要適用中國引渡法和刑事司法協助法,又要適用中國與肯尼亞的引渡條約以及中國與西班牙的引渡條約,同時向肯尼亞和西班牙兩國執法司法提出請求,并跟進請求,以己適彼、依約依法,從而實現引渡。這是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國際追逃的必經程序。
筆者呼吁,中國的調查、偵查、公訴、審判和刑罰執行機關,要通過自身的辦案實踐,逐漸樹立起國際條約和國內法一體配套適用的意識和能力。當然,不可否認,實踐中通過勸返使逃離本國國境的犯罪人員回來接受調查起訴是一項重要的手段,但是國際標準的司法合作,用法治思維來看,必須經過引渡或者遣返等國際標準合作程序來進行。
第二,當前嚴重的跨國網絡犯罪的追贓,多離不開國際條約和國內法的一體適用。除間諜犯罪外的刑事犯罪,通常以獲取利益為目的,要進行跨境、跨國追討涉案乃至犯罪的贓款贓物,離不開國際條約和國內法的一體適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以及中國與有關國家締結的大量刑事司法協助類的條約和公約,中國的調查機關、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和刑罰執行機關有權向有關國家提出司法協助的請求,請他們查封、扣押、凍結乃至最后返還或分享與跨國犯罪甚至與跨國網絡犯罪相關的贓款贓物。
第三,當前嚴重的跨國網絡犯罪的追證,多離不開國際條約和國內法的一體適用。開展刑事追訴的程序離不開證據,對于嚴重的跨國犯罪,特別是跨國網絡犯罪,更離不開境外乃至國外的主管機關或者證人提交證據,以便可以對該起嚴重的跨國犯罪或跨國網絡犯罪進行調查起訴和審判。那么,追索位于國外和境外的證據材料也離不開所締結的國際條約和國內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引渡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有關國家締結的引渡條約,在提出引渡請求的同時,有權向有關國家的主管機關提出刑事司法協助請求,包括但不限于將出庭文書向逃犯送達、查找逃犯下落、查找涉案資產下落、安排證人來華出庭作證以及對犯罪資產承認并執行中國生效的刑事判決等,并將這些證據移交中國的執法司法機關,用于在中國境內的調查、偵查、起訴、審判和刑罰執行。當然,包括證人證言、犯罪工具,乃至司法鑒定的結論,都有權向他們提出請求。
綜上所述,追逃離不開國際條約和國內法的一體 適用,追贓也一樣,追索證據材料更是如此。在此,筆者呼吁司法實證部門的同仁們,能與身處調查、起訴、審判一線的專家和法學院校的師生們一起, 積極參與研究與網絡犯罪相關的刑事執法和司法實際問題,分析成因,為國家開展法治建設和國際合作、打擊嚴重的網絡犯罪提出具有實際價值的政策性建議。
最后,提出以下問題,以供大家共同思考和研究:
第一,如何提高中國執法司法機關一體適用國際條約和國內法的意識和能力問題。當下,國際條約也有,國內法也有,有約可依,有法可依,但是為何實踐中各個階段的執法司法機關運用國際條約的意識和能力,特別是效率還是偏低?筆者認為,其中一 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對外締結批準加入的國際條約還未被列入中國法律體系之內,即國際條約在國內法中的位階問題尚未解決。
第二,截至目前,在中國和俄羅斯等“金磚國家”的推動下,聯合國網絡犯罪公約正在專家層面進行,還未能進入全程的締約談判進程,但這已是一個 非常好的開端。那么,在這個公約出臺尚需時日(通常從締約談判到批約履約得數年之久),且目前又未能與有關國家專門就網絡犯罪締結雙邊條約的情況下,對西方國家制定的《布達佩斯打擊網絡犯罪公約》的實證性研究又應該做什么?做到哪一步? 如何把握這兩個進程之間的平衡,使之為我所用,解決中國有關國際網絡犯罪中的追逃追贓追證,也是一個大問題。
第三,提出另外一個問題,即證據入境的問題。中國的執法司法機關對位于境外的證據需要“請進來”,在為自身的調查、偵查、起訴、審判和刑罰執行提供證據(包括證人證言和電子證據)支持的時候,應當做什么?怎么做?因為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之下,可以明顯地看到線下的跨國犯罪多是挪至了線上,可以預想,中國的執法司法機關對位于境外的證據(特別是網絡數據)的“入境”需求,將可能呈“井噴”之勢。如何把握證據“出境”和證據“入境”二者之間的平衡,也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