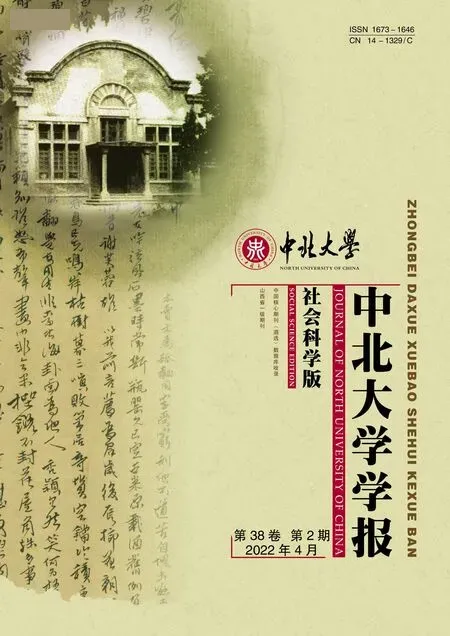從文學地理空間角度看陶淵明詩文中的田園路
方立娟
(廈門大學 中文系, 福建 廈門 361005)
陶淵明作品中存有大量與地理相關的意象, 這些意象大多不是單獨存在于文本中, 亦可形成值得探尋的文學地理空間, 比如田園、 山林等, 關于這點, 本人在《陶淵明詩文中的地理空間書寫》一文已有相關闡述。(1)拙文《陶淵明詩文中的地理空間書寫》于2021年發表在《地域文化研究》第2期。 《從文學地理空間角度看陶淵明詩文中的田園路》一文在2020年歷經數次投稿, 后在2020年12月30號投稿至《中北大學學報》, 特在另一篇文《陶淵明詩文中的地理空間書寫》發表后補上相關信息。陶淵明在論及田園生活時, 有時還會延伸到通往田園之路, 如“道狹草木長, 夕露沾我衣”[1]“揚楫越平湖, 泛隨清壑回”[1]等, 這些路既可看作田園的延伸, 也可分別看作獨立單元。 若以文學地理學的角度看, 這些路還可看成重要的文學地理空間。 關于文學地理空間的概念, 有不少學者述及, 如曾大興認為:“文學作品的地理空間是指存在于文本中的以地理物象、 地理意象、 地理景觀 (地景) 為基礎的空間形態, 如山地空間、 平原空間、 海洋空間、 草原空間、 鄉村空間、 都市空間等等, 這種空間從本質上講乃是一種藝術空間, 是作家藝術創造的產物, 但也不是憑空虛構, 而是與客觀存在的自然或人文地理空間有重要的關系。”[2]杜華平在中國文學地理學會第三屆年會的論文《論文學地理空間的拓展與深進》中指出:“文學地理空間的深進, 就是指寫出‘地方靈魂’, 其實質是作家與地理空間的深度契合。”[3]10田園路作為陶淵明作品中的一個地理空間, 融入了陶淵明的情感, 具有一定的探究價值。
1 陶淵明詩文中的田園路特點
陶淵明筆下的田園, 與其現實接觸的田園有著重要聯系。 《宋書》記載:“親老家貧, 起為州祭酒, 不堪吏職, 少日, 自解歸。 州召主簿, 不就。 躬耕自資, 遂抱羸疾, 復為鎮軍、 建威參軍……”[4]2511陶淵明與田園有著真正的密切接觸, 他筆下的田園, 也有著不一般的現實意義。 首先, 在歷史上, 陶淵明家本來就有田莊, 錢志熙認為:“淵明的田莊, 似乎不止園田居、 南村兩處, 還有西田、 下潠田兩處。”[5]85陶淵明的《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和《丙辰歲八月中于下潠田舍獲》分別指出了他在西田和下潠田的勞作與收獲。 其次, 陶淵明在自己一些作品中展示了不同時期田園的一些景象, 如在《歸園田居》中, 詩人以“種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1]展示了他初歸田園時的景象; 在《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中, 他以“果菜始復生, 驚鳥尚未還”(2)“果菜始復生”句“菜”字下, 宋本注:“一作藥。”[1]展示了遭遇火災后田園的一些狀況; 在《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中以“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 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3)“炎火屢焚如”句“如”字下,宋本注:“一作和。”[1]描繪他在氣候反常時遭遇的田園困境。 陶淵明筆下之田園具有現實意義, 是陶淵明歸田生活的部分記錄。
關于陶淵明筆下的田園, 目前, 學術界已有較多論述, 蔡瑜在《陶淵明的人境詩學》中對陶淵明筆下的“園田” “田園”進行了論述。 她說:“‘田園’指涉一片靜態的產業, 往往是大范圍的田地園圃, 有時甚至即是‘苑囿’ ‘園舍’ ‘田莊’。 田、 園本各有其意, 樹谷曰田, 樹果曰園, ‘園’的意義在‘田園’連詞中或是指大范圍具有經濟效益的果園而與田莊并列, 或是只作為一種休憩區域的意涵。 然而, 陶淵明采用‘園田’連詞時, 則園、 田兩者并重, 同時有從園到田、 由近而遠的推展, 形成很具體的生活化空間”[6]68。 陶淵明家的田園, 大概有遠有近, 其中不乏離家近的園圃, 如在《時運》中, 陶淵明言:“斯晨斯夕, 言息其廬。 花藥分列, 林竹翳如。”[1]“花藥分列”之花, 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注:“一作‘華’”[1],“華”亦有花之意, 此廬外即有類似于園圃的存在; 又如《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果菜始復生”之“菜”, 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注:“一作‘藥’”[1], 但不管陶淵明此處原文作“藥”還是“菜”, 都可以說明陶淵明家附近有一個園圃, 在戊申歲陶淵明某處宅子失火后, 附近的園圃也受到了影響。 當然, 也有一些田地和園圃離家遠, 有時勞動需要經過一段遠路, 陶淵明在作品中也記載了這一類通往田園的偏遠路途。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其一中言:“地為罕人遠”[1]; 《丙辰歲八月中于下潠田舍獲》云:“揚楫越平湖, 泛隨清壑回。 郁郁荒山里, 猿聲閑且哀。”(4)“郁郁荒山里”句“郁郁”后,宋本注:“一作皭皭。”[1]去田園勞作, 先要劃船渡湖, 再隨溪流進去, 所到田園乃處在一荒山中, 還能聽到猿聲。 這一類路途偏遠, 跟陶淵明去往田園勞作的現實生活也密切相關。
《歸去來兮辭》中有“農人告余以春及, 將有事于西疇。 或命巾車, 或棹孤舟。 既窈窕以尋壑, 亦崎嶇而經丘。 木欣欣以向榮, 泉涓涓而始流”(5)“農人告余以春及”句“及”字下, 宋本注:“一無及字,一作暮春,又作仲春。”“經丘”之“經”, 宋本注:“一作尋。”[1]等句, 此處所涉及去往田園之路, 大概出于作者根據以前生活經驗的想象。 錢鍾書在《管錐編》中曾引周振甫之言來闡明觀點:“周君振甫曰:‘《序》稱《辭》作于十一月, 尚在仲冬; 倘為‘追錄’ ‘直述’, 豈有‘木欣欣以向榮’ ‘善萬物之得時’等物色? 豈有‘農人告余以春及, 將有事于西疇’ ‘或植杖而耘耔’等人事?其為未歸前之想象, 不言而可喻矣。 ’本文自‘舟遙遙以輕飏’至‘亦崎嶇而經丘’一節, 敘啟程之初至抵家以后諸況, 心先歷歷想而如身正一一經。”[7]20雖說有想象成分, 但前往西疇之路也比較偏遠, 有時要駕車, 有時需劃船, 還需經過溝壑和山丘。 這樣的路途跟陶淵明去往偏遠田園耕種的現實路途是相似的。
有些通往田園之路不易行走。 偏遠之路, 行走起來容易有諸多不便。 在《歸去來兮辭》中, 陶淵明展示了歸去的放松與愉悅, 可在涉及通往田園之路時, 他并沒有避諱路途之偏遠難行, 還用了“崎嶇”等詞來形容。 在《歸園田居》其三中, 他說:“道狹草木長, 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無違。”(6)“衣沾不足惜”句“沾”字下,宋本注:“一作我衣。”“但使愿無違”句“無”字下,宋本注:“一作莫。”[1]道路狹窄, 草木茂盛, 露水還沾濕了詩人的衣服, 可他這時想到的卻是不違心愿。 這樣的路是一種田園實錄, 實際上也融入了作者的內心情感, 更加突出了詩人歸去心志之堅。
2 陶淵明詩文中田園路與行役路的情感意蘊
陶淵明的一些田莊確實處于偏遠之地, 不易行走, 在陶淵明一些詩文中也有反映。 但如果把通往田園之路與行役路途中呈現出的景象對比可以發現, 陶淵明對于二者有著明顯的情感區別。
陶淵明在行役詩中描繪行役之路時流露過厭倦的情緒。 錢志熙認為:“陶淵明的行旅詩, 多寫留戀山澤、 厭倦途旅之情, 實為古老的行役詩傳統, 與稍后興起的壯賞山川之美的紀游詩有所不同。”[5]237《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言:“眇眇孤舟逝, 綿綿歸思紆。 我行豈不遙, 登陟千里余。 目倦川涂異, 心念山澤居。 望云慚高鳥, 臨水愧游魚。”(7)“登陟千里余”句“陟”字下,宋本注:“一作降。”“目倦川涂異”句“異”字下, 宋本注:“一作修涂永。”[1]路雖遠, 舟可行, 然而, 詩人卻流露出一種歸念以及疲憊感。 筆者在《陶淵明詩文中的地理空間書寫》一文中也已闡明:“園田、 山澤居、 班生廬與‘眇眇孤舟逝’之現實景象相照應, 在虛實交替中, 詩人的仕隱矛盾也進一步凸顯, 然而在這首詩中, 現實地理空間反而涉及較少, 加之詩人自言‘綿綿歸思紆’, 可知在此詩中其歸隱之意要盛于出仕之意。”[8]
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中》(8)此詩題又作:“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一詩里, 詩人有“涼風起將夕, 夜景湛虛明, 昭昭天宇闊, 皛皛川上平”[1]之語, 正初秋, 風微涼, 月澄明, 天宇闊, 川上平, 這般壯闊夜景并沒能安定詩人的內心, 他因惦記行役事難眠, 又言“商歌非吾事, 依依在耦耕”[1], 行役途中仍牽掛著田園之事。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則是陶淵明于返程途中所作。 “鼓棹路崎曲, 指景限西隅。 江山豈不險, 歸子念前涂。”(9)“指景限西隅”句“西”字下, 宋本注:“一作‘四’”。[1]路途崎嶇, 還恰逢夕陽落山, 甚至途中還顯現出險意。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其二的“山川一何曠, 巽坎難與期。 崩浪聒天響, 長風無息時”[1]再一次強調了行役之險。 反觀《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路途雖偏遠不易行, 詩人卻言“日入相與歸, 壺漿勞近鄰”[1], 有一種安寧之意。
陶淵明筆下所呈現的地理空間很多, 田園路、 行役路其實屬于不同類型的文學地理空間, 其中呈現的景象也不一樣。 行役路上往往具有開闊之景, 交通也似更為便捷, 至少有舟可通, 而通往田園之路, 有時可乘車或乘船, 有時還需攜帶農耕用具步行, 這兩者在陶淵明筆下都有著艱辛的意味。 不過, 對于通往田園之路的艱辛, 詩人不僅可以坦然接受, 還能衍生出更為詩意的畫面。
陶淵明對通往田園路和行役路態度之不同, 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 田園路跟陶淵明的自然思想相契合。 老子有“道法自然”[9]79之言, 偏遠的田園路受人類活動影響較小, 不管是雜草還是荒山, 都保存了一定的自然性質, 而行走于田園之路上的陶淵明, 他是一個“質性自然, 非矯厲所得”[1]之人, 在他辭官后, 通往田園之路崎嶇也好, 偏僻也罷, 都契合了他的本性。 與之相反, 行役路跟陶淵明本性有相違處, 行役時任務在身, 難免有身不由己之感, 更何況陶淵明當時所處的大環境較為動蕩, 很難實現志向。 陶淵明不止一次任職于軍幕中, 其詩《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等均可為證。 以“使都”看, 陶淵明在軍幕中還承擔過某種任務, 古直先生認為:“則淵明三月使都, 殆即為敬宣奉表辭職也。”[10]102同年, 陶為彭澤令, “仲秋至冬, 在官八十余日, 因事順心, 命篇曰《歸去來兮》; 乙巳歲十一月也”。 乙巳歲即義熙元年, 據《宋書》, 義熙三年閏月, “凡桓玄余黨, 至是皆誅夷”[4]14, 此時距陶淵明辭官不到兩年。 關于陶淵明是否曾仕桓玄, 學術界目前還有爭議。 但不論陶淵明是否曾仕于桓玄, 都可看出陶離開的官場, 非盛世之普通官場, 而是歷經飄搖動亂后充滿傾軋與血腥、 機謀與暗算之地。 理解了這些, 便可更好地理解陶淵明行役路中所感受到的不安和擔憂。
錢志熙認為:“在天地自然方面, 陶淵明的隱逸行為, 已經明顯地表現了他在廟堂與山水之間是選擇了后一場合的。”[5]152陶淵明的選擇契合了他的自然思想, 不管是不為五斗米折腰, 還是逃離充滿傾軋的官場, 或是遵從內心的選擇, 這種種都跟他的自然思想有關。 這般充滿自然性的、 偏遠的通往田園之路, 可以安放他的自然思想, 雖艱辛卻也給了他一份安寧與詩意。
通往田園之路, 相對于住宅或田園來說更具備自然性的空間。 住宅與田園在一定程度上受人類規劃影響, 雖說植物生長有一定的自然規律, 但園里植物的存在又很難擺脫人為性, 即使野生植物留在園中, 也可能符合了園子主人的規劃意識。 但通往田園之路不一樣, 有些即便是人為規劃的, 但也具自然性, 陶淵明自稱:“見樹木交蔭, 時鳥變聲, 亦復歡然(10)“然”, 宋本注:“一作爾。”有喜。”[1]在通往田園之路上, 應不乏這般景象, 從家到田園的路, 也可以有很多種, 農人對勞作路途的自由選擇度也更高。 而那種偏遠少人行之處, 遠離塵世喧囂, 也適合愛閑靜的陶淵明行走, 通往田園之路也是他精神棲居地之一。
其次, 田園路可以是通往家之路。 邁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學》中說:“創造家或故鄉的感覺是寫作中一個純地理的構建, 這樣一個‘基地’對于帝國時代和當代世界的地理是很重要的。 一篇文章中標準的地理, 就像游記一樣, 是家的創建, 不論是失去的家還是回歸的家。”[11]48在中國古代詩歌中, 可見很多詩人的家園情懷。 通往田園之路, 屬于田園-家或家-田園的路途, 相比行役路而言, 距離家鄉更近, 而行役路雖也可連接故鄉, 卻是詩人遠離家鄉, 漂泊異鄉的見證。
最后, 通往田園之路也可以是通往理想之路。 如《丙辰歲八月中于下潠田舍獲》:“郁郁荒山里, 猿聲閑且哀。” 這跟現實田園周邊環境有關, 而詩歌末兩句“遙謝荷蓧翁, 聊得從君棲”[1]亦含理想寄托。 通往田園之路, 也可以象征著通往理想之路。 這種理想之路跟《桃花源記》中的桃源路又相互映襯。 桃源路是“漁人”進入桃花源的路徑, 也比較偏遠。 這是無意中發現的路:“緣溪行, 忘路之遠近, 忽逢桃花林。”[1]后來, 漁人看到桃花林, 走了數百步, 也看到了兩岸的風光。 “林盡水源, 便得一山。 山有小口, 仿佛若有光”[1], 之后, 漁人從這小口進入, 一開始里面很是狹窄, 走了幾十步才至闊朗之處, 看到了村莊。 不過, 相比田園路而言, 陶淵明對桃源路有著神秘且浪漫的書寫, 緣溪行的隨意, 桃花林的浪漫, 從山的洞口通過又見闊朗天地的驚喜, 通過桃源路, 還出現了比較特殊的村莊。 這條路神秘出現, 后又不見, “太守即遣人隨其往, 尋向所志, 遂迷不復得路”[1]。 《桃花源記》中的田園生活很是美好安定, 這仿佛是處于太平時代的景象, 而陶淵明身處亂世, 他內心自然需要一個太平時代去安放他的理想。
3 陶淵明詩文中田園路的傳播接受及獨特性質
陶淵明筆下的田園路是重要且特殊的文學地理空間, 其融入了作者的內心情感, 也在后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關注, 具有獨特性質。
李志艷認為:“文學文本的傳播也是異域空間的文化旅行。”[12]陶淵明的田園曾一再引人關注和熱議, 也不乏關于陶淵明田園的唱和之作。 通往田園之路方面, 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傳播。 曾被誤收入陶集的《歸園田居》其六(“種苗在東皋”)中就有對通往田園之路的簡單描繪。 文本的傳播自然也會影響讀者的判斷。 這首詩又被認為是江淹所作, 江淹《陶征君潛田居》言:“種苗在東皋, 苗生滿阡陌。 雖有荷鋤倦, 濁酒聊自適。 日暮巾柴車, 路暗光已夕。 歸人望煙火, 稚子候檐隙。 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 但愿桑麻成, 蠶月得紡績。 素心正如此, 開徑望三益。”[13]1577此詩曾被蘇軾當成陶淵明所作,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韓子蒼云:‘《田園》六首, 末篇乃序行役, 與前五首不類。 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皋’為末篇, 東坡亦因其誤和之, 陳述古本止有五首, 予以為皆非也。 當如張相國本題為《雜詩》六首。 江淹《雜擬詩》亦頗似之, 但《擬淵明詩》‘開徑望三益’, 此一句為不類。 故人張子西向余如此說, 余亦以為不然。 淹之比淵明情致, 徒效其語, 乃取《歸去來》句以充入之, 固應不類……”[14]25-26《陶征君潛田居》一詩在本質上確實不類淵明所作, 也確實取了《歸去來兮辭》中的句子, “日暮巾柴車”便是對《歸去來兮辭》中“或命巾車”的接受, “日暮巾柴車, 路暗光已夕”也是對陶淵明通往田園之路的接受。
《歸去來兮辭》中的“農人告余以春及, 將有事于西疇。 或命巾車, 或棹孤舟。 既窈窕以尋壑, 亦崎嶇而經丘”, 在后世其實有不少接受者, 比如, 蘇軾的“北山怨鶴休驚夜, 南畝巾車欲及春”[15]513; 楊萬里的“柴桑臥病一茅廬, 或棹孤舟或命車”[16]; 范成大的“尋壑經丘到此堂, 官閑聊作送春忙”[17]等, 陶淵明通往田園道路的一些描寫, 成了一種文化典故, 得到了一定的傳播與接受, 然而, 他們跟陶淵明筆下那種真實的通往田園的道路書寫尚有區別。
“文學地理學認為, 正是通過文學接受者這個途徑, 文學實現了對地理環境的某些影響, 尤其是對人文環境的影響。”[18]陶淵明通往田園之路在后世得到了一定的關注, 但得到的回應其實有限, 唐初王績的《田家》也有對陶淵明田園的接受, 卻少了通往田園之路的描述, 他的《春日山莊言志》雖有對偏僻之處的描寫, 卻多跟其住處有關, “入谷開斜道, 橫溪渡小船”[19]46雖有“揚楫越平湖, 泛隨清壑回”之意味, 也有陶淵明所描述入桃花源的意味, 但也沒有連接到具體的田園生活。 儲光羲《田家雜興》八首也有學陶之處, 但也不見對通往田園之路的描繪。 宋代吳芾的《和陶丙辰歲八月中于下潠田舍獲》與《和陶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中亦不見對通往田園之路的描述。
后世很多和陶慕陶者, 他們筆下的田園跟陶淵明田園本就不同, 更何談通往田園之路。 這樣的路途, 為陶淵明的田園增添了個性化特征, 盡管慕陶擬陶和陶者眾多, 但有些通往田園之路, 卻是屬于陶淵明的, 很難模仿。 誠如鐘惺所言:“陶公山水朋友詩文之樂, 即從田園耕鑿中一段憂勤討出, 不別作一副曠達之語, 所以為真曠達。”[20]陶淵明真正從這樣一條路走過, 歷盡艱辛, 也享受著自由。
4 結 語
以前的研究者也有對陶淵明行役時情感的關注, 不過關于陶淵明筆下田園路與行役路之區別, 田園路與桃源路的相互映襯等問題還有一定的研究空間。 陶淵明在行役途中易流露出厭倦、 擔憂等情緒, 他筆下的一些田園路雖偏遠不易行, 詩人卻寫出了一種詩意與安寧, 主要是因為通往田園之路契合作者的自然思想, 行役路與其本性有相違之處。 田園路更具自然性, 農人去勞作時對路途的選擇相對更為自由。 通往田園之路又可跟通往桃源之路相互映襯, 田園路有著現實基礎, 又不乏理想與希望, 桃源路隨意浪漫, 卻也有著一定的現實因子。 陶公筆下的田園路在后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關注, 也有其獨特性質。 通往田園之路, 賦予了陶公田園詩獨特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