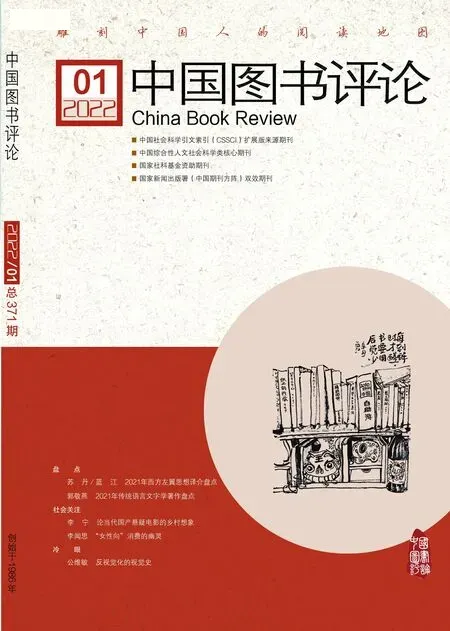論當代國產懸疑電影的鄉村想象
□李 寧
【導 讀】當代國產懸疑電影的鄉村書寫構成了一幅值得關注的文化景觀。其中,《血色清晨》《殺生》等影片將鄉村想象為扼殺啟蒙理性的惡土,《心迷宮》《平原上的夏洛克》等影片則將鄉村書寫為現代化進程所摧殘或遺忘的灰地。鄉村在前者中是作為現代性反面出現的,在后者中是作為現代性后果出現的,它始終是現代化進程中被凝視與改造的異托邦。未來國產電影應超越二元視角,探索鄉村與城市間更復雜的互動關系,找到更多想象鄉村的方式。
長期以來,我國文藝創作以綿延不斷的鄉村想象,呼應著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的變遷。盡管鄉土文化的日益衰微已是不爭的事實,但近年來的各類文藝實踐仍然建構起了紛繁駁雜的鄉村景觀。從《中國在梁莊》(2010)到《回鄉記:我們所看到的鄉土中國》(2014)、《崖邊報告:鄉土中國的裂變記錄》(2015)、《呼喊在風中:一個博士生的返鄉筆記》 (2016)、《大地上的親人》(2017),非虛構寫作中的“返鄉書寫”風行一時,在“鄉關何處”的感喟中抒發著種種鄉愁或鄉怨。網絡短視頻的江湖中,李子柒式的田園烏托邦與各類土味刻奇的鄉野生活構成了魔幻而分裂的雅努斯面孔。與此同時,《十八洞村》(2017)、 《我和我的家鄉》 (2020)、《山海情》 (2021)等影視作品則以鄉村振興的基調為時代鼓與呼。其中十分值得注意的是,《殺生》 (2012)、《心迷宮》(2015)、《喊·山》(2015)、《追兇者也》(2016)、《暴裂無聲》(2017)、《平原上的夏洛克》 (2019)等鄉土懸疑電影在近幾年接連出現,構成了一幅與上述鄉村書寫迥異又相關的文化景觀。
懸疑電影的核心在于各類懸念(suspense)的集中營造。但嚴格來講,懸疑電影稱不上一種特定的類型片,而是常常與犯罪片、驚險片、推理片等類型相勾連。諾埃爾·卡羅爾(Noёl Carroll)曾指出:“不確定性是懸念的必要條件……懸念不是對結果的回應;它從屬于導向某個不確定結果的某一時刻。”[1]因此可以說,懸疑電影的本質便在于展現種種不確定性,例如,編織敘事的迷宮、發掘人性的隱秘或探詢社會的未卜。在我國百余年電影創作中,懸疑電影本就處在邊緣化位置,鄉土懸疑電影創作就更顯冷清。追溯起來,李少紅執導的 《血色清晨》(1990)可視為濫觴,隨后便陷入長期的沉寂,直至近幾年才重煥生機。與城市懸疑電影多停留在故事編織或人性呈現的層面不同,由于“鄉村”早已凝結為含義復雜的文化符號,鄉土懸疑電影往往具有更為深層的現實或歷史指涉意味。因而值得我們去思考的是:為何鄉土懸疑電影會在近幾年接連涌現?從《血色清晨》至今,鄉土懸疑電影的鄉村想象經過了怎樣的嬗變?這種鄉村想象又呼應著怎樣的社會現實?
一、惡土:作為現代性反面的鄉村
汪暉曾指出:“現代化對于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一方面是尋求富強以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方式,另一方面則是以西方現代社會及其文化和價值為規范批判自己的社會和傳統的過程。因此,中國現代性話語的最為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訴諸‘中國/西方’ ‘傳統/現代’的二元對立的語式來對中國問題進行分析。”[2]在 《“新啟蒙”知識檔案》一書中,賀桂梅進一步指出,這一意識形態框架的關鍵之處在于其內部/外部的思維方式,即“其中隱含著內部/外部與中國/世界的對應關系,并將后者 (外部、世界)作為對前者(內部、中國)展開歷史批判的依據”[3]。上述框架同樣成為現當代文藝創作的重要話語模式,成為一把有效但也簡單的“奧卡姆剃刀”。尤其是“新時期”以降的特殊歷史語境下,許多文藝作品在內部鄉 村/傳 統/中 國 與 外 部 世 界/現代/西方的對立中展開對社會結構性弊端的批判,從而建構起一則又一則第三世界民族寓言。
從這一層面而言,問世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血色清晨》是對80年代的文化反思與 “文明與愚昧”這一經典命題的一種延續。當然,這種延續和重寫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波折動蕩中更顯繁復與凝重。在影片所描畫的偏僻鄉村中,少女紅杏被兩個哥哥李平娃、李狗娃以換親方式許配給村民張強國,但因被發現已非處女之身而遭遇退親。鄉村教師李明光被懷疑玷污了紅杏的貞潔,因而成為李平娃二人大肆宣揚復仇的對象,最終在眾目睽睽之下身死人手。顯然,影片中的鄉村被塑造為現代性與啟蒙理性的反面,是扼殺自由的牢籠與禁錮人性的枷鎖。象征著文明與啟蒙的明光是村中父親早亡、母親改嫁的孤兒,其文化知識來自早年停駐此地的知青,因為種地技術差、與女青年過從甚密等而備受村民鄙夷。 “無父”與“外來”的雙重設定顯然指認了他在山村中的邊緣人與異己者身份。而李平娃與李狗娃的當眾行兇,既是恢復家族榮譽與維系倫理秩序的一次儀式,也是傳統愚昧勢力對啟蒙力量的公開絞殺。
頗有意味的是,影片中明光玷污紅杏并非既定事實,而只是出自村民們充滿偏見的一致推斷,“到底誰奪走了紅杏的貞潔”這一懸念實際上始終未解。紅杏跳河自殺的悲劇已經說明,謎題的真相似乎已經并不重要,它只是影片用以指認父權制的荒謬、暴虐與堅固的質詢書。而無論是明光被殺現場還是紅杏自殺現場的圍觀村民,他們不只是作壁上觀的冷漠看客,也是置身其中的合謀者。原本可以避免的兇殺案卻最終上演,實際上展現出了傳統鄉土社會宗法秩序開始頹敗的跡象。與此同時,片中退親的張強國作為村中少有的走出鄉村、見過世面的暴發戶,已經開始成為鄉村中象征意義上的秩序掌控者。影片中有這樣一幕:新婚戲臺上,新郎張強國志得意滿地宣稱“如今有了錢,也可以像城里人一樣過日子了”,并豪邁地向村民們展現一個碩大的由鈔票鋪滿的“喜”字。這一幕的含義不言而喻:現代社會的金錢邏輯正滲入古老鄉村,成為主導鄉土秩序的“新神”。于是,在傳統男權文化與現代金錢邏輯的合謀下,明光之死成為歷史斷裂處的無奈見證,成為鄉土社會開始解體的蒼涼獻祭。影片開頭時作為鄉村學校的古老寺廟,在影片末尾成為國家保護的歷史古跡。這一首尾呼應的設置并非歷史循環式的書寫,其深層指涉在于,一方面鄉土秩序正成為歷史的陳跡,另一方面張強國所代表的現代文明卻沒有成為鄉村的拯救者,反而導致了明光式的啟蒙者的缺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確如戴錦華所言,影片“已不再是對80年代‘文明與愚昧’主題的重現,而且成了對這一主題的解構”[4]。
在《血色清晨》拉開鄉土懸疑大幕的多年后,一向被歸入“第六代”導演群體的管虎在2012年執導了電影《殺生》,講述了一個與前者頗為類似的事先張揚的謀殺案。不過,與“第五代”導演的鄉村想象普遍呈現為貼近現實或叩訪歷史的悲劇書寫不同,《殺生》被編織為一出超現實的悲喜劇,流露出濃郁的抽象思辨與黑色荒誕色彩。影片建構了“長壽鎮”這一封閉的鄉村空間,并將時空設定為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西南部。在長壽鎮中,狂傲不羈的主人公牛結實以種種越軌行為不斷挑戰著當代的宗法制度與倫理秩序,不堪其擾的村民們決定聯手除害。牛結實的父親并非本地人,而是村民口中死于癌癥的外來者。因此同《血色清晨》中的李明光一樣,牛結實也可視為無父與外來的啟蒙者。如果說《血色清晨》更多呈現的是村民們的看客角色,那么《殺生》則赤裸裸地展現了長壽鎮村民們是如何興致勃勃地參與到這場黨同伐異的殺人游戲中的。頗有意思的是,與《血色清晨》中的張強國與紅杏的人物設置類似, 《殺生》設置了走出大山接受過現代文明洗禮又反過來成為殺人幫兇和秩序主導者的“牛醫生”這一角色,同時也設置了深受傳統宗法制度迫害的“馬寡婦”這一人物。由此,在“牛結實是如何死的”這一懸念的牽引下,影片淋漓盡致地展現出傳統宗法制度對于異己者和女性的殘酷迫害。不過,與 “第五代”導演通常建構的沉郁蒼涼而無法擺脫的歷史輪回不同,《殺生》讓任達華飾演的外來官派醫生拯救馬寡婦母子出山,賦予了這個沉重故事以希望的結局。同時,由于《殺生》在敘事空間與鄉村生活上的超現實、架空式書寫,使得影片上升為更普遍意義上的社會對于個體的規訓與懲罰的思考,而并非對“新時期”流行的“文明與愚昧”這一經典主題的重復。
與《殺生》所建構的頗具作者風格的荒誕寓言相比,稍后問世的《喊·山》無論在敘事風格還是話語模式上都更像是對20世紀八九十年代鄉土想象的一次重復。被拐賣的少女紅霞跟隨丈夫移居大山環繞中的偏僻村落,長期經受丈夫暴力虐待的她設下殺夫陷阱,并讓人誤以為他是被村民韓沖的捕獵炸藥誤炸。盡管披著懸疑犯罪的外衣和拐賣女性的噱頭,但這部影片處理的議題仍是《黃土地》 (1984)、 《良家婦女》(1985)、《野山》(1986)等影片聚焦的女性個體與父權制的關系。與《殺生》中馬寡婦的“啞巴”所指代的父權制下女性話語權的喪失相似,主人公紅霞的 “失語”和“失憶”也是男性霸權的結果。不過,馬寡婦要依靠牛結實和外來醫生才能逃離牢籠,而紅霞原本就生長在都市知識分子家庭,是來自現代社會的個體。當紅霞被壓抑的現代性主體意識終于在理想的平等愛情關系中得到激活時,她便能實現自我的解放。影片末尾,面對互生情愫的韓沖即將被作為兇手逮捕,紅霞面臨精神自由與身體自由只能擇取其一的難題,最終選擇投案自首。她的自首,是女性個體反抗父權制的一次勝利的失敗。整體來看,影片對于鄉土社會愚昧落后的書寫以及“紅霞”這一勇于反抗命運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仍然相對陳舊,新意欠奉。頗有意味的是,影片在一開始就點明了故事發生在1984年的太行山岸山坪,似乎指認了這部影片的文化身份。也正因為如此,誠如有論者所言:“它孤單、突兀、不合群,像是出現在了一個原本不該屬于它的地方。”[5]
二、灰地:作為現代性后果的鄉村
在《鄉土中國》一書中,費孝通曾將傳統鄉土社會命名為“熟人社會”,并指出: “我們社會中最重要的親屬關系就是這種丟石頭形成同心圓波紋的性質。親屬關系是根據生育和婚姻事實所發生的社會關系。從生育和婚姻所結成的網絡,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無窮的人,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人物。”[6]然而,當前的生產結構與社會關系已與傳統社會甚至改革開放大幕初啟的“新時期”截然不同。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攻城略地,鄉土不斷被侵蝕,鄉民不斷在流散,鄉土社會也在面目全非中加速解體。土地的黃昏,在新世紀以來越來越成為令人痛心疾首的現實。在《新鄉土中國》一書中,賀雪峰將變化中的當代鄉土社會概括為“半熟人社會”[7]。陳柏峰的《鄉村江湖》等著作則進一步將這一現狀描畫為“農村社會灰色化”,具體指的是“農民在擺脫傳統村莊生活的社會約束和心理約束的同時,都市生活的社會約束和心理約束卻沒有條件取而代之。因此,農民在社會生活和心理上都缺乏約束和控制,村莊因此出現了既非傳統熟人社會,又非現代法理社會的灰色化秩序狀態”。[8]或許正如黃海的《灰地》一書的書名所概括的那樣,鄉村已經淪為“灰地”。
與《血色清晨》《殺生》《喊·山》將鄉村空間想象為扼殺啟蒙理性的惡土不同,近年來涌現出的《心迷宮》《追兇者也》 《暴裂無聲》 《平原上的夏洛克》等懸疑電影越來越熱衷于將鄉村書寫為現代化進程所摧殘或遺忘的灰地。如果說鄉村在前者中是作為現代性的反面出現的,那么它在后者中更多的是作為現代性的后果出現的。這種“灰地”書寫,一方面指向物理層面的鄉村空間景象的變遷,另一方面則指向精神層面的傳統倫理觀念的失落。
忻鈺坤執導的 《心迷宮》和《暴裂無聲》體現出的是對于鄉村現狀的冷峻批判。電影《心迷宮》圍繞一樁失手殺人案,以復雜的多線索敘事聯結起了村干部、混混、外出打工者、留守婦女、知識青年、小賣部老板等諸多人物,描摹了一出黑色荒誕的鄉村怪現狀。“死者何人”成為籠罩村民們的巨大懸念,而圍繞神秘尸體的毀尸滅跡、反復認領等種種行為又將鄉村人性的復雜面暴露無遺。由此,《心迷宮》深入剖解了現代化沖擊之下鄉村倫理秩序失衡與法制觀念薄弱的現狀,指向了鄉土社會淪為精神廢墟的蒼涼處境。影片《暴裂無聲》處理的議題則與曹保平執導的懸疑電影《追兇者也》類似,所關注的都是鄉村被工業化進程摧毀的現實,甚至不謀而合地分別設置了 “張保民”與“宋老二”兩位不愿屈服的主人公。不過,與 《追兇者也》更多著眼于多線敘事的編織和荒誕喜劇風格的營造相比,《暴裂無聲》的悲劇色彩與社會介入性更加強烈,顯示出創作者以種種符號意象指涉現實的野心。影片中,鄉村被大肆推進的煤礦業步步蠶食,由農民無奈變為礦工的張保民為了尋找失蹤的兒子張磊,無意間卷入了當地煤礦主之間的爭奪戰。影片借助三個主要人物建構了一個社會圖景:代表資本階層的煤礦主昌萬年、代表知識階層的律師徐文杰以及代表勞工階層的礦工張保民。在現代化進程中迅速完成資本積累的民營企業家昌萬年身處食物鏈的頂端,表面上樂善好施的他實際上內心暴戾冷酷。他熱愛狩獵,不僅豢養著一幫罔顧法紀的打手,還將現代化辦公室布置為逼真的狩獵場,奉行著剝削與掠奪的游戲法則。知識精英徐文杰本應為社會不公而發聲,卻甘為資本的傀儡,甚至最后在威逼利誘之下選擇為昌萬年隱瞞射殺張磊等種種不法事實。
《暴裂無聲》的英文片名為“Wrath of Silence(沉默的憤怒)”,聯系張保民因與勸其出賣土地的村民大打出手而導致啞巴的設定,加上待哺的羊羔、砧板上的肉等種種意象,不難看出影片根本上指向著鄉土與鄉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失語狀態。片中有這樣耐人尋味的超現實一幕:張保民之子與徐文杰之女手拉手爬上高坡,映入眼簾的是霧霾籠罩的現代化工業城市。結合后者被救而前者始終生死未卜的結局,顯然可以看出影片對鄉民所代表的底層人群未來命運的深深憂慮。片尾,尋子無果的張保民四顧茫然,面前一座龐大山丘轟然倒塌,這既是其心理防線的崩潰,也是傳統鄉土社會的解體。
與《暴裂無聲》浸入骨髓般的悲慟凜冽不同,徐磊執導的電影《平原上的夏洛克》顯得更加詩意溫和。影片中,在空心化、老齡化現象日益嚴重的鄉村,主人公超英執意要重建頹敗的老屋,不料幫忙購買食材的好友樹河被撞成重傷,無奈之下他與另一位好友占義組成類似福爾摩斯/華生的組合,一同踏上了尋找逃逸兇手的路途。片名中的“夏洛克”所指代的夏洛克·福爾摩斯是游蕩在英國現代化都市中的偵探,善于運用理性在種種犯罪迷局中抽絲剝繭、演繹推敲,因而無疑是現代主體的典范。將 “夏洛克”這一現代主體移植到中國華北平原農村,這就構成了一種錯位的荒誕與喜感。仔細揣摩,三位主要人物的名字都各有所指:生于“趕美超英”年代的“超英”指向我國持續推進的現代化進程,“占義”指向鄉土社會的重義傳統,“樹河”則指向土地與家園。這場因樹河被撞而拉開的尋兇之旅實際上也就有了更深層的意涵:尋找鄉土社會備受沖擊的元兇。
影片中,偵探二人組的尋兇之路是循著由村到縣城再到市里的這一不斷“向上”的路線展開的,這本質上是一種在過往文藝作品中司空見慣的 “鄉下人進城”的敘事。在這一過程中,隨著二人所闖入空間的現代化程度不斷提升,他們的主體性與自我認同感也在不斷降低。在如今已經淪為半熟人社會的鄉村中,他們尋兇借助的是熟人網絡甚至“四姑娘”這類靈媒,而在城市中,他們只能以種種宵小行為與陌生的現代化邏輯進行纏斗,直至被困在鋼筋混凝土環繞的樓頂孤島。片中,農村里的年青一代已經紛紛流徙外地,即便留守鄉村的青年也已經被現代化邏輯所改造,在與世無爭的老一輩面前顯得橫沖直撞,流露出汲汲于名利的傾向。影片以種種片段清晰地展現了鄉土社會與現代社會之間的差異:前者是強調人情、重義輕利、自由恬淡的禮俗社會,后者是注重規則、利字當頭、監控泛濫的法理社會。片中有這樣饒有趣味的一幕:當超英與警察上門盤問有撞人嫌疑的 “范總”時,這位當地知名企業家為掩飾自己的出軌行徑而厲聲質疑二人程序有誤,并宣稱跟局長、市長關系密切。與此同時,電影《摩登時代》的畫面在客廳電視機上一閃而過。這是創作者的一種含蓄批判:現代社會的新富階層表面上依靠的是規則與程序,實際上依賴的是權錢色交易。
影片的末尾,超英與占義尋兇未果,而超英為給樹河繳納高額治療費而未能建起新房。《平原上的夏洛克》曾用 “Rebuilding(重建)”這一英文名,但影片為我們呈現了一個無奈而蒼涼的結局:無論是超英的老屋重建還是整個鄉土社會的重建,看上去都注定徒勞無功。不過影片末尾,昏迷許久的樹河在一個田園靜好的夢境后醒來,在鄉村才能重拾主體性的三人在田野上飛馳,一同走向林茂瓜熟的田地深處。博伊姆 (Svetlana Boym)在 《懷舊的未來》一書中曾概括出“修復型懷舊”(restorative nostalgia)和“反思型懷舊”(reflective nostalgia)兩類懷舊情緒: “修復型的懷舊強調‘懷舊’中的‘舊’,提出重建失去的家園和彌補記憶中的空缺。反思型的懷舊注重‘懷舊’的‘懷’,亦即懷想與遺失,記憶的不完備的過程。”[9]從這個角度來看《平原上的夏洛克》,顯然它既表現出了對于鄉村的田園主義式的書寫,又試圖索解和反思鄉土衰微的根源,從而體現出了兩種懷舊情緒的游移和混雜。影片中老屋的廢墟與希望的田野構成的雙重景觀,成為這種游移和混雜的體現。或許這也正是創作者的無奈所在:導致鄉土社會衰落的元兇近在眼前,但我們只能別無他法地面對其繼續衰落的未來。
三、無依之地:現代化的異托邦
由上可見,從 《血色清晨》描畫的“惡土”,到近些年來鄉土懸疑電影頻繁呈現的“灰地”書寫,似乎可以勾勒出改革開放初期啟蒙現代性的高揚到近些年來反思啟蒙現代性傾向越來越顯著的變化。然而一個無奈的事實是,在需要倡導啟蒙的年代,鄉村被書寫為阻礙文明進步的鐵屋子;在亟須反思之時,鄉村又被想象為遭受無情碾壓的荒蕪之地。在現代社會的視域中,無所依靠的鄉村始終是被改造的客體與被凝視的風景,是現代化的異托邦。
“異托邦”(heterotopias)的概念源自福柯 (Michel Foucault),他將異托邦視為一種與現實中不存在的烏托邦所不同的場所。異托邦雖然真實存在,但它是一種異質性的“反場所”[10]。正如有論者所言,福柯“將異托邦理解為能夠出離中心的場所;同時,異托邦相對于日常處所而言,承載著某種強烈的相異性和某種對立或對照的標志”[10]。當代鄉土懸疑電影的普遍特征便是將鄉村想象為現代都市空間的對立面,一個既凝結了悠遠歷史又經歷了沉痛斷裂的他者空間。通過將鄉村書寫為異托邦,現代性的種種正面價值或負面價值才得以凸顯。而總體上看,這種現代化異托邦的建構又體現出廢墟、荒誕與不確定性等顯著特質。
從《血色清晨》中廢棄的古廟,到《暴裂無聲》中衰敗的荒山,再到《平原上的夏洛克》中傾頹的老屋,當代鄉土懸疑電影不斷堆疊起了鄉村的“廢墟”景觀。巫鴻曾在《廢墟的故事》一書中集中探討了中國藝術中種種廢墟意象的呈現,并精確地闡釋了廢墟空間給人的情感體驗:“作為一個‘空’場,這種墟不是通過可見可觸的建筑殘骸來引發觀者心靈或情感的激蕩:在這里,凝結著歷史記憶的不是荒廢的建筑,而是一個特殊的可以感知的‘現場’(site)。因此, ‘墟’不是由外部特征得到識別的,而是被賦予了一種主觀的實在 (subjective reality):激發情思的是觀者對這個空間的記憶和領悟。”[11]當代鄉土懸疑電影的種種廢墟書寫,正是在外部視覺特征營造的基礎上,激發人們對這一空間所聯結的歷史記憶、集體經驗與價值理念等種種內容的體味。
值得注意的是,鄉土懸疑電影的異托邦建構越來越流露出荒誕的意味。如果說《血色清晨》還是以現實主義的筆觸展開悲劇書寫的話,那么21世紀頭十年涌現出的諸多鄉土懸疑電影則普遍呈現出越來越濃烈的現代主義意味,這突出表現在荒誕風格的流行上。荒誕源于現實,荒誕的內在是真實。無論是《心迷宮》《暴裂無聲》的黑色悲劇,還是《追兇者也》 《平原上的夏洛克》的荒謬喜劇,都在看似非理性、不協調的反常事件中去觀照現實。實際上,除了本文論及的影片之外,近年來還有《Hello!樹先生》 (2011)、《一 個 勺 子》(2014)、《驢 得 水》(2016)、《我不是潘金蓮》(2016)、《健忘村》(2017)等一系列影片紛紛在荒誕現實主義的路向中展開鄉村書寫。顯而易見,21世紀以來的鄉村正日益成為荒誕影像之樂土。當然,嚴格來說, “荒誕”(absurd)這一美學范疇與審美體驗是西方現代化進程的產物。荒誕所產生的根源是西方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個體精神危機與社會危機,荒誕感所表現的正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沖突。而荒誕鄉土影像在近些年來的集中涌現,根本上呈現出的正是當下鄉村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斷異化的處境。
當然,懸疑電影的核心要素在于“懸疑”。而頗為有趣的是,當代鄉土懸疑電影盡管設置了不同的敘事懸念,卻普遍拒絕賦予故事以清晰的答案和明確的結局。 《血色清晨》沒有為我們說明究竟是誰奪走了少女紅杏的貞潔,《殺生》中牛結實的直接死因也含混不清,《暴裂無聲》中的張保民始終未能找到自己的兒子,《平原上的夏洛克》中肇事逃逸的兇手仍然逍遙法外。懸念的謎底或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懸念的持續。這些貫穿電影始終的未解之謎,猶如一個盤旋在鄉村上空的巨大問號,指向著這塊無依之地所面臨的不確定的未來。
余論
毋庸諱言,當代鄉土懸疑電影對于鄉村現實給予了深入觀照,也豐富了當代文藝作品的鄉村想象。然而,當這些看似風格多樣的影片始終執著地將鄉村書寫為現代化的異托邦時,或許需要進一步去思考的是,我們何時能夠逃離這種城鄉對立的二元框架?
將鄉村與城市作為兩種生活方式加以對立并以此觀照社會歷史進程的傳統,由來已久。在1973年出版的《鄉村與城市》一書中,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結合英國現代化進程與英國文藝創作中的鄉村想象對這種觀點展開了駁斥。在他看來,城市與鄉村的對立只是表面現象,“城鎮既是鄉村的映象,又是鄉村的代理者”[12]76。他進一步指出,自從工業革命后,“我們心目中鄉村和城市最深刻的意象一直非常明顯地充當著對整個社會發展的反應方式。這就是為什么最終我們決不能將自己局限于城市和鄉村形象之間的對比,而是要進一步看到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并通過這些相互關系看到潛在危機的真實形態”。[12]401這番近半個世紀前的論述,或許對我們理解當前中國現實仍然有所助益。與其不厭其煩地站在現代化的視角去凝視鄉村和描畫城鄉差異,不妨超越二元視角,探索鄉村與城市之間更為復雜的互動關系,找到更多書寫與想象鄉村的方式。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當代中國電影中的青年形象與文 化 編 碼 研 究 (1978—2018)”(19CZW04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Noёl Carroll.Paradox of Suspense[A].Peter Vorderer,Hans J.Wulff,Mike Friedrichsen.Suspense:Conceptualizations,Theoretical Analyses,and Empirical Explorations[C].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6:149-153.
[2]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60-61.
[3]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21.
[4]戴錦華.霧中風景:中國電影文化1978—1998[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307.
[5]石川,張璐璐.《喊·山》:消隱的鄉村與敘事的困境[J].電影藝術,2016(6):34-36.
[6]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23.
[7]賀雪峰.新鄉土中國:轉型期鄉村社會調查筆記[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1.
[8]陳柏峰.鄉村江湖:兩湖平原“混混”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9:370.
[9][美]斯維特蘭娜·博伊姆.懷舊的未來[M].楊德友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46.
[10][法]M.福柯.另類空間[J].王喆譯.世界哲學,2006(6):52-57.
[11][美]巫鴻.廢墟的故事: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中的“在場”與“缺席”[M].肖鐵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7.
[12][英]雷蒙·威廉斯.鄉村與城市[M].韓子滿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