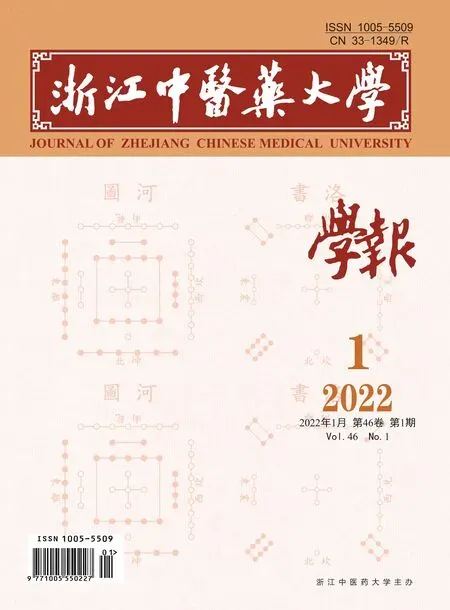系統性紅斑狼瘡中醫藥療效預測模型構建的思路和方法
陳麗瑩 楊科朋 王新昌
1.浙江中醫藥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 杭州 310053 2.浙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系統性紅斑狼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種多臟器受累的自身免疫性炎癥性結締組織病,目前認為其發病是基因、表觀遺傳因素(如DNA甲基化、組蛋白修飾、非編碼RNA等)和環境因素(如紫外線、藥物和感染)等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國SLE患病率為70~100/10萬,居世界第2位,患病人群超過100萬[1]。SLE的高度異質性是風濕病臨床醫師和研究者面臨的巨大挑戰,嚴重影響臨床診斷和治療。目前臨床上尚無根治SLE的方法,患者需長期應用糖皮質激素(以下簡稱激素)、免疫抑制劑等,而且需要基于系統性紅斑狼瘡疾病活動指數(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disease activity index,SLEDAI)、不列顛群島狼瘡評估組(British Isles Lupus Assessment Group,BILAG)、狼瘡活動測量標準(systemic lupus activity measure,SLAM)等定期評估疾病活動度,以調整治療方案。長期的西醫標準治療對患者病程分期及經濟要求高,而且其治療不良反應一定程度上可能超過疾病本身所帶來的危害。因傳統的療效評估及方案調整周期較長[2],部分患者可能因錯過有效方案的最佳干預時機而影響療效。中醫藥的療效評價有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的特點,但四診信息等預測因子缺乏客觀性,通過人腦模糊預測的方式依賴個人經驗,缺乏標準化,因此亟待開發更安全、更有效的中醫藥療效預測方法。本文擬從統計學工具和組學技術創新角度出發,闡述SLE療效預測模型構建的思路和方法,幫助改進現有的臨床療效預測工具,以克服由SLE異質性所造成的療效預測障礙,實現中醫早期診斷和精準治療。
1 SLE中醫療效評價現狀
隨著SLE“精準醫學”和“靶向治療”的發展,新的免疫抑制劑和生物制劑在SLE的治療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中醫藥治療SLE具有“增效減毒”的優勢,能夠減輕激素等藥物產生的不良反應,并提高患者生活質量。然而,SLE的中醫療效評價正面臨著挑戰,這一定程度上影響中醫藥治療特色的發揮,重新審視和探索中醫藥治療SLE的作用變得尤為重要。目前SLE的治療應答時間與醫師治療方案調整時間存在一定差異,這使醫師往往難以把握中醫藥治療的最佳時機。中醫“整體觀念”“辨證論治”“隨證治之”的動態診療思維有利于“個體化診療”“療效預測”模式的建立,如《傷寒論》“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的傳變方式,一定程度上預測了疾病的傳變模式和預后反應[3];《金匱要略》則將“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的治未病思想用于指導臨床用藥;《溫病條辨》提出的溫病衛-氣-營-血的傳變方式則揭示了邪氣漸深、病情加重的規律。由于SLE常常累及多個器官,病程長,易復發,臨床特征和血清學表現存在高度異質性,臨床療效評估需要從多個維度考慮。從癥狀分類角度來看,SLE癥狀可分為2類,一類是以炎癥導致的典型癥狀,包括脫發、皮疹、漿膜炎、關節炎、腎炎、血細胞減少等;另一類則是與炎癥無關的癥狀,主要表現為疲勞、抑郁、疼痛和認知障礙[4]。由此看來,僅僅通過臨床分類標準診斷或以SLEDAI評分來調整治療方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臨床評價SLE的中醫療效時,僅僅以西醫SLEDAI評分、BILAG、SF-36量表、系統性紅斑狼瘡生活質量(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quality of life,SLEQOL) 量表作為評判標準是不全面的,而且忽視了“證”的療效評價;中醫學者一般應用“證候積分法”來評價臨床上常見的中醫證型,然而單純針對“證”的療效評價又一定程度上偏離了SLE療效評價的側重點,忽視了SLE生物學指標在SLE療效預測中的積極作用[5-6]。因此,目前中醫臨床上常采用“病證結合”的思想來指導SLE的治療,采用證素辨證和西醫臨床量表相結合的方法,能夠客觀體現中醫證候的變化和轉歸[7]。綜上所述,中醫個體化療效評價雖然有效整合了復雜動態條件下中醫個體化診療的特征,滿足了患者病證動態演變的規律,但需要一定的時間長度作為療效評價的支撐[8]。因此,科學的、符合SLE病證本質的中醫療效評價方法決定了SLE中醫藥治療的研究方向。中醫藥系統生物學是采用層次化、整合各種組學方法和逐步優化的策略來研究“系統-系統”的中醫藥創新研究模式。包括網絡藥理學在內的系統生物學是探索SLE中醫療效預測靶點的有效方法之一,借助科學化的療效靶點預測,可以彌補中醫藥臨床療效評價多靶點、缺乏精準化、時程長的特點。因此,中醫“整體觀”和“辨證論治”思想指導下的臨床和基礎實驗方法和技術的創新融合是探索SLE等優勢病種中醫藥治療的良好趨勢[9]。
2 SLE中醫療效預測模型構建的工具與方法
中醫藥人工智能發展大有可為,但目前仍然面臨著一定的數據困境和可解釋的難題[10]。SLE發生、預后可能與遺傳因素、環境因素、免疫系統紊亂和性激素水平等相關,其中遺傳因素是SLE發生的根本內因,而環境因素則是促發SLE的外因。目前也有大量文獻證明了表觀遺傳學在SLE發生發展中發揮的作用,表觀遺傳學作為基因和環境的橋梁,其在SLE療效預測中的作用不容小覷。SLE中醫療效的影響因素復雜,療效預測因子的多樣性直接影響著對可信度和精確度較高的總體參數的獲取,從而大大增加了樣本需求量[11],這使得臨床醫師難以構建能夠明確預測疾病進展的療效預測模型[12]。目前國內已經出現了不少SLE預測模型,主要是診斷模型、并發癥相關預測模型、預后模型等[13],這些預測模型多數基于臨床回顧性資料構建。從預測工具的角度看,決策樹、支持向量機、Logistic回歸、Cox回歸和人工神經網絡(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ANN)等方法均可支持建立這類SLE預測模型[14]。根據研究設計類型和分析目的選擇合適的模型構建工具十分重要,如病例對照設計研究應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環境因素、易感基因、免疫表型與SLE的相關性,也可用于SLE診斷模型的構建;臨床隨訪復發或者死亡率的研究中,Cox風險比例模型被用來分析因素對預后的影響;SLE發作頻次的研究則可采用Poisson回歸模型,分析因素對發作頻次的影響[15];Markov模型可以通過動態衡量疾病的變化規律,縱向比較不同階段中醫個體化診療的優勢,同時對疾病的變化趨勢進行預測,以客觀評價中醫個體化治療和療效間的關系[16]。目前中醫藥療效預測模型的構建和驗證較為復雜,依賴于中醫藥療效評價體系和數學統計模型選擇兩方面的完善。靶向藥物的療效評價主要使用SLE應答者指數-4(SLE responder index-4,SRI-4)作為一個復合終點,其定義為:與治療前比較,治療后應滿足下列各項標準:紅斑狼瘡國家評估-系統性紅斑狼瘡疾病活動指數(Lupus Erythematosus National Assessment-SLE Disease Activity Index,SELENA-SLEDAI)≥4分;沒有新的BILAG評定的一個器官評分為A或兩個器官評分為B;醫師全球評估(Physician's Global Assessment,PGA)評分無惡化。中醫療效則主要依賴中醫證候評分表等來衡量。從中醫診療角度看,可將預測模型的療效結局定義為復合結局,構建預測模型;其次,統計學模型的選擇上仍可以是多樣的;再者,長時程的療效預測模型能夠優化模型區分度和校準度。在預測模型構建的初期階段,需要進行一定的外部預試驗,以確定樣本量的大小,對于以有效率和無效率作為結局指標的療效預測模型,以中等效應量為標準,預試驗的樣本量至少要達到120例以上(每組60例)[11]。在樣本量不足或者數據維度高的情況下,用ANN等方法進一步定義和驗證SLE的發病特征,可以克服數據無法獲得訓練集和驗證集的困難,適用于神經精神性SLE或者幼年型SLE等罕見病例預測模型的構建[17-18]。最后,療效評價指標可以從臨床角度上升至多組學層面,以彌補預測模型長時程的缺陷,而且更能反映疾病的本質,有助于達到早期精準診斷和準確判斷預后的目的。
3 多組學技術在SLE療效預測中的應用
3.1 基因組學與SLE療效預測 根據近年來基因組學在中醫體質研究中的應用,筆者認為基因組學能為SLE中醫藥療效預測提供一定借鑒意義。目前國內外一些研究已經發現,基因多態性可用于臨床SLE免疫抑制劑的療效預測。環磷酰胺是SLE誘導緩解和維持治療的常見藥物,其作用于活性代謝物烷化DNA,發揮細胞毒作用,抑制B細胞和抗體生成。有研究發現,中國SLE患者藥物代謝酶基因標志物CYP2C19和CYP2B6可以用于預測環磷酰胺4-羥基化程度、療效和副作用[19]。硫唑嘌呤是SLE患者維持治療的推薦藥物,由于巰嘌呤甲基轉移酶(thiopurine methyltransferase,TPMT) 的單核苷酸多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s)會導致蛋白質結構不穩定和TPMT蛋白降解增強,因此可以通過檢測TPMT的活性來實現對硫唑嘌呤的療效預測[20-22]。一項針對霉酚酸酯治療SLE患兒的藥代動力學/藥效學(pharmacokinetic/pharmacodynamics,PK/PD)研究發現,霉酚酸酯的AUC0-12和Ctrough均可預測兒童SLE患者的疾病活動度[23],由此指出應考慮以AUC0-12或Ctrough為靶點指導霉酚酸酯的個體化給藥方案[24]。
3.2 表觀遺傳組學與SLE的療效預測 目前針對SLE的表觀遺傳療效預測研究較少,但部分基于DNA甲基化的藥物研究提示,DNA甲基化的動態變化與藥物治療存在一定關系。DNA甲基化/羥甲基化修飾是指在DNA甲基轉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s,DNMTs)和羥甲基化酶(ten eleven translocation,TET)介導下的CpG二核苷酸中胞嘧啶的修飾,DNA甲基化修飾與羥甲基化修飾維持著動態平衡,對基因的轉錄表達具有重要的調控作用。全基因組分析表明,SLE患者的T細胞具有更顯著的差異甲基化位點,尤其是Ⅰ型干擾素途徑相關基因顯著低甲基化,與自身抗體產生、淋巴細胞募集相關。針對混合性結締組織病的全基因組甲基化研究發現,PARP14、SPATS2L、DDX58、OAS2、PLSCR1、HLA-F、LGALS3B基因具有特征性的甲基化差異[25]。類風濕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患者早期的T淋巴細胞顯示出明顯的DNA低甲基化表現,使用甲氨蝶呤治療后能夠逆轉這種低甲基化表現,并且與正常人群趨向一致[26]。研究發現5 196個差異甲基化的CpGs與激素的使用有關,125個差異甲基化的CpGs與硫唑嘌呤有關[27],但環磷酰胺等藥物誘導甲基化的機制研究仍不明。中藥治療SLE的表觀遺傳機制研究發現,白芍總苷能夠上調SLE患者外周血CD4+T細胞甲基化基因CD11a的啟動子甲基化水平[28],抑制自身免疫反應。解毒祛瘀滋腎方(狼瘡定)含藥血清能夠上調女性SLE患者外周血單核細胞CD70基因啟動子甲基化水平,抑制SLE患者CD70基因的表達,從而發揮治療效應[29]。筆者認為,建立以DNA甲基化為療效預測因子的臨床預測模型,將有助于評估患者臨床獲益和風險。
3.3 細胞組學與SLE的療效預測 在單細胞測序和單細胞轉錄組學分析技術幫助下,人類免疫圖譜研究已經開始揭示單個SLE患者臨床癥狀和疾病發作或復發的細胞和分子基礎。預測患者自然病程的預后生物標志物以及預測治療應答的免疫標志物對于SLE精準醫療的發展十分重要,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單靶治療、多靶聯合治療以及序貫治療的臨床應用[30]。采用流式細胞術或質譜流式細胞術(mass cytometry,CyTOF)的外周血免疫表型分析可識別疾病異質性的特異細胞亞群,以幫助發現與疾病亞型、疾病活動和復發有關的分子網絡[31]。CyTOF是用金屬同位素標簽代替傳統熒光標簽的高通量流式細胞術,利用探針耦合到獨特穩定的重金屬同位素,因此在特定的質量通道中,報告離子的數量就是分子表達的量,這項技術可在單細胞水平同時分析胞內和胞外40種以上的參數,而且參數之間重疊的信號很少,因此能系統分析細胞表型和功能信息[32]。SLE患者存在高度異質性,而且其臨床治療方案多樣化,中醫藥療效反應的潛在作用機制尚不明確,免疫微環境和免疫細胞的相互作用對SLE的發生和發展具有重要影響,一些特定的SLE細胞亞群可能誘導SLE免疫抑制藥物耐受,甚則可以用于檢測療效應答和復發。Robinson等[18]發現SLE患者外周血單個核細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中Na?ve B細胞和未轉換型B細胞頻率對幼年型SLE患者發病具有較好的預測效能。研究發現,漿母細胞和漿細胞是SLE特異性抗體的主要來源[33]。利妥昔單抗(抗CD20單抗)治療SLE時B細胞清除率相對低,復發率更高,且存在“二次無應答”現象(secondary non-depletion and non-response,2NDNR),而治療前漿母細胞水平差異或許能解釋這一問題[34]。外周血漿母細胞表達CD27水平被認為與SLE的疾病活動度相關,可以作為SLE疾病活動、復發和治療應答的預測因子[35]。對特異分子表型的前瞻性縱向研究可能有助于改善預后評估、臨床試驗設計,以及實現精準治療,因此在多組學技術背景下,測量與疾病相關的細胞群的頻率是監測免疫系統狀態或預測治療反應的候選方法[36-37]。
4 結語和展望
SLE達標治療(treat-to-target,T2T)認為,SLE緩解后的維持治療應盡可能實現零激素用藥,這意味著大部分患者將經歷低疾病活動度到臨床完全緩解的過渡階段。目前免疫抑制劑和生物制劑的臨床運用更加規范,然而這些藥物目前仍然無法完全代替激素,這時中醫藥治療可能發揮著關鍵作用,中醫藥的療效預測為實現零激素方案提供了一定的可能。中醫藥療效預測模型能夠幫助臨床醫師把握中醫藥治療的SLE時機,并且形成規范化的SLE療效網絡,但目前敏感度與特異度兼具的中醫藥SLE預測模型構建面臨著一定的困境,可能存在多維數據(基因、表觀遺傳、臨床信息、分子表型、治療方案等)難以獲得、中醫四診信息缺失嚴重和難以規范、模型測試隊列和驗證隊列樣本量不足的問題。現代人工智能技術可對SLE進行早期診斷和預后分析,如多方計算平臺可以通過分布式統計分析和機器學習實現數據分析和模型訓練,從而幫助解決醫療大數據共享和樣本量不足的問題。或者借鑒以中醫循證病例系統為代表的中醫電子研究平臺,提取多維臨床信息和療效評價量表,通過融合神經網絡,構建中醫個體化療效評價模型。以SLE為代表的中醫藥治療特色的疑難疾病的療效預測模型的構建,一定程度上涵蓋了中醫藥發展的新趨勢、新動向、新理念,對于重塑中醫藥在當代醫學中的地位具有關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