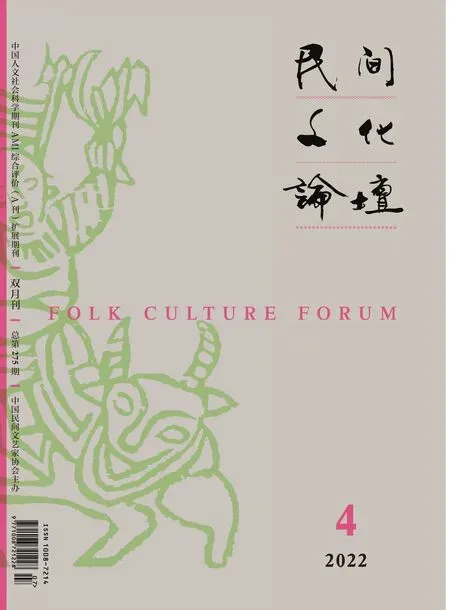社區賦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多方協商與社會治理*
[冰島]瓦爾迪馬·哈夫斯泰因 著 吳世旭 譯
資產階級最近的野心是在這里建一個商場,比清真寺還高。
資產階級靠廣場及其帶來的旅游業維生,但他們沒有意識到,游客來這里不是為了商場。我們正在嘗試改變馬拉喀什居民看待廣場的方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決定將在這方面幫助我們。因此,他們有理由感到自豪。①Juan Goytisolo,“Entrevista de ArcadiEspada a Juan Goytisolo”, La Espia del Sur, 200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21020065811/; http://www.geocities.com/laespia/goytisolo2.htm) Accessed October 15, 2017.除非注明,所有直接引用都來自我自己在本文討論的會議上所作的民族志田野筆記。
“正當的自豪感”
這個廣場是摩洛哥的杰瑪·埃爾夫納。上面的話是持不同政見者、長期居住在馬拉喀什的西班牙作家胡安·戈伊蒂索洛(Juan Goytisolo)說的。他描述的正是這個廣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遺產名錄之后的預期效果。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戈伊蒂索洛帶領一批摩洛哥知識分子共同努力保護這個繁忙的集市,它位于馬拉喀什麥地那或曰老城(1985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入口處。
杰瑪·埃爾夫納是各種各樣表演的場所——講故事、耍蛇、算命、吃玻璃、布道、雜技、舞蹈和音樂表演,不一而足。這些街頭表演者被稱為“海勒奇亞”;他們吸引了外國的和摩洛哥的人群來到杰瑪·埃爾夫納,觀眾們聚集成一圈,形成一個被稱為“哈爾恰”的表演空間①Deborah Kapchan, Gender on the Market: Moroccan Women and the Revoicing of Tradi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6.。廣場還提供各種服務和產品:從水果攤和新鮮肉類到最好的烤肉和烤串;從牙科保健到草藥;從塔羅牌解讀到海娜紋身。晚上,露天餐廳占據了很大一部分空間②Thomas Beardslee,“Questioning Safeguarding: Heritage and Capabilities at the Jemaa el Fnaa”, PhD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14; Thomas Schmitt, “Jemaa el Fna Square in Marrakech: Changes to a Social Space and to a UNESCO Masterpiece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as a Result of Global Influences”, Arab World Geographer 8, no.4, 2005.。
正如戈伊蒂索洛所言,在20世紀90年代,市政當局、商人和承包商計劃拆除廣場周圍的幾棟建筑,以便為一個玻璃幕墻的高層購物中心和一個為購物者服務的地下停車場讓路。戈伊蒂索洛認為杰瑪·埃爾夫納的文化空間不可能在這一發展中幸存下來。
你會在這里看到一個熟悉的故事,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版本。這是一個關于失去和毀滅的故事。如今,它講述了全球化力量對遺產的破壞。150年前,同樣的故事講述了現代力量對傳統的破壞。它是我的學科——民俗學的創作敘事;它推動了故事、歌曲和工具的收集,也推動了對風俗、儀式和民俗的描述,直到現代化的推土機將它們的每一個痕跡都清除殆盡。
文化評論家沃爾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在描述保羅·克萊(Paul Klee)的畫作《新天使》時,用寓言的形式講述了這個故事。“人們就是這樣描繪歷史天使的。他的臉轉向過去”,但他的翅膀卻被強大的進步風暴所困:“這場風暴無可抗拒地將他刮向他背對著的未來,而他面前的殘垣斷壁卻越堆越高直逼天際”③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1968, p.258.。民俗學者、保護專家、遺產工作者走了進來:“天使想停下來喚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補完整”。然而,這場風暴卻違背了他的意愿,帶著他進入了未來。在他面前,瓦礫成堆。過去就像一片廢墟:“這場災難不斷堆積著尸骸,將它們拋棄在他的面前”④Ibid.。換句話說,是一個被拆毀的場地——很像設想中的杰瑪·埃爾夫納。
在馬拉喀什,歷史的天使以戈伊蒂索洛為向導,他和藝術家與知識分子同伴們對施工方案發出了警告。他們成立了一個名為“廣場之友”的非政府組織,并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尋求幫助。時機恰到好處。20世紀90年代中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剛剛在秘書處設立了一個非物質遺產科,并正在為后來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進行初步的籌備。
1996年,戈伊蒂索洛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費德里科·馬約爾(Federico Mayor)取得了聯系。后者是戈伊蒂索洛的同胞(指同國人--譯者),也是一個詩人、作家、學者和政治家。他們早已相識,而且事實證明,馬約爾非常愿意支持戈伊蒂索洛領導的運動⑤Federico Mayor Zaragoza, “Patrimonio cultural inmaterialen el siglo XXI: Entrevista con Federico Mayor Zaragoza, ex director general de la Unesco”, Quaderns de la Mediterrània 13, 2010,pp.231-234.。正如馬約爾后來所說,“我永遠不會忘記,作家和哲學家胡安·戈伊蒂索洛一天晚上在巴黎拜訪我,表達了他的想法:我們應該采取和在文化與自然遺產方面已經取得成功一樣的路數,展示這些音樂、文學和教育方式,它們揭示了人類獨特的能力,即創造力——反思、發明、想象、預見和創新。如果重視和欣賞這些如此珍貴卻又未被充分認識的成果,那么,人類整體將變得更加富強”⑥Ibid., p.232.。
在總干事的支持和“廣場之友”的協助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遺產處和摩洛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于1997年在馬拉喀什組織了一個“國際保護大眾文化空間磋商會”。這次會議匯集了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和口述史的學者以及演員、作家和政治家,制定了一項保護非物質遺產的國際方案,并突出了杰瑪·埃爾夫納的困境和價值,通過國際承認界定了這個集市的價值①Thomas Schmitt,“The UNESCO Concept of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s Background and MarrakchiRoo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14, no.2, 2008.。
換句話說,戈伊蒂索洛和馬拉喀什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借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重點關注②借用邁克爾·迪倫·福斯特(Michael Dylan Foster)的貼切說法, Michael Dylan Foster Lisa Gilman, UNESCO on the Ground:Local Perspective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29.,來拯救杰瑪·埃爾夫納。在戈伊蒂索洛的分析中,拯救這個廣場的關鍵在于,改變當地人——尤其是那些更富裕、更有權勢的人群與杰瑪·埃爾夫納的關系,教會他們用另一種眼光來看待這個廣場③Lionel Gauthier,“Jemaa El-Fnaoul’exotisme durable”, Géographie et cultures, no.72, 2009. (http://gc.revues.org/2258)。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幫助下,戈伊蒂索洛和他的同伴們將國際社會的注意力轉向了杰瑪·埃爾夫納,哪怕只是一瞬間。有影響力的外國人對杰瑪·埃爾夫納贊不絕口,認為它如此非同凡響,不僅應該被認定為摩洛哥人的遺產,而且應該被認定為人類的遺產。根據地理學者托馬斯·施米特(Thomas Schmitt)的說法,一旦國王加入,說服其他有影響力的摩洛哥人就變得容易了;馬拉喀什的市政當局最終明白了這一點,他們沒有解散這個廣場,而是將其保留下來④Thomas Schmitt,“The UNESCO Concept of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s Background and MarrakchiRoo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14, no.2,2008, p.103.。
落后和衰敗的象征
這就是故事變得有趣的地方。摩洛哥當局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一起調查了威脅杰瑪·埃爾夫納活態遺產地位的危險;他們指出,社會經濟轉型是“維護和繁榮這一文化空間的嚴重障礙”,并因現代化、城市化和旅游業的發展而加劇,所有這些都威脅到“行為和表演的真實性(authenticity)”。不過,在接受阿卡迪·埃斯帕達(Arcadi Espada)采訪時,胡安·戈伊蒂索洛本人就馬拉喀什市場面臨的危險,提出了一個相當不同的觀點:“馬拉喀什的資產階級‘社會’對這個廣場不屑一顧,并在各種場合試圖廢除它,因為他們認為它是落后和衰敗的象征。這種態度絕非罕見:往往是外來的重視讓地方回歸美觀和完整。例如,阿爾罕布拉宮是英國作家和旅行者發現的。博羅(Borrow)回憶說,當他向格拉納達的人們詢問阿爾罕布拉宮的情況時,他們稱它為‘這些摩爾人的小玩意兒’。在馬拉喀什,類似的事情正發生。”⑤Juan Goytisolo, “Entrevista de ArcadiEspada a Juan Goytisolo”, LaEspia del Sur, 200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21020065811/; http://www.geocities.com/laespia/goytisolo2.htm) Accessed October 15, 2017.
事實證明,對杰瑪·埃爾夫納的主要威脅不是來自外部,也不是來自幕后的現代化和城市化或上述一連串現代弊端中的其他可疑對象,更不是來自越來越多的游客。相反,主要的威脅來自掌握著政治和經濟權力的當地居民。因此,將這個集市重塑為非物質遺產的目的,是為了改變馬拉喀什本地居民與杰瑪·埃爾夫納的關系。
戈伊蒂索洛對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名錄到底有助于得到什么的解釋,說明了國際榮譽名單如何激勵國家和地方政府維護傳統文化的特定表現形式或空間。在馬拉喀什,一個地方委員會實施了一項十年保護計劃,其中包括一項城市規劃研究、建立一個研究所、確認傳統知識的持有者,以及加強與廣場管理有關的習慣法的規定①UNESCO, Proclamation of 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Guide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Candidature Files, Paris: Intangible Heritage Section, Divis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UNESCO, 2001.。此外,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承認所產生的影響進行的早期分析,確定了每周故事會、設立講故事有獎競賽、為老的故事講述人設立信托基金以鼓勵他們將自己的技藝傳授給年輕學徒的計劃②UNESC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iority Domains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Impacts of the First Proclamation on the Nineteen Masterpieces Proclaimed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Expert Meeting, Rio de Janeiro, 2002.Document RIO/ITH/2002/INF.。然而,想法是好的,這個基金最終并未設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此提供的資金又退回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日本信托基金③Thomas Beardslee, “Whom Does Heritage Empower, and Whom Does It Silenc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the Jemaa el Fnaa, Marrake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2, no.2, 2016.。另一方面,麥地那地方長官確實采取了以下措施:“拆除了兩棟和廣場的大眾與傳統方面不相稱的建筑,撤走了照明廣告牌,將通往廣場的街道改造為步行街,減少了汽車交通”④UNESC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iority Domains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Impacts of the First Proclamation on the Nineteen Masterpieces Proclaimed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Expert Meeting, Rio de Janeiro, Document RIO/ITH/2002/INF, 2002, p.7.。
因此,維護措施相當于協調努力,以防止變化,確保文化空間安排方式的持久性,并促進相關實踐和表現形式不間斷地延續。地方和國家政府部門的支持為這種協調(必要資源的提供)提供了便利。通過改變馬拉喀什精英階層對這個廣場的看法,通過國際承認增加其價值,遺產與世襲體制的融合吸引上層人士的興趣,并鼓勵他們積極參與保護這一遺產。
這種參與很可能是這些事業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但這是有代價的。這種代價就是本土文化的縱向整合:它融合了官方文化的行政結構,并遵循政策和官僚體制的邏輯。杰瑪·埃爾夫納的項目和有獎競賽提供了一個行政結構以何種方式將本土實踐轉變為政府行動對象的例子。麥地那地方長官采取的行動,拆除杰瑪·埃爾夫納“和大眾與傳統方面不相稱”的建筑,撤走照明廣告牌,演示了這種對行政邏輯的遵循如何服務于將日常風俗博物館化、將生活環境和習慣重塑為遺產。因此,這種干預保留了戈伊蒂索洛反對的廣場與落后的關聯,但遺產語言將落后重塑為真實性。作為真實性的象征,這種“落后”需要維持。實際上,不僅僅是維持,因為它正在積極地被重構——在這個案例中是用推土機和炸藥。
通過保護項目,地方理事會、行政人員、國家機構和國際社會試圖在社會領域采取行動。他們的干預將文化空間轉變為管理民眾的資源,社區可以通過這種資源進行自我監督和改造,從而自己能夠按照已經或將要被訓練的看待這個廣場的方式,即以“一種正當的自豪感”來行事。
這種“外來重視”象征性地將杰瑪·埃爾夫納從一個混亂的典型改造成一個具有活力和馬拉喀什特色的公共劇場。恰如芭芭拉·柯申布拉特-金布利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所言,現存的風俗、習慣、休閑活動和表現形式轉變為“自我表現”,因為通過地方、國家和國際的專家參照官方承認的卓越標準實施的計劃,它們成了保存對象⑤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 Destination Culture: Tourism, Museums, and Herit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p.151.。
培養社區意識
需要說明的是,我并不想給人一種印象,好像這些風俗、表現形式和空間以前沒有受到地方和國家政府的措施和政策的影響。但是,這里的新穎之處是它們對這些風俗和表現形式的直接關注,并通過政府干預來進行保護,以使其免受威脅并繼續存活下去,將其作為文化遺產加以重新塑造。憑借新的社會機構(理事會、委員會、評委會、網絡、組委會、協會),利用各種非物質遺產特有的展示形式(名錄、手冊、競賽、展覽、學校項目,尤其是節日),現有的實踐與表現形式已經成為保護的對象,如杰瑪·埃爾夫納。
在民族音樂學者托馬斯·比爾茲利(Thomas Beardslee)看來,“第一個規模較大、較正式的混合型(協會)……哈爾恰大師協會在2002年緊隨著第一次音樂節而成立,這并不奇怪,部分原因是對音樂節的開銷和預期收益進行集體協商的方式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認定”①Thomas Beardslee,“Questioning Safeguarding: Heritage and Capabilities at the Jemaa el Fnaa”, PhD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14, p.276.。此外,在這個廣場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注的地位后,還成立了幾個規模較小的協會,“專門針對特定的流派或族裔——一個柏柏爾協會,兩個艾薩瓦協會,兩個有各種音樂家及其他表演者的協會,四個格納瓦協會,還有一個故事講述人的協會。大多數海勒奇亞(即表演藝人)都聲稱自己是某個協會的成員”②Ibid., pp.266-267; Thomas Beardslee, 2016.“Whom Does Heritage Empower, and Whom Does It Silenc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the Jemaa el Fnaa, Marrake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2, no.2, 2016; ThomasSchmitt, “Jemaa el Fna Square in Marrakech: Changes to a Social Space and to a UNESCO Masterpiece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as a Result of Global Influences”, Arab World Geographer 8, no.4, 2005, p.187.。因此,正如比爾茲利所承認的那樣,非物質遺產已經在杰瑪·埃爾夫納被證明是一種有效的改造技術,“培養了海勒奇亞日益增長的自認為是一個社區的意識,這個社區是一個比由未群體化的個體構成的人群更容易對政府采取行動和被政府采取行動的群體”③Thomas Beardslee, “Questioning Safeguarding: Heritage and Capabilities at the Jemaa el Fnaa”, PhD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14, p.224.。
“廣場還在那兒”
杰瑪·埃爾夫納如何從推土機的利刃下被救出來的故事,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講述其努力保護非物質遺產的成功故事之一。它經常被當作起源故事來講述——一個因原敘事——在安第斯和日本的因原學之外增加了另一種非物質遺產的起源。1997年的馬拉喀什磋商會無疑是個催化劑;它推進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這一領域中的計劃,并為在促成《宣布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以及后來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談判中加以引領提供了幫助。
作為一個創世故事,它設置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喜歡用來描述自己在這一領域所做努力的登記簿。和其他起源故事一樣,杰瑪·埃爾夫納的敘事宣稱要告訴我們關于其創生對象的基本情況。故事往往以“廣場還在那兒”收尾,作為這個敘事的結局。它確實還在那里;代替了購物中心和停車場,故事講述人和吃玻璃的人仍然在杰瑪·埃爾夫納為群眾表演;占星師和賣水的人仍然在兜售他們的服務。這里有很多聲音,而非一種聲音;不是同一性,而是差異性。地理學者托馬斯·施米特將杰瑪·埃爾夫納的故事描述為“‘地方—全球’成功故事,結局圓滿(至少目前如此)”,他補充說,盡管并不是每個人都會接受這種敘事。“因為禁止在馬拉喀什老城建造高樓很重要”,施米特寫道,“所以一個保護世界各地瀕臨消亡的地方文化傳統的國際公約誕生了。”①Thomas Schmitt,“Jemaa el Fna Square in Marrakech: Changes to a Social Space and to a UNESCO Masterpiece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as a Result of Global Influences”, Arab World Geographer 8, no.4, 2005, p.180.
“廣場還在那兒。”然而,一切都不像以前那樣了。已經發生了一些事情。重要的是要明白保護是一種變革的工具。它改變了人們與其地方和實踐的關系,而這種轉變也影響了地方和實踐本身。廣場還在那兒,但現在食品攤販必須使用帶有傳統外觀和感覺的標準化的四輪車,這是馬拉喀什市政局在2005年推出的懷舊設計②Ibid., pp.188-189; Sandra Bessmann and Mathias Rota, “Espace public de la medina. La place ‘Jemaa el Fna’”, in Etude de terrain. La Gentrification dans la Median de Marrakech , Neuchatel: Université de Neuchatel, Institut de géographie, 2008, p.125.。此外,市政府的專門機構還命令廣場周圍的商店統一店面,使用統一的大型綠色遮陽傘③Marie-Astrid Choplin and Vincent Gatin,“L’espace public comme vitrine de la villemarocaine: Conceptions et appropriations des places Jemaa El Fna à Marrakech, Boujloud à Fès et Al Mouahidine à Ouarzazate, Norois. Environnement, aménagement, société 214, no.1, 2010, pp.26-28. (http://norois.revues.org/3095)。通過十年計劃、地方委員會、每周故事會、比賽、基金和表演者清單,馬拉喀什當局不遺余力地協調差異,將杰瑪·埃爾夫納管理成一個健全的文化空間,其特點是和諧以及色彩、聲音、產品和服務的宜人分布。一個行政網格已經被疊加在廣場上。看不見,摸不著,但效果卻真真切切。城市當局和資產階級社會終于在以前失敗的地方取得了成功:為杰瑪·埃爾夫納帶來了秩序。
說狐貍看守雞舍,也許有點過頭了,但方向并沒錯。在保護這個廣場的同時,他們也改變了它。當然,杰瑪·埃爾夫納仍然充滿忙碌,仍然充斥著售賣、購買、表演、觀看、聆聽、參與或路過的人們④Ouidad Tebbaa, “Le patrimoine de la place Jemaa El Fna de Marrakech: Entre le matériel et l’immatériel”, Quaderns de la Mediterrània 13, 2010.。但是,吞火者和樂師、食品攤位和傳教士現在越來越多地各就其位。隨著表演和服務的分區,混亂讓位于秩序。
1994年,遠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行國際磋商會之前,在戈伊蒂索洛和其他藝術家及知識分子成立“廣場之友”協會之前,民俗學者德博拉·卡普尚(Deborah Kapchan)就開始在這個廣場上展開民族志工作。20年后,她回憶起杰瑪·埃爾夫納被宣布為人類非物質遺產所帶來的變化:“在為改造這個廣場做準備期間,摩洛哥當局將所有的草藥師遷到了廣場的另一個單獨區域;更有甚者,他們被告知要停止其口頭表演。顯然,清理和‘維護’馬拉喀什的杰瑪·埃爾夫納需要對廣場上的角色進行編碼,由于草藥師不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故事講述人、雜技演員或樂師’類別中,他們自己的口頭藝術類型沒有得到承認,最終被壓制。”⑤Deborah Kapchan, “Intangible Heritage in Transit. Goytisolo’s Rescue and Moroccan Cultural Rights”, in Cultural Heritage in Transit: Intangible Rights as Human Rights, edited by Deborah Kapcha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4, p.187.
不止如此。如上所述,為了保護杰瑪·埃爾夫納,麥地那地方長官減少了汽車交通,并在通往廣場的街道上設立了步行街。這些措施聽起來可能對廣場上的表演藝人海勒奇亞有幫助,消除了噪音、氣味和機動車交通的干擾。正相反,事實證明它們是毀滅性的,尤其是對故事講述人來說。早在1985年馬拉喀什的麥地那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時,杰瑪·埃爾夫納廣場上的公交車站就已經搬走了。廣場上仍有出租車候車區,但作為地方長官的措施的一部分,隨著杰瑪·埃爾夫納廣場幾乎封閉了機動車交通,出租車候車區也都搬走了。這改變了廣場的文化空間,但并不像保護計劃所希望的那樣。托馬斯·比爾茲利在采訪杰瑪·埃爾夫納的故事講述人時發現,他們將其行業的衰落歸咎于公共汽車站和出租車站的清除,因為一旦這些被清除,他們也就失去了固定的觀眾來源。①Thomas Beardslee,“Questioning Safeguarding: Heritage and Capabilities at the Jemaa el Fnaa”, PhD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14, p.96.
表面是霸權,下面是統治
2013年,海勒奇亞罷工了。在芬蘭航空公司的機上雜志中,一位記者寫道:“今晚,這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地很安靜。在市鎮廣場的中央,男人們誦唱古代故事的地方現在被寬大的橫幅所占據。標語是用柏柏爾語和阿拉伯語寫的,一個用英語寫的紙板標語概括了抗議者的擔憂:‘杰瑪·埃爾夫納藝人的權利在哪里?’”②Ville Palonen, “Winds of Change over Morocco”, Blue Wings Gift Issue,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30, 2016.(https://issuu.com/finnair_bluewings/docs/blue_wings_10_2013_pieni/19)藝人們有兩個主要訴求:首先,成立一個委員會,調查日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信托基金提供的資金的去向,這些資金本應部分用來幫助支持他們,并確保他們的藝術在廣場上的未來;其次,他們重新獲得對廣場某種程度的控制。他們說,他們現在被限制在5%的地面上,而在市政當局的支持下,食品車和商人則占據了95%的地面。幾天后,在很多游客失望之后,市政府承諾為表演者制定一個福利計劃③Thomas Beardslee, “Whom Does Heritage Empower, and Whom Does It Silenc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the Jemaa el Fnaa, Marrake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2, no.2, 2016, pp.95-99.。
還有一個關于這個廣場的故事值得在此講述。它可能會有助于我們讀懂官員、代表、外交官和專家們在聯合國互相講述的關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馬拉喀什起源的因原敘事:戈伊蒂索洛的靈感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拯救杰瑪·埃爾夫納的成功故事。這個故事將我們帶到表面之下;真的就是在集市下面。這是伊爾哈姆·哈斯努尼(Ilham Hasnouni)的故事,她是2008年參加卡迪·阿雅德大學抗議集會的年輕學生積極分子。大約在2010年阿拉伯之春抗議活動開始在北非蔓延時,哈斯努尼被摩洛哥安全警察逮捕,成為摩洛哥最年輕的政治犯。蒙著眼睛,戴著手銬,她被轉移到了馬拉喀什麥地那,墻內的老城:“我被帶到一個黑暗、潮濕的地下室,在那里過夜。”④Zineb ElRhazoui,“Ilham’s Story: Torture to the Beat of Jamaa al FnaDrums”, Kasama Project, July 29, 2011.一開始她還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但后來她慢慢明白了。透過地下牢房的天花板,她聽見了頭頂廣場上慶祝活動的喧鬧聲、鼓聲和舞蹈的節奏。
那么,這是什么?把非物質遺產當做酷刑的工具?情境就是一切,不是嗎?被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權囚禁的意大利政治理論家和活動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讓我們區分霸權和統治。在他的監獄日記中,他把霸權描述為權力的一種柔性形式,包括道德領導和同意統治,一定程度上通過現代的文化、教育和媒體機構來實現。相反,統治利用武力和武力威脅,一定程度上通過警察和法院等機構。在現代社會中,兩者相輔相成。在拒絕同意的地方,就會使用武力。①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Edi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London: Electric Book, 1999.杰瑪·埃爾夫納證明了現代權力的這兩種形式:表面的霸權,下面的統治。
拯救杰瑪·埃爾夫納的故事是以一種在民俗學分類法中被稱為“因原傳說”(etiological legend)的敘事類型來講述的,“因原傳說”就是一個發生在我們或多或少知道的世界中的故事,它聲稱講述了真相,并描述了仍然可以看到的事物或風俗習慣的起源。通常情況下,因原敘事旨在告訴我們一些關于事物或風俗習慣的本質性的東西;其起源是理解它的關鍵。拯救杰瑪·埃爾夫納的故事通常就是這樣來講的。這是一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圈子里講述的關于這個組織保護非物質遺產的成功故事,它展示了當地有遠見的人和國際專家如何共同努力拯救一個豐富的文化空間和傳統實踐,使其免于被商業驅動的全球化和現代化所湮沒,這里全球化和現代化以購物中心和停車場的形式出現。②想想瓊妮·米切爾(Joni Mitchell)的《大黃出租車》:他們鏟平了樂土/造了個停車場/還有情侶酒店精品店/甚至還有熱舞廳。《山鷹之歌》的故事是另一種因原敘事,也是通過敘述其起源來說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非物質遺產領域所做的努力,為反對剝削地方文化的國際準則辯護。這些故事不僅讓我們(故事講述活動的參與者)了解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遺產計劃的起源,而且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由、一個解釋和一個證明:它們傳達了一個關于什么是文化遺產、它的好處是什么以及如何去保護它的觀點。
有人可能會問:這里的論點是什么?把一個起源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廳的故事,回置到其敘事背景中,一個平淡的結局緊隨最初的決議而至:“廣場還在那兒。”我們已經消解了這一權威性描述的結尾,否定了其最后論斷。我們已經揭示了敘事空間。這是一種強有力的批評形式。正如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一篇關于官僚場域的起源和結構的文章中所認為的那樣,“沒有比起源的重構更有力的撕裂工具了:通過重思最初的沖突與對抗和所有被拋棄的可能性,它找回了事情本來可以(而且仍然可能)是另一種樣子的可能性。”③Pierre Bourdieu,“Rethinking the Sta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Bureaucratic Field”, Sociological Theory 12, no.1, 1994, p.4.
可以說,我們已經強烈建議哈爾恰用故事來反駁故事。除了在聯合國的會議室、走廊和出版物中流傳最廣的故事之外,還有其他故事。這些故事相互之間有關聯。畢竟學術批評的核心任務是:增加情境;講述其他故事;用復雜反對簡化;用差異、可能性和替代性來充盈同質性和秩序。本文其余部分將杰瑪·埃爾夫納的教訓置于更廣泛的理論和比較情境中,將非物質遺產作為變革的工具進行研究,并思考那些被認定為非物質遺產的實踐和被認定為社區(遺產的對象和主體)的社會集體之間的關系。
衰退、消亡和毀滅
早在1997年的馬拉喀什磋商會之前,早在1992年日本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之前,甚至早在1973年玻利維亞寫信之前,就有人試圖在國際層面上保護民俗,這與聯合國講述起源故事的敘事傳統背道而馳。最初相互配合為民俗提供國際法律保護的嘗試,是1967年在斯德哥爾摩和1971年在巴黎召開的旨在修訂《伯爾尼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公約》的外交會議上。此外,早在1971年——在收到玻利維亞的信前兩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行政人員就編寫了一份題為“建立一個保護民俗的國際文書的可能性”的研究報告①UNESCO, “Pos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an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Folklore”, Document B/EC/IX/11-IGC/XR.1/15, 1971.。這個文件沒有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但強調民俗的狀況正在“急劇惡化”,并堅持認為進一步努力保護民俗是“最緊迫的”②Samantha Sherkin,“A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1989 Recommenda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 in Safeguarding Traditional Cultures. A Global Assessment, edited by Peter Seitel,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Folklife and Cultural Heritag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01, p44.。
這種緊迫感推動了半個世紀的國際談判,但它有更久遠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歐洲啟蒙運動和地理大發現這兩個時代。自從醫生和牧師開始在歐洲鄉村記錄“粗俗的錯誤”并試圖消滅它們,自從傳教士和殖民官員記錄他們用文明加以教化的殖民地民眾瀕臨滅絕的風俗,大眾傳統的急劇衰退就已經成為這個概念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好是壞,民俗及其同義詞從來沒有完全擺脫衰落和瓦解的隱含意義,而這種危急時刻的警報總是在研究和政策辯論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③Pertti J. Anttonen, Tradition through Modernity. Postmodernism and the Nation-State in Folklore Scholarship, Helsinki: Finnish Literature Society, 2005; Richard Bauman and Charles L. Briggs, Voices of Modernity.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eq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 “Topic Drift: Negotiating the Gap between Our Field and Our Name”,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33, no.3, 1996; Alan Dundes, “The Devolutionary Premise in Folklore Theory”, Journal of the Folklore Institute 6, 1969.。
除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檔案很少提及的1967年和1971年提出的倡議,更廣為人知的1973年玻利維亞政府提出的要求,似乎是將民俗列入國際議程的主要催化劑。經過幾十年的商討之后,參閱1973年的信件,令人驚奇地發現,盡管有數百次專家會議、研討會、圓桌會議、磋商會和團隊實地調查,工作仍非常緊密地按照信中的構想展開,問題也幾乎沒有什么改變。“商業主導的文化移植(transculturation)過程”仍然被認為是一個需要國際社會立即關注的重大威脅,盡管如今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談論這個問題。因此,《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部分理由是其前言所提到的:“在為社區之間開展新的對話創造條件的同時,全球化和社會變革的進程也與不能容忍的現象一樣,導致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衰退、消亡和毀滅的嚴重威脅,在缺乏保護資源的情況下,這種威脅尤為嚴重”。盡管在其限定條件中存在明顯的妥協,這段話仍然描繪了一幅衰退、消亡和毀滅的不祥圖景。過去的幾十年里,這些威脅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所有工作中十分突出,正是通過這些工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得以形成。一般來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內部任何關于非物質遺產的檔案、辯論或展示,都會一次或多次提到全球化及其破壞性影響。
這種危機感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話語中的非物質遺產觀念蒙上了陰影。事實上,全球化的威脅始終與非物質遺產聯系在一起,以至于它似乎是這個概念固有的。在這一點上,這個與緊迫的涵義相伴的概念總是與民俗和大眾傳統聯系在一起,但增加了明顯的全球色彩。事實上,非物質文化遺產似乎永遠處于毀滅的邊緣。
迫在眉睫的威脅為干預提供了理由。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員國的文化部長們在2002年伊斯坦布爾舉行的一次高層會議結束時所宣稱的那樣,“非物質遺產的極度脆弱性……要求各國政府采取果斷行動”④Istanbul Declaration-Final Communiqué, UNESCO. Third Round Table Meeting of Ministers of Culture, September 17, 2002. (http://portal.unesco.org/en/ev.php-URL_ID=6209&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文化和治理術
2003年6月,作為冰島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團成員,我觀察了擬訂《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政府間專家會議第三次會議。在下文中,我使用了這次會議上的爭論,以及訪談與檔案資料。我將其與遺產和治理術(governmentality)的理論并置,認為通過社區來協調分歧和進行治理是這個公約的核心目標。
當然,重要的是記住,盡管被選中的傳統實踐和表現形式受到嘉封(canonized),人們繼續以“與受到嘉封的文化寶庫關系不大,有時甚至是顛覆它們”的方式,重新加工其余的文化表征,并創造新的文化表征。正如民俗學者巴爾布魯·克萊因(Barbro Klein)所指出的:“民俗通過日常生活中源源不斷的創造性重塑而存在,同時它也被用于很多政治的及相關的目的”①Barbro Klein,“Cultural Heritage, the Swedish Folklife Sphere, and the Others”, Cultural Analysis 5, 2006, p.69.。然而,擴大的遺產范圍,延伸到非物質和大眾的領域,將這種邊緣性的實踐(即相對于主流文化的邊緣)重新界定為文化政策和管理的對象。雖然這種擴大的范圍可能更民主,但這種“邊緣化的美學”②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Mistaken Dichotomies.”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01, no.400, 1988, p.149.也重新規劃了治理的領地,將治理進一步延伸到民眾的習性和生境(habitus and habitat)③Henry Collins,“Culture, Content, and the Enclosure of Human Being. UNESCO’s‘Intangible’ Heritage in the New Millenium”, Radical History Review 109, 2011.。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這一領域工作的歷史,在其他地方也有記載。在20世紀90年代,這些努力從歐洲譜系的檔案范式中轉移出來。建檔和研究提上議程,代際傳承成為新的優先事項——試圖確保傳統的連續性。日本和韓國的“人間國寶”與“非物質遺產”的法律保護計劃(在日本1950年以來和韓國1962年以來的書中)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這一領域的活動提供了新的藍圖。從這一范式的轉變開始,1993年出現了所謂“人類活財富”計劃,1997年通過了《宣布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④Peter J. M.Nas, “Masterpieces of Oral and Immaterial Culture: Reflections on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List”, Current Anthropology 43, no.1, 2002.,最終于2003年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⑤Chiara Bortolotto,“Il processo di definizione del concetto di ‘patrimonioculturaleimmateriale’: Elementi per unariflessione”,in Il patrimonioimmateriale secondo l’Unesco. Analisi e prospettive, edited by Chiara Bortolotto, Rome: IstitutoPoligrafico e ZeccadelloStato, 2008.。
20世紀90年代的范式轉變意義重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目標不再是維護表演的文本或音像記錄,而是維護表演的有利條件——社會肌體和生境,并激勵代代相傳。確保人們明天還能繼續唱他們的歌與把他們今天唱的歌歸檔,是非常不同的任務。
政府巧妙地介入本土實踐——以前只是行政人員偶然感興趣的實踐,導致對公共生活的更大監管。實際上,干預非物質遺產所做的,是創造對民眾采取行動的機制——與其說是自上而下地直接形塑他們的行為,不如說是影響民眾,使其主動改變自己的行為。在這一點上,遺產與以往在自由的治理中藝術和美學的使用相似。歷史地看,它們是讓個人成為自己轉變和自我管理過程中的積極行為者的工具⑥Tony Bennett,“Acting on the Social: Art, Culture and Governmen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3, no.9, 2000, p.1415.。同樣,非物質遺產為政府提供了一種既干預社會生活管理又與其保持一定距離的手段。
我在這里的論點得益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出版的大量著作,這些著作圍繞“治理術”的概念構成了一個研究領域。借鑒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78年的《論治理術》一文,本文關注用福柯所說的“行為引導”來進行治理的理由和技藝。這種“遠距離治理”①Nikolas Rose, Powers of Freedom. Reframing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49.是18世紀和19世紀出現的自由主義政治形態的特征。與其他支配形式相比,自由主義并不謀求瓦解其統治對象的行動能力,而是承認這種能力并對其采取行動。行為引導發生在成千上萬的分散的點,需要大量的技術和程序來將政治中心的議程與那些分散地點聯系起來,在這些分散地點,權力的運轉與民眾及其風俗、信仰、健康、衛生、安全和繁榮相聯系。
福柯把這種程序和技術的增加稱為國家的治理化(governmentalization)。它鼓勵相應增加獨立權威組織和專家(人口學者、社會學者、民俗學者、人類學者、醫生、心理學者、經理、社會工作者等等)以及與民眾有關的知識領域和專門技能。它還取決于使政治目標和專家策略保持一致的方法,以及在權威組織的籌劃和自由公民的愿望之間建立溝通渠道。
20世紀90年代,治理化的觀點被引入民俗學、人類學和文化研究中,并在文化政策的批評性分析中取得了特別豐碩的成果。事實上,很多行為引導的技術,都屬于通常所說的“文化”。托尼·貝內特(Tony Bennett)認為,得益于治理理論,我們有能力超越美學的和人類學的這兩種文化概念,將文化理解為一套服務于特定社會目標的獨特工具。從這個角度看,作為一個概念和范疇,文化是伴隨著政府支配形式而產生的一種歷史形態。它建構了一個以前被認為不相關的實踐之間的關系復合體,由此形成了一個新的有效的實在②Tony Bennett, “Culture and Governmentality”, in Foucault, Cultural Studies, and Governmentality, edited by Jack Z. Bratich,Jeremy Packer and Cameron McCart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p.58.。恰如“社會”和“經濟”已經逐漸被視為從以民眾為對象的政府支配形式中產生的歷史形態,貝內特展示了如何“文化制度也可以被看作是由一系列特殊的專門技能形式組成的,這些專門技能形式產生于獨特的處理實況的制度,這種制度通過管理‘行為引導’的各種程序,表現為一系列實踐和技術形式”③Ibid., p.56.。
人們習慣于按照文化概念的大眾性外延來說明文化的“人類學”意義的盛行,即作為早期的文化制度,文化是生活的整體方式,是“世界上被認為和被知道的最好東西”④Matthew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in Cultural Theory & Popular Culture. A Reader, edited by John Storey, 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8, p.8.。然而,貝內特認為,當文化被歷史地理解為作用于社會的工具時,“這種發展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即作為生活方式與治理范圍相融合和由此產生文化與社會之間的結合點的結果”⑤Tony Bennett, “Culture and Governmentality”, in Foucault, Cultural Studies, and Governmentality, edited by Jack Z. Bratich,Jeremy Packer and Cameron McCart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p.59.。民俗也可以以同樣的方式理解為,作用于特定人群(農民、民、“人民”、庶民)之習性和生境的工具的一部分或一套與之類似的工具,或者反過來說,“任何一個至少有一個共同因素的人群”,可以圍繞著這個共同因素組織起一種認同感⑥Alan Dundes, The Study of Folklor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5, p.2; “Who Are the Folk?” in Frontiers of Folklore, edited by William Basco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77.。
遺產和社區
按照芭芭拉·柯申布拉特-金布利特的說法,將“遺址、建筑、物品、技術或生活方式”作為遺產加以再利用,就是賦予這些東西新的生命,并非是作為它們曾經所是,而是作為自己的表征①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 Destination Culture: Tourism, Museums, and Herit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p.151.。因此,給一種實踐或一個遺址貼上遺產的標簽,與其說是一種描述,不如說是一種干預。我們必須認識到文化遺產是一個治理領域,正如蒂姆·溫特(Tim Winter)所強調的那樣:“它出現在現代時期,涉及對空間、民眾、文化和自然、物質世界以及時間的治理。”②Tim Winter, “Heritage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1, no.10, 2015, p.998.事實上,遺產重新安排了人與物、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參照其他被認定為遺產的遺址和實踐,將它們客觀化和再情境化。遺產將以前互不相關的建筑、儀式、繪畫和歌曲集合在一起,并將它們作為需要保護的東西來對待,也就是說,按照專家執行和評估的程序、計劃和策略來采取行動,將當局的籌劃與公民的愿望和雄心聯系在一起。
在接受《世界遺產通訊》采訪時,國際文化財產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的約瑟夫·金(Joseph King)指出:“遺產保存可以成為非洲大陸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即使在“那些面臨更嚴重問題的地方”,他接著說,“文化遺產的保存也可以在改善這種狀況方面發揮作用(即使很小)。”③“AFRICA 2009: Interview with Joseph King of ICCROM”,World Heritage Newsletter, no.32, 2001, p.2.金和國際文化財產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建筑保存計劃負責人尤卡·約基萊赫托(Jukka Jokilehto)在他們就非洲語境下真實性與保存標準合撰的《對當前理解狀態的反思》一文中,更詳細地解釋了這一點。他們在文中澄清說,不可能“總是強調把傳統的生境作為‘冷藏的實體’延續下去”,因為“如果民眾對此不理解,強調保存傳統的生活方式有時可能會被認為是一種傲慢”。他們接著說,因而問題是“如何控制和指引生活方式的這種改變”。對此,他們竭力主張“應該給現在的社區以一切機會來理解和尊重從前幾代人那里繼承下來的東西”。他們解釋說:“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可能需要激勵和榜樣,尤其需要建立在民眾和當局密切合作的基礎上。”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目標是“確定如何產生一種渴望這種遺產并因此關心其保護的文化進程”④Jukka Jokilehto and Joseph King, “Authenticity and Conserv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Understanding”, in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in an African Context: Expert Meeting—Great Zimbabwe, Zimbabwe, 26-29 May 2000, edited by Galia Saouma-Forero, Paris: UNESCO, 2001, p.38.。
這些趨勢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作為一種工具的遺產制造和保護如何在社會領域發揮作用,“控制和指引生活模式的改變”,并“產生一種文化過程”。它們還強調,遺產既是一個教學工程,也是一個變革的過程。它改變了民眾與其實踐之間的關系,并因此改變了他們彼此之間的關系(以這些實踐為媒介)。通過呼吁他們的公民義務和道德責任,以保持過去和現在之間的一種特殊的一致,在這種一致中投入強烈的情感和認同,來實現這一點。正如威廉·馬扎雷拉(William Mazzarella)所言:“任何不只是靠武力強加的社會工程,都必須是情感的才能達到預期效果。”⑤William Mazzarella,“Affect: What Is It Good For?”in Enchantments of Modernity: Empire, Nation,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Saurabh Dube, London: Routledge, 2012, p.229.在這個意義上,遺產是一種作用于社會、引起行為改變的技術。
200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松浦晃一郎(Koichiro Matsuura)在介紹第一批《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名錄》時宣布,他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份旨在提高我們活態遺產的知名度的名錄,將有助于提高對其重要性的認識,并使作為守護者的社區產生自豪感和歸屬感”①UN News Centre,“UN’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 Comes into Being with 90 Entries”, November 4, 2008.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 NewsID=28812#.WeNtAlu0PIU)。比較一下本文開頭胡安·戈伊蒂索洛的話:“我們正在嘗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決定將幫助我們)改變許多馬拉喀什自己的居民看待廣場的方式,以使他們有理由感到自豪”。因此,名錄所帶來的國際承認的威望,旨在引起作為其自身遺產繼承者和守護者的社區的自我認可。應該使民眾產生擁有遺產和關心遺產的愿望;管理他們自己的或當地其他民眾的實踐。
過去與現在的結合是產生“渴望這種遺產”的文化進程的核心。再次引用柯申布拉特-金布利特的話:“擁有遺產——相對于遺產保護的生活方式,是現代化的工具和現代性的標志”②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World Heritage and Cultural Economics”, in Museum Frictions: Public Cultures/Global Transformations, edited by Ivan Karp and Corinne Kratz,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83.。通過將特定地方和實踐圈定為與一個文化傳統或一段歷史性過去保持連續性的場所,其他一切實際上就被與該傳統或歷史切割開來。繼承標志著遺產具體化的社會關系的消亡;它預示著過去和現在的激進斷裂。因此,擁有遺產就是現代的;這是一種與過去聯系的現代方式。這個“過去”在遺產地中被賦予物質形式,并在非物質遺產中表現出來,不可避免地成為認定、管理和代表它的現在的產物③見 Regina Bendix,“ Heritage between Economy and Politics. An Assess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in Intangible Heritage, edited by Laurajane Smith and NatsukoAkagawa, London: Routledge, 2009等。。
從歷史上看,遺產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創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共同擁有的遺產,古跡、景觀和民俗被賦予了國家象征,將政治想象力集中在國家共同體的特定表征上④見PerttiJ.Anttonen, Tradition through Modernity. Postmodernism and the Nation-State in Folklore Scholarship, Helsinki:Finnish Literature Society, 2005;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1991等。。文化和自然財富的確認傳達了一種共同責任感,即把它們傳承給植根于特定領土的集體的未來。這種共同責任催生了一系列國家機構,包括公園、檔案館和各種各樣的博物館。這些新的機構需要有自己的專職人員和自己的專業知識形式;它們是根據一個跨國傳播的模版建立起來的,承擔的任務是改造公民,為他們提供指導,并培養他們對國家共同體的責任和忠誠意識⑤Tony Bennett,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5; “Cultural Policy: Issues of Culture and Governance”, in Culture, Society, Market, edited by Folke Snickars, Stockholm: Bank of Sweden Tercentenary Fund/Swedish National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2001.。
遺產仍然是代表國家、圍繞著共同身份認同和歸屬感來凝聚公民的重要工具。出于這種目的而對民俗加以利用,已在廣泛的語境中得到記載⑥見 Roger D.Abrahams,“Phantoms of Romantic Nationalism in Folkloristics”,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06, no.419,1993;Pertti J.Anttonen, Tradition through Modernity. Postmodernism and the Nation-State in Folklore Scholarship, Helsinki: Finnish Literature Society, 2005等。。然而,因為離散和跨界社區的激增,以及區域認同和本土民眾的重新興起,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難想象國家的單一文化。現代國家主體的強調伴隨著付出代價:它掩蓋了差異性;要求通過有選擇的遺忘、以犧牲其他忠誠為代價,來忠于統一的國家文化和歷史。
在移民劇增、差異明顯的情況下,文化遺產一下子無處不在,這絕非偶然①見 Jeroen Rodenberg and Pieter Wagenaar,“Essentializing ‘Black Pete’: Competing Narratives Surrounding the Sinterklaas Tradition in the Netherland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2, no.9, 2016等。。文化遺產創造了一個可以討論社會變遷的漫談空間,并為討論它們提供了一種特殊的語言②見 Barbro Klein,“Cultural Heritage, the Swedish Folklife Sphere, and the Others”, Cultural Analysis 5, 2006;ólafur Rastrick,“Menningararfur í fj?lmenningarsamfélagi: Einsleitni, fj?lhyggja, tvíbendni”, in Triejaíslenskas?gutingie 18.-21. maí 2006: Ráestefnurit,edited by Benedikt Eytórsson and Hrafnkell Lárusson, Reykjavík: Sagnfr?eingafélagíslands, 2007.。它使人們能夠表達自己對其歷史和認同的理解。但同時,遺產的術語也是一種權力機制:它通過界定什么樣的東西是有意義的來限制表達。
也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政治變革中,民俗(現在打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幌子)再次被工具化,就像19世紀和20世紀民族主義興起時那樣。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政府開始承認甚至提倡將“社區”作為文化和行政單位。雖然這樣的社區意味著民族-國家工程的滑坡效應(slippery slope),但一種新的治理理性形式正在出現,它側重于“組織自我調節和自我管理的社區,這些社區在某些方面與國家界定的社會的更大整體相脫節,或者在離散社區的情況下跨越它們”③Tony Bennett,“Acting on the Social: Art, Culture and Governmen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3, no.9, 2000, p.1421.。
社會學者尼古拉斯·羅斯(Nikolas Rose)認為,通過社區進行治理是自由政府的一個重要轉變④Nikolas Rose, Powers of Freedom. Reframing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它意味著重點從社會中的個人轉向社區,將社區作為個人效忠的中介實體,并通過社區進行改造和管理自己。這種轉變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從平民運動和人權運動中出現的新形式的認同政治以及離散的移民和新發現的本土群體的聲音。然而,這也與經濟和文化全球化進程以及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廣密切相關,這種政策的推廣是通過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執行的貿易協定和援助計劃而實現的。
這種進程和政策使談論新興的全球治理或國際關系的治理成為可能,在這種治理中,國家的作用越來越小,而跨國的組織、公司、聯盟和移民組織則不斷承擔更大的責任。把責任委托給公民是新自由主義政治工程的一個方面,將個人融入他們自己的治理,賦予他們在社區中個人性地或相互地引導自身行為的責任⑤Arnar árnason and Sigurjón Baldur Hafsteinsson, Death and Governmentality in Iceland. Neo-Liberalism, Grief and the Nation-Form, Reykjavík: University of Iceland Press, 2018.。這個轉變還以各種形式體現了“第三條道路”政治的特點;第三條道路的政治家們將社區確定為國家與個人之間的“第三空間”,將這個空間視為一個解決方案,以解決國家過度干涉公民生活以及過度個人主義帶來失范和不安全感的問題。
在從地方到國際的各個層面的治理中,我們看到這種對社區的新的強調,社區被視為使集體存在具有意義并使其可籌劃和可管理的一種創新方式。在過去的25到50年里(始于不同的時間和地點),特別是最近的10年里,“一系列小裝置和小技術已經被發明出來,使社區成為現實”⑥Nikolas Rose, Powers of Freedom. Reframing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89.。在相當短的時期內,一種新類型的專門知識迅速涌現,通過這些專門知識,“社區”(最初作為一種抵抗的語言)已轉變為“專家話語和專門職業”⑦Ibid., p.175.。正如羅斯所指出的,“社區現在是由社區發展方案來規劃的,由社區發展官員來發展的,由社區警察來管理的,由社區安全方案來保護的,由從事‘社區研究’的社會學者使其變得為人所知的”⑧Ibid., p.175.。
我們可以在這個名單上加上很多社區遺產的機構和項目:社區博物館、社區檔案館、社區遺產節、社區遺產登記簿、社區遺產中心、社區遺產委員會和社區遺產撥款。同時還有大量的專家和專業人士,如社區策展人、社區遺產專員、社區歷史學者、社區民俗學者、社區展覽設計師和社區遺產發展官員。這種趨勢不僅限于公共部門;過去幾十年來,這一領域的公私合作種類繁多,隨之而來的是跨學科咨詢公司的大量涌現,比如賓夕法尼亞州的社區遺產合作伙伴,他們幫助“業主、地方政府和社區組織制定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以維護和更新其建筑遺產,加強其社區特色,提高其生活質量”。他們不滿足于僅僅提供維護方面的技術支持,還“制定社區參與和私人倡議的策略,以提高認識和改變態度”①Community Heritage Partners, “Building New Life for Old Places”. (http://www.chpartners.net)。
社區的任何主張都是指已經存在的、我們應該效忠的東西。然而,對社區的忠誠是我們需要意識到的東西,需要“教育者、運動者、活動家、(以及)符號、敘事和確認的掌控者的工作”②NikolasRose, Powers of Freedom. Reframing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77.。正如托尼·貝內特所言,因為在治理概念中的核心作用,“社區不斷地從其即將消失的狀態中被拯救出來,或者,因為對社區的認知需要往往先于社區的存在,社區不斷地被組織起來”③TonyBennett,“Acting on the Social: Art, Culture and Governmen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3, no.9, 2000, pp.1422-1423.。
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個共同遺產被用來建立國家共同體一樣,共同遺產也是地方的、原住民的和離散的社區的核心。遺產和文化政策的社區化有助于形成和改造民眾群體,并協調國家內部的差異。這是一種應對差異的策略。從這個角度看,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種工具出現在社區成員產生強烈的(但不是排他的)歸屬感的過程中。民眾群體將自己主體化為“社區”,并將自己的實踐與表現形式對象化為“非物質遺產”。如此一來,政府就可以通過社區并利用非物質遺產政策等手段在社會領域采取行動。
這與環境保護的發展相類似。在環境保護中,社區受到普遍關注,大量的方案將落實環境政策的責任交給社區。政治學者阿倫·阿格拉瓦爾(Arun Agrawal)創造了“環保術”一詞來描述這種治理理性,在這種理性中,社區被詢喚(interpellated)為“環境主體”④Arun Agrawal,“Environmentality. Community, Intimate Government, and the Making of Environmental Subjects in Kumaon,India”, Current Anthropology 46, no.2, 2005.。人們學會將他們的生境視為“環境”,認識到保護環境的必要性,并通過專業知識的注入和與國家、非政府和政府間組織的合作,負責管理他們自己和他們的環境實踐⑤例如,Arun Agrawal and Clark C. Gibson, The Role of Community in Natural Resource Conservation, in Communities and the Environment. Ethnicity, Gender, and the State in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edited by Arun Agrawal and Clark C. Gibson,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1等。。遺產保存的當代方法也可以用類似的詞語來描述,我們可以說是一種世襲的治理術,或者“世襲術”(patrimoniality),它將個人和民眾詢喚為“世襲的主體”,教導他們從遺產的角度來想象他們的一些實踐和物質文化,認識到保護它們的必要性;并且通過與國家、非政府和政府間組織及專家的合作,將它們引入到一種世襲體制中。
誰的遺產?
與名錄的熱點問題很像,在擬訂《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專家會議上,對社區、社區在國際公約中的適當地位以及社區與國家和政府間組織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當然,會員國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通過社區來進行管理的問題上存在分歧,官方文化和少數群體文化之間的關系在不同的國家也有不同的結構。事實上,在2003年6月于巴黎豐特努瓦廣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舉行的第三次會議上,除了創建名錄外,社區也是最富有爭議的問題。匈牙利代表比任何人都更主張公約中社區的權利,主張需要和社區與非政府組織進行最大限度的協商。他利用一切機會這樣做,而在本次會議上擬訂并通過的幾個條款特別是關于國家一級保護的各項規定(最終文本的第11-15條)時,機會也就來了。然而,他的立場一點也不孤立;瓦努阿圖、巴布亞新幾內亞、津巴布韋、秘魯和芬蘭的代表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這個問題在以前的會議上已經辯論過,在6月會議的第一天又很快提了出來。分發給各代表團的公約草案初稿(第4條)指出:“各締約國承認有義務保護它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會議伊始,匈牙利代表就舉起了牌子,說道:“‘它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存在于其領土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有區別的。不是國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它不是由國家創造的,而是由社區和群體創造的。這是原則問題!”
這里的重點是關于想象社區和定位文化的不同方式,匈牙利的原則認為,這些方式與國家并非同構關系,盡管國家對其境內的社區負有責任。對此,南非代表警告說:“‘存在于其領土內的’一語會引起許多問題”,并請求委員會保留“它的”一詞。
巴布亞新幾內亞代表緊隨其后,反對國家的遺產這種觀念所假定的同質性:“我們不是談論‘我們國家的遺產’,而是談論我們領土內的不同文化。我們反對國家的文化遺產這種觀念。因此,我們支持使用‘存在于其領土內的’一語。”
其他幾個代表團表示傾向于這兩種說法中的一種,然后被智利代表打斷,他提出了同時使用兩種說法的荒謬建議:“保護它的存在于其領土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也許最好把這一建議理解為故意誤讀的例子——這并非一個罕見的外交手段,因為它清楚地保留了國家自身的遺產的觀念,并使“存在于它的領土內的”這一限定詞多少有些多余(或者說將其從包含的意義改為限制的意義)。
關于物主代詞的這一辯論,是聯合國各組織跨國建立協商一致過程中經常出現的典型現象。我在日內瓦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中觀察到了同樣的曲折過程。此外,人類學者薩莉·恩格爾·梅里(Sally Engle Merry)描述了紐約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中類似的辯論,正如她所指出的:“雖然關于措辭的辯論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它們以微妙的方式揭示了政治分歧。”①Sally Engle Merry,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Violence: Translating International Law into Local Just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p.40.談判術語——爭論代詞的使用,是聯合國規避不可調和的分歧、以迂回的方式達成協商一致的方法。很容易同意梅里的觀點,即令人印象深刻地看到“盡管來自世界各國的人們存在分歧,但仍試圖拼湊出一些每個人都能接受的詞語”②Ibid., p.47.。
可想而知,對強調與社區協商提出最強烈批評的,是那些引人注目的族裔和少數文化群體對國家壟斷社區道德資源構成嚴重挑戰的國家,如俄羅斯、土耳其、印度和西班牙。雖然它們沒有說出具體的關切,但這些國家明顯不愿意在一個公約中作出國際承諾,因為可以想象,這可能會被諸如高加索地區的車臣人和印古什人、庫爾德斯坦的庫爾德人、印度東北部的阿薩姆人和哈西人,或加泰羅尼亞的加泰羅尼亞人和歐斯卡迪的巴斯克人等等,用作分裂主義、煽動叛亂或少數文化群體權利斗爭的工具。
在回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0年的一份調查問卷(關于1989年《保護民間文學和傳統文化的建議》的適用情況)時,西班牙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員會強調,西班牙的立法“不允許在‘傳統社區’和‘文化少數群體’兩詞之間有任何概念上的混淆”。根據西班牙法律,文化少數群體不受特別保護,但它對培育和促進傳統社區的實踐作出了規定①JanetBlake, Developing a New Standard-setting Instrument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lements for Consideration, CLT-2001/WS/8, Paris: UNESCO, 2001, p.43.。這種法律敏感性是分類學在政治上應用的一個發人深省的例子,它不支持保護國家領土內所有社區的文化遺產以及讓社區積極參與決策和保護的國際義務。
相反,在某些情況下,同樣明顯的是強調與社區的協商及其在公約中的作用。例如,最直言不諱地捍衛社區權利的匈牙利,也有自己的小算盤。匈牙利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戰敗,隨之而來的歐洲地圖的變化,使匈牙利族裔分散在九個鄰國: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塞爾維亞、烏克蘭、俄羅斯、奧地利、克羅地亞、捷克共和國和斯洛文尼亞(按重要性排序)。毫無疑問,這些匈牙利的文化少數群體的地位是匈牙利當局非常關注的。因此,150萬匈牙利后裔占特蘭西瓦尼亞人口的三分之一,特蘭西瓦尼亞是奧匈帝國的一個省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歸羅馬尼亞所有。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羅馬尼亞當局將他們視為難以駕馭的少數族裔,并試圖通過所謂的羅馬尼亞化政策來同化他們(包括強迫搬遷、重新分配工作與合并學校等)。關于這一少數族裔的爭議,是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政府之間長期敵對的根源。
本著妥協的精神,6月的會議向與會者分發的公約草案初稿第5條規定:“各締約國應努力盡可能以在整體的國家生活的情境中豐富文化多樣性的方式”,在國家層面上采取若干保護措施。②UNESCO,“Intersessional Working Group of Government Experts on the Preliminary Draft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ocument CLT-2003/CONF.206/3, Paris: UNESCO, 2003, Appendix 2,7.這段冗長難解的話不僅兩次消除了“應”(用“努力”和“盡可能”)的義務,還規定了履行這一義務的方式應符合國家多樣性統一的觀點。這一規定最終被刪除,但并非沒有經過激烈的辯論。正如會議主席穆罕默德·貝賈維(Mohammed Bedjaoui)大使③2005年出任阿爾及利亞外交部長。在會議第一天所解釋的那樣:“今天沒有出席會議的印度大使在前幾次會議上一再堅持并爭取使用‘以在整體的國家生活的情境中豐富文化多樣性的方式’一語,當然,印度是一個文化非常多元的國家,有很多東西需要平衡。”
當然,很多保護、傳承、振興和促進傳統實踐與表現形式的方式,并沒有將其置于“整體的國家生活的情境中”。僅舉印度東北部各邦的一個例子——這里是一個族裔社區紛爭的大熔爐,有許多反對新德里政府統治的叛亂運動,民俗學者德斯蒙德·卡瑪弗朗(Desmond Kharmawphlang)在《印度民俗生活》(Indian Folklife,印度國家民俗支持中心的通訊)中講述了叛亂分子如何從他家中劫持了一位親密的同事,并將其帶到一個由卡西族叛亂群體控制的秘密訓練營。“他們讓他在那里呆兩個星期,”卡瑪弗朗講道,“讓他談卡西族的民俗,以便在骨干中激發某種團結。”④Desmond Kharmawphlang, ArupjyotiSaikia, LaltluangianaKhiangte and Chandan Kumar Sharma, “Conversation 2: Folklore and Identity,”Indian Folklife: A Quarterly Newsletter from National Folklore Support Centre 3, no.2, 2004, p.19. (http://www.indianfolklore.org/publications_news.htm)
反過來說,民俗培訓在很多情況下也有助于提高對國家統一的忠誠并激勵其軍隊。舉例來說,1999年頒布的《立陶宛國家保護民族文化原則法》(2006年修訂)規定“國防部與教育和科學部應將民族文化納入軍事人員培訓和愛國主義教育的方案中”①WIPO Lex,“Lithuania: Law on the Principles of State Protection of Ethnic Culture VIII-1328 of September 21, 1999 (as amended on January 9, 2006)”, WIPO Lex No. LT042, 2010, art. 9, para.8.(http://www.wipo.int/wipolex/en/details.jsp?id=5572) 該法第 2條第4款將民族文化界定為“整個國家創造的、代代相傳并不斷更新的文化財產的總和,它使維護國家認同以及民族地區的意識和獨特性成為可能”。。國家保護民族(或傳統、民間)文化,包括其軍事方面和愛國主義教育的內容,在一個擁有大量波蘭、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少數群體的小國,不容小視,在這個國家,立陶宛族裔僅占包括首都維爾紐斯在內的維爾紐斯自治區人口的32.5%左右(但占維爾紐斯市人口的63%,占全國人口的83%)②Statistics Lithuania,“2011 Census”, 2013.(https://osp.stat.gov.lt/en_GB/pradinis)。事實上,該法的前言認為,其必要性是基于“這個事實,即民族文化是國家存在、生存和壯大的本質,而立陶宛各種形式的民族文化,特別是其活態傳統顯然有消亡的危險”③Ibid.。
回到豐特努瓦廣場的會議室,貝賈維竭力主張會議保留“以在整體的國家生活的情境中豐富文化多樣性的方式”這句話,而不是“利用印度缺席的機會,一舉刪除它”。不過,韓國和法國建議刪除這句話,以使文本更簡短、更清晰,因為正如法國代表所說,“這是一份法律文件,幾代年輕律師都將對其進行解釋。”他緊接著補充說,“沒有人會懷疑法國不支持文化多樣性”,但“整個公約都是關于文化多樣性的;為什么要在一個條款中而不是在另一個條款中說呢?”智利代表表示同意,并建議在公約的前言中插入關于文化多樣性的說明。然而,洪都拉斯代表說,他支持目前的條款,特別是相關措辭。此外,土耳其代表堅持認為,“應該保留我們正在討論的這句話”,因為“它會在社區內部促進對其他社區和群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寬容”(而且“我們也應該對印度表示一些尊重,即使他們沒來”)。
有人對“整體的國家生活”與國家在該條款中所承擔的義務之間的相關性提出了疑問,一些代表顯然對這一說法感到有點不適。對此,多米尼加共和國代表坦率地建議委員會不要再用含糊的措辭回避問題,而應公開使用“民族-國家”一詞,因為這顯然就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生活”的意思。“哦不”,貝賈維主席連忙反駁道,“‘民族-國家’是一個爆炸性的詞!”“如果我們說‘民族-國家’”,他接著說道,“政治學者會干掉我們的!”
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最終文本中,締約國承擔的(有條件的)義務是,在國家層面保護活動的框架下,“努力確保創造、延續和傳承這種遺產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最大限度的參與”“并吸收他們積極地參與相關管理”(第十五條)。
主權、領土、社區
乍一看,這場辯論似乎與非物質遺產的主題相去甚遠。然而,盡管表面如此,實際上卻直接道出了由遺產及其保護所構成的各種干預——它在社會行動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方式。無論是社區參與這種干預的程度和方式,還是強加給表達的條件,都與文化社區的傳統實踐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被選擇、促進和保護的方式沒有直接關系。這些都是影響遺產如何被用來想象社區、構建忠誠、引導或壓制不同意見、協調分歧以便在政治統一中組織同質性或文化多樣性的關鍵因素。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擬訂委員會的辯論和談判,為了解遺產的國際政治及其如何與國家政治、全球治理和人權相聯系,提供了重要的見解。
在全球治理中,一個反復出現的問題是國家主權與國際組織的授權之間的緊張關系。主權不斷得到維護和“拯救”,使其不受超國家權力的支配,即便是政府間組織,其合法性也取決于組成政府的主權權力。幾乎在每一項國際文書的創立過程中,這種關系都需要重新談判。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也不例外。在關于社區參與和該公約實施中市民社會代表機制(例如,通過非政府組織協商)的辯論中,哥倫比亞代表提醒擬訂委員會:“這是國家之間的一項公約,并由國家負責。”贊比亞代表警告說:“委員會可能侵犯了國家主權。”盡管他們的反對意見沒有得到批準,但委員會中仍充斥著對潛在的侵犯主權行為的擔憂。
在2003年6月的會議中,德國外交官以積極捍衛國家主權、抵御超國家入侵的姿態出現。他們得到了來自土耳其、奧地利、日本、格林納達和捷克共和國的同事的大力支持。我承認,我很難理解一些外交同盟,這是其中之一。然而,重要的是牢記,大量的討價還價是在會議室之外進行的。討論和談判發生在茶歇和午餐休息期間,以及亞麻布和瓷器裝點的巴黎餐桌上。喝咖啡、飲料或吃牛排薯條時,在事關公約成敗的重大問題上,聯盟時而形成時而破裂,但在許多情況下,這種聯盟還涉及與非物質遺產完全無關的事務。正如林恩·梅斯克爾(Lynn Meskell)和她的合著者在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多邊主義進行分析時指出的那樣,“由非正式的橫向點對點互動(包括選票交易)組成的跨政府網絡已成為常態。”“不管是個體還是公司或非政府組織的私利帶來的壓力,也越來越普遍,特別是在世界遺產方面。”①Lynn Meskell, Claudia Liuzza, Enrico Bertacchini, and Donatella Saccone,“Multilateralism and UNESCO World Heritage:Decision-Making, States Parties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1, no.5, 2015, p.430;另見林恩·梅斯克爾對世界遺產委員會的政治和約、投票集團和申遺政治的深刻分析,LynnMeskell,“States of Conservation: Protection,Politics, and Pacting within UNESCO’s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87, no.1, 2014.關于世界遺產委員會幕后的游說和交易,見布魯曼(Christoph Brumann)的一個特別微妙的描述,Christoph Brumann,“Comment le patrimoinemondial de l’Unesco deviant immatériel”, Gradhiva 18, 2013, p.41.
在6月會議上,圍繞著將特定的非物質遺產項目列入通過公約建立的遺產名錄的權力,展開了一場漫長的主權辯論。公約的執行委員會能自行做到這一點,還是主動權在所有情況下都來自相關締約國?意大利人公開表示支持前一種立場:“我們贊成允許委員會自己主動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列入名錄這種解決方案。因此,我們贊成刪除‘應有關締約國的要求’這句話,意大利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的遺產。”匈牙利代表表示贊同,并同樣強調:“我們在這里關心的是普遍的人類的遺產。”
在回應被認為是以整個人類的名義威脅國家主權這種觀點時,德國強調,至關重要的是,未經有關締約國的同意,不要賦予委員會行動的權力:“我們是想邀請締約國批準一個可能因其領土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而導致被施加政治壓力這種后果的公約嗎?……這是很危險的。”德國并不是唯一一個嗅到危險的國家。中國代表接著發言,并強調中國同意德國的觀點:“對中國來說,保留‘應有關締約國的要求’一語非常重要。”印度代表也堅持保留這個條件,并警告說,刪除它“將是非常危險的”(想想劫持民俗學者以激勵骨干的卡西叛亂分子)。
德國及其盟國在捍衛國家主權方面贏得了勝利。公約最終文本認為遺產名錄的編制取決于有關締約國的提議。盡管德國代表援引的領土主權原則是大多數國際文書談判中的主導主題,但它對于遺產的考慮尤其顯著,并闡明了這個公約的新內容。
1972年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從空間的角度將遺產界定為古跡、建筑群和遺址以及自然保護區和公園。與最近的“環保術”的保存模式相反,這個公約的“自然遺產”概念備受批評,因為它太過空間化,缺乏對人類群體的關注,這些群體生活在被認定為公園和保護區的區域中,或生活在他們賴以維持生計的區域中,遠離沒有驅逐他們的行政部門。因此,根據定義,世界遺產被表述為領土,可以“劃定、測量、繪制”的領土①Léon Pressouyre,“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1972 Convention: Definition and Evolution of a Concept”, in African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Second Global Strategy Meeting, edited by Bertrand Hirsch, Laurent Lévi-Strauss, and Galia Saouma-Forero, Paris: UNESCO, 1997, p.57; Christoph Brumann and David Berliner,“Introduction. UNESCO World Heritage—Grounded?” in World Heritage on the Ground: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edited by Christoph Brumann and David Berliner, New York: Berghahn, 2016, p.3.。
在無數同時屬于治國之道、旅游業和全球治理的遺產地圖和地理區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遺產的這種空間化。在《想象的共同體》中,歷史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評論道,地圖在殖民地被用于進行分類和創建空間,并通過抽象劃界標記出領土,以對空間進行監視。舊的神圣遺址被納入殖民地地圖,為建立新的領土統一增加了時間深度。通過這種方式,制圖者們將自己包裹在古老的威望之中,安德森指出:“如果這種聲望像過去經常發生的那樣消失了,國家將試圖恢復它。”②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1991,pp.181-182.
因此,遺產一直是領土概念的核心:它使目前的領土主權主張與過去的權威保持一致,它使自己加入易于辨認的領土及其統一的表現形式中;它為這種領土主張和表現形式注入了聲望與合法性。相反,領土是遺產的一個決定性特征。事實上,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可以說,在某些方面,遺產是領土。此外它還是別的東西,但不管它是什么,遺產就是領土。
當然,這主要適用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文化和自然遺產。一方面,需要區分古跡、建筑群和遺址,另一方面也需要將它們與其非物質文化遺產區分開來。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再局限于領土。非物質遺產與人群的關系不是以土地或領土為中介的。相反,非物質遺產客體化了人類社區的實踐和表現形式。它是用民族志而非地形學來界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源于對社區實踐的干預,這種干預界定并劃分了社區。如果說物質遺產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領土,同理,很顯然,非物質遺產就是社區(intangible heritage is community)。
保護社區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體現了政府理性的微妙創新,通過將其風俗、實踐和表現形式轉化為遺產來規訓民眾(其受到威脅的性質使干預成為道德上的當務之急)。最終,這種轉變使社區本身在面對據稱其在現代世界中持續衰落時,也得到保存。因此,社區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年的公約著手保護的最基本的非物質遺產。在這個意義上,即使許多國家都小心翼翼地界定這種賦權(empowerment)的條款,建立其成員認同的社區也是這個公約的重要目標。該公約對非物質遺產的定義清楚地表明了賦予社區以權力(empower communities)的愿望:“‘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第二條第一款)
這也許更應該被視為是一個不確定的詞,將界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權力交給了社區本身(和群體,有時是個人)。這樣,該公約“努力確保”社區參與任何保護措施,或至少在未經社區批準的情況下不采取這些措施——它將責任委托給作為集體主體的社區。①Janet Blake,“UNESCO’s 2003 Convention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Implications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Safeguarding’”, in Intangible Heritage, edited by Laurajane Smith and NatsukoAkagawa, London: Routledge, 2009等。
該公約的循環公式——“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社區承認的作為其文化遺產一部分的實踐,提出了“社區”一詞意指什么的問題。事實上,它要求對國家行為者與之協商和合作的社區進行界定。為了讓社區參與保護,首先必須對社區進行界定,確定其成員資格,并指定一個協商或合作的機構(一個“主管部門”)。
社區的政治吸引力部分在于其明顯的自然性。②Dorothy Noyes, “Group”, in Eight Words for the Study of Expressive Culture, edited by Burt Feintuch,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然而,盡管外表如此,就像其面前的國家一樣,社區也需要被制造出來。界限和區隔必須落實到位。社區必須被可視化、調查和動員。非物質文化遺產正是這樣做的:它將文化實踐轉化為管理民眾的資源。如此一來,賦權就取決于服從。這就是經典的主體化悖論,正如福柯所言,主體的形成發生在權力(在法語pouvoir的雙重意義上:名詞“權力”和動詞“能夠”)的要素中。我們獲得主體(我們思想、言語和行為的主體和處于我們自己與他人的關系中的主體)地位的時刻,也是服從的時刻,我們受制于一套規則和行為規范,受制于已經強加給我們從中獲得主體地位的話語的定義、界限和排斥。
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遺產概念本身所指的社區,都被明確定位成國家內部并服從于國家的集體主體。盡管賦權放松了社區與中央政府之間的文化紐帶,但卻強化二者的行政紐帶。通過定義社區,向其提供外部的專業知識,并賦予其邊緣化的實踐與表現形式以官方威望,這一過程展示了殘留的和夾縫間的文化表征——技藝、口頭傳統、儀式、表演藝術——是如何融入到霸權的表征秩序中的。
編排差異
在一個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宣布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及其名錄的前身)所作的評論中,亨利·克萊森(Henri J.M.Claessen)表達了對引導行將滅亡的文化實踐生存下來的擔憂:“政府將支付酬勞給那些跳沒人再看的舞蹈、唱早已失去其意義而無法理解的歌曲、表演現在沒人相信的神秘戲劇的人們。”克萊森問道:“為什么要這樣做?為什么要花費大量的金錢和精力,來制造一個瀕臨滅絕的代表作的名錄呢?”③Henri J. M.Claessen,“Comment on‘Masterpieces of Oral and Intangible Culture: Reflections on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List’by Peter J. M. Nas”, Current Anthropology 43, no.1, 2002, p.144.
到底為什么呢?一個答案可能是,在很多情況下,社區很想看到他們的傳統出現在這種名錄上,這會給他們帶來榮譽,并吸引關注,尤其是來自地方和國家政府部門的關注。如果這些社區覺得它有意義,如果他們看到了其中的好處,并且相信它是值得的,那么他們保護某些實踐的愿望,就部分地回答了克萊森“為什么要這樣做”的問題。我認為,另一個答案是保護和加強社區的愿望。第三個答案是保護和促進文化多樣性的意愿。這三個答案是完全一致的,它們分別在微觀、中觀和宏觀的層面回答了這個問題。那些主張振興瀕危語言的人也經常被問到同樣的問題,南希·多里安(Nancy C.Dorian)回答過這樣的問題。①Nancy C.Dorian,“The Value of Language-Maintenance Efforts Which Are Unlikely to Succe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68, 1987.
200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部長們發布的《伊斯坦布爾宣言》強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多種表現形式構成了人們和社區的文化認同的一些基本資源”,并堅持認為它們是“維護文化多樣性必不可少的一個因素”②UNESCO, Istanbul Declaration—Final Communiqué. Third Round Table Meeting of Ministers of Culture. September17,2002. (http://portal.unesco.org/en/ev.php-URL_ID=6209&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文化認同與文化多樣性之間的這種互惠關系,一直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非物質遺產領域開展活動,特別是創建2003年公約的基本原則的支柱。事實上,伊斯坦布爾圓桌會議是在“非物質遺產:文化多樣性的一面鏡子”的旗號下舉行的。
然而,理解多樣性的方法不止一種,在政策上體現多樣性的方式也不止一種。很多國家至少在口頭上重視這種多樣性,并在國家層面實施促進文化多樣性的政策,盡管這些政策對理想的多樣性類型和如何管理多樣性有不同的設想。③Tony Bennett, Differing Diversities: Cultural Polic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2001等。這樣的政策依賴于一系列的實踐和技術,來控制主體在新的認同與忠誠的多重領域的形成。將社群組織為情感關系的和具有強烈而非排他性的認同感的空間,是這些實踐的一個子集。通過社區來治理和編排差異應被視為一個事業的不同方面。
不同社區之間的差異被安排、頌揚,并經常在媒體上被過度強調和夸大,這些媒體是按照節日和展覽的全球語法精心組織的。這些做法通常將社區融入到一些在多樣性中求統一的程序中。通過這樣的遺產政治,差異被編排成文化多樣性,一個國家內的群體被賦予了一種聲音,同時也被賦予了一個和諧的樂譜。正如阿爾瓊·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所解釋的那樣,這些政治以非常統一的方式在全球范圍內展開:“典型的是,當代民族-國家通過對差異進行分類控制、創造各種國際景觀以使差異本土化、用在某種全球的或世界性的舞臺上自我展示的幻想引誘小群體,來做到這一點。”④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39.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搭建的就是這樣一個世界性的舞臺。它的名錄進行強調和倡導,使選定的地方實踐與表現形式引起注意,并為保護這些實踐與表現形式籌集資源。雖然是以《世界遺產名錄》為藍本,但這些名錄的不同之處在于,列入其中的遺產是由社區中有生命的人所體現的,而且在這些社區之外并不存在。實際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物質遺產名錄展示社區的方式與《世界遺產名錄》一樣,都是以多元文化節日的全球語法為基礎。事實上,節日本身就是非物質遺產保護的主要展示類型之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物質遺產在名錄、手冊、紀錄片、網頁和演出中對差異的美學標記進行組織,積極展示文化的多樣性,并在多樣性中求統一的人類招牌下對之進行協調。
同質與霸權(或丹麥性的轉移)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松浦晃一郎不失時機地強調非物質遺產對促進世界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性。2004年6月,在哥本哈根的一次演講中,松浦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近年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已經成為當務之急?”①UNESCO,“Address by MrKo?chiro Matsuura, Director-General of UNESCO, on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penhagen, Denmark, June 1, 2004. Document DG/2004/079, Paris: UNESCO, 2004, p.1.他自問自答,繼續說道:“我認為,答案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加速的全球化正在給文化多樣性帶來新的巨大壓力。這些壓力已引起人們的恐懼,害怕進一步的文化同質化及其帶來的對世界文化多樣性的威脅,特別是在其地方的、本土的和生活形式的方面。這些普遍存在的擔憂,激發了必須在為時已晚之前采取行動的需要。《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是這一進程中緊急處理全球化的文化挑戰的一個重要部分。”②Ibid.
對全球的文化同質化的恐懼,可能會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支持下的國際政策制定產生獨特的影響。松浦隨后在哥本哈根演講的評論中闡述了這種獨特性:“這次會議本身就是丹麥就非物質文化遺產問題進行國家的自我反思過程的一部分。這樣的反思既令人興奮又令人不安。它可能會引發一些棘手的問題。例如,丹麥認同和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哪些東西是你無論如何也不想失去的?……能否對這一顯著特征進行界定和標示?你想維護它嗎?你能想象沒有它的丹麥和‘丹麥性’(Danishness)嗎?這各種各樣的問題轉移到世界各國,正在形塑著非物質文化遺產議程。”③Ibid.
暫且不談文化作為差異的基本表現形式這一有爭議的觀念,目前困擾我的主要是這一觀念的國家內涵。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在總干事看來,“國家的自我反思”的過程應該處于“非物質文化遺產議程”的中心,這種反思旨在界定“丹麥性”和標示“丹麥認同和文化的核心”。雖然它的目的是為了應對世界文化多樣性所受到的威脅,并減輕對同質化的擔憂,但這樣一個過程——“轉移到世界各國”,將不可避免地違背其目的。
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一次訪談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處的一名成員表達了與總干事類似的觀點。當我問他為什么認為保護非物質遺產很重要時,他斷言這種遺產是保持世界文化多樣性所必需的,因為“這就是哥倫比亞與玻利維亞等國不同的地方!”④私下交流,2003年11月25日。在一篇關于遺產政治的重要文章中,雷吉娜·本迪克斯(Regina Bendix)評論了遺產“隱藏歷史和政治的復雜性”的這種彈性能力。⑤Regina Bendix,“Heredity, Hybridity and Heritage from One Fin-de-Siècle to the Next”, in Folklore, Heritage Politics and Ethnic Diversity, edited by Pertti J. Anttonen, Botkyrka: Multicultural Centre, 2000, p.38.正如我的訪談對象所說的那樣,非物質遺產可以突出某些差異,同時掩蓋其他差異——例如,哥倫比亞和玻利維亞的民兵政治和選舉政治之間的差異,在訪談時,這些差異確實有效地將哥倫比亞和玻利維亞區分開來,就像它們各自的大眾傳統一樣。
為了公平起見,我應該補充一下,在同一次訪談的后面,我的信息提供者承認,非物質遺產“也會對國家認同造成問題,尤其是在跨境社區中”⑥私下交流,2003年11月25日。。這種觀察指向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文化差異被表達為一系列共存的國家性——“丹麥性”“日本性”“印度性”“贊比亞性”“哥倫比亞性”等等的集合,這樣的世界與我們所居住的世界相比,其多樣性不是更多,而是更少。把這樣一個世界想象成其目標的國際政策,如果要產生任何效果的話,對全球文化多樣性的危害可能比引起它的“全球化的文化挑戰”更大。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對此表示懷疑。正如阿帕杜萊所指出的,對同質化的恐懼可能“被民族-國家利用來對付自己的少數群體,通過將全球商品化(或資本主義,或其他這樣的外部敵人)說成是比其自身霸權策略更大的威脅”①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32.。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只需回顧一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其如何關注民俗所做的一個因原描述:面對“商業主導的跨文化過程對傳統文化的破壞”,玻利維亞的部長發出警告;同時發生了玻利維亞對本土認同的壓制和對本土文化的盜用。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承認的以國際多樣性前景和以國家內部文化差異為背景的文化多樣性的頭等大事,能夠、將會而且肯定已經被用來作為壓制少數群體的理由。因此,總干事對文化政策的獨特解讀也許最好理解為結合人權問題談論多樣性。它在國家之間而不是在國家內部分配差異,使以定義、分類的名義來消除差異得以合法化,并最終形成一個內部一致的國家認同的和文化的有序集合。
總干事堅信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保護公約可以成為應對“全球化的文化挑戰”的有用工具,這一點沒有錯。他是對的,但理由是錯誤的。它們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們觸及了國家認同的核心,也不在于它們有助于給國家性格的鮮明特征貼上標簽。重要的是,這個概念和公約如何促成對遺產的重新想象并鼓勵文化在社區中重新配置。2003年的公約所界定并工具化的非物質遺產,賦予了社區自治權和投資能力,它有助于社區組織成為部分自我管理的行政實體。
尼古拉斯·羅斯所分析的社區化模式,無疑最適用于以先進自由主義為特征的國家——無論是新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還是“第三條道路”。然而,重要的是應該注意到,即使是在“發達世界”,這種模式也并非平等或一致地適用于所有自由主義國家。與其將社區化設想為單一的治理模式,不如承認一系列不同程度、不同模式和不同方法的通過社區進行的治理。這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更為重要,因為全球化和自由化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產生相同的結果。當然有許多自由主義,公民也在不同程度上與其治理相融合。②Lawrence Grossberg, Toby Miller and Jeremy Packer,“Mapping the Intersection of Foucault and Cultural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Lawrence Grossberg and Toby Miller, October 2000”, in Foucault, Cultural Studies, and Governmentality, edited by Jack Z.Bratich, Jeremy Packer and Cameron McCart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p.34;Aihwa Ong,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使社區發聲
如果治理的社區化把很多社會治理的任務委托給社區,那么,主權領土內所有社區相互之間及其與國家之間就始終保持著松散的從屬關系。這種從屬關系是圍繞不同社區個體成員的共同公民身份而非他們的文化紐帶組織起來的。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構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部分地由社區或經過與社區協商來指定、匯集與解釋,社區的認同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性交織在一起。只要社區成員融入代理工作并為之負責,非物質文化遺產就能賦予社區自治權,使其發出自己的聲音。然而,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把特定的關系和權威組織成相對穩定的單元(社區),使其能夠用一個聲音說話。
這種目的不可避免地會引發基層權力的角逐。③見 David Berliner,“Perdrel’esprit du lieu: Les politiques de l’Unesco à LuangPrabang (RDP Lao)”, Terrain 55, 2010 等。在對加泰羅尼亞貝爾加的帕圖姆(Patum)節被提名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一些早期后果所進行的敏銳分析中,民俗學者多蘿西·諾伊斯(Dorothy Noyes)敘述了組織社區的嘗試是如何在當地展開的。作為一個歷史悠久、廣受歡迎的街頭節日和集體表演,帕圖姆一直是貝爾加人激烈爭論的工具,但它也通過其多義性和間接性促進了一種微妙的社會平衡。此外,這個節日還幫助新居民成為貝爾加社會生活的正式成員,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隨著新的移民潮涌入城市,它在這方面的重要性也在增加。①Dorothy Noyes,“The Judgment of Solomon: Global Protections for Tradi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ommunity Ownership”,Cultural Analysis 5, 2006.
諾伊斯解釋道,“在20世紀90年代初,一群與市政廳關系密切的節日參與者創建了一個基金會來出資保護帕圖姆:一個擁有成千上萬熱情追隨者的節日,不可能有滅亡或失去其形式完整性的危險。”②Ibid., p.38.這個基金會控制著節日的一些物質要素——樂器、神像、服裝,但它的董事會不是直接選舉產生的,沒有明確的輪值結構,而且它包括一些節日參與者群體的成員,但不包括其他有不同意見的人。然而,如果沒有進一步觀察,局外人沒有理由懷疑這個贊助機構代表了社區。實際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加泰羅尼亞文化部似乎都將其視為管理帕圖姆節的“勝任的權威組織(competent authority)”③Ibid., p.38.。
貝爾加人對這種狀況看法不一。有些人質疑這個贊助機構的權威,而另一些人則選擇撤出、放棄參與。在這個擁有一萬六千名居民的小鎮上,需要所有人的努力來保持當地的活力,“一些最有才華的演員已經把控制權拱手讓給了官僚”④Ibid., p.39.。與節日制度化相伴的退出和排斥所帶來的后果對貝爾加的社區組織和社會生活管理非常重要,正如多蘿西·諾伊斯所表明的:
贊助機構的成員來自帕圖姆輿論“受人尊敬的”的一派,在多年來的許多事件中,這一派一直試圖控制參與,以控制帕圖姆社會變革的潛力。有跡象表明,這種控制……是贊助機構議程的一部分。例如,最近建立了一個“積分”制度,用于認定節日管理人員,這是一個每年給予四對新婚夫婦的榮譽職位。除此之外,出生在貝爾加并在教堂結婚的人也會得到積分。在一個移民人口眾多、工人階級歷來反對牧師的城市里,這些標準是極具分裂性的。⑤Ibid., p.40.
從馬拉喀什到貝爾加以及其他地方,很明顯,非物質遺產的語言——維護、保護、建檔、研究、促進、教育和振興的程序及其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提供了工具和技術,社區作為被確認的空間可以用它們來組織自己,來引導其成員的行為,并在當代多元社會的復調中找到自己的聲音。危險的是,在找到自己的聲音的過程中,這些社區在與管理者和專家的合作中,會壓制自己的多種聲音,會放大一種聲音,淹沒不同意見。在這種情況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所保護的不僅是文化遺產,而且也是一種服從的政治遺產。原則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多樣性中求統一”的口號代表了和諧與理解。在實踐中,它承擔著在認定的多種多樣的社區中內強制推行一致性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