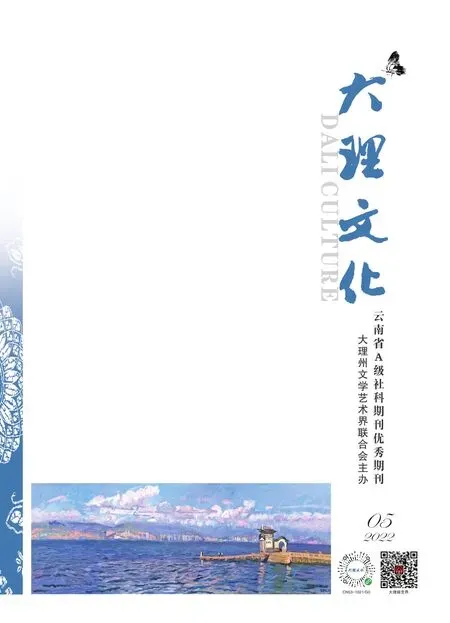昂揚的駿馬,蓬勃的生命
—— 對北雁小說《駿馬》的一種詮釋
●納張元
白族青年作家北雁的小說《駿馬》發表于《中國鐵路文藝》,后被《作品與爭鳴》2022年第1期轉載,產生積極的社會影響。小說以“馴馬——騎馬——賽馬——偷馬”的故事為主線,借重“駿馬”這一表意性象征符號,高揚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與蓬勃旺盛的民族民間文化精神。抒情意蘊濃郁,象征意味深沉。強悍、勁健、迅捷的“駿馬”形象寄寓著矯健頑強、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生命力,傳達出一種堅韌不拔的生命意志和生態意識,也隱含著民族民間文化與現代性的交流與對話,成為作家寄托民族情感,書寫彝族人民生活的文化中介。
作家懷著飽綻的激情禮贊一種勁健的生命存在形式,婚慶禮儀、節慶習俗、賽馬活動的描寫,以及小說里散發著的既鮮明奇特又似曾相識的民族氣質,接續了民族民間文化的傳統。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傳統”,而是一種“現代意義上的傳統”,即把當下作為文化實踐和理論思考的基點,使文化傳統成為現代性資源而非束縛。他關注民族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生命活力與傳承動力,將自由與自在、現實與想象、生存與生命糅合融通,形成一體,建構出一個生命躍動、生機盎然的生命空間,一個詩意棲居、意義充盈的審美世界。
昂揚的駿馬形象象征堅韌的民族精神
“駿馬”這一典型形象具有鮮明的象征意味,揭示出民族精神在外部變遷中不變的姿態和立場。小說中291次出現“馬”這一字眼,10次出現“駿馬”這個詞,它成為一種歷經洗禮和磨難卻依舊剛毅不屈、吃苦耐勞、淳樸豪邁的民族文化精神象征。這匹叫做“閃電”的“在莽莽羅坪山間飛馳的白馬”不僅僅是一個力量勁健、昂揚奔放的動物形象,它維系著民族文化根基和生命活力,象征著一種百折不撓的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氣概。“閃電”從神秘的遠古走來,貫穿于彝族不屈不撓的奮斗史與遷徙史中。“事實上就是因為有了馬,讓彝族人漫長的歷史從此變得多彩和浪漫起來,甚至還因此而充滿了波瀾和起伏跌宕。”“那真是一匹高大英武的駿馬。一身璨白的馬毛沒有一絲雜色,如同一個耀眼的閃電,馱著新娘從村子中心的大路上走過,一頭扎入村后的大山之中,用堅實有力的蹄印擦破黎明。從此,山間鶯歌燕舞、流泉歡唱、鼠戲荊藤。山村的清晨也就這樣開始了。”作家用自然靈動的筆調將一個生機勃勃、活色生香的鄉野景觀清晰地呈現出來。“閃電”身上散發出的神性與靈性,是彝族人萬物有靈觀念的自然表現。人性的淳樸與自然的生機借助兼具“力與美”“剛與柔”的駿馬形象表現得淋漓盡致。“我敬愛的阿普(爺爺)就是一個非常懂馬的彝族人。他把大半輩子心血都交給一匹匹山間的奔馬,最終為我阿達培育了那匹在莽莽羅坪山間飛馳的白馬,如同一道耀眼的霹靂,一眨眼就能從這個山頭越到那個山頭。”“那種帶著征服和統治意味的奔跑,不止征服了賽場,還征服了所有人的眼球。”作家以精神仰望的姿態延留一個矯健昂揚、任情恣性的駿馬形象,表明了人與自然互蘊共榮的文化立場,由此展示彝族人民獨特的道德情感、人文風情和審美趣味,以及特定文化秩序中的民族精神。
小說以隱喻、暗示、特征化的方式,通過情節與精神間的轉換對駿馬進行象征性敘事,注重內心直覺感受的表達,揭示抽象的內在精神本質。駿馬形象是作為一種傳達或生成意義的符號而存在,表達了小說豐沛的生命活力和豐厚的精神內涵,使得文化韻味雋永悠長。著名老作家白樺認為,最好的小說就是“它既是一個現實的故事,又是一個寓言,且具有多義性”。日本文學評論家廚川白村也說:“凡是一切藝術,古往今來,是無不在這樣的意義上,用著象征主義的表現手法的。”多重意義的象征形成豐富的文學隱喻,揭示出隱秘的文化心理結構,而且成為故事情節發展的原動力,滲透于整個敘事空間。
故鄉的風物人情彰顯濃厚的鄉土情結
鄉土是作家獲得文學生命力的源泉。北雁有著濃厚的鄉土依戀情結,故鄉的山山水水成為他生命的來源和最終的歸宿。北雁本人是白族,但從小在彝族、漢族和白族雜居的多民族聚居區長大,從小受多元文化熏陶,他的文學之根帶著“彝人的血脈,在這片土地上延伸”。小說里9次出現“騎龍山”,42次提及“我們陸家村”,43次深情吟唱“羅坪山”這片豐腴的故土。“滋養故鄉人民和牛馬草木的羅坪山”孕育一切,亦包容一切。“為什么我總深愛著羅坪山這片豐腴的故土,那是因為我深愛著和羅坪山一樣豐腴的故鄉女人,還有和羅坪山山脊一樣厚實的男人,以及那一匹匹讓我們彝族人無比自豪的駿馬。”這就是故鄉的分量,思念的重量。韓少功在《文學的“根”》中說:“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的文化土壤中”,作家應該“在立足現實的同時又對現實世界進行超越,去揭示一些決定民族發展和人類生存的謎。”作家在地域選擇的背后隱含著的是文化的抉擇。小說以多維視角呈現亙古不變的山地文化自然景觀和本質特征,透視彝族文化生態的變遷歷程,表達出獨特的地域文化生態理念。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作家沉潛到日常生活的深處,以充沛飽滿、自由自在的民間情感作為作品內在的精神支撐,用生命的姿態去審視和表現民族文化形態,凝聚起歷史與現實、人生與人性之間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作家深情地描摹人群的生活本相:“那一撥撥進出山林的趕馬人、拾菌人、養蜂人、采藥人、砍柴人、牧人、手藝人和生意人。”揭示出獨特地域中人們的欲念、情感、意志、行為和理想。個體生命是如此多維立體,頑強的生命活力、不屈的生存意志、堅定的生活信念是他們面對現實生活時升騰的希望。描摹彝鄉“歌舞升平”的日常生活:“那些被我深愛著的奶奶、媽媽、伯母、嬸姨、舅媽、姐姐和妹妹們,那些被風吹日曬、雨雪霜露和歲月的艱辛反復蹂躪,被滇西北高原強烈的紫外線曬得松弛和粗糙的皮膚,還有常常超負荷勞動而嚴重扭曲了的身體,在十個指頭間長滿厚繭的諾蘇女人,居然會有如此曼妙的舞姿,如此奔放的舞步,如此樂觀的笑容,如此豁達的胸襟,如此嘹亮的歌聲。”“騎龍山村的女子是以歌舞和刺繡著稱的,而阿母的歌聲無疑是整個村子最嘹亮動聽的,像是一只清潤明朗的夜鶯。”作家有意識強化對社會風情和人文景觀的描繪,呈現出充滿生命力的民間世界的理想狀態。在深刻和深情的描摹下,讓我們真切地感受到一顆跳動的心和一個活著的魂。在他們身上,我們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激情與美好,人性的樸實與率真、忠厚與善良。正如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所代表的人性,是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這是一曲生命的贊歌,因了生命的釋放,才有了鮮活飽滿、氣韻生動的人性之美。
多元的敘事手段提供新鮮的審美經驗
北雁熟稔地運用倒敘、插敘、閃回、交叉、復現等敘事手段,重組甚至逆轉歷史敘述的線性鏈條,構建自由穿梭的時間場域,以多元化的方式書寫著族群的歷史記憶與現實生活。特定的話語建制和詩意抒寫形成獨特而復雜的敘事話語結構。語言是思想呈現的基本工具,又是文學存在的本體。《駿馬》算是一篇彝族漢語小說,用漢語寫就,但其中呈現出鮮明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特質,“阿達”(父親)、“阿普”(祖父)、“諾蘇人”(彝族的一個支系)等稱謂語自然地出現在小說中,能夠提供一種新鮮的感覺經驗,產生一種異質性、陌生化語言感受,打破了漢語的習慣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使之成為表達本民族獨特思維和獨有文化之載體。尤其是將神話、史詩、歌謠、傳說故事融為一爐,以神話傳說演繹現代意味,依靠歷史的縱深構筑小說特定的文化歸屬、情感歸屬與民族性格。體現出作家在現代性語境下獨特而復雜的情感體驗、生活經驗和藝術探索。
小說開篇寫道:“作為云嶺高原上我們這個以賽馬著稱的陸家村的孩子,接下來我要給大家講述的就是一個關于駿馬的故事。”開門見山,直擊主題,以第一人稱敘事來建構明確的身份認證和民族認同。民族文化元素與故事情節敘述形成一種對應與對話,情景交融,虛實相生,指向更加豐富的歷史文化和現代語境,豐富了小說的文化內涵和敘述話語結構。小說結尾寫道:“離天空最近的羅坪山彩云崗頂上,歌不止,舞不斷,酒不停。此刻美麗的白馬閃電正靜靜地臥在青草叢中,咀嚼著甘甜……”開放式結局給人無限遐想的空間和理性反思的余地。作家將自我融入天地萬物之間,用文字描繪奇異絢麗的畫卷,感知天地山巒,感知萬物生靈。人、事、物、景彼此相依、密切纏繞,這是融入生命感受的寫作,世間萬物“順從于其本質”,如其本然的存在,真誠而溫暖,詩意且靈動。小說延續著母語的審美傳統和文明體系,同時也涵納了豐盈的社會歷史質素,展現了作家出色的敘事話語建構能力,也賦予了文學作品復雜的現代精神向度和良好的審美品質。
綜上所述,北雁的短篇小說《駿馬》以“駿馬”形象為象征符號,細致多元地展現了彝族賴以生存的文化之根、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脈。蒙太奇式的場景轉換明快跳躍,白描式的環境描寫干凈利落,熱火朝天的賽馬場面驚心動魄。敘事與抒情,靜思與雄辯,樸素的表達與雄奇的想象融為一體,筆觸涉獵現實生活和文化本原回歸,并深情回望本民族的生存處境和發展空間。昭示著他對現代文明的依存和對本民族文化的依歸,以及對生活題材的現代把握和詩性書寫。這是作家個體生活經驗和情感體驗的審美升華,滲透著鮮明的地域特點和獨特的生存范式,蘊藏著耐人尋味的象征意味,深邃多元的文化隱喻和豐富多樣的審美意蘊。感情發自肺腑,才情豐沛,誠摯動人。文風質樸自然,詩意豐美。美中不足的是主題意義缺乏多層面和多向度開掘,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內在質的單薄。激情抒懷有余而理性審視不足,藝術形象的具體性與生動性描摹、文化內涵的層次性與深刻性發掘尚可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