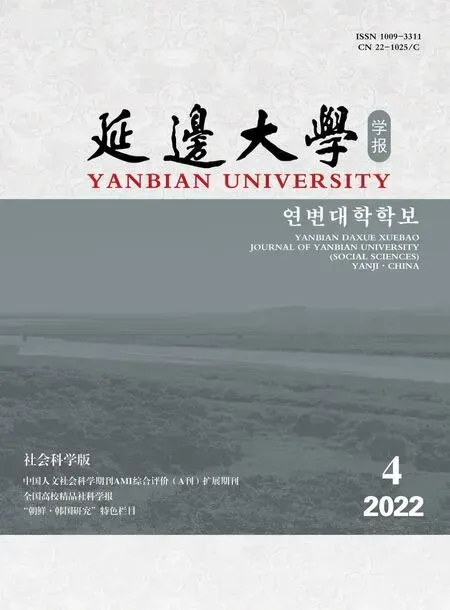百年國學三次熱潮與思考
湯 洪 李 丹
鴉片戰爭后,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西方列強紛至沓來。在西方強勢槍炮之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接踵而來。這期間,國人從被動漸趨主動吸收西方文化,西方學術也大量涌入。我者與他者的碰撞,亡國與亡種的憂慮,遂催生出第一次愛國國學熱。從洋務運動的變革技術到維新變法的變革制度,皆沒有使當時的中國擺脫貧困與落后。五四新文化運動走向變革文化,因而也激蕩“整理國故運動”并產生第二次研究國學熱。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獨立自主政權,特別是改革開放幾十年的經濟成就,讓國人不斷走向文化自覺和自信。經濟的開放,同時也帶來20世紀80年代后西方學術的大量涌入,本土與外來再一次產生碰撞互動,遂引發第三次國學熱,持續至今而未衰歇。本文擬清理百年國學興起與沉寂的三次浪潮,分析背后的歷史動因并試圖探尋國學的未來發展走向。
一、國學興起的時代背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清朝文字獄和閉關鎖國,對民族發展造成巨大傷害,漸使中國進入“停滯社會”。乾隆逝世40年后,國人在鴉片戰爭中表現的愚昧令人咋舌。廣州主將楊芳“傳令甲保遍收所近婦女溺器”以為制勝法寶,企圖以“陰門陣”對抗英國軍艦。鴉片戰爭后,清政府風雨飄搖,太平軍趁亂局一路北上,節節勝利。但是,馬克思在《中國紀事》中認為,當時太平軍“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1)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5頁。因而太平軍并沒有能力拯救中國。緊接著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中國士大夫發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吶喊,在被動中開展“中體西用”理念下的洋務運動。經過30年的建設,清朝在軍事上打造了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艦隊。幾乎在同一時期,日本也興起“明治維新”。但是,1894年日本發動有準備的甲午海戰,卻以北洋艦隊全軍覆沒而告終。中國有識之士再次警醒,于是“百日維新”在康有為、梁啟超的積極呼吁中發起,欲使中國走上變法圖強的革新之路。但僅103天,變法維新即以光緒被囚禁于瀛臺而告失敗。之后,義和團提出“扶清滅洋”口號,卻導致“八國聯軍”對中國更為瘋狂的蠶食和鯨吞。中國該何去何從?早期興中會和同盟會皆在尋求答案,辛亥革命以暴力推翻清朝政權,從而結束了長達2 000多年的君主帝制。1841年5月至1912年2月,晚清70年期間,清政府共簽訂了411個不平等條約,(2)高放:《近現代中國不平等條約的來龍去脈》,《南京社會科學》1999年第2期,第11頁。割地173.9萬平方公里。李鴻章所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誠不虛言。
今人所謂的國學即在這風譎云詭的大動蕩中醞釀、催生、凸顯。國學一名,是晚清時期受日本影響而出現的新事物。日本江戶時代晚期,思想界主張對日本古代典籍進行系統研究,極力反對中國的儒學和佛學,宣揚日本本土的“神道”,即日本國學。1902年,梁啟超在日本創辦了《國學報》。1903年,鄧實在上海創辦了國學保存會,以“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發行刊物《國粹學報》。國學隨即呈現于世人視野。1906年,鄧實于《國粹學報》發表《國學講習記》,他這樣闡釋國學:“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也”。(3)鄧實:《國學講習記》,《國粹學報》1906年第19期。此一概念,歷經百年,仍為學界所普遍認同。
二、“西學東漸”與第一次愛國國學熱
洋務運動興起之后,京師同文館、京師大學堂譯書局、江南制造總局翻譯館以及江楚編譯書局等譯文陣地聚集嚴復、林紓、馬建忠、包天笑、李善蘭、汪鳳藻、華蘅芳、徐壽以及丁韙良、傅蘭雅、藤田豐八等大批干將翻譯西方學術著作,1860年至1904年,譯介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著作達千余種。西學驟然涌入,國人倉促之間,面對他者和我者的碰撞,第一次感到如此劇烈的沖突。1903年,鄧實在上海創辦國學保存會,發行刊物《國粹學報》。鄧實凝聚黃節、章太炎、劉師培等人創立“國粹派”,他們以“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的價值判斷在晚清時期掀起了第一次國學浪潮。
“國粹派”面對當時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形勢,發出振聾發聵的清醒呼聲。黃節在《國粹學報敘》中謂:“立乎地圜而名一國,則必有其立國之精神焉,雖震撼攙雜,而不可以滅之也……昔者英之墟印度也,俄之裂波蘭也……皆先變亂其言語文學,而后其種族乃凌遲衰微……學亡則亡國,國亡則亡族。”(4)黃節:《國粹學報敘》,《國粹學報》1905年第1期。鄧實在《擬設國粹學堂啟》中謂:“中國自古以來,亡國之禍疊見,均國亡而學存。至于今日,則國未亡而學先亡。故近日國學之亡,較嬴秦蒙古之禍為尤酷……學亡則一國之政教禮俗均亡,政教禮俗均亡,則邦國不能獨峙……是則學亡之國,其國必亡,欲謀保國,必先保學。”(5)鄧實:《擬設國粹學堂啟》,《國粹學報》1907年第26期。鄧實在《雞鳴風雨樓獨立書·人種獨立》中謂:“其(按:歐洲人殖民主義)希望偉,其謀慮深,其亡人國也,必先滅其語言,滅其文字,以次滅其種姓。”(6)鄧實:《雞鳴風雨樓獨立書·人種獨立》,《政藝通報》1903年第23期。許守微在《論國粹無阻于歐化》中謂:“是故國有學則雖亡而復興,國無學則一亡而永亡。何者?蓋國有學則國亡而學不亡,學不亡則國猶可再造;國無學則國亡而學亡,學亡而國之亡遂終古矣。”(7)許守微:《論國粹無阻于歐化》,《國粹學報》1905年第7期。章太炎在《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之演講》中謂:“用國粹激勵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8)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頁。章太炎在《國學講習會序》中謂:“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9)章太炎:《國學講習會序》,《民報》1906年第7期。由是可知,這一股國學熱完全是愛國士人在面對西方列強侵吞中國的危難之際所發出的熱血疾呼。
三、“打倒孔家店”與第二次研究國學熱
徹底否定“孔先生”,肯定西方“賽先生”(科學)與“德先生”(民主),發現傳統文化中“理性文化”與“邏輯文化”的闕如,這是“五四”先驅者如陳獨秀、胡適和魯迅的獨到之處。他們以“病理學”的眼光和觀念深刻解剖傳統文化,因而在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上取得了豐碩戰績。但是,面對傳統向現代轉化的新文化體系建設,他們卻并沒有來得及完成這種歷史使命。
主張“全盤西化”應為這一時期的時代潮流,胡適、陳序經二人則是這種主張的代表人物。對于學習西方文化,胡適的態度是堅定的,更是決絕的。1928年,胡適在《請大家來照照鏡子》中認為:“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上不如人,不但機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會道德都不如人……試想何以帝國主義的侵略壓不住日本的發憤自強?何以不平等條約捆不住日本的自由發展?何以我們跌倒了便爬不起來呢?……所以我說,近日的第一要務是要造一種新的心理:要肯認錯,要大澈大悟地承認我們自己百不如人。第二步便是死心塌地的去學人家。”(10)胡適:《請大家來照照鏡子》,《良友》1928年第31期。1935年,發表《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一文,提出了“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全盤西化”)和“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全力現代化”)的主張。(11)胡適:《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大公報》1935年6月23日,第2版。胡適認為,人們應當大膽地、積極地學習西方文化,而無須擔心傳統文化的喪失,胡適在1929年所寫的《文化的沖突》一文中說道:“一個國家的思想家和領導人沒有理由也毫無必要擔心傳統價值的喪失……我在1926年發表了《我們對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我的立場是中國必須充分接受現代文明,特別是科學、技術與民主”。(12)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第376-379頁。此外,1930年胡適將自己十年來的文章總結提煉,作《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以分享給中學生,文中告誡少年人:“不要怕喪失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因為絕大多數的惰性已僅夠保存那舊文化了,用不著你們少年人去擔心。你們的職務在進取,不在保守”。(13)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新月》1930年第4期。1934年,陳序經的《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將“全盤西化”說得更為明確,也更為直接:“總而言之,折衷的辦法既是辦不到,復古的途徑也走不通……我們的惟一辦法,是全盤接受西化”。(14)陳序經:《中國文化的出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82-83頁。在這本書中,陳序經還質疑了胡適“全盤西化”的主張,認為胡適“對于西洋文化其他方面。如宗教態度,尚有多少商量之意”,(15)陳序經:《中國文化的出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94頁。而“主張全盤西化的人,還是不易找得”。(16)陳序經:《中國文化的出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94頁。事實上,胡適與陳序經所主張的“全盤西化”確有一定不同之處,1935年胡適在《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中進一步修正了自己主張的“全盤西化”概念,他認為“所以我主張全盤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向世界化的路……與其說‘全盤西化’,不如說‘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數量上即是‘盡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17)胡適:《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大公報》1935年6月23日,第2版。胡適假設自己穿著長袍、踏著中國緞鞋子、用鋼筆寫著漢字的場景,承認并不能真正做到所謂“全盤西化”。他指出,“況且西洋文化確有不少的歷史因襲的成分,我們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實上也絕不會全盤采取”。(18)胡適:《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大公報》1935年6月23日,第3版。胡適將“全盤西化”的說法替換為“充分世界化”,可見其“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的意圖。
科學主義及其所關聯的“全盤西化”思潮在中國旋即受到傳統知識群體的猛烈批評,致使傳統與外來量長較短,從而在新文化運動內部產生離散分化,導致“新舊”的天壤懸隔。梁啟超在一戰后自歐洲考察歸來,對自己曾經無比崇尚的科學主義產生了懷疑。而后,張君勱帶著這種懷疑與丁文江、胡適等堅持“科學主義”的學者展開了一系列關于“科學與人生觀”的持續爭論。此外,梁漱溟在西潮涌動之際,探尋中國文化未來發展方向,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從中、西、印文化的不同來闡發世界文化的三種人生路向。梁氏認為中國過早走上第二路向而沒有科學和民主,故中國文化須先“連根拔去”并“通盤受用西方化”,把第一路向走一遍。梁氏主張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最優文化,因此人類都得走上中國所走的路向,故我們應該“拿出中國原來態度”“翻身”變成世界文化。梁氏的主張分別受到張君勱和胡適兩方的批評。以吳宓和梅光迪等人為代表的學衡派是“文化守成主義”的支持者,他們批判提倡新文化運動者:“彼等猶以創造自矜,以模仿笑國人……況彼等模仿西人,僅得糟粕”,(19)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學衡》1922年第1期。主張“今欲造成中國之新文化,自當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而熔鑄之,貫通之”。(20)吳宓:《論新文化運動》,《學衡》1922年第4期。
新文化運動正因有此激烈思想對壘,因而同時催生國學的第二次熱潮。在國學第二次熱潮的推動下,一批國學研究機構旋即成立。1920年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成立,1921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創建《國學季刊》,1923年東南大學國文系國學院創建《國學叢刊》,1925年清華國學研究院創建《國學論叢》,1926年廈門大學國學院創建《國學專刊》,1928年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創建《燕京學報》,各大陣地皆以專研國學為務。但是,這些國學研究機構的研究方法已迥異于20世紀初的第一次國學熱。例如,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聚集沈兼士、胡適、李大釗、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朱希祖、蔣夢麟、陳垣、沈尹默等一批大家,但同時也邀請世界知名漢學家,如法國伯希和、德國衛禮賢、日本田邊尚雄等擔任通信員,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已具開放眼光并重視與國外漢學界深入交流。又如,清華國學研究院聚集吳宓、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李濟等大家,共招收四屆74人,其中王力、吳其昌、徐中舒、姜亮夫、陸侃如、劉節、劉盼遂、羅根澤、蔣天樞等皆是20世紀人文學術的中堅力量。但是,王國維主講“古史新證”“說文練習”“尚書”“最近二十年來中國新發現之新學問”,梁啟超主講“中國文化史”“史學研究法”,陳寅恪主講“西人東方學之目錄學”“佛經翻譯文學”,趙元任主講“方言學”“普通語言學”“音韻學”,李濟主講“民族學”“考古學”,他們的講授內容完全超越早期國學的范圍。趙元任的語言學研究已屬現代語言學范疇,李濟的“民族學”和“考古學”都是直接運用人類學的方法。因此,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和清華國學研究院已經是和西方漢學緊密相關的全新國學。20世紀20年代,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胡適發起的“整理國故運動”即是此一時期國學研究的主流范式。胡適于1923年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已有不同于20世紀初的國學概念:“‘國學’在我們的心眼里,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21)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北京大學日刊》1923年3月30日,第2版。他們以中立、不含褒貶的學術態度倡導“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他們充滿對科學方法的自信,試圖通過科學的國故整理來證明“國粹派”和“守舊派”固守傳統文化價值的錯誤。20世紀20年代,科學主義與守成主義兩派間的爭辯沉淀為不同的思維模式,這些矛盾沖突由近代知識階層的內在困境所造成。一方面,以胡適為代表的文化激進派都是民族國家的堅定支持者,希望中國富強,但他們堅信要實現中國富強必須舍棄自己的文化,因此他們側重對傳統文化進行“捉妖打鬼”“解剖死尸”,由此出現國學大師反國學的時代主潮。另一方面,以學衡派為代表的文化守成派堅決反對完全拋棄傳統文化,他們堅信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性,認為民主和科學為中國必須接受,但他們重點在于論證民主和科學為中國文化所本有。因此,兩派都在研究國學,只是出發點和研究視角迥然有別。
四、全球化語境與當代第三次復興優秀傳統文化國學熱
20世紀50年代,由于院系調整,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被合并,齊魯大學以及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被撤銷,北京大學的《國學季刊》停刊,自此,國學概念即從人們視野中銷聲匿跡近40年。鴉片戰爭以來,國人思考中國屢屢失敗的原因多歸罪于傳統文化。迷于西潮,惑于前路,因驚生懼,因懼生媚。批判傳統文化、否定傳統文化成為百年社會主流思潮,傳統文化因此遭遇數次劫難。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20世紀80年代西學再次涌入,一如前兩次國學熱的興起,20世紀第三次國學熱也在西學的映射下風生水起,持續至今而未衰竭。梳理當代國學熱的內因外緣,有更為深層和廣闊的時代成因。
近30年來,中國的成績舉世矚目,國人迫切需要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歷史以及民族的獨特價值,由此激發國人復興傳統文化的強烈愿望。“倉廩實而知禮節”,正是當代中華民族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集中表現。20世紀70年代,歐美經濟蕭條,而儒家文化圈“亞洲四小龍”卻創造了“經濟奇跡”。人們探尋個中原因,發現多得益于儒家思想。例如,日本“企業之父”澀澤榮一十分尊崇孔子,自謂:“畢生都遵從孔子的教誨,把《論語》當作出世的金科玉律,從未離開過案頭”,(22)[日]澀澤榮一:《論語與算盤》,高望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年,第4頁。認為“致富的根源,那就是根據仁義道德的原則,以正確的道理創造財富,唯有如此,這種富裕才能永遠維持下去”。(23)[日]澀澤榮一:《論語與算盤》,高望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年,第2頁。而韓國三星集團創始人李秉喆則受到熱愛儒學的父親的影響,“一直以‘信用’為企業的生命而奉行不渝”。(24)[韓]李秉喆:《第一主義——韓國企業巨人李秉喆自傳》,朱立熙譯,臺北:經濟與生活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8頁。此外,當今中國處于多元價值觀碰撞的時代,社會財富極速增加,但人的精神世界和心靈家園卻日益荒蕪。許多人將金錢至上、享樂在先、精致利己等觀念作為自己為人處世的“寶典”,大大敗壞了社會的道德風氣。我們不禁思考,難道經濟發展與道德滑坡存在必然關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溫柔敦厚、誠信友愛、重禮尚義、知廉明辱、和而不同等品格一時間成為社會最寶貴的精神資源。國家和人民都急需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重塑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質,恢復千年文明之邦的國家形象。
在提振民族自信的同時,當代國學熱也是對西方學術的映射反應。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開始思考用西方學術理論體系整理解釋中國傳統文化的穿鑿附會,不斷對西方話語及自身的學科建設進行理性反思。由此,國學猶如昨日重現,應運而生。波詭云譎的國際形勢,如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也刺激國學絕處逢生。時人發現,傳統文化蘊藏著豐富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需的思想內容,從傳統文化資源中探尋并建構中國文化體系,隨即成為當下的現實需求。
中國因政治、經濟、外交走向世界舞臺中央,這勢必帶給國人昂首闊步向前的民族內在自尊。“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從政治到經濟,21世紀如何建設一個文化中國,即成為當代中國的時代命題。據莊國土介紹,“到2008年,世界華僑華人總數超過4 500萬人”,(25)莊國土:《世界華僑華人數量和分布的歷史變化》,《世界歷史》2011年第5期,第4-14+157頁。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將這些華裔團結在一起,而大陸舉辦的各種尋根祭祖活動也吸引著他們回歸故土,緬懷祖先,而這也成為當代國學再次煥發活力的重要外在推動力。
港臺地區及海外的第三代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杜維明、余英時、成中英、劉述先等人以重塑民族精神、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為己任,試圖在儒學與科學民主思想間找到共通之處,他們創辦雜志、著書講學,四處宣傳其思想,其著述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陸續在中國內地(大陸)出版流傳,中國內地(大陸)出現儒學熱和國學熱即勢所必然。
黨和國家的大力倡導,學界和民間的積極配合,使中國文化逐步走向自信之途。2016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講話中提出“文化自信”,這更是百年來中華文化的鏗鏘誓言。十九大報告再次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26)《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頁。由此可見,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建文化家園和心靈棲居之所,已經成為時代的強烈呼聲。
五、傳承與超越是未來國學發展之途
國學的百年命運引發我們深思。時代呼喚國學,但更期待國學自身蝶變的超越。大江東去,國學永遠是動態發展的過程,而不是僵化凝結的一潭死水。經過百年坎坷曲折,今人再看國學,應撥云見日、廓清迷霧,走出霧里看花的朦朧。除國學一語外,國文、國語、國史、國劇、國畫、國醫、國術、國服等皆有市場。但是,國學到底是什么?是一國所有之學,還是國故學?是傳統學術之總稱,還是專指儒學?是漢服的外在形式,還是傳統思想價值觀念的內生動力?這些紛亂皆是當下亟須解決的問題。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謂:“故我輩雖當一面盡量吸收外來之新文化,一面仍萬不可妄自菲薄,蔑棄其遺產。”(27)梁啟超著,朱維錚校注:《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59頁。事實上,“國粹”“國故”“國學”等概念對“國”的強調往往源自提升民族自信、建設民族精神的需要。當自身文化受到他者的強勢沖擊時,人們便自然而然地從本民族文化中汲取力量來抵抗他者,于是強調文化的本土特色便成為時代的趨勢。中國士大夫除了家國情懷,更有天下意識,“國學”概念也遭到一些學者的質疑。我們呼喚國學,但并不需要完全摒棄外來的優秀文化。王國維等人主張學無中西,傅斯年亦指出:“要想做科學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這學問斷不以國別成邏輯的分別”。(28)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第1期。被譽為“中國最后一位國學大師”的錢穆在《國學概論》之弁言中說:“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29)錢穆:《國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頁。
正確判斷源于自身的強大。自1840年以來,面對西學的強烈沖擊,國人難免倉皇失措,來不及慢慢吸收化用,遂在全盤接受與全盤否定之間形成二元對立。全盤接受西學勢必會喪失文化判斷能力,從而形成西方文化依附,這種情形至今依然存在。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國加入國際話語體系的時間尚短暫,我們所用的西方理論體系還多在照搬階段,還沒有完全建構起自己的模式和方法。但是,不輕言放棄方顯英雄本色,摒棄急功近利,認真研究對世界未來有價值的文化傳統,盡快建構中國模式,是當前學界的緊迫任務。經師易得,人師難求,中國不是沒有講論國學的經師,也不是沒有愿意聆聽國學的受眾,只是時代更需要為國人、為民族、為天下研討國學的任重道遠之士。
國家層面的政策推動已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200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啟動以中華古籍全書數字化出版、中華大典編纂為代表的國家重大出版工程……加強民族古籍和文物搶救工作……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和傳承經典、技藝的傳承”。(30)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2-43頁。201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要求“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與利用……完善《國家珍貴古籍名錄》……開展古籍修復、數字化和出版……系統整理散失海外的中華古籍珍本”。(31)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31頁。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層、更持久的力量”。(32)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人民日報》2017年1月26日,第6版。2017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提出要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堅持客觀科學禮敬的態度,揚棄繼承、轉化創新,推動中華文化現代化,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擁有更多的傳承載體、傳播渠道和傳習人群,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研究挖掘和創新……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普及……加大文化遺產保護”。(33)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政策法規司編:《“十三五”文化發展改革規劃匯編》,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8年,第24頁。然而,國學亦需要體現出我們自己的文化精神,這正如20世紀20年代清華大學校長曹云祥在清華國學研究院開學典禮的致辭中所言:“現在中國所謂新教育,大都抄襲歐美各國之教育,欲謀自動,必須本中國文化精神,悉心研究……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學方法,并參加中國考據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尋出中國之國魂”。(34)曹云祥:《開學詞》,《清華周刊》1925年第1期。
國學研究的根本目的正是守根尋魂。國學的意義更多是讓世人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其學術傳統的獨特地位,引導國民堅定中華民族文化的價值立場,但這并非必須拒絕西方才能延續本土文脈。中華文化猶如長江黃河,江河從不拒絕來自四面八方的涓涓細流,因而才能成就大江大河的恢宏氣象,此正是“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由此觀之,強調國學更需要超越國學。傳承與超越永遠是中華文化流動的根脈,超今越古,才是未來國學發展的康莊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