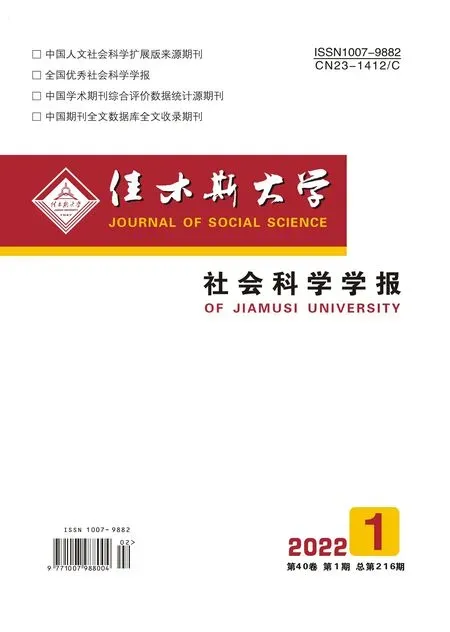撒拉族“花兒”的保護與傳承研究*
陜錦風
(青海民族大學,青海 西寧 810007)
分布在青海省的撒拉族是我國28個人口較少民族之一,因自稱“撒拉爾”,簡稱“撒拉”而得名。據史書記載,撒拉族是古代西突厥烏古斯部撒魯爾的后裔,撒拉族祖先尕勒莽、阿合莽與部落首領產生分歧后遂率其部眾,于13世紀從中亞撒馬爾罕一帶出發,一路向東遷徙,最終定居在今天的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縣街子地區。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撒拉族總人口數為10.45萬人,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及周邊地區,聚居比較集中。撒拉族先民帶著中亞的文化,定居青海省循化縣街子地區后,與當地世居民族——漢族、回族、藏族等多民族雜居,共生互融,深受游牧文明、農耕文明及宗教文化的影響,形成了撒拉族文化兼容并蓄的特點。
“花兒”是流行于廣大西北地區、多個民族共同演唱的一種民歌,也是世界上極為罕見的由多個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俗文化的民族共同創造,卻主要用一種語言——漢語演唱的民歌。清人吳鎮曾說:“花兒饒比興,番女亦風流”,可見,西北花兒的流傳時間之久,演唱民族之眾。甘肅、青海、寧夏等省區是“花兒”的主要流行區域,演唱民族有漢、回、土、藏、東鄉、保安、撒拉、裕固等八個民族。“花兒”流行區域廣闊、歷史源遠流長、歌詞曲令豐富,是西北地區諸多民族的地方性口頭傳統。獲得多個響亮的美譽,如“大西北之魂”“活著的《詩經》”“西北的百科全書”等,并于2006年、2009年分別入選中國和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一般情況下,“花兒”被視為情歌,但也有不少的“花兒”作品反映民眾的現實生活及思想感情。數百年來,“花兒”一直流傳在大西北的鄉村、田野、深山,反映或表達生活在曾經廣袤而又貧瘠的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或歡樂、或憂傷、或苦難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西北“花兒”在民俗圈中既體現出這些民族的精神氣質、文化心理、演唱藝術等方面的共性,又反映出各個民族習俗的個性。但是在當下,作為“花兒”重要組成部分的撒拉族“花兒”,處于瀕危狀態。本文通過對撒拉族“花兒”現狀的調查分析,探討撒拉族“花兒”的傳承與保護路徑。
二、 撒拉族“花兒”現狀
撒拉族“花兒”豐富了西北“花兒”的內容和風格。它來源于撒拉族民眾的日常生活和生產實踐,成為撒拉族民眾表達愛情的主要媒介,也是表達對生活的感受和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
(一)撒拉族“玉爾”
“玉爾”和“花兒”是撒拉族民歌的兩種重要類型。“玉爾”是撒拉語,由突厥語轉化而來,原意是“詩歌”,也被稱作“撒拉曲”,是用撒拉語演唱的一種民間傳統情歌。據青海師范大學藝術學院張蓮葵教授研究分析,認為撒拉曲的旋律和烏孜別克、土庫曼等中亞民族的民歌沒有聯系,所以“撒拉曲”并非產生在撒拉族先民東遷之前,而是在定居青海之后[1]。筆者認為,在使用突厥語的中亞民族中,有“葉爾”“依里”等名稱的傳統情歌,由此可以推測,撒拉族“玉爾”應是撒拉族先民遷居中國后,受到周邊民族的影響,形成語言上保持本民族語言,形式卻是受到當地其他民族民歌的影響的獨具特色的演唱形式。
撒拉族民眾用本民族的突厥語演唱“玉爾”,一般是男女對唱或獨唱,大多表達撒拉族青年男女對婚姻自由和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與封建禮教抗爭的精神。因受到宗教及封建禮教的約束和禁忌,所以“玉爾”的演唱場合受到很嚴格的限制:不準放聲大唱,只能小聲哼唱;也不能在家中、村宅中及有長輩和晚輩同時在場的場合演唱,只能在田間、野外、磨房等背人處演唱。
撒拉族“玉爾”和其他民族的“花兒”一樣,也采用“花兒”常見的比興手法。用生活環境周圍的花草、飛禽、走獸及日常生活用具等,借物抒情,借物喻人。并先言他物,形成起興句,以引起所詠之辭。比如下面這首:白土灘灘里,榆樹葉兒展,河灘地里吆,麥苗綠油油/拔草的艷姑們,好像大雁排成行,右手拿的拔草鏟,左手貼臉唱玉爾。這些修辭手法的運用,使得撒拉族“玉爾”表達生動鮮明,增強了韻味和感染力。一曲“玉爾”一般由數首構成,多采用重章疊句的形式,語言富于口語化特色。“玉爾”的曲調一般為一歌一曲,演唱時可以即興編詞,反復演唱,旋律可隨唱詞不同即興改變。每首又有三句、四句或五句之別,唱詞的基本形式是五言,也有六言、七言。撒拉族“玉爾”傳世之作數量不多,現存的僅有《巴西古溜溜》《尕格尕耶乃安》《阿依吉固毛》《撒拉賽西巴尕》等幾首。其中,《巴西古溜溜》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女)巴西古溜溜①,白號帽哈斜戴上呀,腰兒細溜溜,腰帶系上胡都好②/腿兒粗桿桿,裹腿裹上多帶勁,你這個阿哥呀,只有尕妹來陪襯/美俊的阿哥呀,你若聽得來,話出我心坎,你若聽不來,話出我舌尖/(男)皇上阿吾尼 ,吹的竹笛桿,節節奏妙音/你這個艷姑呀,身材象翠竹,生來就干散/皇上阿吾尼,走馬的黑尾巴,挽成一咕嘟蒜/你這個艷姑呀,頭發賽過馬尾巴,辮子梳成兩條龍/熱情的艷姑呀,你先要甭著急,你先甭熬煎,阿哥定娶你/若是阿哥不娶你,陽世三間里沒活頭,活著世上也不甜。這首“玉爾”表現了撒拉族青年男女互相贊美對方的姿容和裝束,表達相互之間的愛慕之情。運用了比和興的表現手法,用“翠竹”和“黑馬尾”比喻“艷姑”的身材和頭發,并用“竹笛桿”和“黑馬尾”起興,引起“艷姑身材像翠竹”和“頭發賽馬尾”。隨著社會的發展,撒拉族傳統情歌“玉爾”已逐漸被“花兒”取而代之,目前傳承處于瀕危狀態。
(二)撒拉族“花兒”
“花兒”這種民歌之所以有如此美妙的名稱,是因為歌詞中經常把女子比喻為花朵。撒拉族“花兒”也稱為“撒拉少年”,也叫“野曲”,多為情歌,也有抒發對現實生活的感受等主題。不同于“玉爾”的是,撒拉族“花兒”是用漢語演唱,有獨唱、對唱、合唱等多種演唱形式。有學者研究認為撒拉族大約在元代初期遷入青海,所以撒拉族“花兒”產生的年代可能是在明代中葉,因為只有在撒拉族民眾普遍掌握了漢語之后,“花兒”這種用漢語演唱的山歌才可能在撒拉人中廣泛流傳[2]。 據張連葵教授調查研究,撒拉族“花兒”(少年)曲令多樣,最常見的有“撒拉大令”“清水令”“孟達令”“三花草令”“水紅花令”“大眼睛令”等[1],每種令都別有韻味。撒拉族“花兒”的篇幅可以用分節的形式任意增加,能表現更加豐富的內容。因此,撒拉族“花兒”分長調子和短調子兩種形式。長調子由若干節組成,篇幅較長,曲調纏綿婉轉、徐緩悠長,形象生動;而短調子篇幅短小,曲調抒情歡快、平和流暢,結構規整,節奏鮮明。
撒拉族“花兒”的歌詞受到其他民族“花兒”的影響,一般也是四句或六句一首。四句式最常見,即由四句歌詞構成兩對上下句,每句字數基本一致,分為上下兩個樂句,也稱為“頭尾齊”式。如:大力加埡豁里過來了,撒拉的地方上到了;撒拉的艷姑是好艷姑,腳大(么)手大者壞了/大力加埡豁里過來了,撒拉的艷姑(哈)見了,腳大(么)手大的甭談嫌,走兩步大路是干散/白莊(么)清水里過來了,艷姑們走下的正了,端溜溜身材大眼睛,尕模樣咋這(么)俊了/青緞子號帽哈斜戴上,緊身的夾夾(哈)套上,不走大路串塄坎,要唱個“花兒”么“少年”。這是由四首構成的一段長調子,每一首四句,結構形式基本固定,與漢族、回族的“花兒”基本一致,每首的句數固定,節奏也相似,與漢族、回族的“花兒”基本一致。除了四句式以外,撒拉族花兒也有六句式。六句式則是在四句式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即在四句式的每對上下句之間,加進一個3至5字的半截句,形成一四句、二五句、三六句兩兩相對,被當地民眾形象地稱為“兩擔水”或“折斷腰”。如“三間的大房立起了,油漆上,花槽(哈)啊時候按哩;我倆的事情現成了,放心了,一搭里阿時候到哩?”又如“上天的梯子你搭上,我倆人上,天上的星星(哈)摘上;豁出個命來刀山上,緊跟上,五尺的身子(哈)舍上。”“兩擔水”句式增加了歌詞的容量,并且使節奏富于變化。
撒拉族“花兒”的演唱技巧,受到青藏高原歷史悠久的世居民族——藏族所采用的一種古老的歌唱傳統的影響。游牧民族特殊的生存環境造就了藏族民歌高亢悠揚的風格,撒拉族“花兒”也有相似的特點。再加上當地方言的運用,使其演唱風格形成獨特的個性特征,相比其他民族的“花兒”別有韻味,獨具一格。
三、多種因素對撒拉族“花兒”的影響
一個民族的歌謠風格的形成與該民族的地理環境、歷史演進、語言、宗教信仰等多種因素密切相關。撒拉族先民于元初從中亞撒馬爾罕(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遷徙到達青海省循化縣一帶定居后,與當地的世居民族——藏、回、漢等民族長期雜居,交流互融,深受游牧文明、農業文明等影響,逐步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民族共同體——撒拉族。因此,撒拉族文化是多元文化的聚合體,既有中亞先民的文化元素,又有回族、藏族等民族的文化因子,體現了撒拉族文化和其他周邊民族文化的共生性、融合性和兼容性。撒拉族“花兒”作為撒拉族文化的一種表現方式,也同樣體現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點,形成獨特的風格與音樂特征,使其成為地域標志性民歌。
(一)撒拉族“花兒”受到傳統情歌“玉爾”的影響
可以從僅存的幾首“玉爾”中看出撒拉族“花兒”與“玉爾”之間極密切的聯系。撒拉族“花兒”是用漢語演唱,以青海漢語方言為基礎,但在唱詞中出現部分撒拉族詞匯或在句中加“哎西”等有撒拉族特色的襯詞,體現為“玉爾”的影響。如:“(哎吆)刀槍(吆)矛子(者)甭害怕(呀,哎西),沒犯(個)法(呀),九龍的口里站下;尕妹是宮燈(者)阿哥是蠟(呀,哎西),大堂上掛,紅燈的口兒里把蠟照下”。這首六句式“花兒”,為了便于歌唱加了襯字“喲,者,呀”,這是“花兒”的常見特點,襯詞“哎西”是撒拉語中常用的語氣助詞。這里的“甭”讀作“bao”,這里的“站下”讀作“zhanha”,“照下”讀作“zhaoha”,體現出青海方言的特點。撒拉族“花兒”具有獨特的藝術特色,富有表現力,表現出濃郁的民族韻味和鄉土氣息。婉轉悠揚的撒拉族“花兒”是青年男女傳遞愛情的一種重要手段,把姑娘稱作“花兒”,小伙子叫作“少年”,合起來就是“花兒與少年”,隨著撒拉族的發展歷史世代流傳。
(二)撒拉族“花兒”受到漢族、回族文化的影響
撒拉族初到循化地區,受到當地同說漢語的漢族、回族的影響,逐漸掌握漢語,使撒拉族民歌演唱由只用撒拉族演唱的“玉爾”演變創新出用漢語演唱的“花兒”。宗教信仰的一致和風俗習慣的相近,使回族文化成為補充撒拉族文化的重要來源。另外,伊斯蘭教是撒拉族的主要信仰,對其歷史發展和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都產生深遠影響,撒拉族“花兒”就是在這樣的多元文化背景下產生的。撒拉族在自己母語的基礎上還吸收糅合進了阿拉伯語、波斯語等語言成分。因撒拉族沒有保留下本民族的文字,所以常借用漢語詞匯,撒拉族“花兒”的歌詞結構與漢、回族“花兒”大同小異。這些語言特點使撒拉族花兒的風格顯示出獨特之處,并在調式上具有多樣化的特征。如下面這一首《孟達令》,因主要流傳在孟達鄉一帶而得名,歌詞如下:(哎吆)前川后川(哎吆)川套(了)川,下川里(嘛)馱來了果(呀)子;(哎吆)你唱的舌焦(哎吆)口又(了)干,尕妹妹(嘛)潤上個嗓(呀)子。這首四句式花兒,這里的襯字“嘛、了、呀”是為了在演唱時便于聲音的過渡,口語化明顯,這些襯詞對花兒曲令的演唱特色都造成了影響。
(三)撒拉族“花兒”還受到藏族民歌的影響
撒拉族先民初到青海省循化地區時,與當地的世居民族——藏族通婚,與藏族有過交往甚密的關系。因此,由于和周圍藏族的頻繁交往,很多撒拉族民眾都能說一口流利的藏語,語言中自然出現一些藏語借詞。撒拉族“花兒”的風格具有各族“花兒”的共性之外,還具有藏族民歌奔放悠揚和善于抒情的風格,這是因為撒拉族花兒吸收了藏族山歌“拉伊”、藏族酒曲“勒”的特點。“拉伊”是青海藏族表現愛情的山歌,歌聲婉轉抒情,優美動聽,給人以柔和、親切的感覺。“勒”是藏族一種獨唱形式的民歌,高亢悠揚、奔放自由、抒情優美,極富高原特色。撒拉族“花兒”吸收了藏族民歌的特色,顯得獨具韻味。
四、 撒拉族“花兒”的保護與傳承路徑
2009年9月,“花兒”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可以讓“花兒”獲得更好的傳承和弘揚,進一步加大對西北“花兒”的保護、傳承及對其傳承人的保護與扶持。“花兒”是我國西北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間文化多元一體的典型案例。換言之,多民族“共創共享”正是“花兒”的顯著特點。所以,西北各民族必須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覺意識,牢固樹立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價值觀念,使“花兒”在新時代進一步得以傳承與弘揚。撒拉族“花兒”作為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具有自己鮮明的特色,需要對其進行相適宜的傳承與保護。當前,撒拉族“花兒”傳承面臨的困境是農村城鎮化進程加快,撒拉族民眾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態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改變了作為原生態民歌的撒拉族“花兒”生存空間,使之失去了生存的文化土壤,傳播受到了影響和阻礙,生存空間逐漸萎縮。根據撒拉族“花兒”的現狀,筆者提出以下四個方面的保護和傳承路徑。
(一)重視活態傳承
長期以來,人們把對包括撒拉族“花兒”在內的西北各族“花兒”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拍錄、研究等工作,看作是最主要的保護措施。這對于活態的民間文化而言,只是一種“博物館式”的保存,是僵死的保存方式。“花兒”作為一種活形態的民歌,應該以活態的形式傳承,讓它在民眾生活中反復出現,才能真正實現傳承和弘揚。
“花兒”作為民間口頭傳統,其傳承路徑主要是民間“花兒”歌者的代代口耳相傳。在傳承與保護過程中,“花兒”傳承人的重要地位與積極作用是舉足輕重的。而在當下,口頭傳統類非遺面臨的最大危機就是傳承人后繼無人。所以,保護和傳承撒拉族“花兒”,首先要保護與扶持那些今天依然健在的、為數不多的撒拉族“花兒”傳承人——真正的民間老歌手、老唱把式、原生態“花兒”創造者,因為他們是撒拉族“花兒”文化的“活化石”。目前,撒拉族民歌傳承人只有韓英德一位,是一位省級傳承人,其他的撒拉族“花兒”歌手大多已故或年事已高,而一些喜歡唱“花兒”的年輕人,又忙于外出打工掙錢,無暇顧及“花兒”的傳承與保護。對傳承人的保護,主要是提供生存、生活方面相關的保障,政府給予其一定的經濟補償和生活方面的幫助,讓他們能后顧無憂地為傳承本民族的文化遺產做出貢獻。
非遺的世代相傳,不是同一種文化以同一種方式永遠不變地傳下去,而是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成為不斷演進的民間文化的重要形式。“花兒”本身具有濃郁的原生態性、民族性和地域性,撒拉族“花兒”的歌者,用發自內心的歌聲歌唱出不同風格、不同曲令的優秀作品。因此,撒拉族“花兒”在新時代,要創造出與時代相符的新曲目。
(二)民眾的文化自覺意識
“文化自覺”概念是由費孝通先生于1997年首次提出,其基本內涵指生活在一定文化歷史圈的人對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換言之,文化自覺就是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自我創建。費先生進一步指出“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只有在認識自身文化,理解并接觸到多種文化的基礎上,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確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種文化都能和平共處、各抒所長、連手發展的共處原則。”[3]
對于“花兒”的傳承與發揚,一方面需要國家的保護機制和政策法規保駕護航,廣泛傳承與積極保護,努力提高這項文化遺產自身的社會地位,使更多的各族民眾能夠樂于接受和重新喜愛這項珍貴的文化遺產,并重新找到它在現代社會的多元價值及其深遠意義。中國于2010年頒布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各級政府部門也制定出相應的規章制度,使“花兒”等非遺的傳承與保護有了國家層面的保障。另一方面,各民族的每一個成員才是這項文化遺產真正的主人,每一位成員,尤其是年青一代都有關注和自覺傳承文化遺產的責任。2005年,時任中國文化部部長孫家正強調,非遺保護首先應該是全民的一種文化自覺[4]。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倫理原則》,使文化遺產持有者在遺產保護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權利得到進一步重視。因此,文化遺產持有者的文化自覺才是遺產保護的最重要的根本因素。撒拉族“花兒”傳承至今留下了不少原汁原味的“花兒”作品,是歷代撒拉族民眾的思想和智慧的結晶,它記錄的不僅是撒拉民眾的傳統風俗,更是表現出他們特有的文化心理和價值觀念。所以,只有每一位撒拉族成員保有對“花兒”的喜愛和認可,認識到“花兒”對撒拉族文化的重要意義,自覺去傳唱,才有可能將撒拉族“花兒”傳承下去。如果作為撒拉族花兒的傳承主體——撒拉族民眾主動放棄對“花兒”的喜愛和傳唱,只靠政府的外圍保護,那么撒拉族“花兒”的傳承會舉步維艱,甚至很快斷代。通過“讓花兒進校園”等形式,進入中小學音樂課堂,讓撒拉族兒童從小接觸花兒,學習花兒、喜歡花兒,使得撒拉族“花兒”代代相傳。
(三)通過舞臺表演進行傳播
非遺的傳承與保護還要順應時代發展的新需求,與時俱進。開發利用撒拉族“花兒”的文化價值,來促進撒拉族“花兒”藝術的發展與繁榮。為了更好地適應新時代人民群眾的新要求,要逐步將一些撒拉族“花兒”經典曲目和藝術元素經過藝術家加工、創新和再度創作,使古老的民間“花兒”藝術走出田野山林,產生一些類似流行歌曲式的通俗曲目,讓它得以快速流行和傳播,讓更多的民眾接受和喜愛。若在撒拉族地區舉辦大型花兒會,因宗教和傳統觀念的原因,困難較大,但可以通過利用影劇院等場所,舉辦“花兒”演唱會、“花兒”演唱比賽等形式,將其搬上舞臺,讓更多的年輕人參與進來,可以使愛好”花兒”的年青一代通過這樣一個平臺增強對“花兒”的熱愛和傳承。
撒拉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豐富,是其在漫長的發展演進歷史中形成的獨具民族特色、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風俗習慣和社會文化的總和,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撒拉族地區而言是極具吸引力的民族地方旅游資源。因此,可以借助一些大型活動或場所為平臺,將撒拉族“花兒”與當地的旅游業結合起來進行舞臺表演。比如循化撒拉族自治縣每年承辦“國際黃河搶渡賽”,從各地來觀賽的各族群眾人數眾多,這是一個很好的可以通過舞臺形式表演和傳播“花兒”的機會。還有在國家對人口較少民族扶持的背景下興建的“撒拉爾故里民俗園”成為循化縣重要的景點,也可以在此進行“花兒”的舞臺表演,使其成為撒拉族地區的民族文化旅游資源。
(四)數字化保護
在活態保護的同時,還要加強對于“花兒”的靜態保護,搶救、保護、傳承和弘揚原創性的花兒音樂及其唱詞。撒拉族“花兒”中的不少曲調是由撒馬爾罕遷來的先民們帶入并流傳下來的。目前,撒拉族聚居地區的傳統情歌“玉爾”已逐漸被漢語演唱的“花兒”取而代之,陷入瀕危境地,主要傳承人年事已高,大部分曲目面臨消失,所以用視頻、音頻形式將它記錄下來尤為重要。近年來,當地政府日益重視對撒拉民歌的搜集、整理及數字化保護工作,出現了一批關于撒拉族“玉爾”的數字化成果。據青海省委黨校楊明委教授調查統計:2009年,央視音樂頻道的“民歌中國”欄目錄制的《民歌經典》《民歌·發現》等節目中,通過訪談和民俗歌舞演示的方式,將撒拉族“玉爾”部分經典曲目進行數字化展現;2013年,循化當地政府收錄和翻譯了《阿麗瑪》《巴里巴加》《搖籃曲》《連枷號子》等19首撒拉語民歌,其中一部分是瀕臨消亡的撒拉族“玉爾”作品[5]。
撒拉族“花兒”的數字化保護不僅僅是對歌詞、曲目的數字化,還要保護與其相關的文化空間。同時,也要對現存的撒拉族“花兒”進行數字化保護,可以通過唱片錄制的形式傳播,并且以現存的這些曲目和曲令為參考,在以后的撒拉族“花兒”的傳承創新中發揮借鑒作用。數字視頻既包含音頻,也包含圖像,配上字幕可以讓人們了解視頻內容的同時,也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撒拉語唱腔,多個角度的拍攝還可以彌補局部的細節,相比于文字和圖像的數字化方式更具有直觀性。撒拉族“花兒”的數字化保護不僅僅是對歌詞、曲目的數字化,還要保護與其相關的文化空間。除此之外,互聯網也是撒拉族“花兒”傳播和傳承的重要媒介。可以利用互聯網無可匹敵的大眾傳播的能量為口頭傳統創造全新的生存空間,它可以迅速擴大公眾關注度,使區域性的口頭傳統逐漸走進公眾視野,也為口頭傳統的可持續性傳承準備了良好的文化土壤。
五、結語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全球化背景下,每一個國家和民族都要關心自身的身份建構,而非物質文化遺產體現著文化的個別性和地區的差異性,也是人類文化多樣性的體現。撒拉族“花兒”既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又富有深刻的思想價值和珍貴的史料價值。它不僅豐富了西北”花兒”的內容和風格,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而且是研究撒拉族地區的歷史、信仰、民俗等方面重要的口傳資料。因此,保護和傳承撒拉族“花兒”的意義至關重要。
對撒拉族“花兒”的保護和傳承,要充分調動和發揮其流傳地區社會各界的力量,包括政府部門、文化部門及其相關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專家學者、民間歌手、社會團體、學校、新聞媒體、網絡平臺等多方面的綜合力量。但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關鍵在于遺產傳承主體的文化自覺,即傳承主體能夠在自我認識的基礎上進行主動自覺的文化實踐。同時,要注重撒拉族“花兒”的活態傳承,保持它的原汁原味,以及與撒拉族民眾的民俗生活密切聯系,能及時反映當地民眾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為當地民眾所接納,并創作出新的“花兒”曲目和曲令。重新找到它在現代撒拉族社會中的文化價值及現實意義,諸如在繁榮民族民間文化事業,或者形成地方品牌旅游資源等方面的潛在優勢和積極作用,使之在新時代得以有效的保護和傳承。
[注 釋]
①撒拉語,意為“圓圓的頭”。
②撒拉語,意為“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