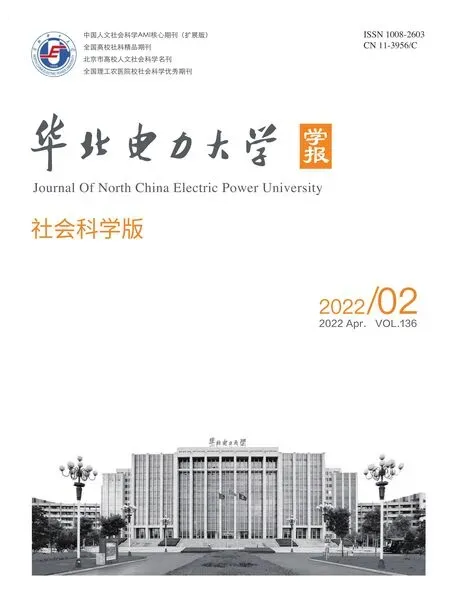農民收入增長:分化與均衡
曹 紅
(首都醫科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100069)
改革開放40 余年來,在整個國家經濟迅速發展和農村改革不斷推進的雙重帶動下,中國農民收入①在本文中“農民收入”和“人均收入”一般指“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成倍數增長,從1978 年的人均純收入134 元以年均提升12.43%的高速率迅速增長至2020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 元②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年度報表與最新發布的相關數據。。然而,伴隨著農民人均收入的迅速攀升,分化現象越來越嚴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在鄉村最為突出”[1]。
一、農民收入增長的分化現象
農民收入增長中的分化現象有三重表現:一是愈加明顯的農村社會內部家庭之間的分化情況,二是農村居民家庭比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分化現象更明顯,三是地區之間農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分化程度較為突出。
(一)農村家庭之間收入增長分化情況突出
農民收入增長中的分化現象最主要地表現在農民家庭之間人均收入增長的分化上。將農村家庭按人均收入的高低分為五個組別,可以發現,從2013 年到2019 年①由于國家統計局從2013 年開始不再統計“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而將統計指標更改為“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者在具體統計范圍上存在一定的差別,因此本文只討論2013 年以來的關于農民收入的相關數據。,越低收入農村家庭其人均收入的增長率越低且增長穩定性越差,越高收入農村家庭人均收入增長率越高且增長穩定性越強,這種“馬太效應”直接導致了農村家庭之間在收入增長上愈加突出的分化現象。
具體來看,從2013 年到2019 年,農村低收入組家庭人均收入由2877.9 元較慢度增長至4262.6 元,2014 年到2019 年的年均增速為7.04%,在五組收入中增速最低;中間偏下收入組人均收入由5965.6 元增長至9754.1 元,6 年間的平均增速為8.61%,高于低收入組1.57 個百分點;中間收入組家庭人均收入從8438.3 元以年均提升1.57 個百分點的速率增加至13984.2 元,平均增速略高于中間偏下收入組,為8.82%,排名居中;中間偏上收入組人均收入以年均提升1.49 個百分點的速率從11816.0 元增長至19732.4 元,年均增速為8.95%;高收入組家庭人均收入則以年均提高1.53 個百分點的高速率從21323.7 元增長到36049.4 元,不僅其年均增速在五組收入戶中最高,而且也是唯一超過9%的,為9.16%。綜合來看,在2014 年到2019 年,農村五組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7.04%、8.61%、8.82%、8.95%、9.16%,呈現出鮮明的由低到高排列的情況。這種情況直接導致了從2013 年到2019 年農村五組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比值總體上不斷拉大:在2013 年,從低收入組到高收入組的人均收入的比值關系為1.00:2.07:2.93:4.11:7.41(低收入組人均收入為1.00);之后五組之間的比值持續拉大,到2016 年,中間三組與低收入組的比值差距最大,比值關系變為1.00:2.60:3.71:5.23:9.46;到2017 年,高收入組與低收入組的比值拉到最大,比值關系變為1.00:2.53:3.63:5.13:9.48;而僅在2018 年農村五個組別人均收入的差距才開始全面縮小,但是到2019 年五組之間的比值差距依然較大,為1.00:2.29:3.28:4.63:8.46②數據通過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中國統計年鑒-2020》中“6-12農村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數據計算得出。。因此,即便從2018 年開始農民家庭之間人均收入差距開始縮小,但從2013 年到2019 年整體來看其人均收入處于不斷拉大的局面。因此,農民家庭內部呈現出的越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增速越低、越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增速越高的情況直接導致了低收入農民家庭人均收入越低、高收入農民家庭人均收入越高,這種情況可以稱為農村社會內部的“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家庭收入分化現象。
不僅如此,這種農村社會內部收入增長的分化現象還伴隨著越高收入農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長波動性越小、穩定性越強,越低收入農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長起伏性越大、穩定性越差的情形。6 年間,農村五組家庭人均收入年度增長率的最高值與最低值之差分別是20.08、12.72、8.02、7.28、6.41 個百分點,數值依次下降意味著越低收入農民家庭人均收入年度增長率的最高值與最低值的差距越大,而越高收入農村家庭則相反,并且在這6 年中的負增長情況均出現在低收入組之中(2014 年的-3.82%、2016 年的-2.56%)③同注釋②。。因此,農村五組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增長的穩定性隨著其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強,農村社會內部家庭人均收入增長的分化情況也表現于此。
(二)農民收入增長上的分化程度比城鎮居民更為明顯
“現代化帶來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鄉差距。”[2]農民收入增長的分化情況更突出地表現在與城鎮居民的對比上。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的分化情況不僅在整體上表現為其人均收入的差距依然較大,而且從收入來源來看農民財產凈收入數額小比重低,此外,農村社會內部家庭間收入增長上的分化程度也明顯高于城鎮居民。
首先,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依然突出。雖然從2013 年到2020 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在縮小,二者之比從2.81:1.00(農民人均收入為1.00)下降至2.56:1.00,趨勢比較樂觀;但是即便到2020 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依然相差1.5 倍以上,其與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最低比值(1983 年的1.82:1.00)依舊存在較大差距。所以,即便2010 年以來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逐漸縮小,但遠未達到一個較理想的狀態。并且,從絕對數字來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還在逐漸拉大:2010 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相差12506.7 元,到2020 年二者之差擴大到了26703.0 元,絕對差距拉大了一倍有余①數據通過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中國統計年鑒-2020》中“6-6城鎮居民人均收支情況”與“6-11農村居民人均收支情況”中的數據以及最新發布的數據計算得出。。因此,無論從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之比還是從二者的絕對數額差距來看,城鄉居民之間人均收入的差距依舊比較突出。
其次,農民財產凈收入數額過小、占比太低。雖然從2014 年到2020 年農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速高于城鎮居民1.42 個百分點,達到了8.91%,其中農民人均財產凈收入年均增速達到了11.59%,高于城鎮居民2.69 個百分點,總體上看,農民人均收入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快速增長趨勢。但是,農民財產凈收入相對于城鎮居民來說數額很小,因此,即便其增速較高,其在人均收入中的占比依然很低。2013 年農民人均財產凈收入僅有194.7 元,僅占其人均收入的2.06%,而當年城鎮居民人均財產凈收入就達到了2551.5 元,是農民人均財產凈收入的13.10 倍;即便在這7 年間農民財產凈收入增速高于城鎮居民,到2020 年農民財產凈收入也只有419.0 元,占比也僅有2.45%,而當年城鎮居民財產凈收入就已達到了4627.0 元,是農民的11.04 倍②同注釋①。。因此,與城鎮居民人均財產凈收入相比,2013 年到2020 年,農民人均財產凈收入不僅數額過小而且比重很低,說明廣大農民基本上處于一種有收入無財產的境地。
最后,農村居民家庭之間的收入分化程度明顯高于城鎮居民。從2014 年到2019 年,城鎮居民家庭五個組別人均可支配收入從低收入組到高收入組的年均增長率分別是7.86%、7.27%、7.79%、8.40%、8.02%。總體上看,在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五個組別中最高與最低年均增長率相差較小,只有1.13 個百分點,而五組農民家庭則相差2.12 個百分點,比城鎮居民高出約1 個百分點。并且,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五個組別最低增長率不在低收入組,最高增長率不在高收入組,其在人均收入增長上錯落有致,并無明顯的“馬太效應”出現。由此,城鎮五個組別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關系也并無明顯的變化:2013 年五組比例關系為1.00:1.78:2.44:3.30:5.84(低收入組為1.00),2016 年后四組與低收入組的比值均有略微的降低,比例關系變為1.00:1.77:2.42:3.21:5.41,而到2019 年中間偏下收入組與低收入組的比值降低,其余三組與低收入組的比值與2016 年相比略微提升,比例關系由此變為1.00:1.72:2.44:3.40:5.90。因此,從城鎮五組家庭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長率和比值關系變化來看,城鎮居民家庭之間人均收入的分化程度比農村居民家庭要低。
(三)地區之間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存在明顯差距
農民收入增長在地區之間也存在明顯的分化現象。一方面,從2013 年到2019 年,東、中、西部及東北地區四個地區的農民收入在絕對數字上差距較大,且絕對數字差距在持續拉大;另一方面,由于東北地區農民收入增速最低,其相較于中部和西部兩地農民收入的優勢在降低。
具體來看,在2014 年到2019 年,東、中、西部及東北地區農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長率分別為9.10%、9.27%、9.81%、7.85%。可見,西部地區農民收入增長率最高,中部次之,東部地區農民收入增長率較低,而東北地區農民收入增長率在四個地區中不僅是最低的,而且與其他三個地區存在明顯差距,比平均增速較低的東部地區低1.25%。由此,從2013 年到2019 年,東、中、西部、東北四個地區農民收入的增長情況各不相同:西部地區農民收入由7436.6 元以年均提升1.63%的速率迅速增長至13035.3 元,年均增速最高;中部地區農民收入以年均提升1.55%的速率從8983.2 元增長至15290.5 元,年均增速排名第二;東部地區農民收入則以年均提升1.52 個百分點的速率從11856.8 元增長到了19988.6 元,雖然年均增速相對較低,但其收入基礎卻是四個地區中最高的;東北地區農民收入則由9761.5 元增長至15356.7 元,年均提升1.31%,提升速率最慢。由此,東、中、西、東北四個地區農民收入的比值關系由2013 年的1.59:1.21:1.00:1.31(西部地區農民收入為1.00)變化到了2019 年的1.53:1.17:1.00:1.18,東、中、東北三個地區與西部地區農民收入的比值降幅雖小,但表現出持續下降的良好趨勢。但是,總體來看,一方面,地區之間農民收入絕對數額差距較為明顯。雖然在2014 年到2019 年農民收入最低的西部地區平均增速最高,與其他三個地區的收入差距不斷縮小,但在絕對數額上差距仍舊較大,即便在2019 年中部地區農民收入還高于西部2255.2 元,收入最高的東部地區更是比西部多出6953.3 元。因此,地區之間農民收入的絕對差距依舊突出。另一方面,東北地區農民收入增長較為緩慢。在2013 年,東北地區農民收入僅次于東部地區,為9761.5 元,比當年收入排名第三的中部地區多出了778.3 元;但是到2019 年,東北地區農民收入僅比中部多出了66.2 元,差額很小,這意味著東北地區在四個地區中的農民收入優勢明顯降低①數據通過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中國統計年鑒-2020》中“6-13 農村居民按東、中、西部及東北地區分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數據計算得出。。由此,農民收入增長在地區之間也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分化情況。
二、促進農民收入均衡增長的主要原則
以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為主要標志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業已勝利完結,我國農村地區在“后小康”時代將進入以鄉村振興戰略為藍圖的全面發展和繁榮的新時期。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中,促進占五分之二農村人口收入實現持續和均衡增長,需要堅持和把握以下原則。
(一)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則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3]農民期盼有更滿意的收入,使農民內部之間、農民與市民之間、地區農民之間的收入實現更加均衡的增長,就需要黨和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發揮促進公平的重要作用。“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4],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5]。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更是將“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列為到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最重要的遠景目標之一。[6]因此,緩解農民收入增長分化情況、促進農民收入實現持續均衡增長,需要黨和政府在改革中堅持共同富裕這個根本原則,在推動收入公平分配中發揮更大作用。
早在1992 年鄧小平分析中國地區之間貧富兩極分化時,就提出“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7]374。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問題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為農民與市民收入差距較大的問題。以2019 年大陸省域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城鎮化率、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三個指標來分析省份之間的貧富差距可以發現,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越低的省份其城鎮化率越低,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越大。以2019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后五位的省份為例:甘肅省居民人均收入為19139.0 元,在大陸31 個省份中排名最末,其城鎮化率也僅有48.49%,排名倒數第二位,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為3.36,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31 個省域內是最大的;西藏自治區以居民人均收入19501.3 元排名倒數第二位,其城鎮化率以31.54%排名最末,而其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之比為2.89,位居第六位(以數值高低排列);貴州省居民人均收入以20397.4 元名列倒數第三位,其城鎮化率只有49.02%,排名倒數第四位,其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以3.20 之高排名第二;云南省居民人均收入為22082.4 元,位列倒數第四,城鎮化率以48.91%排名倒數第三,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為3.04,排名第三;青海省則以居民人均收入22617.7 元排名倒數第五位,其城鎮化率以55.52%排名倒數第九位,其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為2.94,名列第四①數據通過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中國統計年鑒-2020》中“2-8分地區人口的城鄉構成和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2019 年)”“6-17分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3分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9分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數據計算得出。。由此可見,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表現,即地區間人均收入差距的本質是城鄉居民收入存在差距。因此,今后要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主要目標,使農民收入保持不落后于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著力挖掘和開拓農民收入增長的新來源、培養促進農民收入穩定持續增長的新動能,最終使農民與市民收入在絕對數額上達到同一水平。
(二)最低保障的基礎原則
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勝利完結最重要的標志,但是在全面開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還須將廣大農村低收入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納入重點考慮的范圍,由此,在促進農村社會內部家庭收入均衡增長中須堅持最低保障這一基礎性原則。
農村改革40 余年來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到2020 年末“近1 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兩個重要指標是財產和收入,資產或財產是存量概念,而收入則是“財富的服務”,是“一段時間的服務流量”[9]。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一部分農民只是實現了溫飽自足,并未積累多少通過資產交易使自身收入得到持續提高的財產。脫貧之后的農村家庭以及低收入農村家庭如果遇到家庭成員罹患重大疾病、主要勞動力喪失勞動能力、重大災害等困難時,有較大可能在一夜之間一貧如洗甚至背負債務。那么,如何防止低收入農民家庭重返貧困就成為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由此,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中要為低收入和生活困難農民家庭拉起最低生活保障這一“安全線”,這不僅是保障農民家庭個體最低生活的安全線,也是維持農村社會整體基本安定的穩定網。這就需要政府在保障和支持低收入和生活困難農民家庭上投入較多的資金支持。而從2015 年到2018 年,國家財政用于城市和農村的最低生活保障資金支出分別為1665.17 億元、1657.60 億元、1475.83 億元、1462.49 億元,在不斷減少,這雖然是城鄉居民收入不斷增長的良好反映,但也是國家財政對生活困難群眾轉移支付資金減少的直接證明。此外,國家財政在2015 年到2018 年用于自然災害生活救助、臨時救助、特困人員救助供養的三項資金總和分別為487.00 億元、640.55 億元、593.95 億元、582.85 億元,可以看到這三項社會保障資金在2017 年和2018 年明顯減少②數據來源于2016 年至2019 年《中國財政年鑒》中“財經統計資料”中的“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決算收支”。。因此,中央和地方財政應建立各自的農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池,同時適當增加針對農民的臨時性社會救濟資金,從長久性保障和臨時性救濟兩個方面建立起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安全網。作為保障農民最低生活水平的基本制度安排,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應堅持標準性、精準性、動態性,標準性指以縣(縣級市)域為地理范圍、以縣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作為當地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轉移支付的資金標準;精準性指要以居住地、財產存量、收入流量三個指標作為衡量農民家庭申請最低生活保障的主要依據;動態性指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申請標準要與當年當地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保持動態一致,此外,已納入最低生活保障的農民家庭要按照當地縣域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動態標準進行每年度的考察與審核。
由此,在緩解農民收入增長中的分化問題,尤其是在提高低收入農民家庭轉移性收入上,要堅持最低保障這一基礎原則,為低收入農村人口拉起最低保障的安全線和穩定線。
(三)差序格局的秩序原則
“差序格局”源于費孝通論述中國自我為中心的水波紋式的社會基本結構[10],這里借用“差序格局”意指在農民收入增長中出現一定程度的農民內部、城鄉和區域差距是合理的。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中緩解農民收入增長中的分化狀況需要遵守差序格局的秩序原則。
在促進農民收入均衡增長中,絕對的共同富裕并不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也并非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追求的目標。絕對的共同富裕指在一國之內各群體中進行收入分配時堅持平均主義原則,而平均主義卻是一種反對拉開差距的分配不公的表現[11]。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仍應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分配方式。每個人的素質能力和擅長的領域存在先天或后天的差別,所以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分配方式必然導致居民收入存在一定的差別,這種差別應該得到尊重。平均主義和兩極分化都是分配不公平的表現方式,所以絕對的共同富裕和過大的收入差距都是不可取的。而“差序格局的秩序原則”中的“差”指由于每個人在通過自己的能力獲得收入方面必然存在先天或后天的差距,按勞分配必然導致每個人獲得不同數量的收入,但只要這種收入差距在一個合理的范圍之內,不至于導致貧者無法維持基本生活、富者朱門酒肉奢靡不堪,那么這種收入差距應得到肯定;“序”一方面指在農民的收入結構中必然包含一定比例的農業經營收入,而不事農耕的市民其收入結構中工資性收入和經營二、三產業的收入比重更多一些,而在財產凈收入和轉移凈收入的數量和比重上,農民和市民不應存在較大差別,另一方面在農民家庭中較低和較高收入農民家庭都應該是占較小比重的,占較大比例的應該是中等收入農民家庭。由此,“差序格局”肯定農民因能力不同而獲得不同的收入,但這種收入上的差距應該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區間,由此在農民群體內部應形成一個橄欖型的有差異但是有秩序的收入結構。也正因為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才會激勵人們為了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而奮斗,因此合理的收入差距是人們不斷努力和奮斗的良性動力,應該得到肯定和支持。
因此,黨和政府在發揮調節收入分配和促進農民收入均衡增長的作用時,不僅需要堅持共同富裕根本原則,還要堅持最低保障的基礎原則以維持低收入農民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平,同時也須遵守差序格局這一秩序原則,尊重合理的收入差距也是一種收入分配公平公正的表現。
三、促進農民收入均衡增長的制度變革
“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大頭重頭在‘三農’”[12]11,而增加農民收入是“三農”工作的中心任務[13]。促進農民收入實現持續穩定較快的均衡增長需要建立職業農民培養制度、改革農戶宅基地制度、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以三大制度的建立和變革促進農民群體內部、農民與市民以及區域農民之間的收入實現均衡穩定的較快增長。
(一)建立職業農民培養制度增加農業經營收入
增加農民收入的關鍵之一是著力提高務農農民的農業經營收入。但是在2014 年到2020 年的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構成中,經營凈收入是農民四項來源收入中唯一年均增長率低于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 年間,農民人均可支配經營凈收入年均增速只有6.41%,在農民人均收入四項來源中平均增速排名最末,可見增速較低的農民經營凈收入拉低了整個農民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①數據通過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中國統計年鑒-2020》中“6-11農村居民人均收支情況”中以及最新發布的數據計算得出。。而從2014 年到2019 年,農民經營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凈收入年均增速均高于其經營凈收入年均增長率,因此農民較低的經營凈收入增長率是占比最重的第一產業經營凈收入增長乏力的結果。農民第一產業經營凈收入增速緩慢則主要在于占比較重的農業經營凈收入增長速度相對較慢。在2013 年到2019 年,農民農業經營收入不僅在第一產業經營凈收入中占比頗高,其在整個農民人均可支配經營凈收入中也占據著一半左右的較高比重②數據通過《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15》與《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20》中“11-1農村居民可支配收人及構成”中的相關數據計算得出。,但由于占比較高的農民農業經營凈收入增速緩慢,導致農民人均可支配經營凈收入成為農民人均可支配四項來源收入中增速最慢的一項。因此,著力提高農民農業經營收入就成為增加農民收入的關鍵點。
中國傳統的農業經營多以小農作為經營主體。即便到2016 年,全國共有農業經營戶20743 萬,但其中的規模經營戶也只有398 萬,只占農業經營戶的1.92%③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二號)》中的數據。。2016 年全國共有耕地面積13492.1 萬公頃,除去國有農場644.7 萬公頃外,則每戶農業經營戶平均下來不足10 畝耕地④數據通過《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17》中“3-142016 年各地區農用地情況”“13-1農墾系統國有農場基本情況”。此外,2016 年全國6189 萬公頃灌溉耕地面積只占總耕地面積的45.87%,不足一半⑤同注釋③。。因此,“人多地少、人多水少”不僅是我國的最大國情[14],更是我國的基本農情。由此,小農生產依然是中國農業經營的主要方式。“小農是指在特定資源稟賦下以家庭為單位、集生產與消費一體的農業微觀主體”[15]。由于以轉移農村富裕勞動力為實質的城鎮化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12]409,需要“足夠的歷史耐心”,在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征程中還會有相當一部分農民留守農業,因此,需要建立職業農民培養制度以促進農民農業經營凈收入的持續穩定較快增長。只有培養好現代職業農民作為農業經營主體,農民的農業收入安全也才會有保障。
職業農民是“以農業為職業、具有相應的專業技能、收入主要來自農業生產經營并達到相當水平的現代農業從業者。”[16]建立職業農民培養制度,首先,提高全體農民的基礎文化水平。2016 年全國從事農業生產經營人員中只具有初中學歷的人數占比將近一半,為48.4%,而只上過小學的農民則占37.0%,還有6.4%的農民從未接受過任何學校教育,這三部分農業從業者就占據91.8%的比例⑥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五號)》中的數據。。農民的學歷需要提高,這是培養職業農民的基礎。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農民應是具備一定基礎常識性知識和能力,并且在此基礎上能夠學習和掌握先進農業知識和實踐技能的職業農民。擴大土地經營面積進行規模經營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農民農業經營收入,但“人的能力和素質是決定貧富的關鍵”[17]。因此,只有有能力掌握最新農業科技和接收最新市場動向的職業農中的相關數據計算得出。民才能獲得較高的農業經營收入,農民的文化水平便成為培養現代職業農民最重要的基礎。其次,優選中青年農業生產帶頭人接受專門培訓。在2016 年,47.3%從事農業生產經營人員集中在36 歲至54 歲這一中青年階段,還有三分之一左右的55 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在從事農業,因此,中國的農業生產經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中老年農業”。而多數中老年農民并不具備掌握最新農業信息和科技、洞察最新市場走向的能力,所以需要遴選一定數量的中青年農業生產經營帶頭人進行專門培訓。未來的職業農民的帶頭人是全職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中青年人,他們懂生產、會經營并且有敏銳的市場洞察力,不僅明晰市場需求,甚至能夠創造市場需求。最后,在制度和政策上為職業農民的發展創造良好環境。作為弱質產業的農業受到自然和經濟雙重風險的挑戰,光靠農民并不能將農業做大做強,因此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幫助。“農業的發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學”[7]17,因此,還需要在政策創設和制度改革上為職業農民的專業化發展保駕護航。這不僅需要政府財政資金對職業農民的發展予以全方位的支持,也需要不斷改革和完善農產品市場價格形成機制和重要農產品支持保護機制,使職業農民全心全意從事農業生產經營,保障好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農產品供給市場安全和保障自身的收入安全。總之,“主體現代化是農業現代化的關鍵”[18],職業農民是現代化農業的主體,只有建立職業農民培養制度才能使廣大自給自足的兼業農民轉變為以市場交易為導向的職業農民,低迷的農業經營收入才會有實質性的增長。
(二)改革宅基地制度拓寬農民財產凈收入來源
財產凈收入的巨大差別是橫梗在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中的最大障礙。農民財產凈收入由于數額過小導致其對農民人均收入持續較快增長的貢獻很低。“處理好農民與土地的關系”是深化農村改革的主線[13]258,因此,促進農民財產凈收入增長可以通過改革陳舊封閉的宅基地制度以拓寬農民財產凈收入的來源。
農民擁有的財產主要包括農房和土地不動產、集體資產股份和家庭存款等。“資本是財富,而收入是財富的服務。”[9]54農民的財產凈收入只能通過土地、集體資產、存款等市場化交易獲得。由于農民通過流轉承包地獲得的租金一般很小,2016 年到2018 年稻谷、小麥、玉米三種主糧平均每畝的流轉租金分別為38.51 元、38.40 元、41.29 元,在戶均不足10 畝地的條件下,農民家庭每年通過流轉承包地獲得的租金基本上不足400 元,因此,通過流轉承包地獲得的租金對于提高農民的財產凈收入杯水車薪①數據來源于農業農村部網站公布的數據。。此外,多數農村集體資產較小,分配到每個成員中的股份就更小,甚至相當一部分農村集體并無可供分配的集體資產,所以對于多數農民來說,農村集體資產不能作為其財產性收入增長的來源。因此,要增加農民財產凈收入就要將眼光投向農民擁有的現成資產—宅基地及農房。
現行宅基地制度的基本內容包括:在產權結構上“集體所有、成員使用”,在分配原則上“一戶一宅、限定標準”,在管理制度上“規劃管控、無償取得”,在使用規定上“長期占有、內部流轉”[19]。這種使用規定基本上將通過宅基地及農房的市場化交易來增加農民財產凈收入的可能性一筆消除。由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不可動搖,那么如何圍繞流轉宅基地使用權以增加農戶財產凈收入就成為拓寬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途徑之一。由此,在改革宅基地制度中要以完善宅基地用益物權為核心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宅基地財產權,要以增強宅基地使用權流動性為途徑進行宅基地使用權市場化改革。《民法典》將宅基地使用權列入用益物權之中,農戶作為宅基地使用權人對集體所有的宅基地應享受占有、使用、收益權利,同時,《民法典》又規定關于宅基地使用權取得、行使、轉讓三個方面“適用土地管理的法律和國家有關規定”①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323 條、362 條、363 條。。而第三次修正的《土地管理法》提出“鼓勵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盤活利用閑置宅基地和閑置住宅”②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62 條。,將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之外的人員和單位全部排除在盤活利用閑置宅基地和農宅之外。眾所周知,沒有以買賣為核心的市場交易就沒有財產增值的可能。由于現行宅基地制度嚴格規定除繼承外③參見自然資源部網站《對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第3226 號建議的答復》中“六、關于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登記問題”(自然資人議復字[2020]089 號))。宅基地只允許在集體經濟組織之內流轉,那么閑置宅基地的出路只剩下兩條:一是回歸分配宅基地的集體經濟組織之手,二是在村民內部之間流轉。但是由于宅基地是無償分配的,農戶完全可以憑借其集體成員身份無償申請獲得一塊新的宅基地,并且在多數農村家庭沒有兩個以上男性第二代成員以及城鎮化進程推進30 余年8000 萬農民進城的條件下,農村現有宅基地的數量基本已滿足了目前農村人口對現有宅基地的需求,因此絕大多數村民已無對宅基地的需求。由此,改革陳舊封閉的宅基地制度,一方面需要在法律規定上賦予農戶即宅基地使用權人完整的用益物權,即允許農戶通過一定范圍內的流轉形式行使宅基地使用權的收益權能;另一方面則需要在政策上制定出以宅基地使用權市場化流轉為主要內容的具體辦法,維護農民的財產權益。目前情況下,可以允許放寬宅基地使用權流轉范圍至縣域,允許縣域內的常住居民以家庭的名義向初始申請獲得宅基地使用權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即擁有現有農宅和宅基地使用權的農戶購買農宅和租賃相應的宅基地使用權。通過宅基地和農宅在縣域范圍內的市場化交易,可以使市場化了的宅基地和農宅成為增加農民財產凈收入的重要財產,從而使宅基地和農宅不再是國家或集體強行安置在農戶身上的社會保障,而是在“適度放活宅基地和農民房屋使用權”[20]的前提下在一定交易自由程度上的家庭財產。
(三)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促進農民轉移凈收入增長
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以國家公共財政轉移支付為途徑調節收入分配使農民基本生活得以保障以維護社會公平。由于中國社會保障制度仍處于發展完善階段,“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社會保障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所發揮的作用相當有限”[21],尤其是對農民的社會保障不健全不完善,所以在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上還有較大空間以促進農民轉移凈收入的增長。
總體上來看,與城鎮居民相比,農民人均可支配轉移凈收入雖然增速較快,但是數額小,因此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雖然從2014 年至2020 年農民人均轉移凈收入年均增長率在其四項來源收入中最高,為12.09%,且高于城鎮居民2.66 個百分點,但在絕對數額上城鎮居民人均轉移凈收入遠高于農村居民④數據來源于《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年鑒-2013》中“表5-4歷年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待遇水平”的相關數據。。不僅如此,農民轉移凈收入中有相當比例來自家庭內部的私人轉移支付,即在農村社會和家庭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之中[22],外出農民工將自己的務工所得直接轉移到自己家庭中作為家庭獲得的私人轉移收入。因為這種私人轉移收入的收入調節和公共轉移收入之間存在較強的替代性,所以需要加強政府針對農民的公共轉移支付以提高農民的轉移凈收入。作為有效調節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公平普惠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發揮增加農民公共轉移收入的功能以解決農民收入增長的分化問題。
首先,針對農民群體內部收入增長中的分化問題,需要強化社會保障體系中的長久性最低生活保障和臨時性社會救助的功能,使低收入農民家庭或遭遇臨時重大困難的農民家庭得以維持基本生活。由于農民家庭之間資本積累有差異,并且其獲得收入的能力有高低之分,所以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但是對于缺乏主要勞動力導致農民家庭總收入維持在很低水平且無維持基本生活的家庭財產的情況下,就需要建立針對農民家庭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維持其基本生活。即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勝利完結的情況下,低收入農民家庭不僅很難消失,而且還可能因為遭遇重大家庭變故、遭遇經濟風險和自然災害等原因從低收入水平淪落為難以維持基本溫飽的狀態,因此依然需要針對農民家庭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和臨時性社會救助為一體的社會保障體系。這種長久性和臨時性相結合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僅有調節國民收入再分配的經濟功能,也發揮著穩定農村社會的政治功能,不可偏廢。
其次,針對農民與市民之間收入增長中出現的分化問題,需要完善農村以醫療和養老保險為主要內容的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全面提高農民的公共轉移收入。以農民基本養老保險為例,目前雖然城鄉統一的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已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建立,但由于農民收入普遍偏低,農民在12 檔養老保險繳費中大多選擇較低檔次,而多數地方財政對農民養老保險的補貼數額很小,維持在每人每年30 至60 元。而企業退休人員在2012 年已經有平均每月1686 元的退休金,機關和事業單位在2012 年的平均退休費已超過2000 元,相較之下,年老農民領取的基本養老金不足城市機關和企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十分之一①數據通過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中國統計年鑒-2020》中“6-6城鎮居民人均收支情況”與“6-11農村居民人均收支情況”中的數據以及最新發布的數據計算得出。。在職工養老保險和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待遇存在很大差距的情況下,亟需加大國家財政的公共轉移支出以提高農民的基本養老保險收入。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影響深遠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和長期的城市傾向的經濟社會政策使農民享受到的由社會保障而來的各種公共轉移支付非常有限,由此就首先需要消除社會保障的收入分配“逆向調節”作用[23],使農民接收到的來自國家財政社會保障資金的公共轉移收入恢復性地增加,然后再切實將農民養老和醫療保障體系逐步提高到接近城鎮職工養老和醫療保障的水平。
最后,須針對農村特定地區、特定人群、特定家庭實行各種精準扶助類型的社會保障。由于不同地區的農民家庭收入差距較大,且同一村莊內部農民家庭收入也存在較大差距,所以需要對特定地區、特定農村家庭進行專門的具有針對性的社會保障,例如為有接受九年義務教育的少年兒童的困難農民家庭提供特定的兒童教育補貼,為有身患重疾影響整體生活水平的農民家庭發放重疾家庭補助等。當然,這種精準的社會保障內容需要建立起精細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使政府公共財政轉移支付成為精準扶助低收入農民家庭基本生活的主要途徑,低收入農民家庭的轉移凈收入由此得到持久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