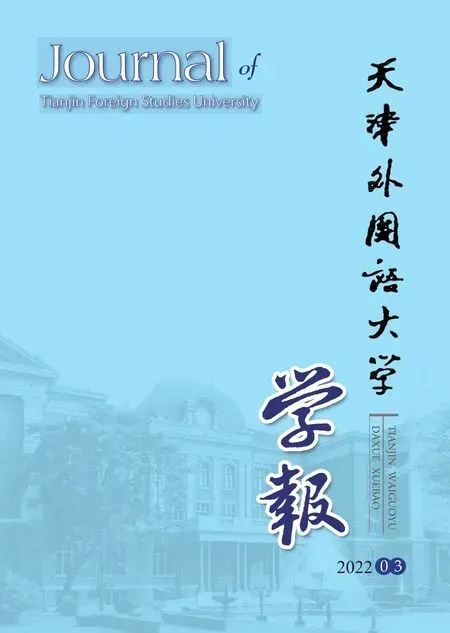從殖民地到國家:加拿大英語詩歌史中的民族想象
張 雯
從殖民地到國家:加拿大英語詩歌史中的民族想象
張 雯
(上海理工大學 外語學院)
從1820年代至今,加拿大英語詩歌走過了差不多兩百年的歷史。以民族想象的流變為主線來追溯與總結加拿大詩歌史,分析其間最具影響力的詩歌流派與最具代表性的詩歌作品,能夠比較全面地概括加拿大詩歌從殖民主義到民族主義再到多元文化主義的發展路徑。在詩歌的傳承與更新過程中,民族想象隨著歷史語境的變遷而呈現不同的時代解讀,這又折射出加拿大不同于英美的文化心理特征。因此,通過民族想象的棱鏡,既可管窺兩個世紀以來加拿大英語詩歌的大致全貌,亦能審視其獨有的民族心理特質與北國自然地理風貌。
加拿大;詩歌;民族想象
一、引言
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他的《想象的共同體》()一書里為民族進行了定義:“這是一個想象的政治共同體——這種想象還體現在它天然的局限性與權威性上。”(Benedict,2006:6)雖然安德森認為,民族主義具有天然的狹隘性,但這一基于“共同體想象”的國家概念,為國別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尤為契合加拿大的歷史與文化狀況。下文即以民族想象為主線對200年來的加拿大英語詩歌史進行簡要綜述。
二、殖民到聯邦時期(19世紀)
1825年,詩人奧里弗·哥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模仿他的同名伯祖父英國詩人哥德史密斯的《荒蕪的村莊》(),寫下加拿大詩歌的開山之作《勃興的村莊》(),這首被認為是加拿大第一部長詩的作品似乎在一開始就標注了加拿大與歐洲文學的同源性。作者的姓名與身份本身就說明了英加兩國文學的血緣關系,此外,后者對前者在內容上的應和更折射出加拿大早期移民作為英國人的身份歸屬:英國的《荒蕪的村莊》哀嘆現代工業對英格蘭鄉村田園生活的破壞,加拿大的《勃興的村莊》則在50多年后表示加拿大的新興農村可以彌補母國在機器革命中失去的東西。長詩最后部分以一句“大不列顛快樂”(Goldsmith,2009:174)引領對英國的滔滔贊美之詞,既是歌德史密斯個人的“表忠心”,也可看成是加拿大文學生發時期殖民心理的概括。早期的加拿大作家多為英國移民,寫作內容也多是英國主題的延續,而且大部分作品本就是寫給英國讀者的。從這個角度看,的確可以說最初的加拿大英語文學是英國文學在北美大陸的一個小分支。
與很多早期殖民地作品一樣,《勃興的村莊》情感高亢,卻被認為水準不高。20世紀作家休·麥克里南(Hugh MacLennan,1960:139)曾斷言:“殖民地文學充其量不過是母國文學的蒼白反映,沒有任何的權威性,直到這個殖民地變得成熟。”如他所預言,殖民地終歸要逐漸變得成熟與獨立。19世紀上半期的文人們固然常常閉目沉湎于對英格蘭的溫柔記憶中,但是一轉身又瞥見了眼前的紅楓樹。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開始更加關注于當下的新大陸風光,并試圖從中尋得自己新的身份定位。在聯邦政府成立前后,建立一個獨立的加拿大文學的愿望達到空前強烈的程度。托馬斯·達西·麥基(Thomas D’Arcy McGee)代表當時的殖民地人民發出了這樣的呼吁:“來吧!讓我們建設一個加拿大的民族文學,不是英國的,不是法國的,也不是美國的,而是這片土地的子民與后代,從所有的地方吸取經驗,但借此發出自己的聲音。”(McGee,1857)
19世紀八九十年代,聯邦詩派(Confederation Poets)響應時代號召,唱出了加拿大詩歌史上的第一波強音。聯邦詩人生在楓樹下、長于建國期(五成員均出生于1860-1861兩年間,親歷加拿大自治領的成立與建設),既感受到了加拿大文學較之英美的文化自卑感(cultural cringe),又目睹了聯邦成立初期前所未有的自信、振奮與理想化。他們主動擔當起建設加拿大民族文學的使命,創作出一系列富有愛國主義熱情的詩歌,比如查爾斯·G. D. 羅伯茨(Charles G. D. Roberts)的《加拿大》(Canada)和《加拿大聯邦頌歌》(An Ode to Canadian Confederacy)、E. 坡琳·約翰遜(E. Pauline Johnson)的《加拿大出生》(Canadian Born)、伊莎貝拉·瓦倫希·克勞福德(Isabella Valancy Crawford)的《從加拿大到英格蘭》(Canada to England)、艾格妮斯·瑪爾·瑪查爾(Agnes Maule Machar)的《我們的加拿大祖地》(Our Canadian Fatherland)、威廉·威爾弗萊德·坎貝爾(William Wilfred Campbell)的《帝國的乞丐》(The Lazarus of Empire)等。這些詩歌在題名上就毫不掩飾地彰顯民族主義訴求,內容上也往往是直白的謳歌與表決心。以聯邦詩派的領軍人物羅伯茨的《加拿大》為例,此詩一方面歌詠加拿大作為一個獨立的“幼兒的國家”(Roberts,1886:2)的光明前途:“在你的胸前、在你的額前,迸射出一輪上升的太陽”(ibid.:5);另一方面通過回顧歷史來強調加拿大的歐洲淵源,暗示詩人的親英立場:“撒克遜魄力與凱爾特火焰/這兩者是你的遺傳的男性氣概”(ibid.:3)。“聯邦詩人”的文學主張在當時頗具代表性,即建設一個與英國同宗但又獨立且強大的加拿大文學。
三、后聯邦時期(20世紀上半期)
20世紀20年代,現代主義橫掃西方世界,可是加拿大作家依舊在寒冷的北風中一遍遍地追問:“這是什么地方?”身份的困惑使加拿大沒能像歐洲及美國那樣張開雙臂迎接藝術的革新。作家大衛·麥克法雷(David Macfarlane,1991:43)這樣評價加拿大的現代主義:
現代主義花了些時間跨過大西洋,當它到達多倫多市中心時,似乎是在高檔的旅途中吃了過多的烤牛肉與喝了太多葡萄酒。它被介紹給了1920年代的加拿大民族主義,被帶去見七人畫派。它在“藝術與文字”社團里一場關于布里斯·卡門與威爾森·麥克唐納德誰是更好的詩人的爭論中睡著了,而且二十年沒醒過來。
當現代主義飄洋過海來到這片荒涼的北美新大陸時,它自己好像也困惑了,原先那種對既有文明與理性秩序的反思與挑戰并沒有很堅實的土壤,因此卷不起像在歐洲文藝界那樣純粹的聲勢。如果說現代主義的要義之一是反對“自身的傳統”,那么加拿大的現實恰恰就在于并沒有多少傳統,而且“自身”是什么也還是個問題。
這并不是說加拿大沒有激進的革新派。事實上當西方世界刮起現代主義的強風時,一些先鋒者們立即接收到了時代的訊息。“麥吉爾派”(McGill Group)或稱“蒙特利爾派”(Montreal Group)就是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的國際激流中應運而生的。與別國的先鋒作家一樣,“麥吉爾派”也是以除舊迎新為己任,是當時加拿大文壇現代主義與革新力量的代表勢力。這一詩派的激進與叛逆集中體現在核心人物F. R. 斯各特(F. R. Scott)的這首《加拿大作家聚會》(The Canadian Authors Meet)短詩中。
加拿大作家聚會
健談的木偶散發著自己涂上的圣油味
在威爾士王子的肖像畫之下。
怪想小姐的繆斯似乎未能顯靈,
但她是個女詩人。面帶微笑,她從一個人群
游走至另一個交談的人群,帶著如此珍貴的
維多利亞式圣潔,作為著她的派頭
對不相識的人報之一聲歡呼——
六十歲的處女依然在寫激情。
空氣因有著加拿大話題而變得沉重,
卡曼、蘭普曼、羅伯茨、坎貝爾、斯各特①
評價標準是他們的信念與慈善,
他們對上帝與國王的熱誠和熱切的想法。
蛋糕是甜的,但更甜的是
人與文學混合在一起的感覺;
溫暖了老的,融化了凍僵的。
真的,這是最另人愉悅的聚會。
我們要去桑樹叢散步嗎,還是
去河邊匯合,還是
選出這個秋季的桂冠詩人,
還是再來一杯茶?
哦加拿大,哦加拿大,能否
有一天沒有新作家出現
來描繪這當地的楓樹,來盤算
還有什么方式可以進行重復的歡呼?(Scott,1966:70)
在這首詩中,斯各特直接點名批評與自己同為詩人的父親F. G. 斯各特(F. G. Scott),足見是以弒父般的反抗精神來批評前一輩作家的。他在詩中全面盤點了當時加拿大文壇的一系列弊病,包括對英國的依賴(“威爾士王子的畫像”)、重復且沒有新意的自然描寫(“描繪當地的楓樹”“重復的歡呼”)等,總之是用毫不留情的諷刺語調來宣泄一個先鋒詩人對維多利亞式矯揉造作、自以為是的文風的極端反感與蔑?視。
然而,正如《加拿大英語文學:文本與語境》()一書所指出的:
斯各特不曾承認的是,他這一代人與聯邦時期有許多共同點。兩個群體都受民族主義感傷浪潮與對于創建一個獨特和在國際上可行的加拿大文學的渴望的影響;兩者都關注寫作藝術的形式與技藝;兩者都試圖取代他們之前的被認為是平庸的加拿大作品……(Moss,2009:83)
其實只要稍稍了解一下斯各特自己的詩歌實踐(大量以加拿大為主題的作品、自然題材的廣泛使用、手法上的浪漫主義傾向等),就可以發現他與被他唾棄的作家之間并沒有那么明晰的界線。以斯各特為代表的“麥吉爾派”雖然在文論上主張用現代主義取代浪漫主義、用國際性代替民族性,但是在創作上很大程度地繼承了早先的文學傳統,并繼續著前輩們談論的話題。
換言之,在當時的加拿大,所謂的現代主義不過是用龐德與艾略特等人的方式來繼續進行身份問題的追尋而已。現代主義與民族主義糾纏在一起,產生出一種獨特的藝術效果,既不同于加拿大本國之前的浪漫主義,也有別于歐洲與美國的現代主義。A. J. M.史密斯(A. J. M. Smith)創作于1926年的著名詩歌《孤獨的土地》(The Lonely Land)很有代表性地詮釋了這種新舊交替的詩風與并不純粹的現代主?義。
柏樹與鋸齒冷杉
聳立著尖刺
沖著灰暗
與烏云密布的天空;
水灣上
飛沫與水紋
和稀薄苦澀的水花
怒向
旋渦的天空;
而松樹
歪向了另一邊。(Smith,1982:98)
這首詩一方面在題材上沿襲加拿大文學對自然景物的依賴與迷戀,詩名“孤獨的土地”本身就再現了早期移民典型的幽怨與困惑;另一方面又背離了浪漫主義詩歌謳歌自然之壯美崇高的傳統風格,而是營造出另一種冷峻、奇崛和黑暗的氛圍,賦予景物以心理層面的寓意。對比一下早先加拿大詩人如查爾斯·桑斯特(Charles Sangster)和羅伯茨等人的作品,《孤獨的土地》從形式上來說詩行就短很多,不難看出是受美國意象主義凝練含蓄詩風的影響,而對“不和諧之美”的推崇又隱約可見波德萊爾式的審美風格。
《孤獨的土地》是受當時極有影響的“七人畫派”(Group of Seven)作品的啟發而寫成的(詩的副標題即“七人畫派”),如“七人畫派”所描繪的那一幅幅北方自然圖景,當筆法的冷峭與地域的嚴酷碰撞在一起時,會產生一種奇異又獨屬于加拿大的畫風。藝術界的“七人畫派”與文學上的“麥吉爾派”一樣,都運用革新的、現代主義的技法來表達原先的題材,開拓了一種更為非個人化與冷靜的創作風格。然而無論是“七人畫派”還是“麥吉爾派”,雖然都以創新革舊為己任,但對本土自然題材的描摹中又都凸顯了民族情懷。先鋒詩人努力走向世界的方式依然是展現這片北方大地獨有的風貌。
諾思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1971:467)說:“加拿大人的身份問題與其說是‘我是誰’,不如說‘這里是哪里’。”在這樣一個“歷史太少,地理太多”的國度,身份更多的是空間而不是時間上的議題。所以當其他歐美國家的現代主義者普遍從外界轉向內在時,加拿大作家依然執著地望著窗外的風雪與樹木。這部分地解釋了為什么“七人畫派”會成為加拿大現代主義的前鋒頭陣,他們開創了用一種全新的手法與視角來描摹自然的風格,從而呈現出一個迥異于浪漫主義時期的加拿大北方。但這種革新依然逃不開“這里是哪里”的追問,結論也暗示加拿大人的身份歸屬與獨特性存在于蒼茫與浩渺的北方自然中。
四、“百年慶”時期(20世紀六七十年代)
就這樣,在“孤獨的土地”的吟唱聲中一個世紀過去了,歷史的車輪輾轉至20世紀60年代,當年的自治領在寒冷的北風中成了地球上版圖最大的國家之一。她既實現了從英國的獨立,又沒有被美國吞并。但是一百歲對于一個國家來說依然是非常年輕的。從行政主權上看,紐芬蘭省1949年才加入聯邦,且此時加拿大的立法權依然附屬于英國。更重要的是,人們糾結了一百多年的身份問題似乎仍沒有明確的答案。厄爾·伯尼(Earle Birney)寫于1962年的短詩《加拿大文學》(Can. Lit)就表達了這種困惑。
加拿大文學
(或者能永遠離開她)
因為我們總是問向天空
即使有鷹來它們也會飛走
留下的影子并不比鷦鷯的大
甚至驚嚇不了最家常的母雞
太過忙于連接寂寞
以至于沒有時間寂寞
我們在鐵路的鏈條上開鑿的是
艾米莉刻在骨頭上的東西
我們的英國人與法國人從來不曾丟失
我們的內戰
延續至今
已是一個血腥的內困
傷者拉響了警報
不需要惠特曼
我們只因無鬼
而被糾纏(Birney,1975:138)
詩的最后一句“我們只因無鬼而被糾纏”(It’s only by our lack of ghosts we’re haunted)一經說出,便在加拿大文壇上陰魂不散。建國一百年了,伯尼還在執著于對民族身份的拷問。該詩創作于建國百年之際,又題為“加拿大文學”,實際上道出了民族文學建構的世紀困惑與難題。“缺鬼”的實質是缺乏足夠的歷史與文化積淀,這也是對加拿大集體定位的迷思。
該詩的小標題“或者能永遠離開她”(or them able leave her ever)是對1867年亞歷山大·繆爾(Alexander Muir)的詩歌《永遠的楓葉》(The Maple Leaf Forever)題名的戲仿。兩者的創作時間相差了一百年。從leaf到leave,我們可以看到一種世紀輪回。同時,從坎貝爾的“我們只吃著她②的名望的碎屑”(Campbell,1987:36)到F. R. 斯各特的“哦加拿大,哦加拿大,能否有一天沒有新作家出現”;從厄文·萊頓(Irving Layton)的“乏味的人,缺乏魅力與想法”(Layton,1975:75)再到伯尼的“我們只因無鬼而被糾纏”,我們可以從中讀出歷經百年卻從不曾間斷的國民性批判與探尋。
這個百年探尋的歷程充滿了曲折與迷惘,詩歌中的“迷路”主題即是一個例證。一個人迷失于原始森林是加拿大文學的母題之一。到20世紀中后期,這一主題更偏重心理層面的展現與挖掘。道格拉斯·拉潘(Douglas LePan)的《一個沒有神話的國家》(A Country without a Mythology)和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一個拓荒者逐漸變瘋》(Progressive Insanities of a Pioneer)都描寫了一個來自歐洲文明的男性在荒野中迷失自我的過程。前者受困在一個“沒有神話的國家”,后者則走不出“有序的虛無”(Atwood,1968:37)。
如弗萊(Frye,1971:225)說的:“我長久以來驚異于加拿大詩歌中說到自然時的那種深深的恐懼語調”,兩首詩里的自然均被定位成與人類對立的冷酷、蠻荒與敵意的形象,而人類改造自然的努力也都歸于失敗。個人的努力在強大蠻橫的自然面前微不足道:“萬物/拒絕給自己命名/也拒絕他的命名”(Atwood,1968:39)。命名行為象征著人類對自然的理性改造,是蠻荒走向文明與有序的第一步,自然拒絕被命名即是拒絕被改造。而自然的蠻荒又往往表現為非理性的虛空。阿特伍德筆下的拓荒者身處的地方是“哪里都沒有墻,沒有界線/在他之上的天空也沒有高度”(ibid.:36),“沒有神話的國家”同樣是“天空中沒有絲毫的記號,沒有表征”(LePan,2000:113),以及“沒有遺跡或地標指導這個陌生人”(ibid.)。虛空反而成了禁錮,這種“曠野恐懼癥”或許是加拿大詩歌所獨有的。
可見,迷路其實是一種人與自然的沖突,也是一個關于身份迷惘性的隱喻,這無非是又一次以“這里是哪里”來詢問“我是誰”的問題。阿特伍德(Atwood,1972:17)在《生存:加拿大文學指南》()一書中指出:
“我是誰”是另一種問題,這是當一個人置身于未知領地時會問的問題,而且隱含了幾個其他的問題:這個地方相較于其他地方處于什么位置?我如何在這里找到自己的路?如果一個人真的迷路了,他可能還會想他一開始是如何到達“這里”的,希望能通過追蹤自己的腳印來找到正確的路徑,或者離開的路。
像加拿大這樣的移民國家,文明與自然的沖突在第一代拓荒者身上幾乎是以撕裂的方式上演。而阿特伍德給出的答案是:“一個迷路的人需要的是這片土域的地圖,標記著在他自己所處的位置,這樣他能看清他與周遭事物的關系。”(ibid.:18)
加拿大文學史中以“加拿大”“土地”“國家”等詞語命名的詩歌之多也足以證明這一點。從A. J. M. 史密斯的《孤獨的土地》到拉潘的《一個沒有神話的國家》(1948),再到伯尼的“我們只因無鬼而被糾纏”,建國一百多年來對民族身份的探求從來沒有停止過,直到1972年艾爾·珀迪(Al Purdy)的這首《貝爾維爾之北的鄉野》(The Country North of Belleville)。
灌木之地矮樹之地——
卡舍爾鎮和沃拉斯頓
埃爾維澤爾麥克盧爾和鄧甘嫩
維斯勒姆昆湖的綠地
在此地一個人可能會理解
什么是美
而且無人能否認他
因為數英里的——
然而這是一個挫敗的鄉野
西西弗斯滾著一塊巨石
年復一年推上古老的山巒
野餐的冰川留下散落的
世紀的碎礫
艱辛操勞的日子
在陽光與雨水中
當領悟緩緩流進大腦
卻并沒有因為作了一個傻瓜
而產生的宏大或自欺欺人
的高貴掙扎——(Purdy,2010:569)
這首詩雖然寫的是一個地方性的區域,但用拓荒生活體驗來探討國民性問題的做法與之前的主題是一脈相承的,再加上英語中“鄉野”與“國家”是同一詞(country),所以整首詩依然可以看作是對民族身份的感嘆。貧瘠的土地、寒冷的氣候以及生活于此的人們的無奈與挫敗感,都是對包括蘇珊娜·穆迪(Susanna Moodie)在內的拓荒者們對加拿大愛恨交織情緒的又一次回應。此詩的名句“這是一個挫敗的鄉野”(This is the country of our defeat)也是對“這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或土地”(This is the country / land of…)句式的終結。也許這就是為什么珀迪被稱為“最后一個加拿大詩人”(Solecki,1999),在他之后就很少有作家再吟唱“這是一片孤獨的土地”或“這是一個失敗的國家”這樣的詩句。因為這種句式一方面強調了身份的迷惘,?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國家層面的集體敘事導向。而從70年代開始,宏大的集體敘事在加拿大受到了史無前例的時代挑戰,同時也意味著詩歌史迎來了一個新的局面與走向。
五、多元文化時期(20世紀后期至21世紀)
萊頓所謂的“從殖民地到國家”的轉變剛一完成,加拿大便開始迅速變得多元化。自20世紀后期,在移民政策與多元文化主義等多重政治與文化力量的導向與沖擊下,不同地區的人希望表達獨特的地域體驗,各族裔的移民也紛紛講述自己的故事,各支系原住民次第發聲。原先單一的歐洲移民的主體聲音被消解,加拿大文學逐漸成為一個多聲部的混合演奏。早先的那種民族挫敗感依然在,卻不再是“加拿大”這個定語就能涵蓋的,而是多地域、多族裔與多元化的。這種多樣性(diversity)正好契合了后現代主義“消解中心,重構邊緣”的訴求。如果說現代主義在加拿大并不純粹的話,后現代主義倒是在這片北方土地上展現得淋漓盡致。
在這樣的新語境中,詩人們不再感嘆“這是一片孤獨的土地”或“這是一個失敗的國家”,也不再那么熱衷于描寫寒冷的北方或是迷失于荒無人煙的森林——那些更多屬于早期歐洲移民的體驗。意識形態上的轉變或許可以從這一時期的一些戲仿或改編作品中看出來。詩人們將早期作家設為描述對象,或者如阿特伍德的《蘇珊娜·穆迪日記》()那樣以第一人稱“我”來表述,或像羅伯特·克羅奇(Robert Kroetsch)的《F. P. 格羅夫:發現》()那樣將對方稱為“你”,直接與之對話。無論哪種形式都包含著對拓荒期作家及其所處時代的反思與重新評估。
其中,較早這么做的是F. R. 斯各特。他的《除了最后一根之外的所有道釘》()是針對E. J. 普拉特(E. J. Pratt)的史詩級長詩《通往最后一根道釘》(Towards the Last Spike)而寫的。后者描寫了19世紀末期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的修建過程,卻幾乎完全忽略了包括華人在內的普通勞工。作為加拿大第一屆聯邦政府的最顯著功績,橫跨北美東西全境的太平洋鐵路歷來是國家敘事的象征。《除了最后一根之外的所有道釘》開門見山地質問普拉特“你詩中的苦力們在哪里”,并進一步反問:“他們③在這片他們幫著聯結的土地上過得好嗎?”斯科特對普拉特的質疑,暗示普拉特等人所倡導的宏大統一的敘事根基開始有所松動。此詩寫于1957年,從“通往最后一根道釘”到“除了最后一根道釘”的轉變已隱約預示著一個新的價值評判體系時代的到來。
阿蒙德·加內特·魯福(Armand Garnet Ruffo)的《給鄧肯·坎貝爾·斯各特的詩》(Poem for Duncan Campbell Scott)則將著名的聯邦詩人鄧肯·坎貝爾·斯各特?④(Duncan Campbell Scott)又一次推向了多元文化主義的審判席。D. C. 斯各特既是加拿大歷史上有成就的作家,同時也曾是聯邦政府印第安事務部的一個主要負責人。魯福的這首詩即是描寫斯各特代表聯邦政府與本土裔奧吉布瓦人談判的一個場景。全詩從印第安人的眼光展開:“這個黑色外套與領帶是誰?”(Ruffo,1994:25)接下來,詩歌便對斯各特所代表的基督教義、聯邦政府的印第安政策以及他的詩歌進行了一系列的嘲諷。
更重要的是,魯福試圖反轉D. C. 斯各特所代表的白人話語權。D. C. 斯各特曾經創作了大量關于印第安人的詩歌。這些作品一方面歌詠印第安人勇敢、純真、隱忍的品質,表達了對他們的深切同情;另一方面又站在白人殖民者的立場上,認為他們是需要被改造、救助,甚至是應被消除的種族。魯福(ibid.)在詩歌中寫道:“他總是忙著在隨身攜帶的日記本上寫東西”,而這些東西:
……他
稱之為詩
并說它能使我們這些注定滅亡人
永生
再聯系一下這首詩的題目“給鄧肯·坎貝爾·斯各特的詩”,其實頗具反諷意味。在D. C. 斯各特眼中,印第安人作為一個終將被同化直至消失的種族,永遠不可能寫詩,因而只能在他的詩中得以永存。可是一百年以后,作為奧吉布瓦人的魯福不但沒有死,還反過來將D. C. 斯各特寫進了自己的詩里。寫與被寫,我們看到的是世紀更迭過程中話語權在雙方手里的幾番交替。
梅蒂(Métis)⑤作家瑪麗蓮·杜蒙特(Marilyn Dumont)則將這種對質又向前推進了一步,她的詩歌《致約翰·A. 麥克唐納德爵士的一封信》(Letter to Sir John A. Macdonald)直接對話加拿大第一任總理約翰·A. 麥克唐納德爵士(Sir John A. Macdonald):“你知道嗎?約翰,/這么多年為了適應移民將我們推來推去/我們卻依然在這里且依然是梅蒂人。”(Dumont,2001:261)麥克唐納德和他極力主張修建的太平洋鐵路已然成了加拿大英裔白人殖民敘事的象征。杜蒙特在鐵路建成100年以后對死去多年的麥克唐納德說:“約翰,那條該死的鐵路并沒有將此地變成一個偉大的國家”(ibid.),而那個被你處死的路易斯·瑞爾(Louis Riel)⑥雖然死了,卻“總是回來”(ibid.:262)。以當時的政治話語的評判標準,麥克唐納德與瑞爾,前者是國家意志的體現,后者則是叛徒;前者是征服者,后者是被征服者。可是,加拿大歷史發展的語境不斷地質疑這個定論。瑞爾“總是回來”,他不斷地出現在20世紀后半期的詩歌中,從兩首“拾得詩”(found poem),即萊蒙德·蘇斯特(Raymond Souster)的《拾得詩:路易斯·瑞爾在法庭上的陳述》(Found Poem: Louis Riel Addressesthe Jury)和約翰·羅伯特·卡倫伯(John Robert Colombo)的《路易斯·瑞爾最后的話》(The Last Words of Louis Riel),到bp尼克爾(bpNichol)的《路易斯·瑞爾的長周末》(The Long Weekend of Louis Riel),再到這首《一封信》,瑞爾是加拿大當代文學中一個“陰魂不散”的形象。這背后是多元價值觀的興起與少數族裔文化的重構,既是多元主義對單一白人文化的挑戰,也是后現代主義對宏大敘事的反?叛。
無論是斯各特為中國勞工打抱不平,還是杜蒙特站在梅蒂人的立場上聲討麥克唐納德,還是魯福作為奧吉布瓦人對D. C. 斯各特的諷刺,都可以看出少數族裔開始逐漸從白人主導的話語歷史語境中解放出來,從而發出自己的聲音。20世紀90年代涌現了不少類似的戲仿詩,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世紀之交加拿大文學對歷史的反思,也預示未來將是一個更為多元與后現代的走向。
六、結語
綜上論述,可以較為清楚地看出加拿大英語詩歌史的大致發展脈絡,即19世紀的殖民主義、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期的民族主義、20世紀后期以來的多元主義。民族想象既是一條貫穿兩個世紀詩歌史的主線,同時本身也是一個隨著時代與語境的更迭而不斷變化內涵的意象。200年來,加拿大既完成了從殖民地到國家的轉變,同時也正進行著從共同體到多元體的演化。
①這些均是“聯邦詩人”的名字。
②指英國。
③指華人勞工。
④為避免與另兩位詩人F. R. 斯各特和F. G. 斯各特的名字搞混,下文將鄧肯·坎貝爾·斯各特稱為D. C. 斯各特。
⑤梅蒂人為北美歐洲移民與當地本土裔結合所生的混血后裔。
⑥路易斯·瑞爾(1844-1885)是梅蒂人的領袖,為保護梅蒂人的文化與權益,抵抗聯邦政府對草原地區的“加拿大化”,曾在1860年代后期和1884年率領梅蒂人發起了兩次反叛運動。1885年,渥太華方借由剛剛建成的太平洋鐵路輸送官兵,平定了叛亂且抓捕了路易斯·瑞爾。他后來被麥克唐納德處死。
[1] Anderson, B. 2006.[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 Atwood, M. 1968.[M]. Boston: Atlantic Monthly Press .
[3] Atwood, M. 1972.[M]. Toronto: Anansi.
[4] Birney, E. 1975.(Vol. 1)[M].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5] Campbell, W. 1987. The Lazarus of Empire[A]. In L. Boone (ed.)[C].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6] Dumont, M. 2001. Letter to Sir John A. Macdonald[A]. In J. Armstrong & L. Grauer (eds.)[C]. 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7] Frye, N. 1971.[M]. Toronto: Anansi.
[8] Frye, N. 2003. Conclusion to the First Edi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of Canada[A]. In J. O’Grady & D. Staines (eds.)(Vol. 12)[C].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9] Goldsmith, O. 2009. The Rising Village[A]. InC. Sugars & L. Moss (eds.)(Vol. I)[C]. Toronto: Pearson Education Canada.
[10] Layton, I. 1975.[M].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d Ltd.
[11] LePan, D. 2000. A Country without A Mythology[A]. In J. Finnbogason & A. Valleau (eds.)[C]. Toronto: Nelson Thomson Learning.
[12] Macfarlane, D. 1991.[M]. Toronto: Macfarlane, Walter & Ross.
[13] MacLennan, H. 1960.[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4] McGee, D. 1857. A National Literature for Canada[N]., 06-17.
[15] Moss, L. 2009. F. R. Scott[A]. InL. Moss & C. Sugars (eds.)(Vol. II)[C]. Toronto: Pearson Education Canada.
[16] Purdy, A. 2010. The Country North of Belleville[A]. In D. Bennett & R. Brown (eds.)[C]. Don Mil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 Roberts, D. 1886.[M]. Boston: D. Lothrop.
[18] Ruffo, G. 1994.[M]. Penticton: Theytus Books.
[19] Scott, F. R. 1966.[M].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 Smith, M. 1982. The Lonely Land[A]. In M. Atwood (ed.)[C].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1] Solecki, S. 1999.[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106.2
A
1008-665X(2022)3-0048-13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加拿大當代英語詩歌‘共同體想象’研究”(15BWW052)
張雯,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加拿大英語文學
(責任編輯:張新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