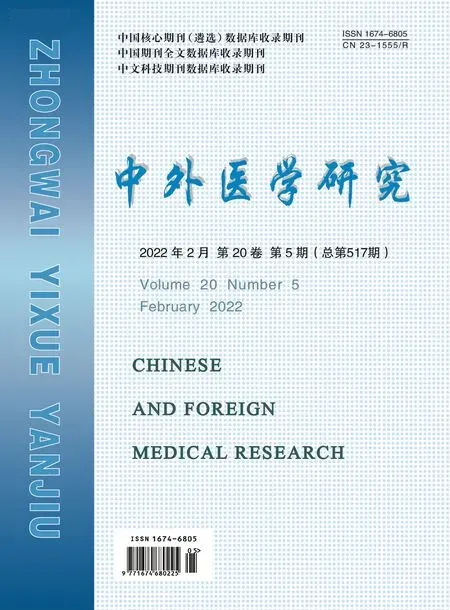PALB2與前列腺癌研究進展
朱光強 唐鐵龍
前列腺癌是2020年男性第二大常見癌癥和第五大癌癥死亡原因,據估計2020年在美國死于癌癥的患者中,前列腺癌死亡人數占10%[1-2]。而在我國僅1/3的初診前列腺癌患者屬于臨床早期,多數患者已處于中晚期,導致中國前列腺癌患者的總體預后遠差于西方發達國家[3]。對于前列腺癌其病因知之甚少,已知的危險因素僅限于年齡的增長、家族史,以及某些基因。因在前列腺癌的基因中除了BRCA1/2外,對于其他基因的研究尚不成熟,而PALB2作為同源重組的重要成員,在前列腺癌的患病機制中還屬于空白部分,因此急需加強填補前列腺癌相關基因圖譜,制定個性化治療及針對性篩查。本文從PALB2的結構功能及已報道的相關突變來闡述與前列腺癌的研究進展。
1 PALB2的結構功能
PALB2基因又名“BRCA2的合作伙伴和定位器基因”,于2006年被發現,其位于染色體16p12上,開放閱讀框由1 186個殘基組成[4],被認為是BRCA1和BRCA2之間的連接蛋白。PALB2蛋白的結構功能域有:N端的卷曲螺旋結構域、C端主要為WD40結構域,以及中間部分的染色質結合基序(CHAM)、MRG15結合部分,其中還包括兩個DNA結合域和兩個RAD51相互作用區域,值得注意的是,PALB2的N端還有KEAP1結合位點,C端的RAD51旁系同源物RAD51C及轉移聚合酶pol η結合位點[5]。WD40結構域是具有7個葉片的環狀β螺旋結構,可介導蛋白質-蛋白質相互作用,WD40域是人類基因組中最豐富和相互作用最多的域之一,也是PALB2致病性的研究熱點之一,其可直接和獨立地結合RAD51和BRCA2進行同源重組,PALB2的截斷或移碼突變體會擾亂WD40結構域,消除PALB2與BRCA2的關聯,細胞對DNA交聯劑(如MMC)產生抗性的突變體的致病性也通常歸因于PALB2與BRCA2相互作用的破壞[6]。Pauty等[7]最近發現了WD40中一個有功能的核輸出序列,PALB2的W1038X突變導致該序列暴露于CRM1,并且結構預測表明PALB2 W1038X突變體中WD40域的一半被去除。PALB2作為BRCA1和BRCA2的功能接頭,PALB2突變體破壞與相應蛋白質的相互作用,導致RAD51病灶組裝和同源重組(HR)缺陷。可見同源重組修復(HRR)受損可能是在攜帶BRCA1、BRCA2或PALB2突變的患者中觀察到的基因組不穩定和腫瘤發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N端存在的卷曲螺旋結構域直接與BRCA1結合,并且這種相互作用是PALB2與BRCA2作用的前提。PALB2視為BRCA1和BRCA2 的連接器,將BRCA1、BRCA2和RAD51連接到DNA損傷反應途徑中。其中卷曲螺旋結構域上的突變,包括癌癥患者衍生的BRCA1突變,會破壞它們復合物的形成。因此PALB2-BRCA1相互作用被破壞時,HRR會受到影響并損害DNA損傷的細胞存活率[8]。Buisson等[9]發現PALB2卷曲螺旋結構域的過度表達嚴重影響RAD51加載到DNA損傷位點,表明PALB2的N端卷曲螺旋基序能調節其自我關聯和同源重組。因此PALB2通過自相作用控制HR,這對于防止正常條件下的異常重組和在需要時激活DNA修復很重要。另外BRCA1-PALB2相互作用的破壞還會對HRR和DNA交聯劑絲裂霉素C(MMC)敏感性產生一定的影響[8,10]。N端另一KEPA1結合位點上,PALB2與NRF2競爭KEAP1,從而促進抗氧化反應,降低細胞ROS導致的DNA損傷間接實現基因組的穩定[5,11]。染色質關聯基序(ChAM)是PALB2上一個新的進化上保守的PALB2基序,介導PALB2核小體關聯。ChAM的缺失會減少PALB2和RAD51在DNA損傷位點的積累,并賦予細胞對基因毒性藥物絲裂霉素C的超敏反應,是PALB2染色質結合所必需,并促進了PALB2在細胞對DNA損傷的抵抗的功能[12]。
MRG15是除了PALB2的N和C末端,而位于序列中間的另一個高度保守的區域,被證實為一種新型的PALB2相關蛋白,PALB2-MRG15相互作用對于抑制姐妹染色單體介導的同源重組起著一定的作用,PALB2和MRG15可能共同作用以應對DNA損傷[13]。隨后有研究發現MRG15與BRCA復合物相互作用,MRG15通過將BRCA復合物募集到受損DNA位點來參與對雙鏈斷裂(DBS)的反應,并且與對MMC的耐藥性有著直接關系[14]。Bleuyard等[15]發現PALB2通過其主要結合伙伴MRG15與活性基因相關聯。表達PALB2變體的細胞,含有阻礙MRG15結合的錯義突變,對拓撲異構酶I(TOP1)抑制劑喜樹堿(CPT)表現出更高的敏感性,并增加異常中期染色體和基因體中的DNA應激水平,DNA復制受到抑制。
由于PALB2以DNA損傷反應因子的特征方式表現,并使BRCA DNA損傷反應的修復成為可能。因此PALB2是否是致病突變成為新的研究目標,這在乳腺癌、卵巢癌、前列腺癌和他腫瘤中都非常重要。
2 PALB2與前列腺癌相關研究
已知PALB2中的雙等位基因突變(也稱為FANCN),會導致范可尼貧血[16]。其次Rahman等[17]發現在單等位基因截斷PALB2突變的家族性乳腺癌患者與對照者相比,此類突變使患乳腺癌的風險高2.3倍。首次鑒定出PALB2為一種新的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1/2基因突變是已知的前列腺癌患病的重要危險因素,PALB2作為BRCA1/2的協作伙伴在DNA同源重組修復通路中起著一定的作用,但因為其變異較罕見,且相關報道不多,有關PALB2基因突變與前列腺癌相關性的研究相對較少。Erkko等[18]首先在芬蘭人群中發現了一列家族性前列腺癌PALB2突變c.1592delT。隨后在研究可能的其他PALB2變體的作用中,Pakkanen等[19]篩選了938名芬蘭前列腺癌患者隊列中的所有PALB2外顯子,對包括c.1592delT在內的4個PALB2變體 1674A>G、2993G>A 和 3300T>G 進行了分析,發現除了1592delT外,沒有其他有害的PALB2變體對芬蘭的前列腺癌風險存在相關性。同樣,Tischkowitz等[20]對95個前列腺癌家族的先證者的PALB2進行了測序,發現了兩個以前未報告的變異,K18R和V925L,它們都不在已知的PALB2功能域中,而且都不太可能致病。可能PALB2中的有害突變對遺傳性前列腺癌沒有顯著貢獻。盡管Erkko等[18]的數據表明PALB2可能與芬蘭前列腺癌家族的遺傳性有關聯。然而,在不同地理人群中,似乎存在著地理差異。因此,雖然PALB2突變不太可能在遺傳性前列腺癌中起主要作用,但有害的PALB2突變仍有可能在一些罕見的家族中易患前列腺癌,所以不排除其有可能是潛在的前列腺癌易感基因。
在對轉移性前列腺癌中發生的體細胞突變分析及對這些男性生殖系DNA外顯子組進行測序時發現8%攜帶致病性生殖DNA修復基因的突變。因此為了證實并進一步確定轉移性前列腺癌中生殖系DNA修復基因突變的譜系和流行率,Pritchard[21]對542名確診為前列腺癌轉移的男性,使用新一代測序來分析與常染色體相關的DNA修復基因。在16個基因中發現了突變,其中BRCA2[37(5.3%)]、ATM[11(1.6%)]、CHEK2[10名(534名有數據),占比1.9%]、BRCA1[6(0.9%)]、RAD51D[3(0.4%)]和PALB2[3(0.4%)],轉移性前列腺癌男性中DNA修復基因種系突變的頻率顯著超過499名局限性前列腺癌男性,但該研究未能排除家族史造成的偏倚。因PALB2突變的罕見性難以準確估計相關的癌癥風險。使用定制的iCOGS陣列對10個罕見突變進行基因分型:PALB2 c.1592delT、c.2816T>G 和 c.3113G>A、CHEK2 c.349A>G、c.538C>T、c.715G>A、c.1036C>T,c.1312G>T,c.1343T>G 和 ATM c.7271T>G,評估了每種變異與乳腺癌(42 671例和 42 164例對照),以及前列腺癌(22 301例和 22 320例對照)和卵巢癌(14 542例和23 491例對照)癌癥風險的相關性。而在PALB2的三種罕見突變中,c.1592delT和c.3113G>A與乳腺癌高風險相關,沒有觀察到與前列腺癌風險的關聯[22]。而在非洲血統的男性中報道了PALB2罕見致病變異與侵襲性前列腺癌高風險的顯著相關性[23],同時強調了風險等位基因發現工作在遺傳多樣性人群中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在波蘭的一個大型病例對照組的研究提出PALB2突變與高級別前列腺癌相關,且PALB2突變特別容易導致侵襲性前列腺癌,患有前列腺癌并伴有PALB2突變的男性5年生存率低于50%。這是第一個評估前列腺癌和PALB2突變的男性生存率的研究。因此,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PALB2突變易導致預后不良的前列腺癌[24]。
除了轉移性去勢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外,對于局部和局部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的HRR基因突變研究中,Jiang等[25]在中國人群中發現,中國局限性和局部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的HRR基因突變頻率(PALB2 1/10,10%)高于對照組。只包括一個機構,樣本量較小。所以還需要更大樣本量及更多種族人群的研究。在最近DNA修復基因中罕見的致病性、可能致病性或有害(P/LP/D)種系變異與侵襲性前列腺癌風險相關性研究中,發現BRCA2和PALB2具有最顯著的基于基因的關聯,因DNA修復基因傳遞的風險主要由BRCA2、PALB2和ATM中的罕見P/LP/D等位基因驅動[26]。因此已有不少研究發現支持了該基因在前列腺癌篩查和疾病管理方面的重要性。
3 前列腺癌PALB2突變的相關治療
目前晚期前列腺癌同源重組修復缺陷的患者治療包括PARP抑制劑、鉑類藥物化療等。在2005年Farmer等[27]意外發現BRCA1或BRCA2功能障礙可使細胞對PARP酶活性抑制劑敏感,導致染色體不穩定、細胞周期阻滯和隨后的凋亡。原來對PARP的抑制導致了由同源重組修復的DNA損傷的持續,因此首先提出了靶向抑制特定的DNA修復途徑來設計特定的、毒性更低的癌癥治療方法(協同致死效應),隨后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使用PARP抑制劑治療前列腺癌對標準治療不再有反應的患者和DNA修復基因缺陷的患者可獲得高反應率[28]。其中奧拉帕尼于2020年5月19日被FDA批準用于在14種同源重組修復(HRR)基因(BRCA1、BRCA2、ATM、BARD1、BRIP1、CDK12、CHEK1、CHEK2、FANCL、PALB2、RAD51B、RAD51C、RAD51D or RAD54L)中存在有害或疑似有害生殖系或體系突變的mCRPC患者[29]。mCRPC中盧卡帕尼的前瞻性、基因組學驅動的研究中發現其他DDR相關基因(包括PALB2)發生改變的患者可能會受益于PARP抑制,FDA于2020年5月15日批準盧卡帕尼用于患有生殖系或體細胞BRCA1/2改變且之前接受過第二代激素藥物和紫杉烷化療的男性mCRPC[30]。
因具有HR缺陷的腫瘤極易受到使DNA復制叉停滯的療法的影響,DNA交聯劑,如鉑類和絲裂霉素C會導致DNA雙螺旋扭曲,使復制叉停滯,從而誘導DSB,且已經有案例研究報告了基因PALB2突變的前列腺癌患者對鉑類化療顯示出的有效性[31-32]。在mCRPC的Ⅱ期研究中,鉑類化療已被證明可帶來姑息性獲益和更長的無進展生存期[33]。Mota等[34]通過對全機構范圍的腫瘤體細胞和種系分子譜分析檢查DNA損傷反應(DDR)中體細胞和種系突變與鉑類化療反應之間的關聯確定了非BRCA DDR基因改變的腫瘤對鉑類化療產生的反應,包括PALB2、FANCA和CDK,因此一部分通過腫瘤或種系測序檢測到的DDR基因改變的患者可能受益于鉑類化療。
前列腺癌是發達國家最常見的癌癥之一,且一部分歸因于遺傳因素,凸顯了基因檢測的重要性,同時也是前列腺癌個性化診斷和治療的重要組成部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PALB2突變與前列腺癌的家族遺傳性和高度侵襲性變異相關,鑒定需要緊急治療的侵襲性和致命形式的前列腺癌是目前臨床實踐中的主要挑戰,而有害生殖系PALB2變體代表了遺傳或晚期前列腺癌中的一個可操作靶標,并支持在該患者群體中進行擴展基因組測試。總之具有PALB2突變的前列腺癌患者可能特別適合精確腫瘤學方法,例如針對PALB2突變的PARP抑制劑,但是并非每個有突變的患者都可能獲得臨床益處,預測性生物標志物的識別和詳細表征是一項持續的工作。在臨床實踐中實施基因檢測,特別是患有侵襲性腫瘤或家族史陽性的年輕患者,代表了未來幾年的新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