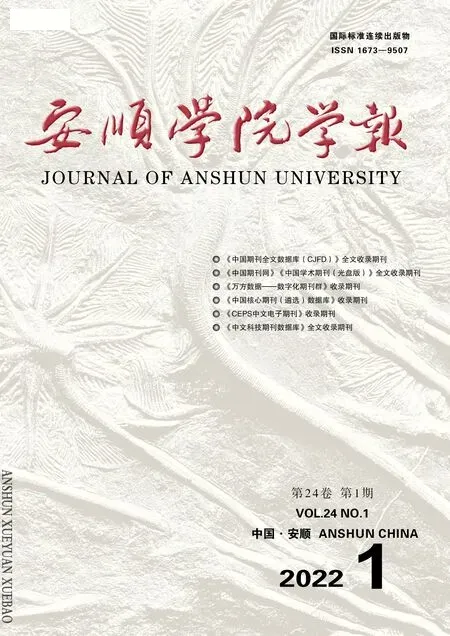盤江流域的衛所屯堡與共生秩序
——以貴陽青巖集市為個案的研究
陳 斌
(安順學院旅游學院,貴州 安順561000)
地處云貴高原的盤江流域,與王朝國家的關聯,肇始于秦朝。在經歷多次改朝換代后,王朝國家在此實施的制度體系不斷完善,內涵日趨豐富。尤其是自元朝以降,該地基本納入王朝國家的政治框架。明朝洪武年間,隨朱元璋“調北征南”行動而建立的衛所屯堡制度,不僅進一步將該區域囊括進王朝國家的政治版圖中,而且為后續貴州建省之舉奠定制度基礎。
明清以前,盤江流域之于王朝國家,象征意義重于治理實踐。當地自發自主的多民族混融共生和民間自我治理,是其社會秩序的主要內涵。明清時期,王朝國家對盤江流域的訴求發生變化,治理實踐躍居象征意義之上。因衛所屯堡制度而遷居于此的中原移民,附著其上的漢文化、以稻作為核心內涵的農耕技術、以平原為基礎而建構的社會生活和文化實踐,逐漸嵌入到盤江流域的社會秩序之中。客觀地說,自秦朝以來歷代王朝國家在該區域實施的治理制度,可視為中央集權制度的衍生物。其制度體系和中原漢文化對其社會秩序的型塑和維續,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有積極作用。
鑒于此,“中原中心主義”主導的文獻記錄和學術研究,一方面,將這種積極作用無限放大,認為歷代中央王朝、中原社會及漢族移民合力,是推動盤江流域社會秩序、經濟發展、文化型塑的主要或唯一力量。另一方面,有意或無意地遮蔽此舉在該區域的適應性問題。總之,這些歷史記錄和學術研究,把邊疆治理和發展作為王朝國家單向度“同化”“漢化”(Cultural assimilation)的過程,而較少探討這種治理和發展過程依存的文化生態環境。也就是說,很少從文化生態學的視角,去討論和分析邊疆治理和發展過程中當地民眾的主體性和能動性。明確歷代王朝國家邊疆治理與發展過程中的文化生態環境,將有助于認識共生何以可能、如何可能等重要問題。本文試圖從文化生態學的視角,以貴陽青巖集市為例,回應和討論上述研究問題。
一、流域構成與自然生境
“盤江有二源,其出烏撒境內者曰北盤江,……其出云南境者曰南盤江。”[1]“北盤江,界滇黔于西南,源自威寧州西界山,入滇沾益、宣威二州界,仍流自黔。東逕普安廳、普安縣、安南縣、郎岱廳、永寧州,而由三江口東合于紅水河。……南盤江,導源沾益州之花山東,經南寧縣東,為東小河,又經陸涼州東,為中延澤。又經宜良縣東北,為大赤江。又南經路南州西,為巴盤江。又東南經師宗、彌勒二縣,環曲靖、云南、澄江三府、廣西一州之境,至羅平州入貴州界,經郡城南,謂之紅水江,亦曰巴皓河。經冊亨,亦曰八渡江,劃黔粵之界,會北盤江入粵達于海。”[2]
考現代地圖可知,盤江流域是由南盤江、北盤江及其交匯而成的紅水河諸支流共同構成的水系。均源自烏蒙山系,是珠江上游主源之一。該流域覆蓋滇、黔、桂三省(區)五十多個縣市,流域面積八萬多平方公里。其中,北盤江26,557平方公里[3]914。按當前行政區劃,其主體覆蓋黔西南州府興義市及普安、晴隆、安龍、冊亨、興仁、貞豐、望謨等7縣市;安順市的普定、紫云、鎮寧、關嶺4縣;六盤水市全境暨水城、六枝、盤州3區縣;畢節市的威寧縣。南盤江54,900平方公里[3]910,自興義市壩達章入貴州境后,主要流經黔西南州安龍、冊亨、興仁、普安以及六盤水市盤州等縣市,最后在望謨縣蔗香雙江口與北盤江匯合。
另外,以貴陽為中心的黔中和黔南部分地區,是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的分水嶺地帶,尤其是位處貴陽而南的部分縣區,其境內的諸多支流,最終皆匯入紅水河。《貴陽府志》記載:
貴陽之為郡,北阻烏江,南極紅水,嶺亙其中。在嶺之北者曰貴陽,曰貴筑,而修文、廣順踞其西,開州、龍里、貴定拓其東。西以滴澄為限,而中賅清鎮之城;東以甕城為池。而外連平、清之勢,《水經》沅水谷即貴定東南之朵蓬山也,沅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洞庭。甕城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烏江。烏江者,延江也,水勢東北通于荊梁,故其民有荊梁之風。在嶺之南者曰定番,而大塘傳其東南,長寨、羅斛蔽其西,廣順之地亦大半在南。其水西以為桑郎劃界,東以藤茶分山,皆北出而南注于紅水。紅水即盤江,《史記》、《漢書》所云牂牁將者也。上流蟠屈于滇東,而下控匯群川,經兩粵以入南海。[4]
由此可見,位處貴陽以南的花溪、龍里、貴定、惠水、羅甸等縣區亦可歸入盤江流域。質言之,貴州境內的這些縣、區、市,是盤江流域主體區域。
從長時段的時間角度看,該流域所處之地,“在二十億年前,與有著世界屋脊之稱的青藏高原一樣,還是一片汪洋,即古地中海。”[5]85地質構造學的研究發現,云貴高原的形成,主要源于后來的喜馬拉雅造山運動。“大約六千五百萬年前(古新世早期),漂移中的印度板塊向歐亞大陸沖撞和擠壓,由此揭開了喜馬拉雅造山運動的序幕。”。[5]86這種地質構造運動,有上升,亦有下降。上升就導致原為汪洋的部分隆起為陸地。云貴高原就是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但由于是掀斜式上升,即今云南部分上升速度較快,而今貴州部分上升速度相對較慢。從而造成云南部分的海拔均高于貴州,且有顯著的高原面。但總體海拔均超過800米,因而統稱云貴高原。由于海拔落差大,今貴州部分常受到來自云南高原面上的水流沖蝕,不僅導致貴州地形地貌支離破碎,而且也使得盤江流域在貴州境內支流如人體的毛細管一樣,遍布黔中、黔南地區。
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在更大的自然空間中,就會發現貴州不僅是云貴高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矗立在周邊諸多盆地或丘陵之中。東面是兩湖(洞庭湖南北)盆地、南面是廣西丘陵、西面是昆明盆地,北面為四川盆地。且西面烏蒙山、北部大婁山、東北面武陵山將貴州與云南、四川、湖廣等地阻隔開來。這些盆地或丘陵,由于海拔較低,生產條件相對優良,且有較為可觀的生計資源,從而導致這四個區域是成熟且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非常適宜人類的生存發展。而貴州作為這四個地理單元的過渡地帶或分割線,正處在斜面上。海拔較高、地表崎嶇不平,多喀斯特地貌。不足以構成一個完整且成熟的地理單元。
二、邊關通道與人群層累
明朝以前,包括盤江流域在內的貴州版圖,分別隸屬四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如黔北遵義地區,隸屬四川;黔東銅仁及黔西南一帶,隸屬湖廣;黔西北一帶,隸屬云南。黔中貴陽、安順一帶未曾隸屬周邊行省,均由夜郎、羅殿等方國實施自治。由此可見,貴州曾經在很長的歷史過程中,與歷代王朝國家的接觸溝通,均是作為四川、湖廣、云南等行省的組成部分而發生,并且扮演這三個行省邊關的角色。這種狀況一直到明朝永樂十一年(1413年)建立貴州行省才得到徹底改變,標志著貴州由此成為王朝國家政治體系中獨立的政治單元。其與周邊行省及王朝國家的關系有了根本性改變,政治地位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自然地理的阻隔作用。“地方性的社會關系必然被納入到一個更為廣闊的社會關系體系中,按照吉登斯的觀點,伴隨著地方上社會關系的‘脫域’(disembeding),國家的滲入對地方而言是一種社會時空的延展,也就是社會關系結構的拓展。”[6]由此,盤江流域的人文生態也就具有更多一層的新內涵。
正因如此,無論是王朝國家,還是周邊省區,盤江流域均與之保持一定關聯。人類對山脈與河流集區隔和交流為一體的結構性特征的熟稔程度,起到重要作用。從而導致他們能根據山形水勢、地形地貌構建適宜通行的道路,即通道。若將歷代王朝國家經略盤江流域的意圖考慮進來,該區域“通道”的出現、延伸、拓展,將具有更加鮮明的人文意圖。因而,這些通道不僅溝通了不同地理單元,“而且因為其超越時空變遷的穩定性”[7]7,一方面,為把握盤江流域與歷代王朝國家的關聯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為理解當地人群形成圖景提供了長時段的歷史視角。
以當前的族稱來看,布依、苗、漢是居住在該區域的三個主要民族。結合文獻史料和田野調查,他們既有相對獨立的居住空間,彼此又無法清楚地劃分居住邊界。
布依族,又稱“仲家”,是盤江流域內一個非常重要的居民群體。“仲家的中心區在靠近廣西的邊境,冊亨、望謨。”[8]39另外還有兩個重要分布區域:一為黔南州羅甸、長順、惠水、平塘等縣;一為自貴陽、安順至貞豐一帶沿線,如安順市鎮寧、關嶺、紫云等縣。總之,“在地理分布上看,仲家是在貴州的西南部”[8]40,即云貴高原上南北盤江、紅水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帶。
根據羅大林的研究[9],當前居住在盤江流域的布依族,是自公元前214年起,到北宋皇祐年間的一千多年里,由原居廣西的越人、俚人、柳州八姓兵和儂人先后四次北上遷徙而來。分別進到王朝國家勢力介入相對薄弱的望謨、冊亨、安龍、貞豐、羅甸等縣,即今貴州西南部。在日常生活中,根據時勢和自身需求,借助境內水系支流眾多的便利條件,在不同區域間遷徙,以致形成不同聚居區。該區域的苗族,主要居住在苗嶺山脈中段。在當地民間敘事中,蚩尤與黃帝、炎帝戰敗后,苗族先祖從黃河流域往南遷移,進入長江流域,然后再西遷至貴州。這一說法,雖史無確載,但基于山形水勢構造而成的自然通道,為其提供了地質構造學上的理論依據。“紹興—萍鄉—北海斷裂帶不但聯系了整個華南地區最主要的水系和平原(洞庭湖盆地、鄱陽湖盆地、金衢盆地),而且西接云貴高原,東入黃淮海平原,承接了整個東亞大陸的南部,無愧于東亞大陸南部人群遷徙‘大動脈’的稱號。”[7]19由此,可以明了貴州苗族遷入貴州的大致路徑。之后,基于自然地理生成的“通道”對其在貴州境內分布格局的形成發揮重要作用。經過長期的內部遷移和發展,形成三大分布區:銅仁和湘西的接壤區域是東部分布區、黔東南是中部分布區、貴陽-安順一帶是西部苗族分布區。中部分布區是貴州苗族的聚居中心區。20世紀50年代,費孝通先生對貴州苗族聚居中心區有明確界定:“在地圖上,把爐山(今凱里市)、臺江、雷山、丹寨四個縣城作為四點,用鉛筆畫成一個四方形,這個四方形就是貴州苗族的中心區,里面的山地大部住著苗族。”[8]23這種聚居結構的形成與橫貫貴州的苗嶺緊密相關。
苗嶺本來是長江水系(北部)和珠江水系(南部)的分水嶺,這一點類似于秦嶺。但苗嶺卻不能像秦嶺那樣將南部和北部完全隔離開。因為苗嶺除個別地方有較高山峰外,整體海拔均低于秦嶺,難以對貴州南北兩個部分起完全阻隔作用。海拔較低的山脊線適于人類通行。沿著苗嶺應該有一條可用于民間溝通交流的道路,并通過南盤江及其支流與廣西相通。
據楊庭碩先生考證:“苗嶺山脊上是高山草原區,地面無大阻礙通行較為方便。”[10]明朝天順二年(1458年),東苗首領干把豬率領族眾就是沿著這一山脊去攻劫都勻衛及其周邊屯堡的。
盤江流域的漢族居民,可追溯到漢代。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從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經略西南。“政治上在西南夷地區設置郡縣,經濟上在西南夷地區設立鹽鐵官,實行鹽鐵專營制度,文化上將漢文化大量而源源不斷地輸入到西南夷地區。”[11]遺憾的是,此后一千多年的時間里,均未曾有大規模的漢人遷入。自明朝洪武年間始,中原漢人大量遷入。
首先,軍士及其家屬進駐衛所。明朝洪武年間,盤江流域先后建立8個衛所:貴州衛、新添衛、龍里衛、貴州前衛、普定衛、安莊衛、安南衛和普安衛。有研究指出,“在貴州,目前還未發現衛所士卒由土人充當的情況。”[12]質言之,衛所軍士及其家屬,皆由外地遷來,中原是主要來源地。以明朝衛所的設置標準,每衛5,600人,八衛計44,800余人。加上其家屬,總數應接近10萬。相關研究發現,衛所軍士及其家屬主要居住在城中。“貴筑縣與貴陽府同城,城內居民主要是明代貴州衛和貴州前衛漢族軍戶的后裔,……龍里縣城內居民也主要是明代龍里衛漢族軍戶的后裔。”[13]
其次,商屯誘致四川等地漢族農民到此屯田。建立商屯,募商人納米中鹽,是明朝解決衛所軍士糧食需求的一種重要手段。洪武十五年(1382年)和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王朝先后在貴州發展商屯,將內地鹽商招募到此“開中”,鹽商招民屯田耕種,以換取鹽引。據統計,“洪武年間,先后在播州及普安、普定、畢節、赤水、層臺、烏撒、平越、興隆、都勻、偏橋、鎮遠、晴隆、銅鼓、五開等衛‘開中’,招募四川等地的漢族農民到此屯田,僅正德、嘉靖間至黔的移民就不少于數萬人。”[14]具體地說,以貴陽為中心,沿西南方向縱深分布,貴陽市花溪區,黔南州龍里、貴定、平塘等縣,黔西南州安龍、普安等縣,以及安順市普定縣等是盤江流域內主要的漢族聚居區。
總之,當前盤江流域的人群,的確是在長時段歷史過程中,不斷層累而成的。縱向看。在自秦至清的兩千多年里,布依族、苗族和漢族先后因不同原因、借助不同“通道”、從不同方向,規模不一地遷入盤江流域。即使是同一民族,經多次遷徙后,形成當前之狀。如布依族,先后四次向盤江流域遷移。或者在進入貴州后,向省內縱深區域多次遷移,從而形成不同聚居區,如苗族。橫向看。不同民族的民眾在進入后,雖有相對獨立的居住空間,但未有明確邊界。明清時期,這種特征更加明顯。不同民族間的交流、溝通,隨之出現。一方面,導致盤江流域的民族格局發生顯著變化,形成多族(布依族、苗族和漢族)混融之狀。另一方面,不僅對明清王朝國家治理和發展該流域提出挑戰,且在相當程度上重組、融合和再構當地民眾的社會生活和文化實踐。
三、集市塑造共生
青巖,又名青崖(明代文獻多書為“青崖”,而清代文獻則皆書為“青巖”)明朝以前,此地為仡佬族、苗族和布依族聚居區。布依語稱“青巖”為“四只把”,意指“人用四肢從大山里扒出來的地方”[15]。苗語將其表述為“格養”(GeilYangx),意為地處相對靠北的羊場。意味著生活于此的民眾,與自然生境、人文生境的關系已發生明顯變化。明朝洪武年間,隨著貴州前衛的建立,“青巖”之內涵,進一步豐富,指“軍隊駐扎的地方”或“大兵們住的營房”或“屯兵住的房子”。
青巖東北面是花溪區高坡鄉,為“背牌苗”(因其女性服飾上有一塊背牌而得名,又名“紅簪苗”“印牌苗”“高坡苗”)聚居區;南面為八番土司區,是布依族聚居區,如惠水、長順、貴定、龍里等地,亦有“海葩苗”(因其女性服飾上綴有海貝而得名,又名“海楩苗”)居于其間;北面的花溪,曾名“花仡佬”,因該地曾為仡佬族居地。就生計資源而言,以南為“長順-惠水丘陵低山壩子小區”,地勢起伏小,農耕歷史悠久,土壤熟化程度較高[16]。作物可一年兩熟,水資源充分,歷來有“貴州糧倉”之稱。
就交通條件而言,湖廣、四川通往云南的諸多驛道在此交匯。黔桂驛道雖建于元朝,且途經青巖,但因當時貴州在全國政治版圖上處于鄰近四省的邊地,“不同民族以無政區統轄、更無規模化內在關聯的地理和文化碎片狀態‘鎖居’于自己的狹小環境之中”[17]174,導致通行性較差。明朝統治者將貴州視為戰略要地后,開始整修驛道,提升通行性,并且,廣順、長寨、惠水為“貴州糧倉”,由此更能凸顯其青巖交通要道的現實意義。
青巖不僅是多民族匯聚之地,而且是連通糧食產區(八番土司)與糧食消費區(衛所屯軍)的交通要道,更是將廣西與貴州關聯起來的沖要之地。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貴州前衛建立時,將青巖作為其權力系統拓展延伸的重要節點,在此建立青巖堡。鑒于其便利的交通條件。外來人群源源不斷的遷入,并在此定居生活。在今青巖鎮轄區諸多姓氏民眾的記憶中,其先祖都是從外地遷徙而來。江西籍趙昉即在此時攜帶千金入黔,購地居于青巖堡附近,以致形成今青巖谷通寨趙氏一族之盛景[18]。無論是漢族或者苗族等,都在商業或農業的名義下,緊緊地嵌入到青巖堡的地方社會中。
青巖堡首任百戶王榮“爽朗慷慨,廣交朋友,和睦四鄰,善待商旅,且對本寨弟兄們之事十分關心”[19]。因而,當地及外地遷來的民眾,將青巖堡稱為“王榮堡”。其治理方式和過程,彰顯出兩方面理論內涵。借助自然地形的有利條件,聯合周邊其他屯堡,共同控扼要道。“青巖堡背靠獅子山,面由青巖河環抱,居高又守險,控制當時貴陽通往惠水、長順、羅甸、都勻的驛道,一兵屯此,萬軍難過。”[15]獅子山地勢較高,山頂寬廣且視野開闊。并且,“獅子山后有楊眉堡,順河而下三五里有余慶堡,均是屯兵駐扎的地方”[20],二者形成犄角之勢,共同守護驛道,使之成為貴州衛、貴州前衛與全國驛道網絡相連通的重要節點,又是連通定番(今惠水縣)、廣順糧倉的關鍵之處。在“建衛設堡——商人遷入——各族融入”的螺旋式進程中,隨著交往頻度的增加,青巖堡的社會變遷過程呈現出集市化的趨勢。“青巖場原系屯堡,……因地當柜員通往廣順、定番道上,市集繁榮,故有二場,一場在寅未日,一場在己亥日。”[21]自此開始,青巖堡在承擔衛所軍事職能的同時,還承擔著“郡邑”的民事職能,成為周邊區域聞名遐邇的集市。
此后,青巖雖有從青巖堡變成青巖司的經歷,也有從青巖土城向青巖石城華麗轉身的過程。無論如何,其集市職能始終未變。進入民國后,隨著公路修建,青巖集市的規模和吸引力受到明顯的影響。但是,無論其市況如何萎縮,青巖作為“貴州糧倉”惠水、長順與貴陽間商業要道的地位始終未曾變過,并且由于青巖無甚產出,同樣吸引周邊民眾將農特產品運往此處銷售。時至今日,青巖仍是盤江流域地方社會中非常典型的集市,是當地民眾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集市。
不管是青巖堡,還是青巖司,其作為明王朝治理盤江流域的重要政治設施和制度安排,一項重要的功能就是將不同自然區域或不同人群區隔開來。但是囿于不同自然區域的生產條件,或者不同人群的生產技能差異,導致他們之間需要通過“物”的交換才能滿足日常生活的需求。總之,青巖作為集市,自其源起的那一天起,在以物品交換為主要形式的基礎上,不僅滿足了明朝衛所屯軍糧食需求,以及不同族屬民眾日常生活需求,而且也將盤江流域地方社會與王朝國家,以及原先被作為政治設施的青巖堡區隔之后的民眾關聯起來,成為一個和諧共生的整體。
以青巖集市為個案勾勒的盤江流域民眾經濟生活圖景,表面彰顯該區域苗族、布依族和漢族等人群在喀斯特地貌中的生計特征,實質表征的是王朝國家在邊疆治理和發展中扮演的角色,與理想的制度預設存在一定距離。盤江流域中的村莊,并非可自給自足的生計單位。王朝國家在此實施的土司制度、衛所制度,并非萬能,尤其是具體實施過程中的強硬武力彈壓手段,并非解決地方民眾日常生活中所有訴求的靈丹妙藥。集市作為創造、維續盤江流域地方社會與王朝國家、土司與衛所屯軍以及不同族屬人群之間相互聯系的機制,在彌補上述缺陷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第一,隨屯軍衛所設立而生成的集市,是明王朝在盤江流域實現“早期國家化”目標的重要手段。據統計,“在貴州全省的1939個集鎮中,處于交通線和設立過衛所的地區的有714個,占總數的36.82%;其中,位于主驛道上的有434個,占總數的22.38%。”[17]188若將統計時段限定在明清時期,這種結構特征會更加明顯。“明朝時期的集鎮處于交通線及衛所所在地的有24個,占總數的68.57%,明清兩代處于交通線及衛所所在地的集鎮有42個,占總數的52.74%。”[17]188它們在推動盤江流域社會秩序、經濟發展、文化型塑的同時,還要盡可能地滿足大量衛所屯軍的糧食等生計資源的訴求,即通過集市的交換功能,將產自于土司聚居區的糧食等生計資源,協調分配給衛所屯軍。為將集市的功能發揮到最大,在衛所權力系統不斷向土司地區縱深延伸過程中,集市也隨之拓展到土司長官司駐地。
第二,“改衛設縣”“改土歸流”后,在延續原有集市的基礎上,產生數量不菲的基層集市。這是大量外來商人和地方民眾,基于地方物產與民眾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此時,集市主要扮演將不同區域、不同族屬之間的物產進行協調分配的角色,以滿足不同人群的日常生活需求。尤其當不同區域、不同族屬人群的生計資源、生產技能、日常生活等方面存在差異時,集市的協調分配功能得到凸顯,且蘊藏在物品交換背后的跨族屬的文化互動與社會交往,集體無意識地消弭了原有的文化邊界。
結 語
盤江流域的集市,是長時段歷史過程中,王朝國家、地方社會基于共同訴求發展出的諸多集市總和,包含區域中心集市、鄉鎮集市和村集市。不同層級的集市,雖輻射范圍不一、覆蓋人群不同,但鄉鎮集市、村集市與交通線或衛所所在地的區域中心集市共同形成集市體系,分工合作,互通有無。“在衛所城鎮的城市商業的推動下,城鄉之間、漢夷之間的經濟往來日益頻繁。”[22]當這種經濟往來與文化生態互嵌時,集市的功能性特征更加凸顯。既是王朝國家治理邊疆的重要載體,更是協調分配生計資源的主要平臺。表面看,是生態、文化以及理念方面差異導致“物”的交換。實質上,在這種交換背后,蘊藏著王朝國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博弈,更潛隱著不同人群間的社會交往、文化融合和邊界重組。在這個意義上,明清時期中央集權體制下的邊疆治理和發展,王朝國家與地方社會、中原移民和地方土著,并非是斗爭哲學視野下的對立二分,而是彼此融合形成新狀態、新樣式和新機制的共生過程。昭示出王朝國家體制下,邊疆民眾社會生活和文化實踐中的重組、融合和再構過程,實質是一種以二元或多元為基本內涵的治理與發展過程。它在延續傳統的邊疆治理與發展理念的前提下,彰顯了邊疆民眾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在豐富和鞏固民族區域自治內涵的同時,更賦予中華民族共同體新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