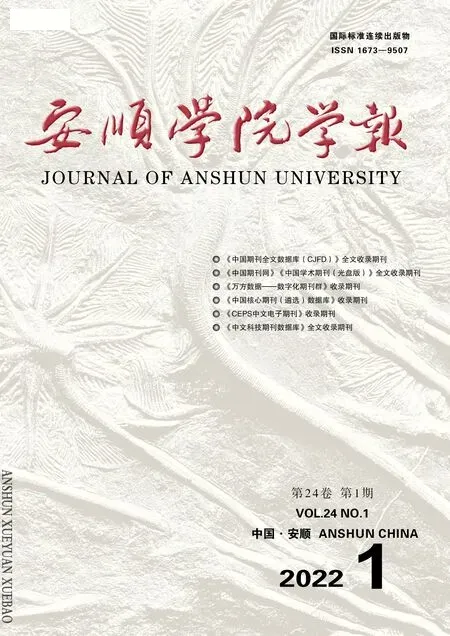道德敘事研究綜述
王嘉儀
(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湖南 長沙410081)
“敘事”的概念,從狹義上看,即是講故事,指敘述者的口頭或書面語言;從廣義上看,敘事是指按時間順序對一系列有關聯的事件或行為進行描述的活動。“道德敘事”同樣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指講道德故事,廣義指人創造意義的整體生活形態。因此,道德敘事的研究按照這兩種思路展開兩條研究進路。國外對道德敘事的研究有兩個不同面向:一是側重于敘事學中倫理因素的分析;二是作為美德倫理學中論證自我統一性的重要概念。中國對道德敘事的起步較晚,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敘事學初步探索出一條梳理傳統文學和史學的新道路。作為一個跨學科的概念,各領域對道德敘事的研究有不同程度的側重點,使其內涵較為豐富和復雜,但也存在過于散亂而缺乏針對性的問題。因此,這一研究意在明晰道德敘事研究的內容,包括概念界定、基本要素、特點和作用,更好地展示敘事與倫理的關聯,為倫理學研究提供新視角、新方法。
一、道德敘事研究現狀
(一)國外研究現狀
1.道德敘事即是講道德故事
西方的“敘事”源于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在《修辭學》中認為“敘事”是“證人在法庭上陳述證詞的行為”[1];柏拉圖則將其與“模仿”相對,認為“敘事”是表達一種“純粹的敘述”[2];而托多羅夫在《〈十日談〉語法》中首次正式提出“敘事學”這一概念。最早將“敘事”定義為“講故事”的是熱拉爾·熱奈特,他和托多羅夫一起創建了“敘事學”。20世紀60年代以來,結構主義敘事學興起和發展。結構主義敘事學以現代語言學中的結構主義理論為基礎,著力探究敘事作品內部的規律與各要素之間的關聯,進而對小說的結構形態,寫作規律和表達方式都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敘事學在這一階段得以全面發展,因而也被稱為“經典敘事學”時期。20世紀90年代以來,后經典敘事學批判結構主義敘事學將敘事學技術化、機械化,在不同程度上隔絕小說與社會、歷史等環境因素的關聯。這一時期,敘事學家開始關注政治、歷史、文化、宗教、倫理等層面上的內容。正是后經典敘事學將眼光從文本的內部結構轉向外部環境,意味著敘事學的研究在認知意義上的轉變和跨學科趨勢的產生,這一轉向離不開布斯和費倫在敘事學理論上做出的努力。他們關于“修辭性敘事理論”的探究推動了敘事倫理研究的進展,使得小說理論與敘事學結合趨向了倫理維度。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強調了修辭的倫理價值,認為修辭學的本質在于“發掘正當信仰”[3],并提出了“隱含作者”這一概念,主張對敘事主體進行倫理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強調作者立場和發掘文本深層意蘊的兩種對立觀點。費倫在《作為修辭的敘事》中將文字作品看作是一個由修辭者向接收者傳遞信息的媒介[4]。他聚焦于敘事形式,形成倫理和審美之間的循環互動,以及多層次性、動態性、開放性的敘事理論,強調敘事技巧中也隱藏著倫理,這對敘事學的倫理轉向有了開創性的突破。由此,對敘事形式、敘述者、隱含作者、受述者之間的分析增添了倫理上的復雜性。
敘事學的轉向是應時代多元化發展的趨勢,道德敘事在后經典敘事學發展到蓬勃之際開始初露鋒芒。J·希利斯·米勒《閱讀倫理》關于“閱讀的倫理問題”的提出與討論具有開創性意義,米勒認為閱讀是能做成某事的行為,是關涉倫理和義務的行動。他從作者、敘述者、人物和讀者四個維度分析閱讀的倫理,在他看來,雖然倫理與敘事的關系并非絕對對稱、和諧,但兩者是不可分的[5]。將敘事文學的內容和形式納入倫理考察的范圍的里程碑式著作當屬亞當·桑查瑞·紐曼的《敘事倫理》。在這一書中,明確提出“敘事倫理”一詞,并進一步分析“敘事倫理”的三重結構:再現倫理、講述倫理和解釋倫理。敘事倫理通過這三層結構分別強調關注文本的敘事內容、敘事形式和敘事交流。敘事與倫理的關聯在敘事學的發展歷程中逐漸建立起來,二者相互融合和張力使得道德與敘事相結合的輪廓逐漸清晰。
2.道德敘事與倫理生活
“敘事”的研究不僅僅停留在語言和文本的層面上,“敘事”概念從語言擴大到對人類實踐生活的描述,美德倫理學中用“道德敘事”來指人創造意義的整體生活形態。實際上,敘事與倫理在古希臘時期就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在古雅典城邦中,智者常常在演講中運用修辭藝術獲得民眾的支持,從而在政治上取得話語權。在公元前4世紀,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一書首次將修辭術理論做了系統的闡述。亞里士多德認為:“修辭術辯證法的對應部分,因為二者關心的對象都是人人皆能有所認識的時期,并且都不屬于任何一種科學。”[1]由此可見,修辭術與辯證法的邏輯三段式不同,修辭術是一種“實踐智慧”,它區別于邏輯學嚴密的推理步驟。修辭作為一種說服力,意在運用比喻、隱喻、寓言、夸張等手法來說服人,其關涉演說者的品格與聽眾的心理情感。在這個意義上,修辭學可以視為倫理學的一個分支,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一直到20世紀末仍然發揮著重要的影響。
麥金泰爾正是通過考察古希臘的社會美德觀念以及亞里士多德對諸美德的解說,力圖在德性理論的框架下構建道德敘事。他通過考察古希臘社會以及英雄史詩的敘事,發現了英雄美德的踐行既依賴于特定的人,又依賴于特定的社會結構。道德在某種程度上受限于社會的特殊性,他的道德敘事是在信念、背景和語言中探討“自我”統一性的主張,為超越實踐界定的德性提供解釋與理解的語境[6]。保羅·利科對麥金太爾敘事理論進行批判并進一步推進,區分文學虛構的敘事與現實生活的敘事。在《作為一個他者的自身》中通過描述、敘述與規范,即:誰在說話和行動、誰在敘述故事、誰負責任來回答“什么是人”這樣的倫理問題。
(二)國內研究研究現狀
中國的敘事傳統同樣在文明初期就已經萌芽。如原始社會先民以畫圖、結繩的方式記載互動。“敘事”最早連綴使用是在《周禮》中,其核心內涵在于正秩序、明規范,“敘”與“序”相同,“敘事”表明不同職官按照周朝禮儀有序安排祭祀活動,因而“敘事”的原初內涵與人倫秩序結合在一起。唐代《通史》特設《敘事》篇,宋代《文章正宗》專列敘事文類,“敘事”作為四類文體之一被明確提出,“敘事”開始作為文類概念并受到廣泛認可。明末清初,隨著古典小說形態的逐漸成熟,開始興起一批評點家,有金圣嘆、張竹坡等人,他們以“追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為起點,又對敘事的技巧和方法傾注了極大熱情,在某種程度上豐富了中國小說評點的敘事理念,也可以被看作中國敘事學的雛形。
20世紀80年代以來,受國外敘事學研究熱潮的影響,中國學者開始大量翻譯西方敘事學著作,并運用西方敘事學的理論框架研究中國的敘事文學作品。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開始關注中國文學的敘事特色,意識到中西方文學之間的“時間差”和“語言差”,從古代典籍中探索出中國文學的內在發展邏輯,并逐漸確立了一種新的敘事學思維。但是中國敘事學對倫理的關注并不完全遵循著西方敘事學的發展脈絡,不像后經典敘事學對經典敘事學那樣有著從內部孵化和突破的關系,而是參照著西方敘事學的方式“摸著石頭過河”,探索出一條梳理自身傳統文學的新道路。浦安迪的《明代小說四大奇書》和《中國敘事學》,開始探討中國古典說的敘事式,并引起國內學者將目光轉向本土資源[7]。之后,楊義在《中國古典小說史論》的基礎上寫成的《中國敘事學》,從敘事學中的結構、時間、視角、意象、評點家五大板塊進行立論,總結出具有自身形態存在的中國敘事學原理[8]。傅修延的《先秦敘事研究》從中國文學的源頭出發,意指構建中國敘事學[9]。隨著中國敘事學的對中國本土資源的挖掘,道德敘事研究在中國也開始有新的研究視角。
其一是講道德故事。萬俊人在《重敘美德的故事》中敘述了貝內特的《美德書》,認為貝內特編寫美德故事的目的在于把美德教育擴展到社會公共領域,并表明美德故事的講述要比道德推理更直截了當、簡明易懂,在他看來,道德知識從原初就是依靠人們的道德生活體驗,通過情感和心靈來傳遞和生成的[10]。他認為講述美德故事不僅蘊含于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更是存在于整個人類的傳統文化之中。李培超在《中國傳統美德敘事中的道德榜樣意象》一文中認為,中國文化是一種倫理型文化,中國傳統敘事從本質上就是美德敘事,美德敘事關注人的修為,因而應當聚焦于道德榜樣意象的研究。與西方美德倫理學中對人品德的強調有所不同,中國敘事中的道德榜樣是完整的人,它具有以下特征:整全性、生活化、歷史性[11]。正是這種具有獨特意義道德榜樣意象,傳承了中華民族的道德精神。其二是將道德敘事視為一系列相關聯的事件和活動中呈現的德性。劉小楓是國內引入“敘事倫理”概念的第一人,他在《沉重的肉身》中區分了理性倫理學和敘事倫理學,開始了漢語界對敘事倫理的探討[12]。馮慶旭、晏輝、文賢慶等學者不再把“敘事”局限于文學所講的敘述故事,而是將“敘事”擴大為一種具有倫理性的人的存在方式,這使得“敘事”成為一種“敘事哲學”。道德敘事就是關乎人類的生命和生活的敘事哲學,是指蘊含道德價值和道德解釋、關于個人的生命成長和人類社會發展的敘事。
二、道德敘事的主要內容
(一)概念界定
從對道德敘事研究現狀的梳理可以看出,“道德敘事”的研究呈現出豐富性和復雜性的基本特征。“道德敘事”是一個跨學科的合成詞,是兼容“敘事”與“倫理”的多元化研究。因而不同學者在各自領域的研究中,對概念的界定有所不同,但具體說來大致分為以下兩個層面。
第一,把道德敘事理解為講道德故事。以丁錦宏為代表,他認為所謂“道德敘事”,是指“教育者通過口頭或書面的話語,借助對道德故事(包括寓言、神話、童話、歌謠、英雄人物、典故等)的敘述,促進受教育者思想品德成長、發展的一種活動過程。”[13]這一定義廣泛運用于教育學的實踐上,被認為是提高德育實效性的有效途徑。另外,在文學領域中,道德敘事也被視為文學敘事的隱藏脈絡,成為現代文學倫理批評的范式之一。張光芒認為中國近代文學是真正的道德敘事,并從其實質內涵進行深入分析[14]。楊慶東運用道德敘事研究初探20世紀中國婚戀文學的道德敘事樣態[15]。
第二,將道德敘事理解為隱藏在個人生命成長和人類生活發展背后的價值觀念。國內學者馮慶旭認為道德敘事,是指蘊含道德價值或具有道德價值解釋力的以言說和行動為主要表現形態的關于人的生命成長和人類社會發展的敘事[16]。晏輝就敘事的道德性質和倫理教化解讀道德敘事,認為道德敘事的目的是為了展現故事情節[17]。文賢慶指出哲學意義上的敘事是人類基于反思能力對生命和生活意義的創造,不同的生命體驗和生活經歷創造了不同的意義,體現為不同的道德敘事[18]。
(二)基本要素
盡管道德敘事研究有跨學科趨勢,但是其理論成果仍然建立在敘事學的基礎之上。道德敘事研究自覺運用敘事學的方法和意圖,借鑒敘事學的研究,有利于建立一種較為清晰的思考框架。依據敘事學的基本研究框架,道德敘事研究可以分為以下基本要素:敘事主體、敘事客體、敘事內容、敘事方式。
第一,敘事主體。按照“故事法”理解道德敘事,敘事主體主要指具有德性的個人或群體通過言傳身教的方式,直接或間接地傳達道德原理。將“故事法”擴展到生命故事的范疇,敘事主體是以自我的生活體驗和生命經驗作為闡釋道德原則的主體,敘事主體不斷創造故事,也在理解故事,敘事主體具有自我意識和反思能力。道德敘事與人相關,人又是歷史中的人,這意味著道德敘事的展開需要敘事主體在歷史時間中去思考和反思生命與生活的道德意義。
第二,敘事客體。敘事客體表現為傾聽故事的個人或群體,即故事的接受者。在德育領域,敘事客體被窄化為是未成年人或者德性不足之人。在道德生活中,每個人都處在敘事之中,在人與人的互動交流中,不斷獲得他人的生活體驗和實踐經驗,并受用于自身。顯然,道德敘事的敘事主體具有能動作用,而敘事客體具有受動性。正是在主體與客體產生的相互影響下,道德敘事具有啟發德性和激發自省的倫理效用。
第三,敘事內容。敘事主體與敘事客體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敘事內容正是敘事主客體的紐帶和橋梁。敘事內容即道德故事,包括了語言文字形態和生活形態,是主客體互動的載體。道德敘事區別于其他敘事之處就在于敘事內容具有道德性,它包含著道德立場或是道德判斷,意圖讓人得以趨向真、趨向善。敘事內容最基本的要素就是人物、事件和情節,它需要通過某些人的某種行為及其所成就的事件展現出來,傳遞出“應當”的訊息,如果沒有這三個基本要素就不能構成敘事,如果沒有傳遞“應當”的訊息就不能構成道德敘事。
第四,敘事方式。在道德敘事中,敘事內容的“應當”訊息如何傳遞出來顯得格外重要。一個道德故事如果無人問津,那么它對我們的生活就無法發揮效用。敘事方式即是傳遞道德原理或道德規范的手段和方法,敘事方式的目的在于使得主體與客體在故事的講述和傾聽過程中獲得共鳴,激發對意義的闡釋,甚至在不經意間改變或塑造了人們的生命感受。
(三)主要特點
從倫理的視角看,國內學者對道德敘事研究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使得道德敘事呈現不同的特點:特殊性、當下性、歷時性、合理性。
第一,道德敘事的特殊性。道德敘事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敘事,它是超越了敘事理論的一種具有方法論意義的研究方式,同時也是人類生活必不可缺的意義形態。道德敘事的目的決定了道德敘事的方式、手段和途徑,晏輝認為道德敘事的目的在于教化,而人類并不意味著天生具有德性,因此道德敘事對于人類是必不可少的。人類的發展和進步依賴于道德教化,道德敘事就是人類具有德性的獨特的重要條件[17]。
第二,道德敘事的當下性。強調道德敘事的當下性重在發揮道德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促使人們意識到道德主體的所在所為都是具有強大的道德力量的,甚至影響個體道德人格的形成乃至社會道德意識的發展。
第三,道德敘事的歷時性。強調道德的當下性并不意味著忽視道德敘事的歷史維度,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9]顯然,人是歷史中的人,沒有歷史則無所謂當下,道德敘事是在歷史文化傳承的過程中敘寫人類的道德生活史。道德敘事的歷時性是在時間中對個人生命和個人生活于其中的傳統的持續反思與發現。
第四, 道德敘事的合理性。人類作為一種敘事的生物,會形成關于自身經驗的倫理觀念,經驗的外化形成群體的倫理觀,從而不同的民族會形成不同的風俗習慣和倫理規約。面對文明的沖突,則需要發揮倫理敘事的合理性,依靠他性的想象規約,強調作為方法的敘事導引出來的倫理觀,用敘事的方式展示倫理的“至善”以解決倫理學的實踐困境。
(四)重要作用
國內不少學者認為,道德敘事研究無論是對道德認知還是道德生活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可以大致歸結為三點:
第一,道德敘事激活對世界的認知。道德敘事是一種歷史悠久的德育形態,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無論是傳記史詩還是虛構小說,敘事都旨在用更生動的、更貼近人們道德生活的方式來傳達生活的意義。美德故事的講述區別于教條式的規約,而是通過簡明記錄和親切描繪,塑造出人類應該有的形象,并不斷地建構歷史文明和道德文化。正如麥金太爾所說的:“失去了美德故事,孩子們的言語和行動就會變成沒有腳本而又渴望張嘴的口吃者。除了通過構成社會最初戲劇資源的那些故事,我們無法理解任何社會。”[5]
第二,道德敘事激發情感共鳴。無論是以文學的形式還是以生命的形式傳達出來的道德故事,都基于生活世界。這意味著道德敘事不是純推理、純概念化的東西,而是一種具體的表達和感性的審美。道德敘事有機地融合了經驗和理論、具體和抽象、感性和理性。它內在蘊含了人類道德生活中的實踐智慧的反思經驗,通過捕捉到人類生活中某些相似的特征,從而激發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共鳴,實現價值傳遞。
第三,道德敘事約束道德行為。道德敘事具有直觀的語言、文字或者行為,這些都對我們的生活產生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道德敘事不以明確的條例規范來約束人們,而是以生動鮮活的形象對人們產生情感連接或者引發認知思考。道德敘事重構一個新的世界,通過這個重構世界來評判什么是美好的生活。道德敘事的旨趣正是要通過有趣的故事或生活經歷,來告訴我們做人做事的道理。
三、道德敘事研究評價
綜上所述,道德敘事研究在21世紀以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然處于起步階段。道德敘事研究始終以倫理學為視點,汲取豐厚的哲學理論和文學資源,形成多向度的跨領域研究,是一項值得進一步探索的研究。
(一)積極意義
傳統倫理學的研究重在探討倫理規范原則和義理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經驗性的道德生活面向。近代以來,在推崇嚴謹的科學推理知識背景下,倫理學的研究更是走向重知識、輕經驗的道路。道德敘事的出現,為倫理思想生活化提供新的理論進路,讓生動鮮明的生活世界成為倫理學研究的源頭活水。
中國文化是一種倫理型文化,中國的傳統敘事本質就是道德敘事。中國傳統敘事文學發揮著巨大的倫理教化功能,上至官方的史傳記載,下至民間的神話傳說,都在提供對待人類生活的總體見識。無論是歷史故事還是虛構的故事,敘事都是一種區別于科學范式的表達,它是需要經驗世界中的人去洞察故事中隱含的信息,從而再對我們的生活世界發生作用的一種重要方式。從實踐意義上看,道德敘事研究是對中國文學文本的縱深觀照,同時啟發中國當代道德文化建設。通過梳理文本背后的道德觀念和價值判斷,有助于推動倫理學話語體系創新,以便用更加易于理解的方式弘揚中華傳統價值觀念,在新時代以新的方式實現文以載道。
(二)不足之處
首先,道德敘事缺乏明晰的概念區別于相近的其他概念。如龔剛在《敘事倫理不是倫理敘事——哲學敘事學對話錄》中對倫理敘事(ethical narrative)與敘事倫理(ethic of narrative)這兩個概念的區分[20]。 “倫理敘事”和“敘事倫理”兩個概念所涉及的定語和主語不同,導致研究的側重點不同。而目前的諸多研究對于這幾個概念的運用沒有做出嚴格區分。從道德敘事的發展脈絡來看,“道德”與“倫理”兩個詞并未做過多的區分,皆看作根據生活經驗而形成的行為規范。但在倫理學領域,“道德”與“倫理”并非完全一致,這兩個詞的詞源、范圍、運用皆有所區別。因此,也使得“道德敘事”“倫理敘事”和“敘事倫理”在進行概念界定和使用時產生混淆。
其次,道德敘事未能形成扎根于中國本土文化的理論研究。中國敘事學在對中國傳統敘事的本土化資源進行梳理之時,已經察覺到中國歷史敘事從產生之際就肩負立法垂教、借事明理的重任。這意味著,倫理性是中國傳統敘事的根本特性。道德敘事為倫理學研究打開了新面向,但是學界還未能將道德敘事作為一種方法論運用于倫理學的研究,尚未構建出一個清晰、完整的理論體系。從研究現狀來看,國內的大多數道德敘事研究仍未越出西方學界的研究范圍,無法兼顧本國深厚的傳統資源。事實上,道德敘事與中國敘事學把握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倫理取位的方式相互關照,因而以道德敘事的視角探究中國敘事文學,是推進中國倫理學研究的創新之途,既彌補了從倫理學維度體察中國古典文學這一研究空白,又試圖以嶄新的視角和立體的方式展現出道德與時代文化語境的深隱關系。
綜上所述,道德敘事的研究還需要進一步明晰相關的概念,拒絕照搬西方敘事學研究的模式,基于中國傳統敘事資源構建具有本土化特色的道德敘事理論,并將其運用于對中國傳統敘事經典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