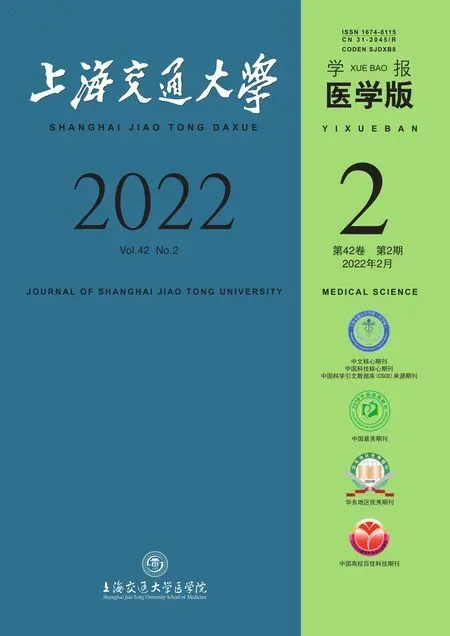糖尿病患者血糖波動異常與認知功能障礙關系的研究進展
張 蓉,陸 麗,王亞昕,董文倩,張 宇,周 健
1.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上海 200025;2.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第六人民醫院內分泌代謝科,上海市糖尿病研究所,上海市糖尿病重點實驗室,上海市糖尿病臨床醫學中心,上海 200233
認知功能障礙是指由一種或多種大腦功能受損(如語言能力降低、注意力和記憶力減退等)導致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學習能力、工作能力和社會交往能力減退的退行性疾病。糖尿病認知功能障礙是指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患者伴有一定的認知功能損傷;根據該疾病的發生、發展進程或嚴重程度,可將其分為無癥狀臨床前期、輕度認知功能障礙和癡呆[1]。研究[2]表明,DM患者罹患認知功能障礙以及其由輕度認知功能障礙轉變為癡呆的風險均較高。血糖水平升高和波動異常是糖代謝紊亂的2 種主要表現形式。既往研究[3-4]表明,反映血糖水平的指標如糖化血紅蛋白(glycosylated hemoglobin A1c,HbA1c)等與認知功能障礙密切相關。近年來的研究[4-5]亦發現,血糖波動異常可能增加DM 患者罹患認知功能障礙的風險。基于此,本文就目前常用的認知功能障礙評估方法進行介紹,對血糖波動異常與糖尿病認知功能障礙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并對血糖波動異常作為糖尿病認知功能障礙防治靶點的可能性進行探索。
1 認知功能障礙的評估方法
DM 對認知功能的不同方面(如執行功能、語言流暢性、記憶力、注意力及整體認知功能等)均會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害[6]。神經心理學測試是目前評估認知功能障礙的主要手段之一,且近年來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等影像學技術也逐漸應用于認知功能的臨床評估。
1.1 神經心理學評估
臨床上,常采用簡易精神狀態檢查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和蒙特利爾認知評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等篩查量表對患者的認知功能進行總體評估。同時,評估特定認知領域的量表也逐漸得到了廣泛應用,如連線測試(trail making test,TMT)對認知功能障礙高度敏感,有A 和B 共2種形式;TMT-A 用于評估患者的注意力和專注力,TMT-B 用于評估患者執行功能,主要對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患者的認知功能減退敏感[7]。斯特魯普色詞測驗(Stroop color word test)也常用于測試患者的執行功能,由于其花費時間較短,尤其適用于老年人和在神經心理學測試中容易感到疲勞的人群。語言流暢性測驗(verbal fluency test,VFT)可評估患者的語言能力、語義記憶和執行功能。聽覺詞語學習測驗(auditory verbal learning test,AVLT)可評估患者的記憶力損害程度,有效鑒別癡呆患者、輕度認知功能障礙患者與認知功能正常者。畫鐘測試(clock drawing test,CDT)可用來評估患者的執行功能、視空間和結構能力,數字廣度測驗(digital span test,DST) 可用來評估患者的注意力和專注力,Rey-Osterrieth 復雜圖形測驗(Rey-Osterrieth Complex Figure Test,CFT)則可評估患者的執行功能、記憶力及視空間和結構能力。
1.2 影像學評估
作為一種無創性檢查手段,氫質子磁共振波譜(1H-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1H-MRS)、彌散張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靜息態腦功能磁共振成像(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rs-fMRI)等新興MRI技術能夠提供大腦的解剖結構、功能連接及代謝物水平等多方面信息,在許多神經和精神疾病的診斷、預后和研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現已被逐漸應用于認知功能障礙領域。
1H-MRS 是一種可以檢測腦代謝物水平及分布的無創性前沿技術。研究[8]發現,在糖尿病認知功能障礙患者[無論是1 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 mellitus,T1DM)患者還是T2DM 患者]的大腦中,其代謝物濃度均存在異常,且該異常亦均與低MoCA得分顯著相關。1H-MRS 可以識別阿爾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患者腦代謝物水平的變化,且其異常水平可能是癡呆的生物學標志物之一,然而很少有研究就異常代謝物水平與認知功能變化的相關性進一步分析[9]。此外,DM 患者腦微結構的變化與認知功能障礙密切相關。研究[10]表明,DTI 技術可量化DM 患者腦部的微結構異常,在鑒別年齡相關的認知功能損傷、輕度認知功能障礙和癡呆方面較為敏感。在認知功能障礙的發生與發展過程中,腦功能異常往往發生在腦結構出現變化之前,而rs-fMRI技術可同時捕捉所有大腦區域之間的相互作用,以識別腦功能的異常。作為一種敏感的成像方式,rsfMRI 技術可在認知功能障礙相關癥狀出現前識別細微的認知功能異常,因此其有望在糖尿病認知功能障礙的早期診斷中發揮作用[11]。
2 血糖波動異常對認知功能的影響及其可能的作用機制
2.1 血糖波動異常對糖尿病認知功能障礙的影響
血糖波動指血糖水平在其高峰和低谷之間變化的不穩定狀態,可分為短期血糖波動和長期血糖波動。短期血糖波動包括日內血糖波動、日間血糖波動、餐后血糖波動等,其評估主要基于持續葡萄糖監測(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CGM)技術;該技術可提供連續、全面、可靠的全天血糖信息,包括平均血糖波動幅度(mean amplitude of glycemic excursions, MAGE)、 葡 萄 糖 標 準 差(standard deviation,SD)、葡萄糖變異系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CV)等參數[12]。長期血糖波動主要指較長時間內同一患者多次隨訪測得空腹血糖、HbA1c等的變異度,多以空腹血糖、HbA1c等的SD 或CV 計算得到。近年來,由于具有定義直觀、易于理解等特點,葡萄糖在目標范圍內時間(time in range,TIR)已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且被認為是反映血糖水平和血糖波動的綜合指標[13-14]。研究發現,TIR與大血管并發癥的替代標志物[15]、糖尿病視網膜病變[16]、尿微量白蛋白[17]、周圍神經病變[18]、自主神經病變[19]等密切相關,但目前鮮少有關于TIR 與糖尿病認知功能障礙的相關報道。
已有研究表明,短期血糖波動異常與DM 患者的認知功能障礙相關。RIZZO 等[20]采用CGM 技術評估121 例T2DM 患者的血糖波動水平,并利用MMSE評估其認知功能;結果發現,MAGE 與MMSE 得分顯著相關(r=0.83,P<0.001),MAGE 也與執行功能和注意力的綜合得分顯著相關(r=0.68,P<0.001)。ZHONG 等[21]使用CGM 技術監測248 例老年T2DM患者的血糖水平,結果顯示其血糖波動異常與患者的認知功能障礙有關,即血糖波動較大的患者的認知功能較差。2020 年,XIA 等[5]采用CGM 技術對97 例T2DM 患者和50 例健康受試者的血糖水平進行監測,依據MAGE 是否小于3.9 mmol/L 將T2DM 患者進一步分為血糖波動正常組和血糖波動異常組,并采用MMSE、MoCA、AVLT、CFT、DST、TMT (A 和B)及CDT 評估3 組被試者的認知功能。結果表明,血糖波動異常組患者的MoCA、TMT-B 和VFT 等測試評分明顯低于血糖波動正常組、健康對照組;同時MRI檢查發現,血糖波動異常組患者的大腦廣泛區域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DC)值亦顯著低于其余2 組(尤其是執行功能的關鍵腦區),即隨訪1.5 年后,相對于健康對照組和血糖波動正常組,血糖波動異常組患者的執行功能和語言能力有明顯降低。1,5-脫水葡糖醇(1,5-anhydroglucitol,1,5-AG)是一種結構與葡萄糖類似的單糖,在高血糖(>10 mmol/L)情況下,其可與葡萄糖競爭重吸收位點,當葡萄糖被重吸收減少時則經尿液排出增多,從而使血中1,5-AG 水平降低,因此1,5-AG 能夠比HbA1c和果糖胺更快速、更敏感地反映血糖波動情況[22]。RAWLINGS等[23]在社區動脈粥樣硬化風險(atherosclerosis risk in communities,ARIC) 研究中納入12 835 例受試者,隨訪平均21 年后發現,血糖控制不佳(HbA1c≥7%)且血1,5-AG 濃度<10 μg/mL 的DM 患者癡呆發生風險比血1,5-AG 濃度≥10 μg/mL 的患者顯著增加86%(P=0.011);且在DM 患者中,血1,5-AG 水平每減少5 μg/mL,癡呆發生風險則增加16%。上述研究提示,短期血糖波動異常可能是引起DM 患者認知功能損害的危險因素之一。
此外,ZHENG 等[4]對1987—2018 年英國臨床實踐研究數據庫中50 歲以上的DM 患者的資料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在6 年中位隨訪期間,有6.3%(28 627 例)的患者發生癡呆。Cox 回歸分析顯示,與HbA1c-CV 最低四分位數(0~25%) 組相比,HbA1c-CV (25%~50%)、HbA1c-CV (50%~75%) 及HbA1c-CV(75~100%)組患者的癡呆發生風險分別增加6%、12%和13%(均P<0.05)。該研究表明,基線HbA1c-CV 升高與DM 患者癡呆發生風險增加顯著相關。因此,長期血糖波動異常亦是T2DM患者認知功能障礙的危險因素之一。
2.2 血糖波動異常對糖尿病認知功能障礙的可能作用機制
血糖波動異常可通過氧化應激和腦血管病變、炎癥損傷和細胞凋亡、胰島素抵抗和β 淀粉樣蛋白(amyloid β-protein,Aβ)的聚集等方面對認知功能產生影響[1],可能的具體機制如下。
2.2.1 氧化應激和腦血管病變 血糖波動異常可加劇細胞的氧化應激,導致糖尿病中樞神經病變。QUINCOZES-SANTOS 等[24]通過更換星形膠質細胞的培養基,即將6 mmol/L 葡萄糖的對照組更換為12 mmol/L 葡萄糖的高糖組、將12 mmol/L 葡萄糖的高糖組更換為0 mmol/L 葡萄糖的無糖組,構建葡萄糖水平波動實驗模型,并對該波動如何誘發星形膠質細胞的細胞毒性進行評價。結果發現:當培養基中葡萄糖水平從6 mmol/L 增加到12 mmol/L 時,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的產生增加了25%;當葡萄糖水平從12 mmol/L降到0 mmol/L時,ROS產生增加了約60%。而ROS 的過量產生對星形膠質細胞的脂質、蛋白質和DNA 等生物分子造成了一定的氧化損傷。因此,培養基葡萄糖濃度的突然變化可能比持續的高水平葡萄糖對細胞的危害更大。
另外,認知功能障礙的發生、發展與腦血管病變也 存 在 一 定 的 關 聯。MAIORINO 等[25]對106 例T1DM 患者進行研究,其中41 例患者行持續皮下胰島素注射、65 例患者每日行多次胰島素注射(對照組)。結果發現,持續皮下胰島素注射組患者的血糖波動更小,循環內皮祖細胞(circulating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EPCs)水平更高,且MAGE 的降低是EPCs數量增加的唯一預測因素。EPCs是骨髓來源的干細胞,能夠在成熟的內皮細胞中分化,參與血管損傷的修復,這表明改善血糖波動可能對T1DM患者內皮穩態產生積極影響。
2.2.2 炎癥損傷和細胞凋亡 血糖波動異常也可以通過炎癥損傷和細胞凋亡,增加糖尿病認知功能障礙的發生風險。急性血糖波動使大鼠海馬中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和白細胞介素-1β(interleukin 1β,IL-1β)表達增多,而大量分泌的IL-1β 可通過誘導黏附分子表達、白細胞浸潤及啟動多種細胞因子級聯反應等導致腦損傷;且TNF-α表達增加可破壞血腦屏障的完整性,導致炎癥和腦損傷的發生[26]。急性血糖波動和長期高血糖都會誘導海馬神經元凋亡,但與長期高血糖相比,急性血糖波動對神經元的損害更為嚴重[26]。此外,HSIEH 等[27]研究發現,急性血糖波動誘發小膠質細胞凋亡可能是慢性DM患者神經退行性疾病的病因之一。
2.2.3 胰島素抵抗和Aβ 聚集 胰島素是機體調節糖代謝的重要激素,也是葡萄糖透過血腦屏障進入神經元所必需的介質,具有神經保護作用[28]。進行性加重的胰島素抵抗可減少神經元對葡萄糖的攝取和利用,導致葡萄糖代謝紊亂及能量失衡,從而引起認知能力下降[29]。
此外,Aβ聚集也是糖尿病認知功能障礙的重要發病機制之一。胰島素降解酶是降解胰島素的蛋白酶,也是降解Aβ 的關鍵酶。發生胰島素抵抗時常伴隨高胰島素血癥,代償性增多的胰島素可與Aβ 競爭性地結合胰島素降解酶,使得部分Aβ不能被降解、清除,從而導致Aβ 發生異常聚集[29]。而Aβ 聚集可對神經細胞產生毒性作用,導致海馬和皮質神經元發生變性、死亡,從而誘發認知功能障礙[29]。目前,關于血糖波動與Aβ聚集間的關系和機制研究尚缺乏相關報道。
糖尿病認知功能障礙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存質量,而具體作用機制尚未被完全闡明。除上述可能的機制外,Tau 蛋白的過度磷酸化、大腦微環境、中樞神經系統類淋巴系統功能障礙等也可能與DM 患者的認知功能障礙的發生和發展有關[30]。未來仍需更多的研究就糖尿病認知功能障礙的病理機制進一步探討,以期為其預防及治療提供新的靶點。
3 降糖藥物與認知功能障礙治療
隨著對DM與認知功能障礙間相關性認識的不斷加深,多項研究已就不同降糖藥物是否可改善DM患者的認知功能障礙進行了深入探索,并為該類患者的臨床治療提供了循證醫學證據。大量臨床研究表明,胰高血糖素樣肽-1(glucagon-like peptide 1,GLP-1)受體激動劑具有改善糖尿病認知功能障礙的作用,其他降糖藥物如二肽基肽酶-4(dipeptidyl peptidase-4,DPP-4)抑制劑、 鈉-葡萄糖共轉運蛋白-2 (sodium-glucose cotransporter protein-2,SGLT-2)抑制劑及二甲雙胍等是否可有效改善糖尿病認知功能障礙仍存在爭議。
3.1 GLP-1受體激動劑
最近的基礎研究[31]發現,除降糖作用外,GLP-1受體激動劑——Exendin-4能夠抑制氧化應激和神經元凋亡、促進軸突生長及修復并改善胰島素抵抗。已有臨床研究[32]表明,GLP-1受體激動劑——利拉魯肽可改善50歲以上T2DM患者的認知功能障礙。另一項針對20 名使用二甲雙胍單藥治療但血糖控制不佳(HbA1c7%~9%)的肥胖T2DM 患者的研究[33]發現,在給予GLP-1受體激動劑(利拉魯肽或艾塞那肽)治療3個月后,受試者的MoCA評分均有所提高、體質量明顯下降、血糖水平得到了明顯改善,且分別接受利拉魯肽和艾塞那肽治療的患者的MoCA評分無顯著差異;繼而提示,GLP-1受體激動劑可能通過控制血糖、減輕體質量來改善肥胖T2DM患者的認知功能障礙。
3.2 DPP-4抑制劑
目前,DPP-4 抑制劑與糖尿病認知功能障礙的關系尚缺少相關臨床研究。動物實驗發現,西他列汀能改善高脂飲食小鼠的記憶障礙和胰島素敏感性,減輕認知功能障礙。而BIESSELS 等[34]發現,利格列汀在2.5 年內并不能改善T2DM 患者的認知功能障礙。ATES BULUT 等[35]發現,維格列汀可在治療T2DM患者6 個月后改善其血糖水平和認知功能。因此,有關DPP-4抑制劑是否能改善認知功能障礙尚需開展更深入的研究。
3.3 SGLT-2抑制劑
有研究[36]發現,采用SGLT-2 抑制劑——恩格列凈治療T2DM 模型小鼠22 周后,小鼠的腦萎縮、大腦皮質淀粉樣蛋白沉積均有所減少,同時伴隨著學習和記憶能力的改善,顯著預防了認知功能障礙的發生。但在PERNA 等[37]進行的一項臨床試驗中發現,SGLT-2 抑制劑治療組和對照組在治療的12 個月中,受試者的認知功能均未發生明顯變化。
3.4 其他降糖藥物
目前,尚無大型臨床試驗報道其他類型降糖藥物治療DM 合并認知功能障礙有效。CUKIERMANYAFFE 等[38]在甘精胰島素初始干預改善臨床結局試驗 (outcome reduction with an initial glargine intervention,ORIGIN)的一項子研究中發現,甘精胰島素和ω-3 脂肪酸不能降低DM 患者認知功能障礙的發生率。目前,磺脲類藥物治療DM 患者認知功能障礙的效果尚無明確的結論,二甲雙胍對DM 患者認知功能障礙的影響亦存在爭議。WEINSTEIN 等[39]對5 項隊列研究的分析表明,二甲雙胍或磺脲類藥物的使用均與腦功能、腦結構變化無顯著關聯。而SAMARAS 等[40]的前瞻性研究發現,相較于對照組,接受二甲雙胍治療6 年的DM 患者的認知功能障礙發生率及罹患癡呆的風險均有所下降;繼而表明,二甲雙胍對認知功能的保護作用可能與抑制Tau 蛋白過度磷酸化、抑制炎癥反應及改善胰島素抵抗有關。
吡格列酮為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PPARγ)的激動劑,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特性,可改善胰島素抵抗、減少Aβ聚集、抑制神經炎癥、提高大腦能量利用率并改善脂質代謝[41]。XUE等[42]對144項DM與認知功能障礙發生風險的前瞻性研究進行meta分析,結果發現吡格列酮可使DM 人群的癡呆發生風險降低47%。但BURNS等[43]最新的臨床3期雙盲對照試驗表明,吡格列酮不能降低輕度認知功能障礙的發生風險。
4 總結與展望
目前,尚無有效緩解糖尿病認知功能障礙進展的治療方法,因此早期明確該疾病發病的危險因素并進行干預是治療糖尿病認知功能障礙的主要手段[1]。研究表明,除血糖水平升高外,血糖波動異常亦與DM 患者認知功能障礙的發生風險相關,即血糖波動異常幅度越大,發生認知功能障礙的風險則越高。然而,在該領域內鮮少有關于血糖波動異常與DM 患者認知功能障礙關系的前瞻性研究證據,且由DM 所致認知功能障礙的病理機制尚未被完全闡明,因此仍需進一步的探索。此外,TIR 是評估血糖控制的新型指標,但現階段還沒有TIR 與糖尿病認知功能障礙的相關報道。
總之,在實現HbA1c達標的同時,控制血糖波動、實現血糖精細化管理將有助于降低糖尿病認知功能障礙的發生風險。此外,由于認知功能障礙發病隱匿,臨床醫師可借助量表和MRI 技術對患者進行早期篩查、明確診斷及有效干預,從而改善患者預后。期望在不久的將來,有關血糖波動異常導致糖尿病認知功能障礙的病理生理機制能夠得到進一步闡明,這對控制血糖波動靶點的尋找、糖尿病認知功能障礙的預防及其新型降糖藥物的研發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