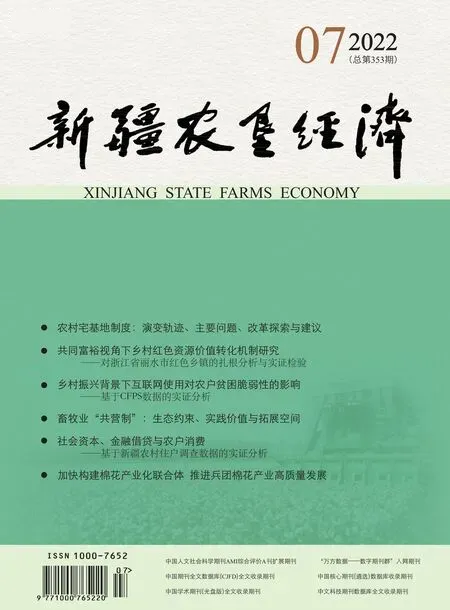畜牧業“共營制”:生態約束、實踐價值與拓展空間
○李先東 魏傳玲 都格爾加甫·斯爾布德
(1新疆農業大學農林經濟管理博士后流動站,新疆 烏魯木齊 830052;2新疆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52)
一、引言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我國草原呈現出不同程度的退化,綜合來看是人禍和天災的共同影響。由歷史角度來看,人口數量激增是重要原因。隨著牧區人口數量增加,牧民為滿足家庭生計需求大量開墾草原,導致草原承載力大幅提升,因此帶來的沙化、水土流失等生態問題接踵而至。人禍與天災的交織進一步推動草原環境惡化,使得畜牧業可持續發展面臨嚴重的生態約束。當前,畜牧業高質量發展強調恢復、發展草原生產能力和生態功能,以實現生態產品價值轉化、推動畜牧業經濟綠色健康發展。2020年9月27日,國務院辦公廳頒布《關于促進畜牧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中,主要強調以草定畜,通過加大對草原的合理使用,加速恢復草原生態環境,發展具有生態意義的家庭牧場和牧業合作社。2021年3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加強草原保護修復的若干意見》,提出加快推進草原確權登記頒證,明確所有權、使用權,穩定承包權,放活經營權,引導鼓勵按照放牧系統單元實行合作經營,合理利用草原資源,提高草原合理經營水平,防止草原碎片化。以上文件內容主要側重于兩點:第一,注重草原生態保護。第二,鼓勵新型合作經營。如何圍繞兩個關鍵創新推動畜牧業轉型升級,發揮草原生態功能與生產功能,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局面是值得探討的話題。
本研究通過草原制度變遷、生態變遷以及勞動力變化三個層面,揭示草原畜牧業迫切需要轉型的原因,探討畜牧業“共營制”在新疆青河縣的創造性實踐,通過剖釋其中的內在機制,探尋“共營制”的實踐價值和擴展空間。
二、畜牧業經營方式轉型的背景
(一)畜牧業經營方式的歷史變遷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草原管理大體經過“公地共管—公地私管—私地私管—私地共管”的過程。草地由“公”到“私”的轉變與兩層因素密不可分。第一,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推動牲畜參與市場經濟系統。為滿足市場變化需求,牲畜被賦予商品屬性,以期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第二,防止陷入哈丁“公地的悲劇”之中。“公地的悲劇”說明公共資源在產權不明的情況下,理性人(牧民)受到利益驅使,導致公共資源(草原)過度使用而引發的悲劇[1]。為此,基于科斯定理的草地產權制度逐漸在牧區展開,試圖通過私有化方式明晰草地產權,阻止開放式公共資源無節制的浪費行為,緩解草原退化、沙化等問題。
自二十世紀后期實施草地承包經營責任制以來,國家試圖通過草場承包方式約束牧民主體行為,解決外部性(社會成本、延期成本)問題[2]。其中,隨著草地管理制度的發生與變化,草原產權由“集體”轉為“分權”,表現為草地權力由集體向牧民家庭的流動[3]。總體歷經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草畜雙承包”階段。此階段草地承包到村,牲畜作價歸戶,牧民積極性大幅提升,牲畜養殖規模增大,集中于公共草場共同放牧。然而對于草地這種公共資源來說,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則的群體性增畜的行為將影響草原生態的穩定性。第二階段,“雙權一制”的實施。經過第一階段的發展,過度放牧產生的草地退化問題嚴峻,因此以確定草場承包面積、年限以及核定草場載畜量控制放牧強度。此階段草場承包逐漸由組到戶,明確牧民草場使用權。草場界限由圍欄劃分,用以明晰草場使用權和阻擋外部不確定因素。然而,草原生態系統多樣性和整體性受到破壞,畜牧業經濟和草原生態面臨雙重威脅。第三階段,草原管理政策的發展。針對草地長期的“人—草—畜”關系失衡,原農業部、財政部印發《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政策實施指導意見》,引導牧民參與草原保護建設,積極恢復草場生態環境,推動草原可持續發展。另外,基于城鎮化進程和牧民勞動力轉移,草地經營權流轉興起,并日趨制度化、規范化、市場化。
由歷史變遷的軌跡來看,畜牧經營與草原管理之間存在重要關聯,草原管理隨著國家政權建設而發生轉變,同時深刻影響著畜牧業的經營方式。首先是基于歷史背景的游牧文化與習俗約定的傳統集體經營[4],它是依賴于草原基礎的自然資源發展畜牧經濟;其次是依托于產權制度的現代家庭經營,是農地土地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延續[5]。由集體向家庭經營的轉變既是滿足現代經濟發展的需求,又是牧民增收與生態保護的大膽嘗試。聚焦牧民生計與草原生態的視角,草原可持續與畜牧業循環發展息息相關,畜牧業是保持牧民生計、生活的基本產業,草原為傳統畜牧業提供重要生產資料,畜牧經濟的發展依賴于草原生態的可持續。當前,草原退化、沙化問題嚴峻,依托草原資源的畜牧業經濟若不破除生態約束,現代畜牧業的發展將存在很大的困難和挑戰。
(二)畜牧業發展存在的問題
畜牧業家庭經營在保障牧民權利和提升生產積極性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確權過程中的草場“細碎化”問題卻日益嚴峻。實施草場承包后,家庭作為畜牧生產經營主體,逐漸脫離傳統規范趨于獨立,草畜糾紛成為常態。另外,在草地承包的過程中,遏制草原退化僅能獲得短期效應,進一步衍生的細碎化問題正威脅草原生態安全,重點表現為牧區管理層面圍欄的生態破壞效應。圍欄對于草原社會和生態具有不同影響:一方面,圍欄是我國現代草原產權確認的物理邊界,支撐著我國現代草原產權體系[6];另一方面,分割“人居—草地—畜群”放牧系統[5],破壞草原生態系統平衡。圍欄在執行制度安排的同時影響著草原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大大降低草原的自我修復能力,進一步地制約畜牧業的生產經營。
此外,在城鎮化的背景下,土地和勞動力加速流轉,開始出現農村勞動力老齡化、牧區治理空心化等問題。賈鵬和莊晉財[7]認為在城鎮化的進程中,大量年輕勞動力流向城市,呈現農村空巢現象。尤其在牧區繁忙時期,勞動力短缺問題更加突出,這一現象無疑不利于畜牧經濟的發展。牧區城鎮化主要以生態移民為推手、生態環境問題為誘因,開展生態整治與扶貧活動[8],強調牧區生態環境治理。若無法保證治理過程中生態與經濟均衡發展,將會引發一系列新問題,如牧區治理空心化,即牧區人口、牲畜減少而出現的草地無人看管現象。
概言之,單一的家庭經營一定程度上激發了牧民畜牧生產的積極性,卻忽視了基本的生態保護。畜牧經濟與草原生態緊密相連,草原環境安全是保證畜牧業循環發展的基礎,畜牧業的生產經營更加依托于天然草原的資源基礎。因此,草原生態環境惡化將會大大制約現代畜牧業的發展,探索更加有效的畜牧業經營方式和生態治理手段十分必要。
(三)畜牧業的轉型方向
通過以上問題的探討,可以了解到草原生態安全對于畜牧生產經營的重要性,以及畜牧業迫切轉型的必要性。《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畜牧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國辦發〔2020〕31號)中強調,建設現代養殖體系,鼓勵開展合作(養殖專業合作社)經營、發展現代家庭牧場。另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中對于新疆各區域畜牧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即堅持冬春舍飼、夏秋放牧,牧區繁育、農區育肥的道路,加快傳統畜牧業生產方式的轉變以及加快草原生態環境的恢復。因此,合作經營是畜牧業轉型的關鍵之一,如何基于畜牧業“共營制”破除生態約束、加快畜牧業轉型升級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
畜牧業合作經營主要依托產權、資金、勞動、技術、產品等要素,搭建畜牧業經濟主體間緊密聯系橋梁,以期推動畜牧業現代化發展。例如學者陳秋紅[9]探討的社區主導型草地共管模式,詳釋了社會資本對社區機制建設的關鍵作用,該合作模式對于草地狀況改善以及牧民增收皆有積極作用。傳統粗放的畜牧業正向專業化、規模化、集約化的現代畜牧業轉變,草原生態資源資產化的地位也在草場生態補償機制中得以穩固,不僅順應現代農業發展變化,更為草原突出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新思路。其中,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簡稱“生態補獎政策”)作為國家針對草原退化提出的生態保護政策措施,主要在生態、經濟中起到調節平衡的作用,調控機制表現為“政策—生態—經濟”的相互影響。生態補獎政策作為調控過程的基礎,引導恢復草原生態環境,主要依靠禁牧補助、草畜平衡獎勵、績效考核獎勵給予生態保護對等的生態補償[10],更需要適應現有經濟的發展。
綜合來看,畜牧業的發展受到草原生態約束。天然草原資源是畜牧經濟發展的基礎,生態補獎政策主要促進草原生態穩步恢復,適應、發展當前畜牧業經濟,同時生態約束畜牧業的發展。本研究通過探討青河縣畜牧業“共營制”的具體做法,基于制度變遷理論剖析其中的內在邏輯,探尋畜牧業“共營制”的實踐價值與擴展空間。
三、畜牧“共營制”:做法與效果
(一)研究區域概況
青河縣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區,富蘊縣位其東,南鄰昌吉州奇臺縣,東北鄰蒙古國,總面積1.57 萬平方千米。屬大陸性北溫帶氣候,縣域境內氣候干旱,降水量與蒸發量具有顯著差異,年均降水量165 毫升,蒸發量可至1 495 毫升。境內自然災害多發,導致農牧業經濟嚴重受損。2016年之前,青河縣是一個典型的“少、邊、牧、窮”多災易災縣,人均耕地及生產資料十分匱乏。2017 年后,青河縣實現脫貧摘帽,作為傳統的牧業縣,畜牧業成為該縣的重要經濟來源產業。目前,全縣可利用草場面積108萬公頃,較好草場僅占54.15%,1.7萬公頃的草場因干旱或過牧演變為退化草場。
過去受制于自然和人為的雙重因素,青河縣“一方水土不能養一方人”問題突出,即惡化的草原生態環境難以滿足當地畜牧業實際發展需求,嚴重引發農牧民生計困難。自1996 年起,青河縣作為“自治區級重點貧困縣”“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以及“艱苦邊遠五類地區”,獲得了國家和自治區的巨大支持。近年來,青河縣以生態建設作為發展重心,積極落實草原生態獎補機制,針對符合規定的草場實行禁牧、草畜平衡管理,促進牧民定居,鼓勵舍飼圈養,引導農牧民群眾科學養殖,使農牧民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提高、草場自然環境得到有效恢復、畜牧經濟取得快速發展。青河縣的成功做法對于豐富農業合作理論具有積極作用,更加為畜牧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新思路,其成功轉型的經驗及做法值得深入探討。
(二)畜牧“共營制”的具體做法
青河縣是新疆畜牧大縣之一,草原文明和游牧文化密不可分。牧民秉持對自然的崇敬和生活的追求,能夠參與、配合政府的草原保護和監管工作。此外,各利益主體圍繞合作社協同推進畜牧轉型。例如,公司對于畜牧業轉型的投資,能夠為自身提升經濟效應;政府的有效引導能夠促進畜牧經濟穩定運行以及草原生態的可持續發展。簡言之,社區居民、政府和公司三者在青河縣的畜牧業“共營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種養結合模式也為生態畜牧業的發展提供重要動力,具體如圖1所示。
1.社區居民與政府。政府機構依托國家的政策支持和資金項目,引導社區基層組織、群眾創新發展合作經濟,穩步提升區域經濟水平,促進政府資金循環,進一步奠定畜牧經濟基礎。截至2021年,青河縣銜接推進鄉村振興補助資金項目累計30項,其中養殖項目扶持3項,主要包括良種牛養殖建設項目、駱駝養殖項目、牲畜棚圈養殖建設項目,累計完工2項、竣工驗收合格1項。青河縣依托國家項目資金,大力發展圈棚養殖、草業經濟、良種經濟等,為緩解草原生態壓力做出重要貢獻。同時項目資金著力開發公益性崗位,能夠提升牧民增收效益,扶持推動畜牧經濟的發展。
此外,基于畜牧合作經濟同步加強人居環境整治,打造“草原水鄉,城市牧場”品牌。據收集材料可知,十三五以來,青河縣推進退耕還林、三北防護林、防沙治沙等重大生態工程,截至目前,修復21 000 畝退化林、造林16 159 畝。此外,積極發展具有草原文化的旅游業,投資1.25億元改造升級大青河景區、三道海子景區、青格里狼山景區等區域的基礎設施,實現農牧區的轉變。草原環境退化將會嚴重影響生態和經濟的良性發展,青河縣建立發展草原景區,既能修復和保護草原生態環境,還能從中獲得一定的經濟效益,有利于推動區域生態和經濟的雙重發展。
2.社區居民與公司。公司作為社會資本主要為社區提供配套服務,通過大量的人才、技術和資金輸送,推動社區合作社的機制和設施建設,進一步促進牧民轉移就業,實現經營效益的穩步提升。社區基層組織鼓勵社會資本進入社區,并通過成立專門的合作社,配套相關基礎設施(飼草料庫、藥浴池、草料加工廠等),參與養殖、育種、加工等環節,包括協調利益分配與矛盾問題。社區牧民主要以牲畜、草地入股合作社,為其提供勞動力或初級產品。企業作用則體現在各環節的技術支持、項目資金扶持和專業人才培訓等方面,積極發揮企業的人才、技術、資金優勢,共同構建畜牧業科學養殖格局,進一步促進經濟增收。
3.社區居民、政府與公司。依托社區的政府、企業、牧民共同形成的互惠共享發展格局,進一步推進了現代畜牧業的發展,為激活草原活力做出巨大貢獻。即基于畜牧業“共營制”的圈棚養殖、草業種植大大緩解了草原生態壓力、進一步推進了草原生態的修復,同時草原生態旅游的發展也為實現草原生態資本化做出了大膽嘗試。由于阿格達拉鎮是青河縣易地搬遷的主陣地,集中了全縣29.90%的建檔立卡貧困戶,所以將其作為青河縣畜牧產業轉型的典型區域展開探討。阿格達拉鎮轄一村三社區(即阿格達拉村、新牧社區、和平社區、創業社區),在圈棚養殖和草業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多元主體間的緊密合作共同推進畜牧合作經濟的發展。
在養殖經濟的發展中,該鎮依據“人畜分離,宜居宜業”的建設標準發展合作社,依托社區集中養殖牲畜。其中,社區基層組織是政府政策的執行者,主要發揮協調、監督作用,同時開展相關技能培訓、培育養殖能人工作;企業則提供技術和資金支持,加強基礎設施(飼草料庫、藥浴池、草料加工廠等)的建設;牧民則依據傳統畜牧業生產經營經驗以及現代畜牧養殖知識,參與牲畜的培育、養殖等階段,其中牧民牲畜養殖過程的反饋,對于合作社未來養殖規劃的制定具有重要參考。
在草業經濟的發展中,該鎮的土地分配遵循“集中管理、統一經營、收益共享、統一分配”的原則,人均可獲得10 畝耕地,同時由黨組織搭建聯系,引入涉農企業和合作社發展有機種植。青河縣福生農牧業開發有限公司著重進行阿格達拉鎮的土地流轉、飼草養殖和安置牧民務工等工作,已種植優質飼料2.7 萬畝,主要包括青貯玉米、飼料玉米、苜蓿等,逐步改變草原畜牧業過去依賴天然牧草的生產現狀。
(三)青河縣實施“共營制”的成效
青河縣種養結合的生態循環模式對于推動畜牧業綠色轉型具有重要意義。其中,以社區為依托聯系企業帶動畜牧業轉型升級,助力牧民勞動力轉移就業,對于拓寬牧民收入渠道,推動發展畜牧綠色循環經濟,減少草原生態環境壓力具有積極意義。同時進一步促進了青河縣草業經濟、暖棚經濟、良種經濟和畜肉經濟的快速發展。
1.提升區域經濟水平。2016年前,青河縣是脫貧攻堅重點難點區域。由于艱苦的地理條件以及頻發的自然災害,當地牧民出現嚴重的生計困難,區域經濟發展也受到嚴重約束。2017年,青河縣正式退出貧困縣行列,將環境條件艱苦的村進行了大量異地搬遷,穩步推進以社區為基礎的圈棚養殖、草料種植等合作經濟,進一步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同年,青河縣獲得“自治區優秀平安縣”稱號,區域經濟獲得一定幅度的提升。2019年,全縣第一產業生產總值達到9.8 億元,其中牧業產值達到4.9億元,約占農林牧漁總產值的50%,較上一年牧業產值增長2.6%。此外,青河縣通過企業參與、牧民入股(產權入股或牲畜入股)的方式,推進畜牧“種、養、育、加工、銷售”全產業發展,進一步提升了養殖增產和牧民增收。
2.加快草原生態恢復。青河縣在實施草原生態保護政策前,區域草場已經受到不同程度的退化,難以繼續滿足畜牧業的發展需求,經過“農區發展養殖、牧區修復生態”多項舉措的有效實施,草原環境逐漸得到改善。此外,通過禁牧、草畜平衡、草原封育、核定載畜等草原保護政策的有效實施,以及青河縣易地扶貧搬遷的政策推動,飼草料作物種植發展穩定,基本實現飼草料作物自給自足,為草場恢復提供良好契機,進一步推動了草原生態恢復進程。同時,草場植被恢復明顯,空氣質量顯著提升,為推動草原生態旅游打下基礎。
3.推進生態畜牧轉變。過去,青河縣傳統放牧方式強調“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形式。現今,主要發展圈棚養殖、草業種植等合作經濟。傳統畜牧生產經營經常受到自然的兩層約束:第一,牧區地處高寒山區,氣候干旱少雨,降水與蒸發差異顯著;第二,暴風雪、鼠災、蟲災等自然災害頻發。牧民一方面需要獲取大量牧草,保證牲畜營養和能量供應,另一方面則需要通過遷移牲畜躲避災害,牧業發展十分艱苦。隨著草地產權制度的推行,牧民牲畜養殖規模大幅提升,過度放牧進一步加重了當地草原的生態壓力,嚴重制約畜牧業經濟發展。當前,青河縣由傳統畜牧業轉向舍飼圈養,通過品種改良、技術推廣等形式發展畜牧業合作經濟,積極推動牛、羊養殖合作社的發展,以“企業+”帶動養殖專業合作社、家庭牧場合作經營,推動養殖示范基地建設,打造畜牧業品牌效應,推動縣域經濟蓬勃發展。青河縣易地扶貧搬遷政策既推動草原植被恢復進程,還組織推行牲畜圈棚養殖和優質飼草料種植,其中,種植業基本實現“供給鏈”自給自足、畜牧生產經營日趨規模化、專業化,進一步推動了生態畜牧業的轉變進程。
四、制度變遷理論:內在機理分析
制度變遷是以高收益替代低收益的制度變化過程,是制度的變更和創立[11]。依據不同學者對制度經濟學的假設、方法和理論表現形式來看,盧瑟福將其劃分為兩類:老制度主義學派和新制度主義學派[12]。其中,新制度主義學派認為制度變遷存在誘致變遷和強制變遷兩條路徑。首先,由國家或政府以行政命令主導的制度變革稱之為“強制性變遷”;其次,通過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導致民眾自發的變革叫作“誘致性變遷”。二者對應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社會變革,相互作用、共同推進制度變遷。
(一)畜牧業共營制的強制性變遷
過度放牧導致草原生態嚴重退化,加劇人草畜矛盾和生態問題,從而引起國家或政府的關注,進一步推進國家或政府的強制性變遷。長期以來,草原生態系統具有調控天氣、穩定水土、資源供應等作用,對于發展畜牧業經濟、穩定草原生態方面意義重大。基于利益驅動的過度放牧行為,深刻影響著草原天然生態屏障。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將生態建設與社會建設連成一個整體,二者相互促進、互相影響。因此,積極推進草原保護、恢復意義重大。
強制性變遷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國家政府機構針對草原生態環境退化做出政策反應;另一方面,國家政府機構通過資金和項目扶持集體經濟發展。青河縣政府嚴格執行國家草原獎補政策,促進草原生態保護和修復。其中,對草原實行禁牧、輪牧、休牧與草畜平衡管理,對環境脆弱地區進行永久禁牧,對涉及的牧戶按照標準發放禁牧補償和草畜平衡獎金。針對政績突出的區域實施獎金鼓勵措施,循環助力草原生態保護和畜牧業健康發展。同時,與鄉村振興補助資金項目有效銜接,為助力區域經濟發展提供重要的資金支持。
(二)畜牧業共營制的誘致性變遷
產權改革作為我國草地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部分,影響著我國草原畜牧業的經濟與生態。牧民長期以草地資源作為生計發展基礎,草原退化勢必影響牧民生活。基于相同的困境,不同地區開始嘗試各種轉變。內蒙古一些地區出于減低生產成本、保留游牧文化或是資源的不可分割性等方面考慮,探索出“共用牧場,合作放牧”的草原管理模式[13],即使監管、制度等層面尚需完善,但對于草原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來說具有積極意義。陸益龍和孟根達來[14]兩位學者研究錫林郭勒盟錫林浩特市C 嘎查的“散戶聯合牧場、集中家畜”的合作模式,這種由牧民自發組織并具有傳統游牧文化的經營模式是迫于高額生產成本與不確定自然因素的壓力應運而生,強調資源的整合分配及勞動力的解放,以此解決生計難題。
基于草原的生態約束,青河縣牧民迫切需要擺脫生計困境。問題突出表現為:牧民層面的“環境惡劣,生活困難”和政府層面的“貧困人口多,扶貧難度大”。大量貧困戶受制于自然環境和傳統畜牧方式,經濟收入十分微薄,不僅拉低了縣域經濟發展水平,更加影響著農業現代化發展進程。因此,基層群眾希望引起政府等國家機構的重視,以尋求政府機構的扶持和幫助。政府機構向下(牧民)傳達上級(決策者)政策措施,引導基層組織合作創新,建立多元合作機制,實現現代化發展需求,為提高牧民收入水平,拓寬牧民增收渠道提供重要動力。
(三)相互作用下的變遷
政府和牧民作為變遷主體著眼于生態和經濟的雙重發展,因此積極探索有效轉型是適應現代化規模經濟發展的強烈需求。青河縣的“共營制”模式是由強制性變遷與誘致性變遷的共同作用,是圍繞草原恢復和畜牧升級做出的重大嘗試,為發展畜牧生態循環、草原生態資本化提供了基礎。此外,為加快牧民轉移就業、穩步提升生活水平、改善畜牧生產條件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由圖2 可知,二者相互作用下的變遷體現于:在生態、生產、生活的多重壓力下,產生自上而下的影響作用,即決策者通過制度措施引導牧民的生產經營方式改變,嘗試走出生態約束的困境難題。同時,自下而上的推進政策措施的完善優化,即通過經營方式的改變進一步推動政策的調整,進一步匹配畜牧轉型的需求。概言之,基于決策者和基層群眾的相互作用,能夠共同促進畜牧合作經濟的發展,逐步緩解人草畜矛盾。
五、實踐價值與拓展空間
(一)實踐價值
農業經營體制作為農業現代化水平的一項重要安排[15],其經營方式創新是其中的關鍵之處。本文探討的畜牧共營作為一種經營方式的創新,尚且需要明確以下三個目標:其一,保證畜產品供給,保障糧食安全;其二,提升生產效率,促進牧民增收;其三,堅持生態優先,穩定草原安全。在此基礎上,需要積極落實生態補獎政策,加強推進草原確權登記頒證,在保障牧民基本權益的同時進一步推進區域畜牧經濟的穩定發展。
青河縣探索畜牧業“共營制”取得的良好成績,關鍵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通過建立合作機制,提升牧民參與積極性。牧民以產權證或牲畜入股合作社,使得小農戶以低成本參與合作經濟,進一步激發了牧民畜牧生產經營的積極性。第二,根據畜牧生產特點,匹配基礎設施和專業技術。通過配置暖棚、藥池等基礎設施以及專業育種、科學飼養等專業方式,滿足牲畜各階段的條件需求,進一步推動了牲畜培育、生長、繁殖等環節的專業化發展,有效保障并提高了畜產品的安全供給和市場競爭力。第三,通過資源整合利用,推動了土地、牲畜的規模經營。合作社的統一管理、統一經營使得土地、牲畜呈現一定的規模化特征,大大提升了養殖、種植的生產效率,進一步提高了牧民的收入水平。此外,青河縣還兼顧草原的修復工程,通過禁牧、草畜平衡等方式,穩步推進草原的修復,進一步為草原觀光旅游業的發展提供保障。這一系列的轉變為畜牧轉型探索出了一條可行的良性循環道路,更加為草原的休養生息創造了有利條件,有效規避了草原對傳統畜牧業的生態約束,為畜牧業高質量發展打下夯實基礎。
概言之,青河縣的畜牧業“共營制”模式切實推進了規模經濟的發展,進一步促進了區域畜牧業的規模化、專業化進程,對于傳統畜牧業轉型具有借鑒意義。此外,該模式緩解了草原生態壓力、穩定了牧民草地權利、促使土地(草地)經營權靈活運轉、提升了畜牧生產活力,為保障牧民經濟收入和穩定畜產品安全做出重要貢獻。同時,對于具有生態約束的傳統畜牧業來說有顯著改善作用。青河縣這種以社區為中心的“集中管理、統一分配、多元經營”的新型經營方式,對于受制于生態壓力的草原畜牧業具有普遍的適用性,為草場細碎化、牧民勞動力轉移等問題提供了新思路,也對相關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二)拓展空間
當前我國畜牧業正由傳統粗放型向集約化、現代化的生產經營方式轉變,更加注重環境保護、生產效率、成本收益、資源節約等方面[16]。通過發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優勢,促進畜牧業經營方式創新必然需要一定的基礎要求。創新過程需要依托幾點內容展開:其一,保證畜產品市場供給,提升畜牧業供給保障能力。畜牧業經營方式創新需要滿足市場對畜產品的需求,推動發展暖棚經濟、草業經濟以及畜肉經濟等,加強畜產品供給保障能力,順利推進畜牧業轉型升級。其二,改善畜產品生產效率,確保農牧民及其他參與主體實現經濟增收。合作經營主要由科學養殖、合理配比飼料、專業技能培訓等手段協調推進畜牧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穩步提升。其三,協同推動家畜繁育與草地保護,以推動畜牧業的可持續發展。運用科學的方法規劃畜禽養殖格局,推動草原畜牧業由傳統放牧方式轉向舍飼、半舍飼方式。實現禁牧不禁養[17],推進畜禽糞污資源化利用,加強糞肥在種植業的科學利用,通過構建評價體系推廣相應的配套技術。
青河縣的畜牧業“共營制”模式確實在生態與經濟兩個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并具有巨大潛力。對于合作社來說,可以積極發揮組織投資能力,以土地經營權為基礎獲取企業或政府的項目和資金支持,推進畜牧養殖合作的進一步發展。對于企業來說,以社區養殖、種植為基礎,發展畜牧業加工、運輸產業,同時拓寬企業銷售渠道,加強產業鏈延伸、畜牧品牌建設。對于政府來說,需要積極發揮政府和市場的調節功能,打造生態產品和服務,即政府確定生態資產,結合市場力量轉化為生態資本,推動生態資源(土地)資本化[18],實現生態產品資本化過程。此外,青河縣探索的畜牧業“共營制”正處于發展階段,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良好成效,仍具有廣闊的擴展空間,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延伸產業鏈條,推進品牌化建設的可能性。在穩定畜牧生產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產業體系建設,即提升畜牧業的“產、銷、服”能力。其中,在產業鏈橫向延伸方面,由“加工”向“深加工”推進,進一步達到“精深加工”狀態;在產業鏈縱向延伸方面,加強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或者推動“農牧旅”多元化經營[19]。此外,推進畜產品品牌化建設,以此提升產品附加值以及增強盈利收入,進一步促進產業升級。
2.推進合作社再組織化的可能性。《國務院關于促進鄉村產業振興的指導意見》中指出,促進在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民合作社和貧困戶之間建立形式多樣的利益聯結機制。單個的合作社普遍具有“小、散、亂、弱”的發展難題,而合作社的再組織化能夠有效解決以上困境。通過合作社的再組織化加強資源整合,推動形成利益共同體,即由合作社內部與群體形成的共同體[20],以此獲取一定的規模效益和競爭優勢。因此,可以通過“社社聯合”“社企聯合”“社村聯合”等模式推動合作社的再組織化[21],進而實現資源的高效利用和收益的有效提升。
3.畜牧業“共營制”與城鎮化相互促進的可能性。勞動力轉移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畜牧業“共營制”的發展,而畜牧業“共營制”進一步推動著新型城鎮化的進程。牧民向城鎮轉移的就業形式也發生轉變,即牧民逐漸由短期不確定兼業轉為長期穩定務工狀態,牧民既能獲得畜牧業的基本收入,又能外出務工提升家庭總收入。總體來說,畜牧業“共營制”與新型城鎮化呈現出一片相互促進的景象。
六、主要結論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幾點結論:第一,青河縣以社區為基礎的牲畜集中管理模式,能夠有效轉移草原生態壓力。經過扶貧搬遷工程,青河縣大力推行圈棚養殖,替代傳統草原放牧方式,取得良好成效。牧民利用土地統一進行飼草種植,為冬春做好飼料儲備工作,最大程度減輕草場壓力。第二,各利益相關機制在畜牧業“共營制”中發揮積極作用。牧民、公司、政府等在畜牧業經營過程中扮演著不同角色。其中,牧民從事基本的牲畜養殖工作,農閑時期可以承擔其他工作;公司下設合作社主要配套養殖基礎設施、建設現代化棚圈、科學合理配制飼草料、提供技術支持等,是大型“種、養、產、銷”基地;政府則采取政策引領、項目幫扶辦法,助力畜牧業規模化、專業化發展,促進區域經濟提升。概言之,規模化、專業化的經營有利于畜牧業經濟和生態的雙重發展,同時畜牧業“共營制”對于實現草原生態資本化、推進生態畜牧業發展皆具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