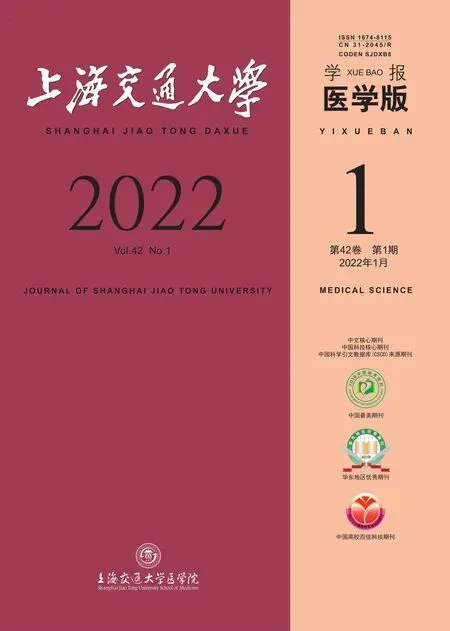ICU環境中患者早期康復影響因素的研究進展
楊 富,方 芳,2,陳 蘭,王秋莉
1.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護理部,上海 200080;2.上海交通大學護理學院,上海 200025
隨著我國“大健康”理念的逐步深入,康復醫學理論及康復技術得以迅速發展。早期康復越來越受到國內學者們的重視。“早期康復”理念也被逐漸應用至重癥監護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環境中,成為目前危重癥研究領域的關注焦點。早期康復活動有助于改善危重癥患者的預后,提高其生存質量和生活質量,在ICU環境中具有可行性和安全性,在主動運動過程中不良事件發生率低于3%,已被納入相應的國際實踐指南中[1-2]。盡管早期康復對患者具有重要意義,但國內外ICU環境中早期康復整體情況不太理想;尤其是在亞洲地區,早期康復的標準、康復團隊的組建及干預方案的執行均較少見[3-4]。如何改善ICU 環境中早期康復的實踐現狀,提高早期康復實踐的依從性,是目前危重癥領域亟需解決的問題之一。本文綜述ICU 環境中早期康復的實踐現況及其影響因素,以期為我國重癥早期康復的實踐與臨床研究提供依據。
1 ICU環境中患者早期康復實踐的現況
目前,臨床上重癥康復包括基礎康復(運動康復、營養支持、物理治療、作業治療)和專科康復(心臟康復、肺康復、神經康復、心理康復)兩部分;其中運動康復是重癥康復的核心,也是重癥早期康復的關鍵[5]。就危重癥患者或機械通氣患者而言,早期康復運動是指在血流穩定及血氧水平允許的情況下,患者通過自身肌力和控制力,在一定的輔助條件下參與一系列的運動或鍛煉,一般在危重疾病發病或受傷后2~5 d 內開始[6-7],主要形式為被動運動、主動運動以及漸進式康復[8]。
早期康復運動是成人ICU 患者疼痛、躁動和譫妄管理臨床實踐指南的六要素之一[9],但是其在國外ICU 環境中的實踐水平不高。美國ICU 早期康復實踐調查數據[10]表明,有部分早期康復實踐的ICU 占45%,無早期康復實踐的ICU 占55%,考慮早期康復計劃的ICU 占78%,未聽說過早期康復的ICU 占2.4%。一項英、法、美、德國際調研結果[11]顯示,來自這4 個國家的951 個ICU 的早期康復實踐率為40%~59%,具有早期康復方案相關書面文件的ICU 僅為20%~30%。其中,早期康復項目以被動運動、主動運動以及體位轉移為主,占整個康復項目內容的90%~100%;床旁功率自行車與神經肌肉電刺激的使用率較低(<40%);機械通氣患者的離床行走訓練實踐率,除法國偏低(31%)外,美、英、德3 個國家ICU 的實踐率為64%~73%。NYDAHL 等[12]對德國116 個ICU 機械通氣患者某一日的早期康復項目實踐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床上活動的患者占76%,離床活動的患者占24%;其中僅8%的氣管插管患者接受了部分早期康復項目,以床邊坐位訓練為主,尚未實施離床站立與行走訓練。巴西一項研究[13]報道,ICU 機械通氣患者的離床活動率不超過10%。由此可見,早期康復在發達國家ICU 環境中的實踐現況并不理想,尤其是機械通氣患者的早期康復實踐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近年來,我國學者逐步開始進行重癥早期康復的相關研究,如早期肺康復方案[14]、早期四級康復訓練[15]、早期漸進式康復方案[16]等,并取得了一定的臨床效果。但我國對ICU 早期康復理念的認識較晚,理念推行較為緩慢,且大部分干預研究樣本量都偏少,ICU 早期康復實踐范圍較窄,實踐項目內容較單一。因此,目前尚無關于我國ICU環境中早期康復實踐現況的相關數據報道。
2 ICU環境中患者早期康復的影響因素
2.1 患者因素
ICU 患者具有病情危重度高、發展變化快、并發癥多且嚴重等特點,其臨床癥狀和狀況是ICU患者早期康復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一項關于ICU早期康復障礙因素的文獻meta 分析顯示[17],患者因素在早期康復障礙因素中占50%。身體因素和神經心理因素是影響ICU 早期康復的2 個主要患者相關性因素:身體因素表現為疾病嚴重度高、血流動力學不穩定、心律失常、呼吸不穩定或窘迫,以及機械通氣患者的人機不同步、疼痛、營養狀況差或肥胖等;神經心理因素則表現為深度鎮靜和/或癱瘓、譫妄、易激惹、不配合、缺乏動機、抑郁、姑息治療等。其中以血流動力學不穩定為最常見的患者因素,其次是鎮靜或意識水平下降以及患者疾病與治療相關因素等。LIN 等[18]對澳大利亞某三級醫院綜合ICU 的82 位護士、醫師及物理康復治療師的調查結果顯示,與患者相關的ICU 早期康復最主要障礙因素為醫學狀況不穩定(85.4%)、譫妄(85.4%) 和過度鎮靜(69.5%)。BROCK等[19]通過對202例綜合ICU患者早期康復的現況調研發現,總的患者住院日數為742 d,未活動日數為364 d(49.1%),康復活動的主要障礙因素分別為嗜睡或格拉斯哥昏迷指數(glasgow coma scale,GCS)<10 分(18%)、血流動力學不穩定(11%)、患者因不能遵醫囑未依從(11%);而GCS >10 分、性別為男性則是促進早期康復(主動運動、主動與被動相結合體位轉移)成功的主要預測因子。性別因素在ICU早期康復中是否存在差異尚未明確,其生理性偏倚或社會性偏倚還有待進一步探究。此外,患者和/或其家屬的康復意愿水平、患者的預后也影響ICU 早期康復的啟動時間以及臨床醫護人員的康復決策[20]。
2.2 安全因素
安全是患者參與康復活動與否的重要決定性因素,也是ICU早期康復的首要考慮因素。安全問題是ICU 環境中早期康復的重要障礙因素。在ICU 早期康復的臨床實踐過程中,不良事件發生率較低(2.2%),以患者不耐受(54%) 和直立性低血壓(46%)為主[21]。此外,ICU 環境、醫療儀器或設備等也是安全的重要影響因素,如導管、導線和探針滑脫或脫離的潛在風險影響了ICU醫師對患者早期康復的考慮,也限制了物理治療師制定康復方案,從而影響了早期康復的實施。LIU 等[21]對232 例ICU 患者的587 次康復活動進行調查,結果顯示,中心靜脈導管、氣管內導管與胸腔引流管相關不良事件發生率分別為4.8%、5.1%、3.6%;其中中心靜脈導管以股靜脈置管位置的不良事件發生率最高(占8.1%),體外膜肺氧合相關不良事件發生率為3.6%。在導管相關性障礙因素中,以氣管內導管最為常見,其次是血液透析。有研究報道[22],澳大利亞ICU 患者的氣管內導管性障礙因素占18.1%,而蘇格蘭ICU 患者中該因素占5.4%;血液透析性障礙因素均低于5.0%。另一項關于ICU 早期康復的障礙因素調研數據[23]顯示,氣管內導管占21.5%,持續性血液透析占4.0%。另外,導管位置也會影響康復活動的水平。有研究[24]表明,超過60%的受訪者(ICU 醫師和物理治療師)認為橈動脈置管的患者和鎖骨下置入透析導管的患者(在非透析期間)可自由行走,約有1/3的受訪者認為使用股中心靜脈導管或股透析導管的患者應限制活動范圍,而近80%的受訪者認為使用胸管、尿管或全劑量抗凝治療的患者不需要限制活動。因此,在實施ICU 康復運動前,需對患者及其周邊的環境進行充分評估。有專家共識[25-26]建議,采用“紅綠燈系統”識別出重大風險(紅)、潛在風險(黃)和低風險(綠)的患者,并預先計劃所需的工作人員和設備(如便攜式監護儀、搶救物品、康復設備等)等,對于有效地實施ICU早期康復和最大限度地減少不良事件發生,是必不可少的。
2.3 文化因素
近年來,歐美發達國家對ICU早期康復進行了大量相關研究和實踐并取得了較好的臨床成效,形成了ICU 早期康復專員或團隊,并發展了“早期活動”文化[27]。ICU文化是ICU早期康復障礙因素之一[20,28]。有研究報道,ICU 文化因素在早期康復障礙因素中占60%,主要表現為早期活動文化(35%)、員工知識技能和認同感(30%)、組織層面支持度(25%)、患者或家庭的知識(8%)4個方面存在不足。其中早期活動文化主要是指多學科團隊協作、康復運動目標與方案、康復相關證據及其適用性等。KRUPP 等[29]通過對20 名護士的半結構式訪談發現,康復目的、信息收集、康復計劃的制定與啟動是護士決策和推進早期康復的障礙因素。ICU 早期康復的實踐與推進受醫師、護士、康復治療師等相關知識、態度與行為影響較大,且與其工作經歷有一定相關性[30-31]。國內多項研究[32-34]結果表明,我國ICU 護士對患者早期活動的認知和態度不樂觀,在早期活動中缺乏主動性及積極性,且臨床實踐存在較多困難,限制了早期活動的臨床實施及發展。文化因素在ICU環境下早期康復中屬于可調控的因素,既是障礙因素,又是促進因素。國外多項研究證實[35-38],基于教育培訓、多學科團隊建立、有效的交流溝通、領導層面的支持等質量改進項目,能促進ICU文化的建立或轉變,從而推進ICU早期康復的實施,提高早期康復的依從性。因此,ICU 早期康復的成功需要ICU 文化的形成或改變來產生效益。
2.4 多學科合作相關因素
目前,ICU 早期康復尚未形成全球公認的臨床實踐指南。運動康復劑量應根據臨床療效、患者個體耐受性、患者年齡及既往情況而定。巴西ICU早期康復運動指南推薦關節被動運動10~20組/次(2次/d),主動運動1 h/d(≤30 min/次)(B 級證據);被動功率自行車運動20 min(20 圈/min),主動功率自行車運動10 min/次(2 次/d)(A 級證據)[39]。因ICU 患者病情等特殊性,早期康復活動的實施需要醫師、護士、物理治療師等參與,且受其知識、技能、經驗等影響;有效的多學科協作團隊(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或跨學科團隊是ICU 早期康復成功的必要條件[40]。有研究顯示,ICU 專職治療師(OR=6.83,95%CI2.17~21.50,P=0.001) 和高效率康復團隊(OR=2.37,95%CI1.03~5.51,P=0.043)是ICU 機械通氣患者離床活動成功的獨立影響因素[41]。MDT負責確定早期康復活動的適應證和禁忌證;物理治療師確定最佳干預模式及其強度、頻率、連續性或中斷,在ICU 早期康復中起到重要作用[39]。在歐洲,75%的ICU 至少有1 名專職物理治療師,澳大利亞大部分ICU 也至少有1 名資深物理治療師[4]。然而,在臨床實踐中,物理治療師在絕大部分ICU的工作形式是“按需”(on-demand)模式。日本研究數據顯示,77% 的被調查者是按需模式,僅17.9%的被調查者有全職的物理治療師、言語治療師及作業治療師[4]。目前,國內關于ICU 全職或專職物理治療師的相關報道鮮見,部分ICU 配備有專職呼吸治療師。強調MDT 的作用、引進全職或專職ICU 治療師,對促進與推動ICU 早期康復的成功實施具有重要意義。
3 結語
ICU早期康復對危重癥患者的預后具有重要意義,在臨床實踐過程中存在著不可調控與可調控兩方面障礙,影響其推行與實施,從而導致全球ICU環境中早期康復的實踐狀況不太理想,尤其是ICU患者早期離床活動率總體上偏低。未來需要著手于可調控障礙因素(如文化、人員等)進行以單位文化和跨專業視角為目標的研究。此外,現有ICU早期康復相關干預研究在國外開展較多,而我國重癥康復尚在起步階段。考慮國內外文化與區域差異,建議基于循證證據,進行適合于我國文化背景和ICU環境的早期康復相應干預研究,建立切實可行、可復制推廣的標準化早期康復方案或模式,以利于ICU 早期康復的推行與實施,從而提升危重癥護理的服務質量,提高危重癥患者的生存質量和生活質量,促進其盡早回歸家庭和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