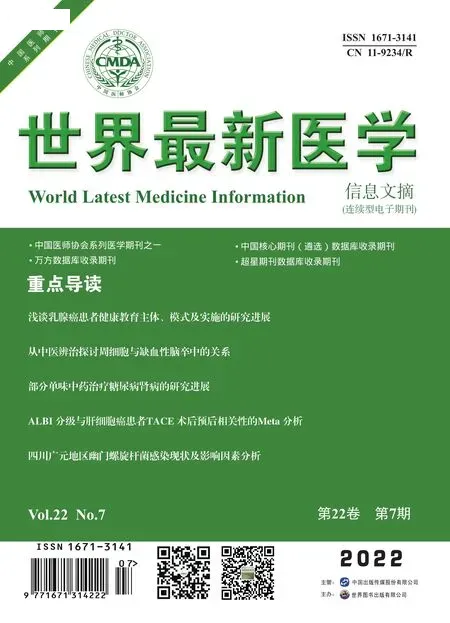單核細胞與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比值在冠心病中的 研究進展
席楚杰,黃晏
(1.甘肅中醫藥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2.甘肅省人民醫院心血管內科,甘肅 蘭州 730000)
0 引言
根據2020 年的調查結果,我國居民的死亡原因中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 仍居首位,農村為46.66%,城鎮為43.81%[1]。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是CVD 中的常見類型,與之相關的并發癥包括急性冠脈綜合癥(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都是引起患者再入院甚至死亡的常見疾病。近年來提出的新型炎癥標志物單核細胞與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比值(monocyte to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ratio,MHR) 不但具有簡單易得、可重復性強、價格低廉等優勢,而且在評估CHD 等其他疾病方面的效果超過采用傳統單一指標[2,3],是當前心血管領域的研究熱點。下面就MHR 在CHD 中的作用和研究進展進行闡述,以期為臨床診療提供新思路。
1 單核細胞、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及MHR在動脈粥樣硬化中的作用
動脈粥樣硬化(atherosclerosis,AS)的具體病因和發病機理尚不清楚,目前提出了眾多假說,其中比較全面的解釋是損傷引起的免疫應答導致炎性細胞聚集和脂質滲入,逐漸演變形成動脈粥樣斑塊[4,5]。
單核細胞作為重要的炎細胞,具有趨化、吞噬、分泌、參與泡沫細胞形成等多種功能,并常常通過分化為巨噬細胞發揮作用[6]。當血管壁受到生物、物理、化學等因子刺激后,血漿中的脂質通過受損的內皮細胞滲入血管內膜,另外由于自我保護機制內皮細胞會分泌炎癥因子,招募炎細胞聚集,單核細胞不斷吞噬進入內膜被氧化的脂質形成單核源性泡沫細胞,引起后續一系列炎癥反應,最終導致粥樣斑塊形成以及后期引起鈣化、斑塊破裂出血、血栓形成等病變[7,8]。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是致AS 的重要因素,而LDL-C 經動脈壁細胞氧化修飾后形成的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idize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ox-LDL)是最重要的致粥樣硬化因子。相反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有抑制單核細胞活化和抗氧化的作用,還能通過膽固醇逆向轉運機制清除動脈壁的膽固醇[9,10],預防AS 的發生。
單核細胞在AS 形成過程中起促進作用[11],是CHD 的獨立危險因素,HDL-C 則有抗AS 的作用,是CHD 的保護因素,兩個炎癥指標的比值反映了促AS 和抗AS 因素之間的動態平衡[12],其在CHD患者中的臨床應用價值優于單一的單核細胞計數或HDL-C 濃度。
2 MHR 與CHD 之間的關系
2.1 MHR 與冠狀動脈慢血流/無復流
冠狀動脈慢血流/無復流(coronary slow blood flow/coronary no flow, CSF/CNF) 常指因冠狀動脈( 冠脈) 血流不暢行再灌注治療后,冠狀動脈造 影(coronary artery anthography,CAG) 顯 示 冠脈無明顯痙攣、狹窄、阻塞等病變,但仍出現梗死相關動脈所供應心肌組織灌注不良/無灌注的現象[13-15]。CSF/CNF 的具體病因尚不明確,目前大多研究認為炎癥反應、氧化應激、內皮功能障礙等過程在其發病機理中起重要作用[16-18]。Canpolat等[19]研究發現MHR 是CSF 的獨立危險因子,預測CSF 的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75.9% 和68.2%(OR=1.24,95%CI:1.230~1.451),且與血清超敏C 反應蛋白(hyper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 含量成正比,可作為全身炎癥反應的常規標志物。同樣Balta 等[20]將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 的急性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STEMI)患者分為CSF/CNF 組及正常血流組,Logistic 分析得出MHR 是PCI 后CSF/CNF的獨立危險因子,且CNF 的最佳診斷點為22.5,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70.2% 和73.3%( 曲線下面積:0.768,95%CI:0.725~0.811),這雖與我國一項研究[21]得出對CSF/CNF 預測的最佳MHR 值有所差異,但隨著MHR 升高CSF/CNF 風險增加是無容置疑的。另外,Kalyoncuoglu 等[22]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患者出現CSF/CNF 時MHR 水平較高。
2.2 MHR 與冠狀動脈病變程度
SYNTAX 評分和Gensini 評分廣泛用于評估冠脈病變程度,評分越高冠脈病變程度越重[23]。一項對1229 例CHD 患者的橫斷面研究表明,MHR每升高1U,SYNTAX 評分增高的風險增加8.3%[24]。Kundi 等[25]研究發現MHR 評估高SYNTAX 評分的臨界值為24,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66% 和65.1%。我國一項研究[26]也發現MHR 與Gensini評分呈正相關,當取值為0.35 時,其診斷效率最高,敏感度為62.7%,特異度為77.2%,準確度為73.5%。因此,MHR 可作為一項新型炎癥指標用于預測冠脈病變程度,但其最佳MHR 值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2.3 MHR 與CHD 相關預后
PCI 仍然是目前治療冠脈血流受阻的主要有效措施。然而即使是當前藥物涂層洗脫支架的廣泛應用,術后規律服用雙聯抗血小板、調脂等治療,仍有約10% 的患者發生支架內再狹窄(in-stent restenosis,ISR),支架內血栓(in-stent thrombosis,ST)遠期發生率也為10%,而極晚期ST 更是占PCI術后新發心肌梗死(myocardial infarction,MI) 的20%,不但嚴重影響了治療效果,而且給患者帶來了巨大的生命危險和經濟負擔[27-31]。ISR 和ST的影響因素眾多,具體原因尚不明確,目前研究表明單核細胞激活及術后持續炎癥反應在其中起重要作用[32-34]。Avci 等[35]對患者分組研究后發現ISR 組MHR 更高(1.67vs1.47)。另有研究發現術前MHR 最高者的再狹窄率(OR=1.45,95% CI:1.06~1.88)[36]高于MHR 最低者(OR=1.29,95% CI:1.15~1.49)[37]。Cetin 等[38]研究也表明高MHR 水平是STEMI 患者發生的ST 的獨立危險因素。
A?k?n 等[39]研究表明,MHR 可作為STEMI 患者隨訪期間QRS 評分的獨立預測指標(OR=0.390,95% CI:0.252~0.605),此評分對MI 面積有預測價值。研究表明,MHR 是STEMI 患者院內死亡率(HR=3.74,95% CI:1.31~5.95)、5 年 死 亡 率(HR=2.048,95%CI:1.225~4.091)、院內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ac events,MACE)(HR=1.50,95% CI:1.02~1.99)以及5 年MACE(HR=1.285,95%CI:1.064~1.552)的獨立預測因子[40]。一項多因素cox 分析[41]也表明MHR可作為PCI 術后全因死亡率和MACE 的獨立預測因子,高MHR 使MACE 風險增加了2.83~3.26 倍。因此MHR 對行PCI 患者術后不良事件判斷有重要意義,可用于預測疾病進展,是反映CHD 相關預后的重要指標[42]。
2.4 CHD 的靶向抗炎進展
血脂異常和炎癥反應被認為是致AS 的兩大重要因素,雖然降脂和抗血小板治療已廣泛應用臨床,并有效降低了MACE 發生率,但CHD 患者并發血栓栓塞的風險依舊很高,全球ACS 的發病率仍然逐年上升[43,44]。目前CHD 的二級預防主要針對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等危險因素,目前國內外指南及專家共識尚未推薦抗炎治療。AS 的炎癥反應復雜,靶點眾多,其中IL-1β 參與的信號通路是目前的研究熱點,2017 年的卡那單抗抗炎性血栓形成結果研究(canakinum-abanti-inflammatory thrombosis outcomes study,CAN-TOS) 表 明,白 介素(IL)在AS 的炎癥反應中起重要作用,而IL-1β單克隆抗體卡那單抗能夠在不影響血糖和血脂的情況下,顯著降低炎癥標志物hsCRP 水平[45,46],并降低AMI 后MACE 的發生風險[47-51]。COLCOT 研究是一項對新發AMI 的患者發生MACE 的大型多中心、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的臨床試驗[52],結果表明秋水仙堿不僅能抑制AMI 過程中心肌壞死誘導的急性炎癥反應,也可以降低CHD 穩定階段的殘余炎癥風險[53][(residual inflammation risk,RIR),hsCRP ≥2 mg/L]。另也有研究表明對CHD 患者抗炎治療后可明顯降低MACE[54]。但Ridker 等[55]研究發現低劑量甲氨蝶呤抑制炎癥的治療并未改善CHD 患者的預后。
其他潛在抗炎靶點如IL-6、IL-1α、p38 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p38 MAPK)、TNF-α、脂蛋白相關的磷脂酶A2(lipoprotein-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Lp-PLA2)、NLRP3 炎癥小體[56-58],其在CHD 中的作用尚在研究階段。因此,抗炎治療是否有利CHD 患者的遠期預后以及有無其他尚未知曉的風險仍有待考證。但已有研究更加證實炎癥是AS 的基礎,存在潛在治療靶點,為CHD 的抗炎治療提供了新思路。
3 總結與展望
多項研究表明MHR 與AS 形成、CSF/CNF、冠脈病變程度、CHD 患者相關預后、抗炎治療等方面相關,作為一種新型炎癥標志物,具有容易獲得、適用范圍廣、患者易接受等優勢,對CHD 患者的危險分層、病情評估及治療、預后判斷等方面有較高的應用價值。但CHD 整個病程受多種因素影響,MHR 只能部分的反應炎癥的一方面,且MHR 在病情判斷及預后評估等方面的具體界值尚不確定,另外在靶向抗炎方面仍需大規模、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未來有望在生物標志物及靶向抗炎等領域取得突破,為高危人群篩選提供更多理論依據,為CHD 患者乃至其他CVD 患者帶來更多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