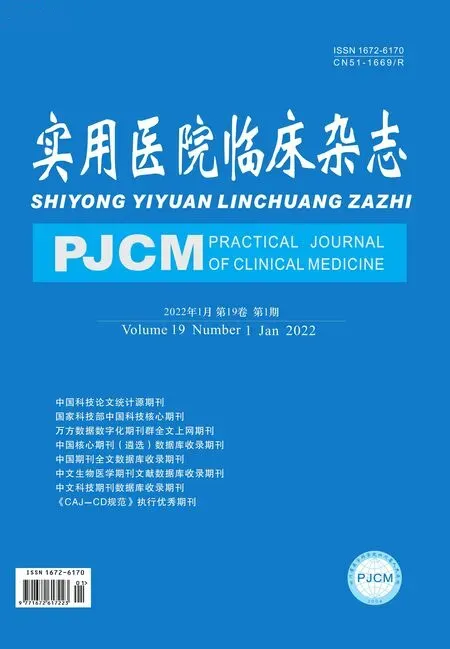侵襲性曲霉菌病患者行異基因造血干細胞移植1例報告
李祥飛,董 天,靳雪蓮,陳心傳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血液科,四川成都610041)
患者,女,22歲,于2020年4月5日因乏力收入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血液科。2016年確診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貧血(AIHA)后間斷強的松治療。2019年出現全血細胞減少,經相關檢查確診華氏巨球蛋白血癥,接受利妥昔單抗+苯丁酸氮芥治療。M蛋白轉陰,全血細胞減少進行性加重,輸血依賴。2019年12月骨髓活檢提示增生極度低下,考慮骨髓造血功能衰竭。2020年4月出現發熱,咳嗽。血常規:白細胞(WBC)0.1×109/L,血紅蛋白(HB)66 g/L,血小板(PLT)4×109/L,胸部CT提示右肺上葉后段及下葉背段大片實變。半乳甘露聚糖(GM)5.78 GMI,降鈣素原(PCT)0.1 ng/ml。使用伏立康唑+脂質體兩性霉素B抗真菌后病灶縮小。2020年6月7日采用氟達拉濱+抗人胸腺細胞免疫球蛋白+環磷酰胺+馬法蘭(Flu-Cy-ATG-Mel)預處理(抗人胸腺細胞免疫球蛋白總量125 mg D-9~-7,氟達拉濱50 mg D-6~-2,環磷酰胺540 mg D-6、-5,馬法蘭80 mg D-3、-2),2020年6月17日回輸非血緣供者人類白細胞抗原0/10相合外周血造血干細胞209 ml,總有核細胞(TNC)29.54×108/kg,CD34+細胞10.47×106/kg。甲氨蝶呤+環孢霉素預防移植物抗宿主病。繼續伏立康唑+脂質體兩性霉素B抗真菌。D+16中性粒細胞植活。D+19胸部CT:病灶進一步縮小,邊緣模糊,內部空洞影。GM試驗 2.87 GMI。D+28 癲癇發作,頭CT未見明顯異常。腦脊液常規、生化正常,墨汁染色(-),腦脊液NGS(-)。停用伏立康唑與環孢霉素A,使用霉酚酸酯+美卓樂預防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繼續脂質體兩性霉素B抗真菌,加用德巴金、左乙拉西坦抗癲癇。D+42天:血常規:WBC 3.61×109/L,HB 92 g/L,PLT 25×109/L。骨髓涂片:增生低下;流式:未見克隆性B淋巴細胞。繼續脂質體兩性霉素B治療,肺部病灶穩定。患者血小板一直未植入。2020年9月22日(+97天)開始口服艾曲波帕50 mg/d。2020年11月22日骨髓涂片:骨髓小粒內增生活躍,粒系35%,紅系40%,形態未見異常,全片巨核細胞6個。流式:CD3+細胞中CD8+細胞占78.7%,CD4+細胞占比13.6%。骨髓活檢:增生極低下,三系均低。嵌合:全骨髓96.7%,T淋巴細胞分選95.6%。2020年11月26日(+162天)予美羅華500 mg輸注,2020年11月30日(+166天)復查胸部CT感染灶較前進一步吸收,2020年12月2日(+168天)停用脂質體兩性霉素B,換用泊沙康唑。2020年12月5日(+171天)血常規:PLT 26×109/L,脫離血小板輸注。2020年12月16日血常規WBC 8.72×109/L,HB 116 g/L,PLT 85×109/L,CD4+222/μl,CD8+1066 /μl,IgG 11.0 g/L,IgM 653.0 mg/L。患者出院,口服泊沙康唑預防真菌。
討論未完全控制的侵襲性真菌病(IFDs)因為在異基因造血干細胞移植移植(allo-HSCT)期間復發所致的死亡風險很高,所以曾被視為禁忌。但隨著早期診斷快速發展和抗真菌藥物的不斷更新,目前認為即使存在相對活躍的IFD,只要配合有效的抗真菌治療,也不是HSCT的絕對禁忌證,但是對于移植時間的把控,移植方案的選擇,目前尚無統一定論,仍需高度個體化的判斷。有研究顯示施行HSCT前治療IFD至少4周[1],但較為棘手的是移植前的IFD對治療的反應評估通常較為困難。對于炎癥后瘢痕和活躍的真菌病變是很難通過普通CT加以鑒別的,有人提出PET/CT是評估抗真菌治療療效和評估IFD復發潛力的有前景的手段[2],但因診斷成本過高所以目前在臨床的應用還仍有受限。因為半乳甘露聚糖在曲霉菌菌絲活躍生長時釋出,所以當經過抗真菌治療后,菌絲生長會受到抑制而導致GM試驗呈現假陰性,故對于治療反應的評估無法提供可靠依據。本例患者使用糖皮質激素超過5年,利妥昔單抗進一步損害體液免疫功能,長時間粒細胞缺乏,輸血依賴導致鐵過載,這些都成為IFDs的高危因素。其曲霉菌病灶在肺外周,經過6周伏立康唑聯合二性霉素B治療,病灶周圍滲出明顯減少,早實施HSCT以恢復免疫力可能有助于阻止IFD進展,于是按計劃實施移植。值得注意的是,對于充分的抗真菌治療仍然表現頑固的鼻-眶-腦感染和肺部感染,由于霉菌的嗜血管特點,位于肺部中央的病灶尤其有導致大咯血危險,中樞神經系統霉菌病死亡率也非常高。這些情況下,在HSCT之前實施外科手術是必要的。需要控制手術規模,以最小損傷切除病灶,最大程度地縮短術后恢復期。
對有真菌感染病史患者需要高度個性化地設計移植方案。一般而言,降低預處理方案化療強度(RIC),盡量減輕黏膜炎程度,使用動員的同胞HLA全合的外周血干細胞,盡量縮短白細胞減少癥的持續時間有利于減少IFD復發。干細胞移植類型因病人疾病本身特點和干細胞來源限制而不具備選擇的靈活性,但是術后IFD風險差異決定了圍移植期抗真菌策略不同。制定預處理方案需要權衡降低移植后IFD相關死亡率的潛在益處與移植后白血病復發的風險。本例患者為無關供者造血干細胞移植,通常免疫重建既緩慢又不完全,GVHD風險高。為了盡量減少對免疫重建過程影響,我們減量抗胸腺細胞球蛋白(ATG)總量,并前置到預處理最初3天,術后使用環磷酰胺處理增殖的自身反應性T淋巴細胞。干細胞輸注量大。經過以上處理,患者D+16 中性粒細胞植活,D+171天 CD4+T淋巴細胞超過200/μl ,免疫重建過程正常,也沒有發生明顯GVHD。
移植后IFDs預防措施需要考慮抗真菌藥物的藥理作用、免疫抑制狀態、既往真菌感染類型。在廣泛使用唑類抗真菌藥物預防的時代,侵襲性念珠菌病不太常見,侵襲性肺曲霉病成為最常見真菌感染類型[3]。通常筆者更愿意選擇靜脈滴注棘白菌素類的米卡芬凈和卡泊芬凈作為IFDs一級預防,相對伏立康唑和伊曲康唑,它們肝和心臟毒性較輕,較少干擾CYP450酶系統。但是,對于曲霉菌,棘白菌素僅有抑菌的效果。本例患者還是選擇伏立康唑+脂質體兩性霉素B抗真菌治療,盡管小心地監測相關藥物的血藥濃度,仍然發生中樞神經系統異常,臨床考慮可逆腦后部白質病變。可能因為伏立康唑本身神經毒性,也不排除干擾環孢霉素血藥濃度,加重內皮損害。停用伏立康唑后意識恢復。沒有有效的標準可以預測何時可以安全停止HSCT后的抗真菌藥物預防。研究顯示,移植后100天內發生IFD突破風險最大[4, 5],對于本病完全緩解(CR),粒細胞植入,沒有活動性IFD征兆的患者,文獻支持在HSCT后100天至6個月后停止預防[6],除非因GVHD治療增加額外的免疫抑制治療[7]。但是,移植后免疫重建是一個完全異質的過程,單純以移植后時間劃線決定抗真菌治療的療程并不合適[8, 9]。本例患者胸部CT一直有殘留病灶,選擇兩性霉素B治療,但是出現血小板植入明顯延遲,考慮藥物的骨髓毒性。停用兩性霉素B,輔以造血刺激藥物后血小板植入成功。國內外指南將泊沙康唑推薦為移植后預防IFD的一線藥物,血藥濃度不穩定是預防失敗的可能原因[10]。移植后多種炎癥性肺綜合癥(如閉塞性細支氣管炎,彌漫性肺泡出血)經常模擬肺部真菌感染,治療上需要加強免疫抑制,由于和IFD在處理上矛盾,必須首先排除感染。需要常規進行支氣管肺泡灌洗,進行真菌培養,GM和G試驗以及PCR檢測真菌病原體。對不典型病灶,建議支氣管鏡下或經皮CT引導下活檢,術前需要進行風險獲益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