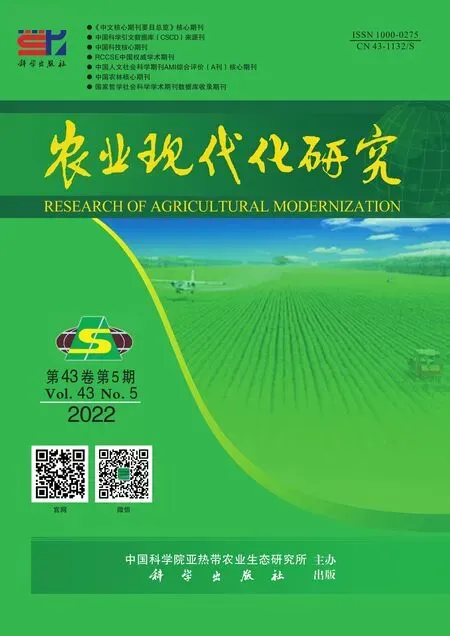欠發達地區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與阻礙因素分析
——以云南省為例
肖露,張榆琴*,李新然,李學坤,
(1.云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云南 昆明 650201;2.云南省高原特色農業產業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204)
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是新時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必然要求,關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的成敗[1]。我國計劃到2035年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目標,為現代化經濟體系奠定基礎[2]。然而,農業農村是我國“新四 化”中相對落后板塊。村莊空心化、土地荒廢和環境污染等“鄉村病”在某些地區依然存在,甚至更為嚴峻[3]。因此,在“三農”工作重心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歷史性轉移之際,跟蹤評價和分析我國欠發達地區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及其制約因素,既可以為監測農業農村現代化進展提供數據支撐,又可以為順利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目標提供決策參考,這對于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重大研究意義。
梳理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西方對農業現代化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舒爾茨[4]認為,傳統農業無法對經濟發展作出實質性貢獻,需依靠技術進步,使之現代化,才能促進經濟增長。Bo?ovi?和?ura?kovi?[5]認為,隨著人口遷移,農業生產以老年人居多,導致農業生產滯后和鄉村凋敝,強調在未來的農業發展中更應注重人的因素。Li等[6]認為,應發展在經濟、社會、人口、環境和資源等多層面實現均衡的現代農業,這對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后,我國學者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思考與研究更加深入。從定性層面上看,學者對農業農村現代化內涵的理解更加全面。姜長云和李俊茹[7]、陸益龍[8]認為農業現代化屬于產業的范疇,農村現代化是區域現代化的概念,是使農業適應現代社會生活需要和農村與現代社會融合的過程。解安和路子 達[9]、孔祥智和趙昶[10]提出農村現代化不止是過去常說的新農村建設和農村城鎮化,更多是有關鄉村文化、生態、生活和治理,乃至人的現代化。從定量層面上看,目前研究熱點之一是基于農業農村現代化內涵,構建科學合理的指標體系,測算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尋找阻礙因素,明確我國及各地區農業農村現代化未來發展方向。張應武和歐陽子怡[11]、魏后凱等[12]從鄉村振興五大總體要求層面構建指標體系,發現發展水平良好或優秀的地區大多集中在我國東部和中部,而西部地區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普遍較低。其原因在于受經濟發展和區位條件的影響,農業投資晚,農村基礎設施薄弱,農業生產難以實施。在此基礎上,學者們對我國省域農業農村現代化結構差異已基本達成共識,但阻礙因素表現各異。辛嶺等[13]認為還有農業面源污染、城鄉多維差距和鄉村治理能力失調等因素。覃誠 等[14]認為阻礙因素還表現在農業經營和支持等方面,提出未來必須注重農村產業融合、金融支持和構建多元參與的鄉村建設機制等措施。張俊婕[15]則強調農村環境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制約,由此,提出今后要大力推進農村“廁所革命”、農業生產方式低碳化和打造國家農業綠色發展先行區等建議。將研究區域下沉至某一省份,如巴·哥爾拉等[16]、章磷和姜楠[17]、何正燕和張艷榮[18]、李剛和李雙元[19]分別對新疆、黑龍江、甘肅和青海省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進行測度,發現阻礙因素多集中在農業科技、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村基礎設施、治理和環境等幾個方面,并分別對研究區域提出了針對性的 建議。
總之,關于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內涵辨析、發展水平評價和阻礙因素探究已有一定研究基礎,推動農業農村發展有理可依。但還存在有拓展的空間: 1)相對于農業現代化,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研究還較為薄弱;2)從農業生產、經營和產業等方面構建指標體系考慮較少,且對于內部系統間耦合協調程度的分析也較缺乏;3)對于阻礙欠發達地區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因素研究關注還不夠。基于此,本文以西部欠發達地區的云南省為研究對象,從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2個子系統出發,利用綜合評價方法對2006—2020年云南省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進行測算,借助耦合協調度模型,分析內部子系統之間的耦合協調水平,并通過障礙度模型對目前制約云南省農業農村發展的主要因素進行診斷,從而提出有針對性的建議意見。
1 研究方法
1.1 測度指標體系的構建
構建科學合理的指標體系,必須首先明確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內涵。本文認為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一個由農業農村各要素組合而成的動態系統,在發展的過程中,面對出現的農業產業融合和農村全面發展趨勢,利用現代化、科技化、信息化和特色化打破傳統農業的束縛,推進農業和農村全方位、多元化的發展,最終實現農業農村整體的現代化。在此基礎上構建的指標體系更多從農業農村現代化過程中表現的發展趨勢進行一個系統性的考慮。本文參考現有同類研究成果[20-23],并遵循科學性、典型性和可及性等基本原則,結合云南自身實際情況,圍繞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2個子系統,從農業產業、農業生產、農業經營、農業生態環境、農村公共建設與服務、農村居民生活、農村治理和城鄉融合8個方面,構建由38項具體指標組成的評價體系(表1)。

表1 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及其權重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the weight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發展現代化農業,須以推進農業提質增效為導向,建立健全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創新農業經營管理方式,加快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農業產業現代化應表現為農業產業結構優化、產業鏈長,農產品附加值高和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所選取的指標能反映畜牧業產值、鄉村旅游收入、農村非農就業人員占比和農產品加工值與農業總產值比。農業生產現代化應表現為在嚴守“耕地紅線”的基礎上,以政府支出、科技投入和信息技術為支撐,通過農業科技和物質裝備改造傳統農業,提高產出效率。所選取的指標能反映農業生產機械化、信息化、農田水利設施便利化、糧食單產、耕地資源狀況、農林水事務財政投入和農業科技人員支撐力度。農業經營現代化應表現為新型農業經營體制,即集約化、組織化、專業化和社會化,各要素優化形成強的生產力。所選取的指標能反映農業組織化、農林牧漁服務業產值占比水平,以及通過土地經營管理,達到的土地生產率和抵抗風險的能力。農業生態環境現代化應是堅持“兩山”理論,踐行可持續發展理念,發展綠色生態農業。所選取的指標能反映森林、濕地等自然資源狀況和農藥化肥施用量程度。
建設現代化農村,須以提高農村居民生活品質為導向,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保障公共服務基本需求,提升農村治理能力,實現城鄉融合發展。農村公共建設與服務現代化是在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便利的情況下實現的。所選取的指標能反映農村電力、交通和衛生等基礎設施以及就醫、教育和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的保障水平。農村居民生活現代化是村民幸福感、獲得感和滿足感的主要來源。所選取的指標能反映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消費結構、生活質量、生活方式市民化和思想觀念開化程度。農村治理現代化應表現為以經濟發展為依托,實現農村社會關系的良性發展,鄉村社會和諧有序。所選取的指標能反映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水平、法治示范、德治文明程度和社會救助力度。城鄉融合應表現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均等化。所選取的指標能反映城鄉居民收入、消費水平差距和城鎮化水平。
1.2 綜合評價方法
指標權重的賦值是形成科學評價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排除主觀因素的干擾,本文參考辛嶺和安曉寧[24]、劉暢等[25]的分析方法,采用客觀賦值的熵值法確定指標權重。熵值法的熵是系統混亂程度的度量,與數據信息量呈反向變動,熵越小,系統越有序,數據信息量越大,權重也就越大。而在確定指標權重之前,需采用極大極小值法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以剔除不同指標量綱的影響。最后通過多元線性加權法,得到云南省農業農村現代化綜合評價值,具體計算方法為:

式中:AM為農業農村現代化綜合評價值;wj為第j個指標的權重,xj為第j個指標標準化后的值。
本文參照國內大多數研究者的劃分標準[26],并結合已有同類研究成果[19],將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劃分為5個階段,準備階段∈[0, 0.3),起步階段∈[0.3, 0.5),初步實現階段∈[0.5, 0.7),基本實現階段∈[0.7, 0.9),完全實現階段∈[0.9, 1]。
1.3 耦合協調度模型
耦合度能評價兩個或兩個子系統以上相互作用的大小,但不能反映子系統協同發展的程度,正如兩個子系統是高耦合,但其可能是處于一個低水平狀態下的高耦合[27-28]。因此,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能更好的了解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兩個子系統的耦合協調狀況,發揮耦合乘數效應,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其計算方法為:

式中:MOD、CON分別是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的評價值,αi為熵值法得出的子系統的權重。C為耦合度,C越大,說明子系統間的耦合度越高,相互作用也就越強烈。T為綜合協調指數。D是耦合協調度,能衡量子系統整體發展的協同效應。
目前,國內一般常用廖重斌[29]所劃分的協調等級評價耦合協調狀況,協調程度主要分為三大類,失調衰退類∈[0, 0.4),過渡發展類∈[0.4, 0.6),協調發展類∈[0.6, 1],再細分,可分為10種耦合協調類型,從極度失調∈[0, 0.1)到優質協調∈[0.9, 1],反映子系統耦合協調發展狀況不斷向好,最終實現整體協同發展。
1.4 障礙度模型
為進一步分析制約云南省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的因素,本文參考李春燕和南靈[30]、陳強強等[31]的研究,運用因子貢獻度、指標偏離度和障礙度,診斷影響云南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的障礙因素。特選取2006年、2013年和2020年對比分析主要制約因素的變化情況,明確當前云南省的主要阻礙因素,具體計算方法為:

式中:Uij為因子貢獻度,反映個體指標對總目標的影響程度;Wi為第i個準則層的權重。Eij為指標偏離度,反映個體指標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目標之間的差距。Mij為個體指標對總目標的制約度。Ri為準則層指標的制約度。
1.5 數據來源
本文中的指標數據主要來自2006—2020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交通運輸統計年鑒》《中國住戶調查年鑒》《云南統計年鑒》《云南調查年鑒》等,部分數據通過中國文明網、中國民政部和司法部官網、云南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和云南省農業農村廳官網整理、計算獲取,其中個別缺失數據,通過移動平均值法預測和線性插線值法獲得。
2 結果與分析
2.1 云南省農業農村現代化綜合發展水平分析
云南省2006—2020年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整體呈快速增長趨勢,綜合發展指數從2006年的0.055到2020年的0.462(圖1),年均增長率達17.19%。但是,云南目前仍處于剛起步階段,農業農村基礎差、底子薄和發展滯后的現狀還依然存在,與完全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還有較大差距。

圖1 2006—2020年云南省農業農村現代化綜合發展水平Fig.1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Yunna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from 2006 to 2020
從子系統看,農業現代化發展指數從2006年的0.072增長到2020年的0.469,年均增長率為14.79%;農村現代化發展指數從2006年的0.036增長到2020年的0.454,年均增長率達21.66%。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指數要高于農村現代化,但農村現代化的增速明顯快于農業現代化。
2.2 云南省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結構特征分析
農業現代化由農業產業現代化、農業生產現代化、農業經營現代化和農業生態環境現代化4個準則層構成。其中在糧食單產、農業信息化和耕地保有量水平的顯著提升下,農業生產現代化發展指數較高,而農業經營現代化受農林牧漁服務業產值占比的限制,發展指數較低(圖2)。農業生態環境現代化相比于農業產業現代化水平波動較大,關鍵在于農藥和化肥施用量的變化,這也為農藥化肥減量增效,強化有機肥替代的農業綠色生產行為提供了空間。
農村現代化由農村公共建設與服務現代化、農村居民生活現代化、農村治理現代化和城鄉融合4個準則層構成。2012年前,4個準則層的發展指數較為接近(圖2)。在此之后,由于農村生活用電、交通和衛生廁所等條件的明顯改善、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費結構不斷優化,拉動農村公共建設與服務現代化和農村居民生活現代化水平快速提升;而與此同時,云南屬于邊疆少數民族欠發達地區,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城鎮化率偏低,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差距較大,致使農村治理現代化和城鄉融合發展指數明顯落后。

圖2 2006-2020年云南省農業農村現代化各準則層發展水平Fig.2 Development level of various standards of Yunna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from 2006 to 2020
2.3 云南省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耦合協調度分析
農業現代化是實現農村現代化的基礎,它能為農村的發展提供可靠的物質保障,農村現代化是農業發展的依托,它能為農業各種資源要素形成生產力提供空間載體,兩者相互促進、交叉滲透,若實現耦合互動和協調發展,能加快向現代農業農村的轉變。
云南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的耦合協調度結果顯示,兩個子系統的耦合度很高,整體都在0.94以上(圖3),兩者的關聯度高,彼此間的相互作用 強,在政策激勵和運行機制的影響下,呈現一個高耦合狀態。
耦合協調度表現為持續增長,從2006年的0.227增長到2020年的0.680(圖3),表明兩者逐漸走向協調發展。在此期間,耦合協調度的變化大致為失調衰退(2006—2011年)、過渡發展(2012—2016年)和初級耦合協調(2017—2020年)3個階段,發展趨勢向好,但就目前僅達到的初級耦合協調程度,更多表現為一種高耦合低協調的狀態,兩者雖交互作用強,但并沒有實現協調發展,不能很好的發揮相互促進,互相繁榮的耦合乘數效應。由于資源的有限性,在發展前期農業獲得更多投入,農村基礎相對薄弱,但到發展中后期,農業的帶動效應開始顯現,農村迅速發展,發展速度甚至超過了農業。鑒于云南氣候的多樣化、地形的復雜性和人口分布的分散性,這與農業現代化內涵的標準化、產業化、規模化不相適應,農業可持續發展面臨壓力,從而使得目前云南省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表現出非中高耦合協調水平。

圖3 2006—2020年云南省農業現代化與農村 現代化耦合協調度Fig.3 Coupling coordinative degree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of Yunna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from 2006 to 2020
2.4 云南省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阻礙因素分析
本文分別選取2006年、2013年和2020年測算云南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制約因子。2006年和2013年較高制約因子排序一樣,分別是農業生產現代化、農村公共建設與服務現代化、農村居民生活現代化,但在2013年這三者制約度的結構有所變化,其中農業生產現代化的制約度從2006年的25.75%降至2013年的24.64%(圖4),農村公共建設與服務現代化、農村居民生活現代化的制約度在2013年也都有所緩解。在該階段隨著云南省持續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實施百億斤糧食增產、興水潤滇、山區綜合開發等措施,農村改革“四梁八柱”發揮成效,全省在2013年糧食產量達1 824萬t,農業總產值達3 056.04億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較2006年增加了接近3倍,農民生活水平得到提升,生產生活條件明顯改善,農民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斷增強,鄉村社會得以發展。
2020年云南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主要制約因子與2006年和2013年相比,農業產業現代化的制約度呈上升趨勢,從2006年的9.85%到2020年的22.40%(圖4),成為2020年云南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較高制約因子。同時,農業生產現代化、農村公共建設與服務現代化對云南省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阻礙仍較高,一方面云南省目前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農業產業結構相對單一,產業融合發展不夠的問題,離打造全產業鏈還有一段距離。另一方面,受區位條件、資源稟賦和經濟基礎的限制,云南省還面臨完善農村公共基礎設施,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和農業科技引領生產的挑戰。

圖4 云南省農業農村現代化準則層指標的制約度Fig.4 Index restriction of criterions in Yunna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為更進一步深入探究阻礙云南省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的主要因素及其變化規律,分別測算這3個時間節點具體指標的制約度,以障礙度大于5%為界,將其從大到小進行排序。結果顯示,2020年阻礙云南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主要因素是鄉村旅游收入占比、千人村衛生室人員數、千人農業科技人員數、農林牧漁服務業產值占比、養老服務機構收養人數占比、農藥和化肥施用量,制約度分別為
21.09%、18.55%、16.23%、10.84%、10.63%、7.27%
和5.25%(表2)。一方面,云南省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主要障礙因素向多維性和多重性轉變,這一發現與辛嶺[13]相一致;另一方面,隨著時間推移,農村現代化主要障礙因素逐漸減少,農業現代化主要障礙因素相對增加,這表明國家出臺的一系列戰略政策,如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推進農村綜合改革和城鎮化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等,特別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對農村經濟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發揮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但農業明顯面臨加速向現代農業轉型升級的挑戰。
鄉村旅游收入占比是阻礙農業產業現代化最主要的因素。2006年其制約度為3.20%,2013年為1.90%,2020年大幅上升到21.09%(表2)。云南省被稱為“動植物王國”、具有良好的生態環境、絢麗的民族文化,豐富的旅游資源,旅游業一直是云南的支柱性產業,但由于受疫情影響,旅游接待人次和收入出現斷崖式下跌,從而對云南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造成顯著的影響。

表2 云南省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主要障礙因素Table 2 Main constraint factors of Yunna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千人村衛生室人員數和養老服務機構收養人數占比是阻礙農村公共建設與服務現代化的兩個主要因素。云南村寨分散、交通不便,從事村級衛生室的醫療衛生人員收入偏低,從業意愿相對也較低,另外村衛生室醫務人員年齡結構不合理,學歷普遍偏低,醫療技術和設施環境不足以滿足農村居民的需求。目前,農村出現空巢、留守、失能、高齡和貧困老年人數量龐大的現象,村莊空心化和人口老齡化進一步加大對養老資源的需求。而云南省農村養老機構和設施缺乏、養老服務模式較為單一,農村養老服務供給滯后,難以成為積極應對日益加劇的農村老齡化的重要支撐,致使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缺位。
千人農業科技人員數是阻礙農業生產現代化最主要的因素。受云南特殊地理位置和少數民族因素的限制,全省勞動力文化水平相對較低,高素質農業科技和管理人才儲備不足,且基層農業科技人員年齡和知識老化明顯,接受新事物和新知識的能力相對較弱,導致在推廣新品種、新技術和科技成果轉化方面創新能力不足,無法滿足云南省高原特色現代農業的發展。
農林牧漁服務業產值占比是阻礙農業經營現代化最主要的因素。2006—2020年農林牧漁服務業產值占比的制約度整體呈逐漸上升的動態變化特征。自2013年以來,農林牧漁服務業產值占比的制約度加快增加,其原因可能是隨著農業產業發展不均衡、農業機械化服務水平相對較低、農業經營主體力量薄弱等因素積累放大,最終導致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不足以支撐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
農藥和化肥施用量是阻礙農業生態環境現代化的兩個主要因素。黃曉丹等[32]通過研究發現2006—2015年云南化肥和農藥施用量都在增加,其無論是年均增長率還是平均水平都高于其他30個省份的均值。依托良好的自然環境,云南致力于打造綠色食品牌,走綠色、有機的可持續發展道路,過度的農藥化肥施用量會給云南生態農業的發展帶來巨大壓力。
3 結論與政策建議
3.1 結論
研究表明,2006—2020年云南省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的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綜合作用下使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總體呈快速上升態勢。但其整體水平不高,目前仍處于起步階段,與完全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還存在一些差距。另外,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呈高耦合低協調狀態,無法很好的發揮耦合乘數效應,說明在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必須協同推進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加快提高兩者的協調水平,實現走向農業農村高質發展的良性耦合。
現階段云南省農村地區的公共基礎設施與服務還較為薄弱、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不夠,農業科技支撐生產力度不足,重點體現在千人村衛生室人員數、養老服務機構收養人數占比、鄉村旅游收入占比和千人農業科技人員數等方面。同時,農林牧漁服務業產值占比、農藥和化肥施用量也是阻礙云南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因素。針對主要障礙因素,結合整體情況,以農業現代化為重點,重視農村發展,加速補齊鄉村發展短板,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
農業農村現代化內涵隨時代的發展不斷豐富,未來的研究重點是下沉研究對象至市域、縣域及鄉村層面,因時因地完善指標體系,科學制定階段性目標,為梯次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新視角。
3.2 政策建議
1)以綜合生產力提升和鄉村建設為重點,實現農業與農村現代化協調發展。必須從系統性、整體性和綜合性的視角出發,一體設計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一方面,不能淡化或偏離農業現代化,應全面提升農業綜合生產力,以農業強帶動農村美,實現鄉村富裕。另一方面更應注重加強鄉村建設,補齊農村各項硬件設施等短板,推進農村現代化,為現代農業提供人才保障,促進二者耦合協調發展。
2)著力發展高原特色現代農業,不斷推進農旅融合。立足于云南多樣性資源,持續發展普洱茶、花卉、蔬菜、水果、肉牛、中藥材、咖啡、核桃等高原特色產業,推動農特產品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延長產業鏈,打造全產業鏈。充分利用當地民族文化元素、特色產業和自然資源稟賦,構建全域旅游新格局,發展體驗經濟,加強農業、旅游、文化和健康養老等相關產業互融,實現一二三產融合發展。
3)強化完善村級衛生室和養老服務設施建設,提升農村基層公共服務水平。政府應加大對村級衛生室醫療設施的投入,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勵機制,提高村衛生室醫務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同時定期組織培訓,培養懂少數民族語言的專業醫務人員,增強醫療隊伍建設。擴大農村地區養老服務機構配套設施供給,探索居家養老、社區養老、互助養老和 “互聯網+養老”服務,構建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滿足養老多樣化需求,提升養老服務供給質量,充分發揮基層公共服務的托底保障作用。
4)加強引進和培養農業科技人員,推動農業科技創新引領生產。根據云南農業生產實際情況,以科學技術為導向,加快農業科技轉化成農業生產力,進一步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一方面,大量引進農業科技人才,培養善于與少數民族農戶溝通的本土化農業科技人才,加大對農業科技人員的培訓力度,增強其對新品種、新技術的接受和操作能力。另一方面,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提升科技創新能力,促進農業快速發展。
5)加快提升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促進農業經營現代化。強化龍頭企業、農民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建設,培養具有地方優勢的大農業小巨人,著力構建“公司+基地+專業合作社+農戶”等的產業發展模式,大力培育煙草、普洱茶、花卉、蔬菜、咖啡等特色產業的社會化服務組織,支持開展代耕代種、聯耕聯種和土地托管等專業化規模化服務,引導社會化服務主體依托信息技術,提升農業社會化服務供給水平,促進農林牧漁服務業產值占比的增加。
6)持續開展農藥化肥減量、增施有機肥行動,保障生態農業穩定發展。加強科學施用農藥和化肥引導,建立安全用藥制度,持續推進農藥、化肥減量增效示范建設,采用綜合防治農作物病蟲技術,使農藥和化肥用量減少。大力推廣使用畜禽糞便積造的有機肥,提高肥料利用率,夯實農業生態安全基礎,推動農業綠色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