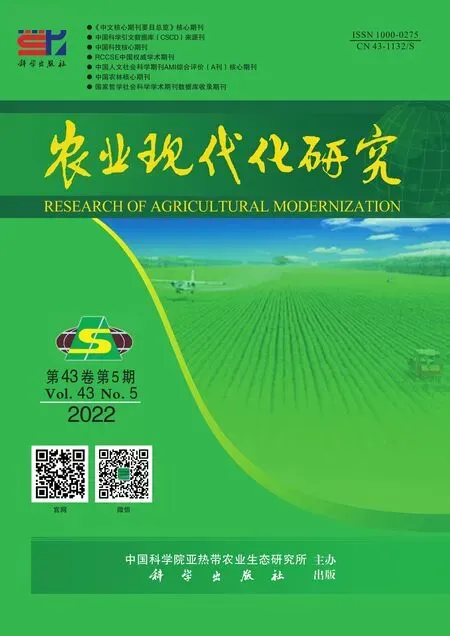社會資本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與行為的影響
莊騰躍,胡杰,羅劍朝,
(1.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陜西 楊凌 712199;2.陜西省農村金融研究中心,陜西 楊凌 712199)
農業信用擔保融資作為農村金融發展的一大進步,在抑制農村資金外流,滿足農戶資金需求,促進農戶收入增長上具有明顯的效果[1]。依賴于第三方的信用或財產作保證,農業信用擔保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農戶傳遞真實信息,降低信息成本,從而規避因農戶與銀行之間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風險,進而緩解農戶“抵押難”“擔保難”“貸款難”的困境,提高農戶貸款可得性[2]。近年來,為充分發揮農業信用擔保在農村金融市場上的杠桿作用,國家先后出臺建立和完善農業信用擔保相關政策法規,如《關于財政支持建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的指導意見》《關于進一步做好全國農業信貸擔保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由此看來,我國農業信用擔保制度在不斷完善。然而自農業信用擔保政策實施以來,農戶對農業信用擔保融資反應并不積極,實際參與意愿和行為未達到理想目標,且意愿與行為間出現一定的偏差。究竟是哪些因素影響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如何減少融資意愿和行為間的偏差,提高農業信用擔保制度的有效性,是促進農業信用擔保政策在我國農村金融市場進一步發展的關鍵所在。
一直以來,學術界就農戶借貸意愿和行為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大量的探討,主要從幾個角度展開:第一,在農戶個人特征方面。相較于女性,男性更容易具有借貸意愿和行為,女性家庭決策權程度越高,參與信貸市場的概率越低[3],農戶年齡對其借貸行為產生負向顯著影響[4],農戶的受教育程度顯著促進其正規借貸行為[5]。第二,在農戶家庭經濟特征方面。經營類型和耕地面積對農戶借貸需求和借貸可得性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6],而家庭儲蓄余額、家庭年收入和收入來源對農戶借貸行為產生負向顯著影響[7],除此之外,家庭資產對農戶正規金融借貸產生正向顯著影響,而對其民間借貸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8]。第三,在機構特征和借貸成本方 面。利率對農戶正規金融借貸需求產生負向顯著影響[9],貸款額度、期限和還款方式均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農戶的借貸需求和借貸行為[10]。除此之外,金融機構數量和交通便利程度對農戶正規借貸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而農戶與金融機構間的距離對農戶借貸具有負向顯著影響[11]。第四,在農戶認知特征方面。認知能力對農戶的各類信貸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且對正規信貸獲取的作用更大[12]。農戶對借貸政策和流程的認知程度越高,農戶借貸需求越強,參與借貸市場的概率越大[13],與未發生借貸行為的農戶相比,農戶經濟自我效能感越高,越不傾向于農業生產性投資借貸[14]。
除上述各類因素外,我國農村作為一個人情社會,社會資本對農戶借貸意愿和行為的影響也受到了學者們的廣泛研究,主要歸結為兩類。第一,關于社會資本的測度及其對農戶借貸行為的影響。張珩等[15]分別測度了農戶與銀行、政府和本村等人員的交往情況,并通過主成分分析法計算社會資本總指標,認為相較于民間借貸,社會資本對農戶正規貸款響應更為強烈。秦海林等[16]從社會網絡、信任和互惠性規范三個維度選擇指標,采用改進的變異系數法測度社會資本,指出社會資本能夠顯著提升農戶獲得銀行借貸和民間借貸的概率。第二,關于社會資本對農戶借貸行為的作用機理。Biggart和Castanias[17]認為社會資本具有金融契約中類似抵押物的作用,為了緩解農戶信貸中的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問題,可以借助社會資本的信息傳遞功能,極大提高金融機構搜尋信息的效率[18],促進農戶與金融機構間的借貸往來。趙振宗[19]認為借助政府或銀行資本,可以增進農戶與正規金融機構之間的信任關系,代替抵押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農戶貸款可得性。上述研究均表明,社會資本對農戶借貸意愿和行為產生重要影響,而農業信用擔保融資作為農戶借貸方式的一種,依賴第三方的信用或財產作保證,更加需要社會資本發揮作用。那么,社會資本是否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產生影響,若產生影響,影響機制是什么?這種影響在不同類型的農戶群體間是否存在差異?這些問題均有待探討。
現有研究為本文的開展提供了參考和借鑒,但可能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現有研究大多從農戶融資渠道的角度研究農戶借貸行為,較少從具體的融資模式角度出發研究。第二,關于社會資本對農戶借貸行為影響的文獻較豐富,認知特征也被納入到影響農戶借貸行為的因素中,并形成由認知到意愿再到行為的農戶心理決策過程[20],但少有研究考慮到社會資本和認知水平間或存在某種機制在二者對農戶借貸行為的影響中發揮作用。因此本文基于陜西3縣(區)666戶農戶調查數據,采用Bivariate Probit模型,將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納入同一分析框架,分析社會資本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的影響,并進行內生性和穩健性檢驗,不僅驗證了社會資本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及二者間偏差的影響,還深入從流程認知、積極度認知和政策認知角度討論其作用機制,并針對農戶的異質性進行分析,以期為引導和促進農戶參與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提供科學依據。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 社會資本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與行為的直接影響
在農業信用擔保融資中,無論是抵押擔保、質押擔保或保證擔保,均需要第三方的信用或財產作擔保[21]。在農戶缺乏金融機構認可的抵押物或擔 保品情況下,社會資本便成為其獲得擔保和貸款 的重要資源,對農戶的融資意愿和行為產生重要影響[22-23]。在農村金融市場,因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各種道德風險、逆向選擇等問題是產生信貸抑制和困境的主要來源,而社會資本有利于緩解由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對滿足農村金融需求具有積極意義[24]。社會資本派生于人際網絡,包含了農戶所擁有的社會資源,通常指“社區成員在特定社區內積累的力量和機會”或者“由社會關系所得到的個人資源”[25]。本文將社會資本具體劃分為政府關系資本、銀行關系資本和村級關系資本,并通過信息傳遞效應和替代效應分析其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的影響。
農戶的政府關系資本分為內延和外延兩種類 型[26]。并非每個農戶家庭都具有內延資本,根據實際情況,只有極少數農村精英能夠成為政府工作人員,在村中具備較高的社會地位和聲望。外延資本主要側重于與政府工作人員的交往程度,其影響力較之內延資本偏弱。但無論是何種類型的政府關系資本,均能夠賦予農戶復雜的人際關系,形成極強的個人關系網絡來發揮信息傳遞效應[27],在此龐大的人際關系網中,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相關政策信息的傳遞速度和深度較之普通農戶更快更深,農戶在一定程度上擁有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的優先權,從而提高其參與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的意愿和獲得貸款的概率。同時,政府關系資本賦予農戶較高的社會地位、聲望和權力,能夠增進其與金融機構間的信任度,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抵押擔保的功能[28]。另外,豐富的政府關系資本意味著農戶具有值得金融機構信賴的擔保人員,即政府工作人員,使其容易獲得貸款。基于以上分析,政府關系資本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具有正向影響。
農戶的銀行關系資本主要涉及其與銀行等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往來和人情關系。農戶與銀行等金融機構業務往來頻繁,信用評級記錄在冊,與金融機構間信任度較高,一定程度上能夠替代金融機構對抵押物的要求,破除金融機構的排斥壁壘,節省尋找抵押擔保的費用[15],促進農戶參與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此外,農戶與銀行等金融機構工作人員交往頻繁,有機會接觸到銀行內部信息,甚至是一些利率優惠活動,且容易知道貸款具體操作流程[7],同時內部信息使其貸款流程簡單化,節約交易成本,也降低金融機構搜尋農戶信息的業務成本和信貸風險,從而使得農戶獲得貸款的概率增加,影響其參與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的意愿和行為。基于以上分析,銀行關系資本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具有正向影響。
農戶的村級關系資本主要包含農戶與村干部、本村村民和近鄰之間交往關系。農戶與這些群體交往越頻繁、關系越熟悉,越有助于其加入一些村集體組織,如合作社、協會等,這些組織在農業信用擔保融資中可發揮第三方擔保的作用。如農戶僅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而無其他金融機構認可的抵押物,農戶可加入本村的合作社或土地協會等合作組織,在需要信貸資金時,由土地協會作為第三方向金融機構提供擔保,從而金融機構向農戶放款。此時,村級關系資本既是農戶加入土地協會、獲得擔保的資源,也是對農戶合理使用信貸資金、按時還貸的一種約束[29]。除此之外,龐大的村級關系網使得農戶間可互相作保,也可互相監督約束,減少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風險顧慮,提高貸款可得性。基于以上分析,村級關系資本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具有正向影響。
1.2 社會資本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與行為的間接影響
已有研究表明,個體對事物的認知會在一定程度上對個體行為產生影響[20]。計劃行為理論認為,認知是個體后續行為的發端,從認知到意愿再到行為,是一個連續完整的過程,因此,農戶是否具有參與農業信用擔保的意愿和行為受到農戶本身對于農業信用擔保的認知影響,并且農戶的認知水平在社會資本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的影響中起到中介作用,具體可將農戶的認知水平劃分為流程認知、積極度認知和政策認知。
農戶對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的流程認知,是影響農戶進行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的一個重要因素,只有農戶對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的辦理流程有一定的了解,才有可能具備后續的融資意愿和行為[13]。而農戶社會資本的豐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農戶對農業信用擔保融資辦理流程的了解,尤其是銀行關系資本,有助于農戶對農業信用擔保辦理的流程、所需材料等有清晰的了解,并且能夠幫助農戶分析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的利弊所在,使農戶對農業信用擔保有清晰的認知。因此,在社會資本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產生影響的過程中,農戶對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的流程認知發揮著一定的中介作用。
積極度認知,指農戶認為當地金融機構開展農業信用擔保業務是否積極,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金融機構對該項貸款業務的宣傳程度。宣傳程度越高,農戶認為金融機構開展農業信用擔保業務越積極,就越有可能去了解農業信用擔保[30],從而提高其參與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的概率。社會資本對農戶積極度認知存在一定的影響,社會資本的信息傳遞功能會加快金融機構宣傳的速度和深度,從而加深農戶對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的興趣和了解,進而影響到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因此,農戶的積極度認知可能在社會資本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的影響中發揮中介作用。
政策認知,指農戶對農業信用擔保政策的了解程度,如對利息優惠、擔保扶持和貼息等政策的了解。以上優惠政策會對農戶參與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有所吸引,農戶對相關政策的了解會影響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31]。同時,農戶對相關政策的認知受到其社會資本的影響,農戶的政府關系資本越豐富,其接觸到相關政策的機會越多,認知會更加深刻,從而有助于其參加農業信用擔保融資[32]。因此,在社會資本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 和行為的影響中,政策認知同樣發揮著一定的中介效應。
綜上所述,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不僅受到社會資本的直接影響、社會資本以認知水平為中介的間接影響,還受到農戶個人特征、家庭特征和金融環境特征等因素的影響,具體作用機制如圖1所示。

圖1 社會資本影響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與行為的作用機制Fig.1 Mechanism of social capital a§ecting rural households’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s to use credit guarantee loan financing
2 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數據來源于課題組2021年7月對陜西省農戶的問卷調查。考慮到本文研究的主要內容和陜西省各縣在農業產業發展水平上存在差異,農業大縣以及具有特色農業產業的縣區,農戶對資金的需求會更加強烈,更需要金融機構貸款的支持,因此選取具有柿餅和奶山羊產業的富平縣、獼猴桃產業的武功縣和農業大區楊凌區作為研究的樣本縣(區),更具有代表性。調查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從每個縣(區)隨機抽取2~3個鄉鎮,每個鄉鎮隨機抽取3~4個自然村,每個自然村隨機抽取30~40戶居民作為調查對象。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703份,其中有效問卷666份,有效率達94.74%。問卷主要包含農戶基本信息、貸款經歷與評價、未來融資需要與打算、信用擔保政策落實情況等內容。
2.2 變量選擇
1)因變量。本文的因變量為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表1)。具有融資意愿賦值為1,反之賦值為0;具有融資行為賦值為1,反之賦值 為0。
2)核心自變量。本研究的核心自變量為農戶社會資本,具體劃分為政府關系資本、銀行關系資本和村級關系資本三個維度,并計算三者的算術平均值作為社會資本的綜合指標。其中政府關系資本使用“農戶與當地政府工作人員之間的交往程度”來測度,銀行關系資本使用“農戶與當地金融機構工作人員之間的交往程度”來刻畫,村級關系資本使用“農戶與村干部之間的交往程度”來表征。各維度采用五級分類進行表示。
3)中介變量。認知水平,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認知水平包括流程認知、積極度認知和政策認知。流程認知采用農戶對農業信用擔保辦理流程的了解程度進行測度,將了解程度從“沒聽說過”到 “非常了解”劃為五個程度。以“農戶認為當地金融機構開展農業信用擔保業務是否積極”測度積極度認知,采用五級分類進行表示。以“農戶對農業信用擔保政策了解程度”表示政策認知,同樣采用五級分類測度。
4)控制變量。根據前文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影響因素的總結以及調研地區的實際情況,本文從農戶個人特征、家庭特征和金融環境特征3個方面選擇共同影響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的一組控制變量。
上述各變量賦值說明與描述性統計見表1。

表1 變量賦值說明與描述性統計Table 1 Variable assignment descrip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2.3 模型設計
本文需要檢驗社會資本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的影響,因此,把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作為因變量,由于其均為二值變量,故選擇Probit模型。計劃行為理論認為,個體意愿會對其行為產生影響,個體意愿的加強有助于個體行為的實施,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之間存在一定的關系,通過提高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能夠促進其融資行為的實施。因此,如果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融資行為分別進行Probit回歸,由于兩個Probit方程的隨機擾動項之間可能存在相關性[33],會損失效率,因此應采用Bivariate Probit模型進行估計,模型設定形式為:

式中:Yi表示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或融資行為,Xi表示社會資本,Ci為控制變量,εi為融資意愿或融資行為的隨機擾動項。
2.4 內生性處理
基準回歸模型中可能存在因遺漏變量、變量測度偏差和反向因果關系等導致的內生性問題,使得回歸結果出現偏誤,需采用工具變量法進行修正。本文選取的工具變量為農戶受表彰情況,具體用農戶個人或家庭累計受表彰次數進行表示。顯然,農戶受表彰次數越多,其在村子的知名度和聲望就越高,社交圈子就越廣,社會資本越豐富,因此具備相關性。另外,農戶受表彰情況不會直接影響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同時,影響農戶受表彰情況的主要因素為農戶及其家庭的優秀品質或奉獻事跡等,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很難反作用于農戶受表彰情況,因而具備外生性,故本文選取農戶受表彰情況作為工具變量進行IV-Probit估計,減少內生性問題造成的結果偏誤。
3 結果與分析
3.1 農戶社會資本、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與行為分析
調研結果表明,受訪農戶的政府關系資本、銀行關系資本和村級關系資本平均水平分別為1.721、1.770和2.236,社會資本綜合指標平均值為1.907 (表1),受訪農戶社會資本整體水平偏低,尤其是政府和銀行關系資本,說明調研地區政府和銀行等金融機構與農戶間的交往和業務往來密切程度不高,農戶所掌握的社會關系較為簡單,人際關系網絡廣度和深度均需進一步拓展和提升。
愿意進行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的受訪農戶占50.4%(表1),并且76.3%的受訪農戶認為農業信用擔保融資優于其他融資方式,說明農業信用擔保剛好為農戶提供了一個合適的融資方式,農戶在有資金需求時會優先考慮農業信用擔保融資。但也有一半的受訪農戶并未產生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可能是由于農戶自身各類資本的匱乏使得其對于自己獲得貸款沒有信心,也可能是由于年齡、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收入和資產水平等原因,使得這類農戶沒有較大的資金需求,不需要進行融資。本次調查中,受訪農戶的平均年齡為54.779歲,老齡化問題較為嚴重,風險承受能力和生產經營意愿下降,資金需求不強烈,并且受訪農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189年,處于小學和初中之間,表明農戶整體受教育程度偏低,對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的認知可能不足,從而并未產生融資意愿。除此之外,還有部分受訪農戶家庭收入和資產水平較高,并不需要進行融資。由此可見,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的有效需求和意愿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實際參與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的受訪農戶占比僅為18.6%(表1),遠小于具有融資意愿的農戶,說明具有融資意愿的農戶并非同時具有融資行為,融資意愿和行為間存在一定的偏差。可能的原因是在農戶融資意愿向融資行為轉化的過程中,存在諸多因素制約著這種轉化,比如農戶對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的額度不滿足、認為辦理流程太過繁瑣、利率較高 等,從而使農戶實際融資行為率較低。由此可見,農 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均有待進一步提高。
3.2 社會資本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與行為的影響分析
基于Bivariate Probit模型估計結果表明,各類社會資本中,銀行關系資本、村級關系資本和社會資本綜合水平均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產生正向顯著影響,回歸系數分別為0.223和0.208,0.124和0.152,0.254和0.232(表2),即三者水平的提高能夠同時提升農戶的融資意愿和行為。而政府關系資本僅對農戶融資意愿產生正向顯著影響,回歸系數為0.164,對農戶融資行為的影響不顯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受訪農戶整體政府關系資本水平不高,均值僅為1.721(表1),是三類社會資本中最低的,雖然擁有政府關系資本的農戶融資意愿會更強,但可能由于所擁有的政府關系資本深度和強度不足,在抵押和擔保的功能上有所欠缺,并未顯著提升其貸款可得性,因此對農戶融資行為影響并不顯著。

表2 社會資本影響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與行為的估計結果Table 2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s of social capital on rural households’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s to use agricultural credit guarantee financing
控制變量中,健康狀況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的影響均顯著且為正,說明身體健康的農戶從事生產的積極性較強,愿意進行融資擴大生產,并將這種意愿付諸行動,故其同時具有融資意愿和行為的概率會更高。經營類型對農戶融資意愿產生顯著影響,說明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戶融資意愿更強,但對其融資行為并未產生顯著影響,可能是因為農業生產的脆弱性使得農戶資本積累緩慢,需要外部資金注入,但又因為自身各類資本的匱乏尋不到合適的擔保人或承擔不起反擔保的成本,從而使得農戶對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望而卻步”。土地規模對農戶融資意愿并未產生顯著影響,但卻對其行為具有正向顯著影響,與已有研究和理論分析不符,可能是因為受訪農戶中,土地規模較大的農戶在生產經營中因為臨時的流動性資金短缺,更偏好于速度快、期限短的民間借貸,而對審核周期長、擔保程序復雜的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并不強烈,但是在金融機構眼中,這類農戶是優質客戶,為完成本機構的業績指標等,會上門為該類農戶提供貸款融資服務,并且提供較多優惠條件,從而使得這類農戶獲得貸款。年收入水平僅對農戶融資行為產生正向顯著影響,可能的原因與上述類似。除此之外,農戶家庭資產總額越高,交通越便利,農戶同時具有融資意愿和行為的概率也越高,主要原因在于農戶家庭資產越豐富,越有把握按時還貸,符合金融機構設置的“門檻”,農戶就更愿意申請貸款并且容易獲得貸款從事生產;距離金融機構的交通便利,農戶與金融機構間的外部阻礙減少,農戶在有資金需求時就會更加愿意去金融機構了解相關信息,辦理流程手續會更加便利,因此其融資意愿也會更強,進而提升其融資行為的概率。
3.3 社會資本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與行為偏差的影響分析
基準回歸結果表明,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不僅受社會資本的影響,而且與部分農戶個人特征、家庭特征和金融環境特征顯著相關。然而,并非所有具有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的農戶最后都參與農業信用擔保融資。因此,究竟是哪些因素影響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向融資行為的轉化,這些因素對二者間的偏差有何影響,回答這些問題不僅能厘清社會資本與控制變量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偏差的影響,而且能為本文政策啟示的提出提供實證參考。考慮到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共存在4種情況,即無意愿無行為(0, 0);無意愿有行為(0, 1);有意愿無行為(1, 0)和有意愿有行為(1, 1),因此本文基于Bivariate Probit模型,進一步計算了各解釋變量在這四種情況下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的邊際效應,并據此分析各解釋變量對其意愿和行為偏差的影響。
回歸結果顯示,社會資本對農戶同時不具備融資意愿和行為產生顯著負向影響,對農戶同時具備融資意愿和行為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具體表現為農戶社會資本水平每提高1單位,其同時不具備融資意愿和行為的概率下降8.9%,而同時具備融資意愿和行為的概率上升5.1%(表3),說明社會資本不僅能夠促進農戶參與農業信用擔保融資,而且能夠減少農戶融資意愿和行為間的偏差,促進意愿向行為的轉化。控制變量中,健康狀況和交通便利程度同樣對農戶同時不具備融資意愿和行為產生顯著負向影響,對農戶同時具備融資意愿和行為產生顯著正向影響,上述變量每增加1單位,農戶同時不具備融資意愿和行為的概率下降7.1%和5.9%,同時具備融資意愿和行為的概率上升4.6%和9.3%,進而減少融資意愿和行為間的偏差。

表3 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與行為偏差分析結果Table 3 Analysis of rural households’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deviation in agricultural credit guarantee financing
對農戶僅具備融資意愿而不具備融資行為的選擇,若解釋變量對該種選擇產生顯著影響,那么就有可能是使農戶融資意愿和行為間產生偏差的因素。結果顯示,經營類型、土地規模和家庭資產總額對農戶僅具備融資意愿不具備融資行為產生顯著影響。具體來看,農戶越傾向于從事純農業生產,農戶同時不具備融資意愿和行為的概率越低,但僅具有融資意愿而不具備融資行為的概率越高,且后者邊際效應絕對值大于前者,從而造成農戶融資意愿和行為間產生偏差。農戶土地規模提升1單位,其僅具備融資意愿不具備融資行為的概率降低6.2%,并且同時具備融資意愿和行為的概率提升3.6%,能夠減少融資意愿和行為間的偏差。農戶家庭資產總額增加1單位,其僅具有融資意愿而不具備融資行為的概率上升9.1%,大于同時具有融資意愿和行為上升的概率4.4%,因此也可能造成農戶融資意愿和行為間的偏差。
3.4 內生性檢驗分析
表4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農戶受表彰情況顯著影響其社會資本,符合工具變量的相關性特點,一階段F值為15.16,大于臨界值10,且在IVProbit模型的弱工具變量檢驗中,Wald內生性檢驗P值、AR檢驗P值均小于0.001,表明拒絕存在弱工具變量的原假設,排除了弱工具變量的問題。由此可知,本文選取的工具變量合理,且原模型存在內生性問題。結果表明,在消除內生性后,社會資本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的影響仍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為正,回歸系數為2.514和4.442,相比基準回歸結果有所提升,說明若不考慮內生性問題,則會低估社會資本對農戶融資意愿和行為的影響。

表4 內生性檢驗結果Table 4 Endogenous test results
3.5 穩健性檢驗分析
為了保證計量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進行三種穩健性檢驗。
1)更換實證模型。由于暫無與Bivariate Probit模型類似的雙變量回歸模型,故本文在此放松了社會資本在意愿和行為中擾動項相關的假定,從而利用Probit模型對其進行穩健性檢驗。由表5穩健性檢驗結果可知,放松擾動項相關的假定后,Probit模型回歸結果蘊含的經濟學含義與Bivariate Probit模型基準回歸結果具有一致性,即社會資本的豐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影響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融資行為,社會資本水平越高越豐富,農戶同時具有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融資行為的概率越高。

表5 穩健性檢驗結果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2)縮減樣本。對農戶總體回歸樣本上下縮減3%后再進行Bivariate Probit估計,回歸系數分別為0.282和0.257,估計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在系數大小、正負和顯著性方面未發生明顯變化。可見對回歸樣本縮減后所得到的估計結果與上文類似,說明本文實證結果較為穩健。
3)因子分析法。采用因子分析法重新計算社會資本綜合指標,進行穩健性檢驗。KMO統計量和Bartlett球形檢驗結果表明,KMO 統計量為 0.682,Bartlett球形檢驗的卡方值為480.006,P值小于0.001,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適合進行因子分析。根據各公因子得分以及方差貢獻率重新計算社會資本綜合指數,用來替代原有社會資本。將得出的社會資本綜合指標進行Bivariate Probit估計,結果表明,社會資本仍在1%的顯著水平下正向影響農戶融資意愿和融資行為,回歸系數分別為0.308和0.281,與表2結果基本保持一致,以上充分說明,本文的估計結果穩健,研究結論可靠。
4 進一步分析
4.1 影響機制檢驗分析
依據上述分析可知,社會資本可通過提高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認知水平,進而提升和促進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本文使用SPSS25.0統計軟件,運用基本Bootstrap再抽樣技術檢驗社會資本的顯著性,檢驗社會資本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的作用機制。對于農戶融資意愿來講,流程認知、積極度認知和政策認知的中介效應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這三個變量均具存在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分別為1.142、0.565和 0.628(表6),其中流程認知和政策認知的中介效應路徑中,社會資本對農戶融資意愿的直接效應不顯著,發揮的是完全中介效應,而在積極度認知的中介路徑中,社會資本對農戶融資意愿的直接效應顯著,直接效應為0.320,因此為部分中介效應。同樣,流程認知和政策認知在社會資本對農戶融資行為的影響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而積極度認知仍發揮部分中介作用。

表6 Bootstrap中介效應檢驗結果Table 6 Bootstrap mediation e§ect test results
結合已有研究,社會資本完全通過提高農戶對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的流程認知和政策認知進而對農戶融資意愿和行為產生影響的作用機制,體現了社會資本的信息傳遞效應。而為何積極度認知僅發揮部分中介作用,原因可能在于,流程認知和政策認知使得農戶能夠直接接觸到農業信用擔保的相關信息,社會資本可以完全通過促進農戶這兩項認知水平進而影響農戶融資意愿和行為,而積極度認知僅表明金融機構開展此項業務的積極程度,農戶基于該項認知并不能直接對農業信用擔保有過多了解,因此還需要社會資本的直接效應來提升和促進農戶的融資意愿和行為。
4.2 異質性分析
本文從農戶年齡、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角度出發,分組進行回歸,分析社會資本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影響的異質性。
將受訪農戶按照年齡分為60歲以下和60歲及以上兩個年齡組,60歲以下的農戶有424位,60歲及以上的農戶為242位,對兩組農戶分別進行Bivariate Probit回歸。結果表明,社會資本對60歲以下的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而對60歲及以上年齡組的農戶影響則不顯著(表7)。其原因可能在于,60歲以下的農戶承擔著養家糊口的重擔,更加需要資金投入生產經營,也更愿意承擔一定的風險去獲得貸款進行發展,因此在擁有一定社會資本的情況下會向金融機構申請農業信用擔保融資。而60歲以上的農戶多為在家接受贍養的老人,用到大筆款項的機會不多,不需要進行貸款,且該年齡組農戶本身思想較為保守,認為需要擔保品、抵押品或保證人的農業信用擔保風險較大,因此不愿意冒風險申請貸款。
根據受訪農戶實際受教育程度,將農戶分為高中以下和高中及以上兩組,高中以下的農戶有513位,高中及以上的農戶為153位。兩組農戶回歸結果表明,社會資本僅對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的農戶融資意愿和融資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顯著水平為1%,而對受教育程度為高中及以上的農戶融資意愿和融資行為影響不顯著(表7)。這可能是因為在農村地區,文化水平為高中及以上的農戶占比較少,并且這類農戶因自身受教育程度人力資本較高,積累財富和從事生產經營的能力較強,各類資本也較為豐富,依靠自身收入或資產便足以申請到農業信用擔保,因此社會資本對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的作用并不顯著。

表7 不同年齡、受教育程度組分析結果Table 7 Analysis results of groups with di§erent age and education levels
將農戶分為低收入水平、中等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三個組別,探討在不同收入水平下社會資本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行為的影響差異。低收入水平農戶有212位,中等收入水平農戶有236位,高收入水平為218位,收入分布較為均勻。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社會資本對低收入水平的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融資行為分別在5%和10%的置信水平下產生正向影響,對高收入水平的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在1%的置信水平下產生正向影響,而對中等收入水平的農戶融資意愿和融資行為影響均不顯著(表8)。可能的原因在于,低收入水平的農戶對資金需求更加強烈,但自身財富和資產積累程度不足,缺乏金融機構要求的抵質押物和擔保品,在面對可以采用保證擔保的方式進行貸款時,只能依靠無形的社會資本的替代效應滿足金融機構的要求。與Grootaert[34]認為社會資本是“窮人的資本”觀點一致。中等收入水平的農戶大多從事較為穩定且規模不大的產業,資金需求并不像低收入水平農戶那樣強烈,并且保守的風險意識使得這類農戶不愿承擔喪失抵押物或擔保品的風險,也不愿影響自身在社會網絡中的信譽,因此對于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參與程度均不高。高收入水平的農戶大多從事規模較大且存在一定風險的行業,進一步擴張經營規模使得該類農戶對資金需求尤為強烈,但是可能由于當地金融機構對風險的評級較為嚴格,因此即使有符合條件的抵質押物和擔保品,貸款可得性依舊不高。

表8 不同收入水平組分析結果Table 8 Analysis results of di§erent income groups
5 結論與對策建議
5.1 結論
研究表明,當前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農戶融資意愿向融資行為的轉化率較低,出現農戶具有融資意愿而并未實際參與融資行為的矛盾現象。農戶的銀行關系資本、村級關系資本越豐富,農戶獲得相關融資信息的渠道就越多,具備一定的第三方擔保資源,其同時具有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的概率就越高。社會資本能夠促進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向行為的轉化,減少融資意愿和行為之間的偏差,提高農業信用擔保政策的有效性。
進一步對社會資本影響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機制的分析表明,社會資本的信息傳遞效應能夠不斷提升農戶對農業信用擔保的流程、積極度和政策認知水平,進而使農戶充分了解相關信息,農戶可根據自身資金需求狀況決定是否進行農業信用擔保融資,從而影響其融資意愿和行為。除此之外,農戶的異質性使得社會資本對其融資意愿和行為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60歲以下的農戶由于生產經營的需要,使得這類農戶對資金需求更為強烈,社會資本對其融資意愿和行為的影響也更加明顯。并且對于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較低的農戶,自身其他資本的稀缺使得該類農戶更加依賴社會資本為其帶來的貸款可能性,因而社會資本的影響更加顯著。
當前,本文圍繞社會資本、認知水平與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展開剖析,但對農戶融資意愿和行為之間偏差的研究不夠深入,從農戶融資意愿到融資行為的過程較為復雜,影響二者之間偏差的因素和機制需從不同角度進行深入探討。因此,未來可以對影響農戶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意愿和行為之間偏差的因素和機制進行討論,不斷豐富當前研究成果。
5.2 對策建議
第一,政府應發揮組織者的角色,推動農戶參與“政銀農保擔”等多方聯動模式,加強農戶與各類金融機構的合作關系,豐富農戶的銀行關系資本。還可以通過成立農村經濟合作組織,舉辦多樣化的鄉村活動,鼓勵農戶積極參與村集體事務,拓展農戶人際關系網絡,深化農戶村級關系資本。
第二,政府、金融機構與村集體應加大對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的宣傳力度,提高農戶對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的政策認知和流程認知,充分發揮各類認知的中介作用,進而促進農戶參與農業信用擔保融資。具體可以通過完善農村信息公共服務設施,創建良好的合作溝通環境,構建農業信用擔保融資信息交流平臺。諸如利用網絡、知識講座、村集體會議等多種渠道定期與農戶溝通交流,尤其是關于利率、金額、擔保條件等具體信息。
第三,針對不同類型的農戶,政府和金融機構應根據農戶年齡、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對農戶制定差異化的農業信用擔保貸款政策和申請條件,特別是年齡處于60歲以下、受教育程度為高中以下和低收入水平的農戶,是金融機構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業務的重點服務對象,社會資本應成為該類農戶獲得貸款的重要倚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