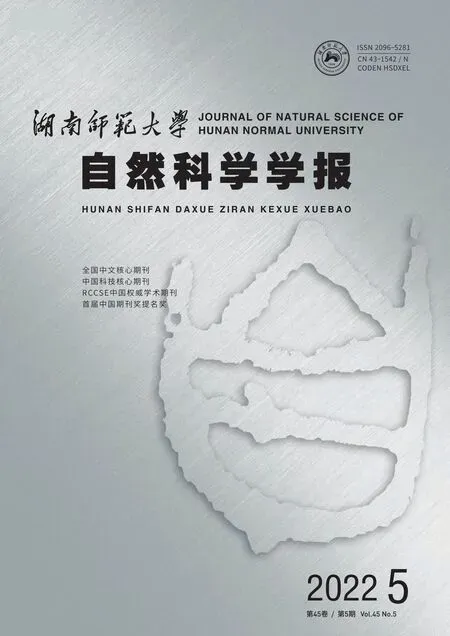中國縣域人口集聚時空演變特征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姜 菁,張曉青,王玉琳
(山東師范大學地理與環境學院,中國 濟南 250358)
人口集聚是指基于各種原因,在一定地理范圍內的部分甚至全部人口向該地理范圍內的一個或多個特定區域匯聚的現象[1]。人口集聚通過增加勞動力供給、改善人口的年齡結構、增加有效需求等為人口集聚區域帶來持續的經濟增長動力[2]。縣域是我國區域經濟的基本組成單元,是連接城鄉市場、吸納農業轉移人口、承接城市產業轉移的重要載體,同時也是構建完整內需體系、暢通國內循環的重點難點所在[3]。伴隨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邁向高質量發展,中國縣域發展越來越受到國家各級政府的重視,“十四五”規劃要求“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以促使更多人民群眾享有更高品質的城市生活。隨著中國人口發展形勢的重大變化[4],眾多縣域地區出現傳統產業聚集效應削弱、人口流失趨勢加重等問題。人口集聚程度是評判縣域地區競爭力和發展潛力的重要指標,面對新階段新問題,亟需探索縣域人口聚集的新動向新特點。此外,人口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同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關乎區域人口生活質量[5],經濟發展作為影響人口集聚的核心要素,分析經濟高質量發展背景下經濟集聚對縣域人口集聚的影響有利于合理規劃縣城建設,引導人口合理布局。目前關于人口集聚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成果頗豐,從研究尺度和區域上看,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國省域、市域[6]或者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7];近年來有關都市圈人口集聚的研究明顯增加,例如有學者對東京都市圈[8]、中國三大城市群[9]進行研究,同時由于“一帶一路”國家級頂層合作倡議的提出,“一帶一路”背景下西部地區[10]人口集聚的研究受到重視;還有學者對某一省份人口集聚現狀進行研究,主要集中于山西省[11]、廣東省[12]、云南省[13]、東北地區[14]等區域。在研究方法上,學者們普遍采用空間計量模型、PVAR模型、GMM模型、地理加權回歸和逐步多元回歸[15]等方法對經濟集聚與人口集聚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在研究數據方面,主要采用人口普查數據和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大部分學者認為經濟集聚對人口集聚具有正向的非線性促進作用,也有部分學者認為人口集聚與經濟集聚呈倒“U”型關系[16]。
通過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發現有關全國縣域尺度的人口集聚問題研究較少;且已有研究側重解析人口集聚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作用,較少關注經濟社會發展對人口集聚的影響機制;此外,中國各地區縣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其對人口集聚的影響力度同樣具有異質性,經濟集聚對各地區人口集聚的影響是非線性的,有必要引用門限變量進行分析。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中國縣級行政單元為研究對象,在對縣域人口集聚時空演變特征分析的基礎上,利用面板門檻回歸模型實證分析中國縣域經濟集聚對人口集聚的影響。考慮到地域差異和東北地區近年來人口大量遷出的問題,本研究進一步對四大經濟板塊的縣域經濟集聚與人口集聚的關系進行比較分析,以期為促進縣域經濟發展、吸引人口集聚以及制定合理人口政策等提供理論依據,從而促進縣域中小城鎮人口與經濟協調發展。
1 經濟發展對縣域人口聚集的影響機制分析
經濟集聚影響人口集聚的傳導機制是本文研究的重要理論基礎(圖1)。人口集聚本質是區域人口分布的空間差異問題,空間異質性是產生人口集聚的前提。在經濟發展初期,地區異質性導致區域發展差異,優勢區域形成中心區[17],中心區由于自然條件優越且經濟發展水平高吸引大量人口集聚。進一步講,人口集聚的核心問題是勞動力集聚,經濟發達地區對周邊欠發達地區勞動力具有顯著“極化”作用,勞動者為追求更高的工資和生活水平遷往臨近發達地區,勞動者的集聚促進地區經濟集聚,促使地區市場規模擴大,產業規模擴展,形成因果累積循環效應,集聚力越強,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所需勞動力數量越多,從而形成人口集聚區。從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的兩部門模型[18]中可以進一步分析經濟因素對勞動力遷移的影響: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結構中,同時存在著傳統落后的農業部門與現代發達的城市工業部門,由于兩部門勞動生產率與勞動邊際收益率存在差異引起農業剩余勞動力在產業間流動,即剩余勞動力普遍集聚于發達的城市工業部門從而使地區人口集聚。
具體分析經濟因素對人口集聚的影響,主要從產業集聚入手。從馬歇爾(1890)外部性理論中的勞動力池效應中可以得出,產業集聚引起人口集聚,人口集聚提高了本地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的匹配性,本地產業因為擁有了“一個穩定的技能市場”而獲得巨大收益,產業進一步集聚,產生更大的勞動力需求,進一步吸引勞動力,促進人口集聚。此外,以政府主導的“空間拓展→產業集聚→人口集聚”的發展邏輯,將產業、人口與空間布局有效地銜接起來[12]。從近代城市發展歷程來看,一個城市首先出現產業集聚,產業集聚提供就業機會,吸引工人做工居住,工人收入增加,進而家庭定居甚至進一步吸引親朋遷移導致“鏈式遷移”,人口開始呈聚集趨勢。勞動力增加可以帶動產業集聚,產業集聚使地區產值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增加,建設交通、學校、醫院等基礎設施,良好的生活和發展環境產生吸引人口遷入的拉力[19],吸引更多人口集聚成為人口集聚區。依據上述理論,本文進一步分析縣域人口集聚空間分布格局及其演變機制。

圖1 經濟發展對人口集聚的影響機制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研究區域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全國縣級行政單位作為基本研究單元,包括縣、縣級市、自治縣、旗、自治旗,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統計得到2019年中國縣級行政單位共有1862個。其中,2000—2019年間部分縣級行政單位進行了名稱或者范圍的調整,為方便統計分析,本文采用2019年的行政區劃對2019年以前的縣域名稱和范圍進行校正。數據來源于2000—2019年《中國縣域統計年鑒》,主要包括縣域戶籍人口數(萬人)、地區生產總值(億元)、行政區域面積(km2)、地均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萬元/km2)、地均居民儲蓄存款余額(萬元/km2)、地均普通中學生在校學生數(萬人/km2)、地均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萬元/km2)、地均第二產業增加值(萬元/km2)和地均第一產業增加值(萬元/km2)等指標,在構建面板數據時對部分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進行補充。
2.2 研究方法與變量描述
2.2.1 研究方法 采用劉睿文[1]的研究計算縣域經濟集中度和人口集中度,并利用2000—2019年中國縣域面板數據進行面板門檻回歸分析,具體分析過程如下:
1)經濟集中度和人口集中度
經濟集中度和人口集中度測量公式如下:
(1)
(2)
上式中:ec表示經濟集中度,Gi表示i地的地區生產總值(GDP),Gn表示全國GDP,Pi表示i地的戶籍人口數,Pn表示全國人口總數,Ai表示i地行政區劃面積,An表示全國行政區面積。
為進一步分析我國縣域人口聚集與經濟發展的空間分布一致性,利用蔣子龍[20]的研究計算縣域人口與GDP的不均衡指數。計算公式如下:
(3)
2)面板門限回歸模型
Hansen[21]提出的個體固定效應變截距面板門檻回歸模型的基本方程為
pc=αi+α2xit+β1qit(qit≤γ)+β2qit(qit>γ)+εit。
(4)
式(4)中:i表示地區,t表示年份,αi反映模型的個體固定效應,qit為門檻變量,γ為未知門檻,εit(0,δ2)為隨機擾動項,式(4)等價于:
(5)
該模型(5)實際上相當于一個分段函數模型,當qit≤γ時,xit的系數為β1;而當qit>γ時,xit的系數為β2。根據這一思想,假設存在“門檻效應”,在(5)的基礎上構建門檻模型,檢驗全國、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不同區域縣域經濟集中度對人口集中度的影響。因此,本文研究的門檻回歸模型設定如下:
pc=α1+α2xit+β1ecwhit(ecwhit≤γ1)+β2ecwhit(ecwhit>γ1)+εit,
(6)
pc=α1+α2xit+β1eceait(eceait≤γ2)+β2eceait(eceait>γ2)+εit,
(7)
pc=α1+α2xit+β1ececit(ececit≤γ3)+β2ececit(ececit>γ3)+εit,
(8)
pc=α1+α2xit+β1ecweit(ecweit≤γ4)+β2ecweit(ecweit>γ4)+εit,
(9)
pc=α1+α2xit+β1ecneit(ecneit≤γ5)+β2ecneit(ecneit>γ5)+εit。
(10)
式中:p為被解釋變量,xit表示控制變量,ecwh,ecea,ecec,ecwe和ecne分別表示全國、東、中、西和東北地區的縣域經濟集中度,γi為門限值。模型(6)、(7)、(8)、(9)、(10)依次表示全國、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門檻效應模型。
2.2.2 變量描述 本文按照式(2)計算所得的人口集中度作為被解釋變量;根據式(1)計算所得的經濟集中度作為核心解釋變量;為分析經濟集中度對人口集中度的門檻效應,將經濟集中度作為門檻變量構建模型。為進一步保證統計回歸的客觀性,本文在已有數據的基礎上選擇多個對人口集聚產生影響的變量作為控制變量,這些變量主要包括:①地均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該變量表示某地基礎設施發展水平。②地均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居民儲蓄是影響人口集聚的重要因素。③普通中學在校學生數,本文用該變量表示教育水平,教育水平高的地區更容易吸引家庭定居。④地均第二產業增加值表示地區工業發展水平,工業化是城市化的直接因素,在一定條件下工業化發展直接帶動城市人口集聚,為減小其數據波動,將其做取對數處理。⑤地均第一產業增加值,該變量表示地區農業發展水平,代指地區自然條件,自然條件是影響人口集聚的先決條件,優良的自然條件是人口集聚的重要因素。表1是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
3 中國縣域人口聚集在2000—2019年時空演變特征
3.1 縣域人口聚集的空間特征
本研究將2019年縣域人口集中度劃分為低人口集聚地區(pc≤0.5)、較低人口集聚地區(0.5 注:基于國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務平臺下載的審圖號為GS(2016)1579號的標準地圖制作,底圖無修改。 由表2可知,2000—2010年縣域人口集聚度增長率100%以上的地區有2個,2010—2019年人口集聚度增長率100%以上的縣域數量明顯增加,達到46個。2000—2010年與2010—2019年大部分縣域人口集聚度增減度分布于(0,30%]與(-10%,0]區間內,與2000—2010年相比,2010—2019年人口集中度增長率處于(0,30%]區間的縣域數量明顯減少,而(-10%,0]區間內縣域數量顯著增加。2000—2010年縣域人口集聚度減少30%以上的地區有6個,而2010—2019年達到69個,綜上所述,2000—2019年間中國縣域人口集聚度減少的縣域明顯增加,部分縣域出現人口集聚度急劇減少趨向。 表2 2000—2019年中縣域人口集聚度增減數量 圖3表示2000—2019年中國縣域人口集聚變化情況,其中圖3a表示2010與2000年中國縣域人口集中度差值的分布情況,從該圖中可以看出:2000—2010年中國縣域人口集中度減少的區域主要集中在東北地區的遼寧和吉林中部、山東半島地區、川渝地區和長江中下游沿岸地區,此外,人口集中度減少區域集中分布于各省中心城市周圍;中國北方人口集中度減少的縣域明顯多于南方地區;西部地區大部分縣域人口集中度均有所上升。圖3b表示2015與2010年中國縣域人口集中度差值分布狀況,與圖3a相比,2000—2015年人口集中度減少區域除東北和川渝地區之外還包括江蘇地區和廣東北部。圖3c表示2019與2015年中國縣域人口集中度差值分布,從圖中可以看出,與圖3b相比,縣域人口集中度減少的地區數量明顯增加,尤其是東北地區、長江流域和川渝地區縣域人口集中度明顯減少;西部地區人口集中度整體上仍然呈增加趨勢。綜上,中國縣域人口集中度減少的區域主要集中在東北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和川渝地區及廣東地區,同時呈現中心城市周邊縣域人口集中度普遍減少的分布特點,人口集中度增加的地區主要集中于西部和南方地區。以上中國縣域人口集中度的時空分布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人口集中的主要因素:由歷次人口普查數據可知,近年來由于東北地區產業結構老化,經濟發展活力不足導致人口大量外流;長江中下游和江蘇地區縣域人口大量流入上海等中心城市,川渝地區縣域人口流入廣東等地的趨勢顯著,中心城市對周邊縣域人口的“極化”作用顯著。得益于國家經濟發展支持政策和“一帶一路”經濟帶建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較快,勞動力需求增加,出現人口“回流”現象,人口集中度有所增加。地區經濟發展導致勞動力需求增加,在“極化”作用影響下,中心城市等經濟發達地區對周邊經濟欠發達地區人口的吸引增加,使人口集中分布于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區域。 注:基于國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務平臺下載的審圖號為GS(2016)1579號的標準地圖制作,底圖無修改。 本文通過統計分析可知2000—2010年人口集聚度和經濟集聚度均降低的縣域有403個,占總縣域數22.07%;兩者均增加的縣域有567個,占比31.05%;經濟集聚度增加而人口集聚度減少的縣域有400個,占比21.91%;經濟集聚度減少而人口集聚度增加的縣域有456個,占比24.97%。2010—2019年人口集聚度和經濟集聚度均降低的縣域明顯增加共635個,占比為35.30%;兩者均增加的縣域有359個,占比19.96%;經濟集聚度增加而人口集聚度減少的縣域有572個,占比31.80%;經濟集聚度減少而人口集聚度增加的縣域有233個,占比12.95%。綜上,中國縣域經濟集聚度與人口集聚度的增減趨勢具有一致性,但有相當部分縣域兩者增減情況相反,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經濟集聚與人口集聚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 為進一步明確中國縣域經濟發展與人口聚集的空間一致性,本文計算了全國縣域和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不均衡指數,2019年中國縣域經濟與人口的不均衡指數為0.000 481,數值低說明中國縣域經濟發展和人口聚集空間分布具有高度一致性;東部地區2019年不均衡指數為0.001 772,東北地區2019年不均衡指數為0.002 514,均高于中國中部和西部地區,同樣高于全國發展水平。其中東北地區在2000—2019年間不均衡指數呈現不斷下降趨勢,東部地區在2000—2010年間不均衡指數呈上升趨勢,而2010之后不均衡指數呈下降趨勢。中部和西部地區不均衡指數基本一致,明顯低于東部和東北地區且略高于全國水平,其中,中部地區2019年不均衡指數為0.000 992且2000年來中部地區不均衡水平一直呈不斷上升趨勢;西部地區2019年不均衡指數為0.000 990, 2000年以來不均衡水平呈現先升后降的發展趨勢。綜上,中國縣域經濟聚集與人口集聚空間分布具有高度一致性,但東部和東北地區縣域經濟集聚與人口集聚存在一定的不協調發展趨勢。 在進行實證分析前,為避免出現偽回歸,造成結果不準確以致得出錯誤的結論。首先,對所有解釋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表明,各解釋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均小于10,各解釋變量平均方差膨脹因子為2.30小于10,即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本文根據式(4)設定的模型對人口集聚中經濟集聚的非線性效應進行實證分析。首先對全國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在進行模型估計之前,首先進行門檻模型效應檢驗。根據前文的模型設計,以經濟集聚度作為門檻變量,運用Hansen(1999)提供的檢驗方法進行門檻效應檢驗,結果見表3。 表3 人口集聚中經濟集聚水平的門檻效應檢驗 表3的統計結果表明,經濟集聚對人口集聚的影響存在著雙門檻效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可得到基于全國縣域樣本的雙門檻估計值分別為6.186和10.503。求得門檻估計值之后,以經濟集聚度作為門檻變量進行門檻回歸分析,結果見表4。為了對比整體水平上經濟集中對人口集中度的影響,表4同時報告了線性個體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固定效應結果顯示,經濟集聚度對人口集聚度的影響系數為0.045,其對人口集聚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其余控制變量同樣對人口集聚存在正向促進作用。由表4可知,在全國縣域模型中,當經濟集中度小于6.186時,經濟集中度對人口集中度的影響系數為0.607;當經濟集中度大于6.186且小于10.503時,其對人口集中度的影響系數為0.374;當經濟集中度大于10.503時,經濟集中度對人口集中度的影響系數為0.199。總體來看,經濟集中對人口集中度具有正向效應,但該正向影響隨著經濟集中度的增加而減弱。 表4 基于全國樣本數據的門檻回歸結果 為進一步分析全國縣域經濟集中度對人口集中度的門檻效應,本文將經濟集聚水平高于10.503的縣域稱為高經濟集聚度分布區,經濟集中度大于6.186且小于10.503時為中經濟集聚度分布區,經濟集中度小于6.186為低經濟集聚度分布區。由統計可知,2019年高經濟集聚度分布區的縣域共28個,主要有南安市、昆山市、江陰市、晉江市和張家港市等縣域,集中分布于江蘇、浙江、山東等東部沿海地區;這一部分縣域對人口集聚的影響效應較弱,可能的原因是這部分縣域經濟發展起步早,經濟發展迅速,在過去發展過程中已經吸引大量人口集聚于此,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該部分縣域生活水平提高,房價上升,外來勞動力在該部分縣域定居成本高,對人口集聚的邊際效應減弱。2019年處于中經濟集中度分布區的縣域共33個,主要有丹陽市、海鹽縣、東山縣、臨夏市和海安縣等縣域地區,集中分布區是河北、湖南和山東等地,該部分縣域對人口集聚的影響力度高于高經濟集聚度縣域但低于低經濟集聚度縣域,可能的原因是這些地區相比高經濟集聚度縣域其經濟發展水平尚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房價較低但高于低經濟集聚度縣域,同時該部分縣域普遍具有較好的基礎設施以吸引人口集聚;從空間分布上看,中經濟集聚度縣域多分布于省級中心城市周邊,中心城市對其人口的“虹吸效應”也使該部分縣域對人口集聚的吸引力所有減少。2019年低經濟集聚度縣域數量為1764個,遠高于中、高經濟集聚度縣域數量,該部分縣域分布廣泛,說明中國大部分縣域經濟集聚度水平低,正處于經濟發展起步或快速發展階段,需要大量勞動力支持,且隨著農業發展水平的提高,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務工,該部分縣域是連接城鄉市場、吸納農業轉移人口、承接城市產業轉移的重要載體,對人口集聚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 為研究經濟集聚對人口集聚影響力的區域差異,將全國分為東、中、西和東北地區進行進一步分析。按照前文步驟,依次進行門檻效應檢驗、門檻值估計以及面板門檻回歸分析,得到的F統計量和p值結果如表5所示。當經濟集中度作為門檻變量時,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門檻模型均具有顯著的單一門檻效應,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門檻值依次為7.825,4.268,4.171和3.184。 表5 門檻效應檢驗結果 表6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顯示,中國東、中、西、東北四個經濟板塊經濟集聚對人口集聚均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其中經濟集聚對東部地區人口集聚影響力最小,影響系數為0.015,西部影響系數最大為0.150,中部和東北地區影響系數分別為0.086和0.051。面板門檻回歸模型顯示,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縣域經濟集聚對人口集聚的影響均具有顯著的門檻效應。當模型未跨越門檻值時,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經濟集聚對人口集聚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045,0.150,0.292和0.161,當跨越門檻值時影響系數依次為0.013,0.086,0.128和0.063,因此,中國四大經濟板塊經濟集中度對人口集中度的促進作用在突破門檻值后呈現出明顯的衰減效應。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數量整體高于中、西部地區,其在本身具有大量人口的前提下對人口的進一步接納能力有所減少。中西部地區地域廣闊但人口數量低于東部地區,具有較大的人口增長空間,其中中部地區大部分縣域處于經濟發展起步或快速發展階段,且近年來中部縣域吸納東部轉移產業數量增加,導致中部地區勞動力需求大,進一步促進人口集聚。西部地區由于普遍環境惡劣,人口數量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導致少數幾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縣域集聚了大量人口,且西部地區普遍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所以經濟集聚度對人口集聚的邊際效應明顯高于其他地區。由圖2可知,東北地區人口集聚水平普遍較低,人口集聚度高的縣域集中分布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中心城市周邊,但這些縣域在經濟集聚度跨越門檻值后對人口集聚的影響力大幅下降,主要是因為該部分地區城鎮化水平高但產業結構老化,致使其經濟地位下降,大量城鎮人口遷往東部沿海地區進一步引發“鏈式遷移”,導致該部分縣域對人口集聚的吸引力有所下降。當經濟集中度相對較低時其對縣域人口集聚具有重要影響,低經濟發展水平縣域要想吸引足夠人口集聚,仍然需要進一步提高經濟實力。 表6 分區域門檻估計模型 為了進一步說明結果的合理性,本文在原有模型變量的基礎上添加了地均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單位為萬元/km2,用lngio表示)進行穩健性檢驗,但由于該變量在2017—2019年《中國縣域統計年鑒》中并未統計,所以本研究構建了2000—2016年中國縣域面板數據進行面板門檻回歸,回歸結果如表7和表8所示。從表7的結果看,增加變量并縮短面板時間后經濟集中對人口集中度仍然具有正向效應,且該正向影響在跨越門檻值后同樣呈現衰減趨勢。表8的結果顯示東部、中部、西部以及東北地區縣域經濟集聚對人口集聚均呈現出明顯的門檻效應,且當模型跨越門檻值時,各模型的影響系數同樣呈現減小趨勢。這說明穩健性檢驗結果與前文回歸結果基本一致。 表7 更換變量后全國樣本數據的門檻回歸結果 表8 更換變量后的分區域門檻估計模型 本文通過計算縣域人口集中度和經濟集中度,分析中國縣域人口集聚的時空分布特征,并構建了2000—2019年縣域面板數據進行面板門檻回歸,實證分析經濟集聚對人口集聚的影響,具體分析結果如下: 從空間分布上看,2000—2019年中國縣域人口聚集并未發生根本性變化,仍然以胡煥庸線為界呈現東部聚集和西部稀疏的人口空間分布格局。西部地區地域廣闊但人口集中度低,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東部地區人口集中度普遍較高。從時間分布上看,中國縣域人口集中度減少的區域主要集中在東北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和川渝地區及廣東地區,人口集中度增加的地區主要集中于西部和南方地區,中心城市對周邊縣域人口具有較強的“極化”作用,經濟發展仍然是影響人口集聚的主要因素。通過計算不均衡指數可知中國縣域經濟聚集與人口集聚空間分布具有高度一致性,但東部和東北地區縣域經濟集聚與人口集聚呈現一定不協調趨勢。 由門檻回歸結果可知:經濟集聚對人口集聚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經濟集聚對人口集聚的影響具有顯著的門檻效應,當經濟集中度跨域門檻值時,經濟集中度對人口集中度的影響系數低于未跨越門檻系數。具體來看,全國縣域跨越經濟集中度門檻值的地區相對較少,集中于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西部地區經濟集聚對人口集聚的影響高于全國和東、中、東北地區。當經濟集中度相對較低時其對縣域人口集聚具有重要影響,中國大部分縣域地區仍然需要通過提高經濟實力以吸引人口集聚。 本文對人口集聚的空間格局分析和經濟集聚對人口集聚的面板門檻回歸實證分析結果與部分文獻的研究結果一致,經濟集聚對人口集聚具有重要促進作用。但由面板門檻模型實證分析可知,隨著縣域經濟集聚程度加深,其對人口集聚的影響力度有所降低,經濟集聚力度的進一步加深將有可能對人口集聚產生一定抑制作用。其次,由于中國縣級行政單元數量眾多,考慮到地區異質性,存在一部分經濟落后地區人口集聚程度過高而經濟發展難以支撐的現象,需要對這些地區進一步篩選以制定正確發展戰略。此外,由于面板數據本身存在一定內生性影響,可能導致回歸結果與真實情況存在一定誤差,且由于數據缺失,未能對全國縣域進行研究,隨著夜光數據與POI等大數據的廣泛應用,需要借助多元數據進行進一步分析。
3.2 縣域人口聚集的演變格局


3.3 中國縣域人口聚集與經濟集聚不均衡指數
4 基于門檻效應模型的中國縣域經濟發展對人口聚集的影響模擬
4.1 門檻效應分析


4.2 門檻效應的空間差異分析


4.3 穩健性檢驗


5 結論與討論
5.1 結論
5.2 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