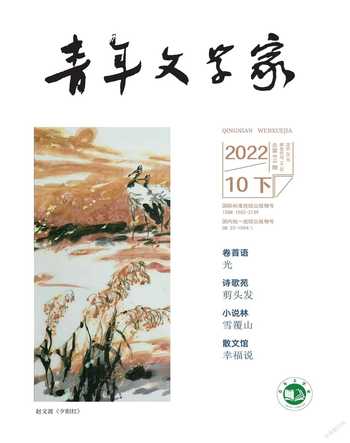論威廉·福克納小說的敘事特征
段海艷
威廉·福克納的小說因對敘事形式的專注而對現代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成為英美文學史上“礁石般鼎立的文學大師”。福克納的小說具有顯著的意識流特征,他的作品因復雜的結構形式和多重敘事視角的疊加而猶如一個景致豐富的“萬花筒”,具有超凡脫俗的敘事魅力。
一、多元復雜的結構形式
威廉·福克納對小說技法的革新決定了其拒絕以傳統敘事平鋪直敘的方式結構小說,他對小說外部形式的變革突出地表現在其小說復雜的敘事結構上。他著意在不同的篇目中實踐不同的小說結構形式,使其小說結構呈現出多元、復雜的敘事特征。
弗蘭克的空間敘事理論揭示了具有不同面的小說情節可以“并置性”地放置在文本中,只要它們統攝在共同的主題下,便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完整的整體。福克納在《喧嘩與躁動》中便進行了這種空間形式的敘事實驗,使小說呈現出了橘瓣式的敘事結構。小說以不同的敘事主體為依據,分為四個敘事單元,講述了不同敘事者的生活經驗及其帶來的心理體驗,然而他們看似迥異的講述都共同指向了康普生家族的發展歷史,因涉及公共的話題而有了統一的敘事指向。第一部分班吉的敘述是極為模糊的,完全以其意識流動為導向引領讀者了解這個家族的歷史。通過班吉的講述,我們得以知曉康普生家族衰落的現狀以及凱蒂的離去,并對其原因產生好奇。第二部分昆丁的敘述為我們揭開了康普生家族沒落的原因,不僅袒露了家族內部的各種分歧,還提示了外部社會環境的移置。讀者也能夠從其對凱蒂的追憶中逐漸拼湊出凱蒂遠走的動因,在滿足了對家族往事的探秘心理后,產生對康普生家族未來的好奇。于是,在第三部分福克納以杰生的敘事視角講述了其振興康普生家族的經歷,以及家族下一代人的成長故事,以接續性的敘述使家族故事具有完整的發展脈絡。第四部分的敘事者迪爾西則從“旁觀者”更為全知、客觀的角度講述了康普生家族的故事,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對前幾部分敘事情節的補充。四個敘事單元各自講述了不同的故事,任何敘事單元都是不完整的,然而它們統攝在共同的主題下,呈現出“發散且集中”的結構特征,恰如一個完整橘子的各個橘瓣,只有拼湊在一起才能構成完整的敘事內容。這種結構上“發散且集中”的特征使小說充滿了懸念,令讀者在閱讀接受的過程中不斷試圖拼湊出缺失的情節,從而產生了高度的閱讀期待。
而在《野棕櫚》中,福克納則形構了對位式的小說結構,讓小說的各個章節發生的背景在“野棕櫚”和“老人河”之間交叉著置換,形成了復調的結構特征。兩個交織并行的故事在初看時并無聯系,卻在逐漸深入的過程中使讀者覺察其主題層面的對比意義,引發讀者深刻的反思。“野棕櫚”講述了夏洛特與維爾伯恩充滿原始激情的愛情故事,他們忘情地追逐著理想化的愛情,不想以平淡的方式度過自己的人生。但是在短暫的激情退去后,他們卻因未能履行應盡的責任而感到羞愧,維爾伯恩更因此失去了成為醫生的機遇。與之相對的,“老人河”看似講述了與“野棕櫚”毫不相關的故事,卻從另一個角度證實了理性精神的可貴。高個子的囚犯面對洶涌而來的洪水時沒有選擇獨善其身,而是冒著被洪水沖走的危險拯救了懷孕女子的生命,并在嚴苛的條件下協助其順利生產。在默默地完成全部善舉后,高個子沒有選擇就此逃亡自由的世界,而是返歸監獄。他以可貴的理性作出了正確的抉擇,以對責任的承擔洗去了曾經的污點,呈現出了人格的高貴。兩個故事形成了有意味的對位式結構,激情與理性、失序與正序、瀆職與負責,接受者對于“理智與激情的沖突”這個命題的思索只有在對比閱讀中才能更加深刻。此外,在《押沙龍!押沙龍!》中,福克納則創造性地采用了倒置的“U”型結構展開小說敘事,以倒“U”型的曲線反映了主人公薩德本起伏跌宕的生命軌跡,使小說的結構形式與人物的命運達成完美的和諧;《八月之光》則采取了嵌套式的敘事結構,在莉娜尋找盧卡斯的主線故事之中嵌套了花樣繁多的輔線故事,使女主人公單調的尋找之旅變得豐富復雜,讓小說成為展覽世相、觀照眾生的舞臺,同時也使得敘事的節奏由平鋪直敘變得波瀾叢生。
敘事結構的復雜令福克納的敘事呈現了多元化的特征,使讀者能夠在文學接受的過程中獲得內容之外的形式美感。同時,其小說的結構與主題之間存在內部的呼應,達成了形式與內容的和諧之境。
二、動態流動的心理時間
威廉·福克納對內在心理的關注使其小說具有顯著的意識流特質,人的意識流動與客觀的現實時間之間并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他認為客觀物理時間的線性發展決定了時間具有當下性,而人的意識與心理卻可以將過去、當下和未來統攝在同一時空中,人的時間感知取決于主體的心理體驗,因而人的心理時間較之于客觀的物理時間更加具有權威性。這種獨特的時間觀讓福克納小說中的敘事時間經常處于“失序”的狀態,情節自然發展的時間狀態,也即“故事時間”經常為敘事文本的時間狀態,也即“敘事時間”打亂,使讀者必須在文學接受的過程中不斷依靠自己的判斷重新整理、建立情節的發展秩序,從而獲得延宕性的審美體驗。
福克納小說的敘事時間常呈現出隨著主體內在心理與思維的轉變而流動的特質,如《押沙龍!押沙龍!》中敘事時間的流動便呈現出顯著的心理特質:“一位先生注視著舞池中舞動著的舞者,她的裙擺帶起一個利落的旋轉,如水的發絲弧形地傾瀉在半空,于是三年前的夜晚搖曳著浮動在眼前。”敘事時間的切換完全不合乎物理時間的邏輯,僅僅依憑主人公心理的轉換而由當下的敘事時間流轉到過去的敘事時間,小說的敘事場景也隨之而立即切換。這種變動不居的敘事時間呈現出強烈的意識流特征,往往通過感覺器官為中間媒介加以實現。而在《喧嘩與躁動》中,這種心理化的敘事時間被表述得更為具象,在以班吉為主體的講述中,敘事時間變得極為模糊,極具流動性的特征,他完全是依憑自己感官體驗與情緒流動進行敘事。在接觸到外部潮濕的空氣后,他腦海中時而浮現出康普生家的老宅“外墻上濕漉的苔蘚與室內稀薄的光線”,宅邸的年久失修揭示出康普生家族沒落的處境。他時而又懷念起凱蒂身上“清新的樹木的氣味”,并因為無法嗅聞到這種氣味而滾地哭叫,味道的消散暗示著凱蒂已經離開家族遠去的現狀。小說中的敘事時間完全沒有遵循客觀的時間秩序,而是在過去與當下之間反復跳蕩,在有限的時空中串聯起了豐富的敘事內容,顯示出心理化的敘事時間具有的敘事潛能。
同時,現代先鋒性的敘事技法使福克納小說中對敘事時間的表述充滿了象征性,“鐘表”無疑是福克納小說中重要的時間象喻。它與現實的物理時間保持著高度的同步性,可以被視為傳統的線性發展時間的象征。例如,《獻給艾米麗的玫瑰花》中,南方貴族小姐艾米麗身上總是攜帶著一只“精巧的金色懷表”,鐘表古舊精致的外部造型象征著艾米麗沒落的南方貴族小姐的身份,表征著南方的黃金時代已經隨著工業文明的勃興而逐漸遠去了。且艾米麗經常忽視鐘表的存在,任由其“落入衣服的褶皺間”而不去理會。主人公對鐘表的忽視象征著其對客觀自然時間的隱性拒斥,艾米麗不愿認同南方社會的經濟結構業已發生內部的質變,她的思想深處盤桓著對過去的深刻眷戀,因而只能以擱置鐘表的形式拒絕進入現在的時空。這種時間的象征意義也揭示了福克納對心理時間的認同,人類可以憑借自己的主觀意識調節自身對時間的體驗,從而掙脫時間線性發展的規律的束縛抵達自由的境地。而《喧嘩與躁動》中的“鐘表”也同樣具有深刻的時間象征意義,主人公昆丁打碎了那只“從祖父那里繼承來的,由父親傳下來的手表”,將“兩只指針從表盤上拔下來”。然而,被損壞的鐘表依舊沒有停止運轉,“清脆而急促的嘀嗒聲”依舊從鐘表的內部傳來。昆丁打碎鐘表的行為象征著其希望阻斷物理時間流逝的心理意向,康普生家族的榮譽在日漸稀薄,而身為長子的昆丁卻無力帶領家族恢復往日的輝煌,只能借由打斷鐘表的時間指向的方式希冀延緩這個過程。但鐘表依舊嘀嗒作響,揭示著昆丁在心理層面對時間的意識仍舊清晰,他內在心理時間的流動并不因失去了對物理時間的有效認知而停止,隨之也就無法釋懷自己內心因責任感而帶來的緊張。
敘事時間的流動使福克納的小說顛覆了傳統線性時間的發展秩序,呈現出一種新的時間哲學。心理化的敘事時間帶給了小說敘事以極大的自由,使小說突破了文本篇幅的限制,可以包涵豐富的敘事內容。
三、多重變幻的敘事視角
威廉·福克納小說的敘事視角呈現出多重變幻的特質,他的小說往往不會從單一的角度進行故事的講述,而是通過變幻的敘事視角敞開情節的豐富可能,以敘事視角的變幻制造多樣的敘事效果。同時,福克納常常在小說中引入特殊敘事主體的視角,以偏離常規的敘事視角制造陌生化的審美效果。
福克納認為“現實具有駁雜的細節,因而從不同的角度觀瞻會呈現多義性的效果”(李文俊《福克納評論集》),因而他的小說常常采取多視角的敘述方式,力圖從不同的視角對現實本相加以表述。在《押沙龍!押沙龍!》中,福克納在講述薩德本的人生軌跡時采取了四重敘事視角疊加的敘事策略,令身份各異、立場不同的敘述者共同還原主人公薩德本的形象。羅莎小姐視角下的薩德本無疑是個“脾性暴躁且自私自利”的“外來者”,薩德本與自己的姐姐埃倫成婚卻并未帶給姐姐幸福,她認為薩德本只是因為想要融入小鎮才締結了這樁婚事。康普生先生視角下的薩德本卻是個“理想化的進取者”形象,他赤手空拳地在陌生的土地上開辟了“百里地”的莊園,親自和工人們一起投入勞動且從不輕易斥責他們。他機警而冷靜地化解了小鎮人對他的各種刁難,最終成功地在約克納帕塔法縣落地生根。昆丁視角下的薩德本最為復雜,因敘述者本人對南方傳統“愛恨交織”的特殊情結,因而昆丁視角下的薩德本既是“父輩輝煌歷史的象征”,又是缺少道德規制的“不擇手段的開拓者”,具有雙重的面向。而施禮夫視角下的敘事則更加具有不可靠性,因為他全然是通過他人的話語來對薩德本的形象進行推測的,其間還夾雜著他自己的虛構與再創作,這種間接性的想象建構根本無法還原人物薩德本的真實面目。敘事者通過多重視角形塑薩德本的人物形象,然而讀者發現多重敘事視角并未讓薩德本的形象變得清晰,反而因敘事者各自立場的矛盾而變得駁雜難辨。多重變幻的敘事視角使薩德本變成了“迷宮式”的人物,因其形象的多義性而富有藝術的魅力。
與此同時,福克納的小說常出現特殊的敘事視角,如兒童的敘事視角等。特殊的敘事視角往往能夠看到與常人不同的風景,兒童角度的敘事同成人的隱含視角構成了小說中的“復調”,在互照間帶來陌生化的驚異性審美體驗。例如,《清晨的追逐》中,福克納以兒童的視角講述了一次清晨的獵鹿之旅,以兒童為主體的視角帶有不諳世事的天真,當他們觀照自然生命時總能覺察其中的詩意:“河邊潮濕的霧氣像棉花般柔軟,堆疊在幽深的水面上,安靜地好像溫馨的睡床……森林在等待著太陽的出現,使它們在金色的光暈中沐浴,驅散夜晚的惺忪。”自然景物在兒童的視角下被賦予了擬人化的特質,具有成人視角下不曾得見的勃勃生機,兩種視角的對照令讀者獲得了更細膩的感受。而當那頭雄壯的公鹿出現時,獵手歐內斯特先生視角下的鹿是“尋覓已久的大家伙”,而兒童視角下的鹿則“頂著巨大的,如樹杈般的棕色鹿角,陽光將它鍍成了金紅色,我們的喧擾弄驚了它”。成人視角下的公鹿是等待狩獵的獵物,而兒童視角下的鹿卻是森林中的自然生靈,它那雄偉的外表象征著自然造化的神奇,金紅色的公鹿無疑具有某種自然的靈性或神性,而只有兒童的視角才能與自然建立如此親近的關系。
敘事視角的多重變幻使福克納的小說突破了單一性的敘事效果,帶給讀者層次豐富的閱讀體驗。視角的切換與比照使小說敘事更具有開放性,也揭示了現實世界的豐富多彩。
福克納在小說表現形式上的創新令其小說具有濃厚的個人化特質,多變的結構形式和變幻的敘事視角呈現出了現代文學的先鋒特質,其心理化的敘事時間更帶有意識流小說的突出特征,折射出作家獨特的時間哲學與對人的認知的思索。我們可以說,福克納的小說的表現形式與思想主題達成了有機統一,在手法與內容的契合間獲得了令人矚目的藝術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