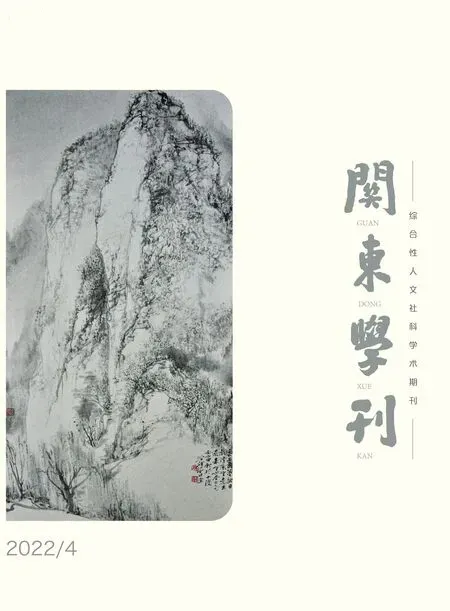清末民初文學中的疾病與診療敘事
曹曉華
清末民初文學對各種“病癥”和醫治過程的鋪陳與描繪,成為動蕩年代特殊的文字“診療”。對此,學界的相關研究大致按兩條線索展開:一是圍繞“疾病”隱喻的修辭分析,包括對醫療題材、醫者形象以及相關作品敘事手法的討論,常借用福柯“生命政治”和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的理論視域;二是將相關作品中的疾病與診療敘事視為尚在進行中的現代性表征,將其提升至醫療話語層面做進一步的探討。
實際上,創作者對疾病的“再發現”不僅是一種文學修辭或文學表征,還關聯著中西醫的攻守進退,其中隱含著探尋國族“富強”的不同路徑,是考察清末民初文學的另一種視角。包括醫界小說在內的文學創作對國民個體到國族群體的“病”“癥”剖析,除了從具體到抽象的文本“診療”行為之外,作為醫文互通傳統的延伸,還折射出中西醫對話的早期語境。在進化論和優生學的交替影響下,國人對“療救”的反思投射在了更多“個人/集體”的文學文本對峙中。本文將在文學史和醫療史的雙重視角中,解讀清末民初作品中的“病”“癥”二分對疾病的“再發現”乃至“富國強種”敘事的由來。
一、“病”與“癥”的文學“診斷”
五四運動前夕,魯迅筆下的華小栓,吃完了人血饅頭。不久,華家的茶館熱鬧起來,滿臉橫肉的康大叔,也到店鋪里來邀功了——“包好,包好!這樣的趁熱吃下。這樣的人血饅頭,什么癆病都包好!”面對康大叔的嚷嚷,華大媽“聽到‘癆病’這兩個字,變了一點臉色,似乎有些不高興;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訕著走開了”。(1)魯迅:《藥》,《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468頁。《藥》中的華小栓滿頭大汗,咳嗽不止,瘦得脫了形。《黃帝內經》所謂“咳,脫形,身熱,脈小以疾”,(2)郝易整理:《靈樞 玉版第六十》,《黃帝內經》,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31頁。是中醫認為的肺癆之癥,五逆之一。但在病癥如此明顯的情況下,華大媽依然對康大叔這樣公開嚷出“肺癆”兩字而心生不滿。
《藥》在《新青年》發表,正值五四運動爆發。華大媽對康大叔的不滿,是辛亥革命前后直至五四運動前夕中國普通民眾對疾病和診療認知的縮影。《藥》作為恰好在“五四”時間節點上的創作,不僅是魯迅個人創作生涯中的重要作品,與清末以來的文學景觀和社會心理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可借以考察中西醫“病”“癥”話語如何影響現代文學的發生。
解讀小說《藥》,自然要提到棄醫從文的魯迅從關注肉體病痛轉向“精神的療救”,他從社會痼疾的“橫截面”中挖掘出國民性的病根。1903年,赴日不久的魯迅應許壽裳的稿約在《浙江潮》上發表了歷史小說《斯巴達之魂》,講述了一位斯巴達婦女因為丈夫茍且偷生沒有和三百戰友戰死沙場而自刎的故事。此時的魯迅,還是在弘文書院學習日文的青年,尚未正式學醫。此時正值拒俄運動,小說中斯巴達勇士三百人戰波斯三百萬敵軍,最后全軍壯烈犧牲,文字間以命相搏的強力和勇氣背后是愛國青年魯迅的赤誠之心。《斯巴達之魂》受梁啟超1902年發表在《新民叢報》的《斯巴達小志》影響,(3)魯迅《斯巴達之魂》與梁啟超《斯巴達小志》之間的關聯,參見高旭東:《魯迅:從〈斯巴達之魂〉到民族之魂——〈斯巴達之魂〉的命意、文體及注釋研究》,《文學評論》2015年第5期。而此時的梁啟超已開始倡導國人體育,中國學人對西人所謂“東亞病夫”的反思從政體弊端的探討逐漸延伸到提升國人身體機能的討論。(4)近代學人對“東亞病夫”的認識,經歷了從提升“國力”到提升“族力”的轉變,參見楊瑞松:《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005年第23期。1896年10月17日的《字林西報》,轉載了外報評論《中國現狀》(The Condition of China),同年末《時務報》登載了該文的中譯版,“夫中國——東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5)張坤德:《英文報譯中國實情》,《時務報》1896年第10期。事實上外刊的原文著重對無能的清政府進行抨擊,并沒有涉及具體中國人的身體素質。然而在當時學人的解讀和翻譯中,“東方之病夫”承載了國人病痛和政治之弊的雙重重負。以斯巴達人的尚武精神注入國民教育的想法,可視為對“東方之病夫”的回應,帶著革命理想化的色彩。然而魯迅后來也發現這劑梁啟超認為的“良藥”,并不對“癥”——“現在看起來,自己也不免耳朵發熱”,但他依然留下了這學醫前的舊作——“我慚愧我的少年之作,卻并不后悔,甚而至于還有些愛,這真好像是‘乳犢不怕虎’,亂攻一通,雖然無謀,但自有天真存在”。(6)魯迅:《集外集序言》,《魯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4頁。可以想象學醫期間的幻燈片事件,對帶著“無謀”的“天真”的魯迅,造成了何種強烈的戰栗和震動。但即便“棄醫從文”,魯迅個人對疾病的體驗和感知融進了學醫生涯積累的專業知識,又與他對中國社會的觀察相結合,滲透進長期的文學實踐中。魯迅對國民性的“診療”,逐漸褪去了《斯巴達之魂》那樣一往無前的豪邁熱切,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深思熟慮后沉重又銳利的筆風。
《藥》中的“診療”過程,首先對應的是公開的疾病“命名”行為。華大媽抗拒康大叔將華小栓的病“確診”為“肺癆”,即便她和丈夫還是在按照治療“癆病”的偏方給小栓尋藥。對疾病的命名意味著確診,在此之前卻是折磨病患的藥方試探。現實中,魯迅的父親至死也沒有被中醫診斷出明確的疾病,而成年后的魯迅對那些奇怪的藥引還記憶猶新,從河邊現掘的蘆根到經霜三年的甘蔗,從原配的蟋蟀到老弗大,然后便是那陳年破鼓皮做成的“敗鼓皮丸”,但是對于一日日水腫起來的父親都沒效果,黔驢技窮的大夫暗示沒有找到前世的“冤愆”。(7)魯迅:《父親的病》,《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95-296頁。和華小栓抑制不住的咳嗽一樣,魯迅父親的病也只有日益嚴重的水腫和喘氣,對于病癥發作和病人受苦的情形,魯迅著墨甚多。有關病痛的細節越來越豐富,但疾病的診斷卻一直懸而未決,這種文本中的延宕也體現出魯迅對傳統醫方的懷疑,進而開始思索具體疾病以外的病因。無論是人血饅頭的偏方和中醫開的藥方,都只是對“癥”下藥,對于病因的追索只停留在應對季節“以氣感氣”的“六氣”“六化”,再進一步便是“冤愆”,玄論中沒有半點病菌的影子。傳統中醫缺乏實證也給華大媽對兒子疾病的幻想留了可乘之機,這在早期的魯迅看來,是老大中國“瞞”和“騙”的又一重要證據。如果我們繼續將視線轉向中西醫剛開始“交鋒”時的“病”“癥”二分,還可以給清末民初文學的疾病和診療敘事添加另外的解讀線索。
比較中西醫的診療模式,中醫著重的是病癥和發病過程,而西醫著重的是引起病癥的本源,與西方現代醫學發現的細菌、病毒、寄生蟲等不同,中醫眼中的病癥因人而異,而藥方也各不相同。傾聽病人的訴說,依照不同體質下藥,這本是中醫的優勢和特長,但這種特長在西醫東漸中受到挑戰。“病”“癥”二分首先給清末民初醫學名詞的翻譯審定帶來了麻煩,高似蘭等人“醫務傳道”時便發現了“病”與“癥”的矛盾。1908年,高似蘭編撰的《高氏醫學辭匯》(Cousland’s Medical Lexicon:an English-Chinese Lexicon of Medical Terms)出版,這是經過名詞委員會認定的成果。在出版說明中,高似蘭特別提到了合信編纂并在1858年出版的《醫學英華字釋》(A Medical Vocabulary in English and Chinese),合信在書中列舉的1829個醫學條目,經過管嗣復的幫助,試圖將西醫理念與古雅的中國文言結合起來。(8)孫琢:《近代醫學術語的創立——以合信及其〈醫學英華字釋〉為中心》,《自然科學史研究》2010年第4期。而高似蘭和博醫會名詞委員會的同仁,延續了合信中西兼采的翻譯方式。在1908年初版的《高氏醫學辭匯》(時名《醫學辭匯:漢英對照》)的凡例中,高似蘭試圖對disease的內涵進行說明,“‘病’與‘癥’的區別很隨意,前者是所有疾病的泛稱,既可以是具體的疾病也可以是疾病的癥狀;后者則僅限于具體的疾病,比如腹水(ascites)是‘病’,天花(small-pox)是‘癥’”。(9)P.B.Cousland:《醫學辭匯:漢英對照》,上海:中國博醫會,1908年。但是高似蘭在1930年第五、六版的辭匯序言中承認,編纂辭典時為了方便起見,將“病”“癥”二者區分開來,“‘病’指的是明確的疾病,而‘癥’指的是癥狀,但實際上二者很難區分”。(10)P.B.Cousland,“Extracts from Prefaces to Fifth and Sixth Editions”,魯德馨、孟合理編:A Cousland’s Medical Lexicon(Ninth Editon),中華醫學會出版委員會,1939年。在西方醫學定義的“疾病”進入中國之前,中醫對各類疾病已經有了相應的指稱,并有關于病癥的描述性語句。事實上對于某一種疾病的命名,在一開始只是圍繞這種疾病的發病癥狀,對于引起這種疾病的病原(如細菌或者病毒)缺乏科學的甄別,這意味著高似蘭等人進行術語翻譯時必須進行中西結合的考辯。吳章(Bridie J.Andrews)分析肺結核與細菌學說在晚清民國時期的在地化時,指出在細菌學說流行起來之前,包括合信在內的傳教士在翻譯“肺結核”時依然沿用中醫的指稱——“癆”,一個來自于“傳尸癆”與“癆蟲”的詞。(11)吳章:《肺結核與細菌學說在中國的在地化(1895-1937)》,余新忠、杜麗紅編:《醫療、社會與文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24-229頁。
高似蘭等人的困境部分來自中醫中說不清、道不明的玄學部分,這種不同于西醫通過實證確診病因的診療過程,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解釋部分國人價值觀念的遲滯。隨著西醫抗菌體系的成型和東傳,1910年已有報紙登載“衛生歌”:“肺不運動葉漸縮,細菌寄生肺癆伏;肺若運動葉舒張,細菌祛除空氣足”,(12)佚名:《肺之養生歌》,《女學生》1910年第20期。雖有“細菌”的概念,但依然使用“肺癆”之名。而魯迅筆下受看不見的“癆蟲”侵擾的華小栓一家,還沒有結核菌的概念,華大媽對“癆病”二字的排斥,也并非對疾病有自己的見解,而是一種“自欺欺人”,似乎只要病名不定,無論現時“癥狀”幾何,華小栓吃下去的人血饅頭定能帶來病愈的希望,而這種“確診”的“延宕”帶來的“治愈”“虛妄”還不如魯迅所說的“絕望”。(13)魯迅:《希望》,《魯迅全集》第二卷,第182頁。小說結尾處,在夏瑜的墳前,夏瑜母親對害死兒子的人發出詛咒,希望烏鴉飛上墳頂“顯靈”,魯迅讓夏瑜母親的“希望”落了空,而華大媽“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擔”。(14)魯迅:《藥》,《魯迅全集》第一卷,第472頁。華大媽一定是慶幸老天沒有“顯靈”,使這惡毒的詛咒無處應驗。其實她此時卸下重擔的心態,如同當時對康大叔嚷出“癆病”不高興一樣,似乎只要不點破、不說破、不顯靈,一切可安之若素,可見無論是兒子的死還是夏瑜的死,都未能真正推動華大媽對革命的觀念產生變化。
圍繞“人血饅頭”展現出的形形色色的“癥”,華小栓突起如八字的肩胛骨印出“吃人社會”馴化出的麻木和愚昧,在魯迅眼中就是那個經過實證和臨床觀察發現的侵蝕國人精神的病菌。通過魯迅留日期間的醫學筆記可以了解到他系統學習過《解剖學》《血管學》《組織學》《有機化學》《五官學》《病變學》等課程。(15)楊燕麗:《關于魯迅的“醫學筆記”》,《魯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1期。早在1899年,還在礦務學堂的魯迅已經接觸到了一些基本的西醫知識,“在這學堂里,我才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并不教,但我們卻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于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于西方醫學的事實。”(16)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一卷,第438頁。回看魯迅追索國人精神痼疾的過程,從呈現傳統中醫辨證的各種“癥”入手,最后在民族的比較間找出了國民蒙昧麻木的“病因”,其中析微察異、剖析病情的思路,又偏重于西醫觀照下的“病”和引起“病”的“菌體”。
二、“疾病”的文學“發現”
魯迅文學創作中的“疾病”和“診療”并非孤例,中國文壇素有“醫文互通”的傳統。借著顯微鏡,清末民初作家重新發現了“病態”與“病體”。劉鶚、陸士諤、郁聞堯等人的作品,通過主人公行醫的過程揭示社會的頑疾。柄谷行人在分析日本前現代文學時,曾經提出一種“風景的發現”,也就是“發現”原本并不存在的事物,并使之成為不證自明的存在。(17)[日]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9-12頁。這種認識論上的“顛倒”也可以在清末民初文學的疾病敘事中發現,在中西醫療觀念的碰撞中,創作者“發現”了新的“風景”。清末一則筆記小說,寫一醫者自警,墻上掛了一幅圖,圖中除了搗藥老翁,還有一只突兀的狐貍,觀者看了題跋才知道,只因狐貍“善假且譎,而當時之醫專喜偷竊古人陳說,用以欺人,毫無新穎知識,齷齪險詐,其去狐也幾希”。(18)佚名:《狐耶醫耶》,《醫藥學報》1909年第1期。觀者一開始不解其意,看了題跋后恍然大悟,明白了狐貍和庸醫之間的相通之處。文學中的疾病“發現”和“診治”,常開始于“正本清源”的精神自救(暗示這不是“真正的”中醫),但隨著“疾病”嚴重程度的揭露,縱使真正的行醫高人也“黔驢技窮”,這其中又透露著作者的無奈。
劉鶚《老殘游記》中的老殘,未能走科舉之路,而是和道士學了幾個行醫口訣,做了云游四方的江湖郎中。出身醫學世家的劉鶚,在小說中展示了豐富的中醫診療細節,小說第三回便寫了他如何醫喉疾:“這病本不甚重,原起只是一點火氣,被醫家用苦寒藥一逼,火不得發,兼之平常肝氣易動,抑郁而成。目下只須吃兩劑辛涼發散藥就好了。”(19)劉鶚:《老殘游記》,長沙:岳麓書社,2014年,第15頁。老殘開了“加味甘桔湯”藥方,治好了高老爺的小妾,但劉鶚在小說中詳細開出的藥方,卻只是導向社會病態的藥引。引藥歸經,老殘的醫術經過高老爺的宣傳,很快人盡皆知,不久他便上了高檔的宴席,就在宴席上,曹州知府玉賢的故事傳了出來。在這個“清官”的治理下,曹州不僅沒有了強盜,百姓也“路不拾遺”,玉賢由此還得到了嘉獎。然而他的政績只是不問黑白、濫施酷刑的結果,曹州的匪患看似已平,實際老百姓卻迎來了更大的禍患,即“清官誤國”。老殘的藥方引出了更加嚴重的國禍,玉賢并未將曹州“治”好,政績掩蓋下的暴虐和酷烈,在江湖郎中眼里也成了害人害國的“重癥”——“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則一府傷,撫一省則一省殘,宰天下則天下死!由此看來,請教還是有才的做官害大,還是無才的做官害大呢?倘若他也像我,搖蚌串鈴子混混,正經病,人家不要他治;些小病痛,也死不了人。即使他一年醫死一個,歷一萬年,還抵不上他一任曹州府害的人數呢!”(20)劉鶚:《老殘游記》,第38頁。舊疾新病,滿目瘡痍,劉鶚在給黃葆年的信中寫到,“弟固未嘗知天,弟固未嘗不信天。惟其不能知天,故竟以天下為己任。天下之安危,匹夫與有責焉。今日國之大病,在民失其養。”(21)劉德隆、朱禧、劉德平:《劉鶚及老殘游記資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0頁。因為興辦實業而受到太谷學派同仁壓力的劉鶚,向當時的學派領袖表明心志,《老殘游記》中“抱殘守缺”的殘棋隱喻,不僅是老殘的名號由來,還埋有扭轉殘局、治療“國族之病”的“暗線”。
如果說《老殘游記》類似一部失敗醫案的合集,那么頗具影響力的“醫學小說”《醫界鏡》就是一部“醫場現形記”。該作可視為奇方異術和黑幕小說的結合體,于1908年出版,署名“儒林醫隱”,正是作者郁聞堯根據自己在1906年出版的舊作《醫界現形記》改編重印的。“醫界鏡”,取的是傳統小說中常見的“照妖鏡”比喻,對晚清醫界進行了全景式的描繪。就小說的創作來看,無外乎才子佳人、官場黑幕、房中秘術的雜糅,貝氏父子行醫經歷看似貫穿期間,實際上還是各種醫界形象的堆砌。《醫界鏡》將華洋雜處時國人對中西醫的態度,以及部分學人意識到的中西醫優劣進行了較為完整的呈現。小說中的中醫,多是借迷信或是借西醫畫皮招搖撞騙,偶有一兩個真正精通醫道的中醫,儼然是不可多得的清流。小說發現的“疾病”,與其說是書中錄入的各種疑難雜癥,不如說是人心浮蕩加上時運不濟導致的中國傳統醫道和醫術的崩壞,作者接著又從這種崩壞反思中醫的劣勢。作者借書中人物之口道出,“茍能采取西法,洞明全體,習化學而明西藥,知其然且明其所以然,官為考取,設局施醫,從此精益求精,將至于完全不難也”。(22)儒林醫隱:《醫界鏡》,嘉興:同源祥書莊,1908年,第171頁。小說一方面用了諸如“微生物”、“養氣”之類的舶來術語,但另一方面,因果報應不爽的敘事討論又無時無刻不提醒著讀者,即便有科學的術語,若是沒有科學思想的啟蒙,也只能發現個體之病,羅列醫界亂象并不能深入到國族之病的根本。《醫界鏡》的序言中提到,“爰作《醫界鏡》四卷,俾平人閱之可預先稔知醫生之高下,一旦有病或不為庸庸者所誤;醫家閱之可以警惕深造而勉為良醫,而與衛生之道尤時時致意焉”。(23)儒林醫隱:《序·醫界鏡》,第1頁。小說就像是嬉笑怒罵的“打假指南”,庸醫橫行,丑態畢現,但隱藏在游戲文章之中的作者態度隱而不顯。前半部分的主人公貝仲英用燭油和身上污垢和成“濁垢丸”,因為前世福佑歪打正著治好了趙家公子,而趙家老爺精曉“衛生之道”,竟然也并未對療法有任何懷疑。其中敘事,舊疾依舊,但診療之法新舊摻雜。由此可見,郁聞堯雖然對庸醫極盡諷刺之能事,但對傳統中醫未曾有過懷疑,他只是希望通過對“庸醫”的“發現”,喚起醫生和病家的警惕,遏制中醫界的亂象。這也不難理解《醫界鏡》一度被認為出自陸士諤之手。民國期間廢止中醫案中力主中醫的陸士諤,曾著有《寒魔自述記》《環游人身記》等醫界小說。《寒魔自述記》和《環游人身記》連載于《金剛鉆》報紙上,都用擬人化的手法展開敘述。(24)《寒魔自述記》見《金剛鉆》1924年4月14、21、24日三期,《環游人身記》見《金剛鉆》1925年1月1、3、6日。《寒魔自述記》中,風、寒、暑、濕、燥、火六魔,由外侵入人體,人體內四魔酒、色、財、氣,若人破衛生之法,便會迎接六魔共游。而《環游人身記》的內容和《寒魔自述記》大同小異,多了腎水、經脈等中醫術語。陸士諤在小說中所謂的“衛生”和《醫界鏡》一樣,沿用的是中醫“保衛生命”的養生之意,和西醫提倡的“衛生”不同。
“寡人有疾”的敘事由來已久,只不過隨著時代的沿革有了全新的版本。小說中主人公開的藥方,只能醫治個體,但對牽扯出的病入膏肓的群體卻束手無策。在文學實踐的場域內外,注重個體養生的傳統醫方受到了質疑和挑戰,追名逐利的庸醫使中醫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梁啟超曾以“疾病”的“診治”論洋務運動的弊病:“今有病者,其治之也,則必滌其滯積,養其榮衛,培其元氣,使之與無病人等,然后可以及它事,此不易之理也。今授以甲胄,予之以戈戟,而曰爾盍從事焉,吾見其舞蹈不終日,而死期已至矣。彼西人之練兵也,其猶壯士之披甲胄而執戈鋋也。若今日之中國,則病夫也。”(25)梁啟超:《變法通議·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梁啟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6頁。國本未固,“病夫”披“甲胄”,洋務不能醫國,這與庸醫用和緩的方子行騙一樣,只會貽誤病情。有想要“正本清源”的小說,卻無意間揭示了當時的中醫“弊病”。1909年有報紙登載《醫林外史正傳》,希望能借小兒學醫的故事為中醫正名,但是小兒出游前父親一番苦口婆心的勸告,卻將中醫界的亂象揭出:“如今有種醫生,賣弄手段,不肯問人,不管好歹,胡亂用藥……高抬身價,神乎其神,那曉得見了重癥,無非寫了一張不關痛癢的藥方,以為服藥之后,一時不死,可以卸卻干系,病家反講他用藥平穩,見識老成……”(26)佚名:《醫林外史正傳》,《紹興醫藥學報》1909年第16期。庸醫“藥不對癥”的拖延戰術,梁啟超對此十分清楚。他改學制、育新民的宣傳,本就脫胎于“病體(病國)”的分析,其《新中國未來記》直接借李去病之口提倡西醫峻急的“療法”,用上“雷霆霹靂手段,做那西醫治瘟疫蟲的方法”,將中國的病蟲“鏟到干干凈凈”。(27)飲冰室主人:《新中國未來記》,《新小說》1902年第2期。
道光年間的學者兼醫者陸以湉,看了合信的《西醫略論》頗有感觸:“西國醫士合信氏《西醫略論》,略內癥而詳外癥,其割肉鋸骨等法,皆中國醫人所不敢用者……其診脈至數驗以時表,取其旋運有準,謂華人用鼻息呼吸,恐有遲速長短,不如時表之準也。”(28)陸以湉:《今書》,《冷廬醫話》,呂志連校,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9頁。雖對西醫內治之法難以茍同,但陸以湉還是贊賞時表診脈的有效性,殊不知這“時表”后來成為“雷霆霹靂手段”的隱喻,表針移動,疾病凸顯,在國族危亡境中主攻“辯證”的中醫危機加劇。
三、“醫人”“醫國”與“造人”
清末民初文壇對中醫的貶低成為較為普遍的現象,逐漸演變為當時社會革命的組成部分。楊念群指出,“‘中醫’沒有資格成為現代社會醫學的最重要的理由是,中醫總是呈分散狀態面向每個病人個體,而現代的‘社會醫學’應以群體體魄的改造為基本職能,最終指向保國與保種以及民族國家建設的終極目標”。(29)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沖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59頁。“發現疾病”的小說中,已暗含從“醫人”到“醫國”的轉變。清末民國時期文學文本,摻雜著對中西醫攻守的回應,“疼痛”“畸形”和“殘缺”的個體上升為蒙昧落后的國族象征。
俞樾在《廢醫論·去疾篇》中認為,“夫人之病,由心生也;心者,氣之帥也;氣者,人之所以生者也。善養生者,長善心而消惡心……不善養生者,消善心而長惡心”。(30)俞樾:《廢醫論》,《俞樓雜纂》卷四十五,《春在堂全書》第三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755頁。可是俞樾并不懂醫,他只是將修身之道套用在了“衛生”之道上,并將朝政之上君子與小人的進退與“衛生”之道類比。亦有人提出“小醫醫一人,大醫醫一國;小醫而自病矣,人將誰醫之?大醫又自病矣,國將誰醫之?”(31)馬世杰:《醫國篇》,《新世界學報》1903年第13期。跳出中西醫論爭,清末民初學人能夠達成共識的是,國體“病入膏肓”顯然不能“諱疾忌醫”,這疾病不限于個體肌理,更在于種族弱勢和朝政衰敗導致的國民的精神病態。
清末民初文學的“診斷”從個體延及群體。筆記小說《醫皮》講述外國人售賣“能使黑奴變白”的香皂,作者靈機一動,想到看到消息說國外醫生已有技術可變膚色,無需香皂即可讓人由黑變白,至于黃種人變膚色就更加方便了,然而“我黃種人之大病,又不專在于皮之黃而實在于皮之厚,忝然面目,固有針之,全無點血,炙之不損一毛者,不識該醫生亦能別出心裁,以療此惡疾否?”(32)佚名:《醫皮》,《新世界小說社報》1906年第6期。作者戲謔的筆觸背后,是對恬不知恥的國人的鞭撻,而開玩笑間將治愈的希望寄托在了據說掌握變膚色技術的西人醫生身上,種族的恥感被壓抑在了膚色變化的笑料中。游戲文章批駁族群之惡,名為醫治,實為撻伐。無獨有偶,小說《醫意》也用幽默的筆調寫了一出“治病救人”的“鬧劇”,小學徒在師傅不在的時候擅自給病人開方,建議向難產的產婦投擲錢幣,老醫生得知后大發雷霆,不料家屬卻上門道謝,稱照著“神醫”醫囑,產婦順利生產。訝異之余,老醫生詢問徒弟為何開此方,反遭徒弟嘲笑:“何師之愚也!今世之中國,孰是見錢而不出攫者哉?”(33)武:《醫意》,《月月小說》1907年第7期。未出世的嬰孩也“見錢眼開”,看見錢幣便呱呱墜地,聯系小說數次重復的中醫“醫者意也”,諷刺極為辛辣。小說《劉醫》則將矛頭對準了上海一些唯利是圖的醫生,有某老爺為了占有繼女,拜托劉醫毒死繼女病重的未婚夫,劉醫趁機敲詐了老爺一筆巨款,反而將病人治愈,并拿這筆錢促成了兩位年輕人的婚事,老爺得知后暴跳如雷卻又無可奈何。這篇小說出現在《醫話叢存續編》里,收入丁福保主編的《丁氏醫學叢書》,小說結尾處寫道:“滬上醫家,慣做其前半段”,(34)佚名:《醫話叢存續編:劉醫》,《中西醫學報》1910年第3期。小說以坊間花邊新聞為背景,對劉醫俠義行為的贊許帶上了對上海醫界怪象的批判。小說《醫界鏡》中也揭露不學無術之人中西醫通吃,以洋商招牌兜售“救貧戒煙丸”,“廣請通人,做了許多淺近俚俗的歌詞,登在報紙,使人人皆易明白,又請人做了保證書,各處招搖,使各州各縣的生意人,皆替他行銷,報上登的告白,每說要富國先強種,要強種先戒煙,本社以救濟同胞為心,故創這良藥……”(35)儒林醫隱:《醫界鏡》,第124頁。這個賣假藥宣傳的情節有多處值得玩味。首先買的是丸散,卻要借用洋招牌,可見當時西醫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其次登載淺近歌詞宣傳,此處的歌詞應指類似于歌本、時令小調之類的過渡文體,本是啟蒙的重要環節,卻在小說中成為招搖撞騙的工具。再次便是戒煙與富國強種的聯系,戒煙丸成了國民藥方,加入了“診療”體系,戒煙由此不再是個人行為,而是強國保種的重要途徑。可以看到,醫人/醫國的主線凸顯出來,同時以西方為標桿的現代文明想象又強化了文人啟蒙大眾時對自身傳統的反思。只是這種敘述和黑幕小說一樣,在“獵奇”的過程中削弱了揭露黑暗的深度和力度。
要想掃除舊“疾”,除了肅清社會制度的弊端,還有一部分文人開始了“強國保種”框架內的“改造”敘事。早在1897年,浙江名醫陳虬已作《保種首當習醫論》,他認為保種救世應號召全民學醫,“夫醫也者,不獨其能療疾衛生延年也,人類之藩道昌而運隆,罔不基此”。(36)陳虬:《保種首當習醫論》,《利濟學堂報》1897年第4期。然而在陳虬看來,人類是地球萬物之首,其中又以中國人最為聰穎,但當時面對西方民族的崛起,華族處處受制。陳虬提出的保種習醫,雖也涉及中西交流,甚至論及婚嫁優生,但歸根結底對華族的信心仍在,而他所提倡的醫學,也是傳統中醫。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昔日如陳虬這樣的民族自信逐漸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對種族改造的想象。嚴復《天演論》帶來的“物競天擇”,給原本判定國族“體弱多病”的知識分子提供了一條人種進化的線索。經過翻譯和再闡釋的“東方之病夫”猶如民族恥辱的烙印,想要擺脫它,原本的“醫治”成為“替代”,“雷霆霹靂”的西醫手段變成西方科學家造出“新人”。
魯迅在1906年的《女子世界》上以“索子”為筆名,刊發了名為《造人術》的譯作。日本學者發現《造人術》是按照日譯本翻譯的,原文是Louise J.Strong發表在Cosmopolitan雜志1903年1月號上的An Unscientific Story(《一個非科幻小說》)。(37)[日]神田一三:《魯迅〈造人術〉的原作·補遺——英文原作的秘密》,許昌福譯,《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期。無獨有偶,包天笑也翻譯了這篇《造人術》,登載在1906年4月26日的《時報》上。有學者認為魯迅的《造人術》通過日本詞組和英文詞組“life-germ”之間的對譯,為晚清文學打開新的想象空間,“將不同的生物種類,不論是人,還是植物,都統一在‘人’‘芽’一體的細胞概念之中,而這個概念,體現的正是現代生物學有關生命起源的理論”。(38)[美]劉禾:《魯迅生命觀中的科學與宗教(上)》,孟慶澍譯,《魯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3期。事實上,包天笑和魯迅翻譯《造人術》的時間很相近,且包譯版本也用了“人芽”這個詞。對于魯迅《造人術》的具體刊發日期,學界尚有爭論。2005年版的《魯迅全集》注明魯迅《造人術》刊于《女子世界》第二年第4、5期合刊,即1905年。但據宋聲泉和夏曉虹考證,《女子世界》第二年第4、5期合刊應出版于1906年。(39)宋聲泉:《魯迅譯〈造人術〉刊載時間新探——兼及新版〈魯迅全集〉的相關訛誤》,《魯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5期。對于生物學的接受是晚清學人的普遍現象,但面對同樣的文本,魯譯和包譯風格迥異,按語立意也各不相同。魯迅和包天笑都翻譯了原小說的開頭部分,大致說的是科學家伊尼他氏苦心經營數年,終于創造出“人芽”,可以視為現代科學中人工胚胎的原型,只不過對于“人芽”的誕生過程并無生理化學細節描述。兩人的譯文在科學家成功創造出“人芽”后都戛然而止。其實小說之后的情節發展是“人芽”變成怪物,引發了科學災難。更有學者考證,小說原作者是根據黑人和中國人的形象創造了怪物的外觀。(40)王家平:《魯迅譯作〈造人術〉的英語原著、翻譯情況及文本解讀》,《魯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12期。撇去兩人翻譯風格的差異不談,兩個譯本都側重于激動人心的“新造物主”誕生部分。魯譯版本后,周作人(萍云)按語認為“世界之女子,負國民母人之格,為祖國誕育強壯之男兒……新造物主之稱號,乃不能不移之以贈我女子”。(41)索子:《造人術》,《女子世界》1906年第4、5期。丁初我則補充道,“鑄造國民者,視國民母之原質,鑄造國民母者,乃視教育之材料”。(42)索子:《造人術》,《女子世界》1906年第4、5期。無論是魯迅和包天笑筆下造物主的“大歡喜”,還是周作人和丁初我強調的女子“造物主”,都離不開對國家人種改造的想象,“人芽”狂想是當時文人在小說中進行“改造種族”的縮影。
“新造物主”的誕生之所以激動人心,不僅是科學幻想的感染力,背后還有“進化論”和“優生學”影響下的“治愈”期許。清末民初興女學、復女權都離不開對女性生育能力的強調,女性作為“造物主”,承擔著繁衍優等“國民”的責任,這種生物學意義上的解讀直接涉及國族人種的改良。19世紀末弗朗西斯·高爾登(Francis Galton,1822-1911)正式創建優生學(Eugenics),該學科與進化論緊密相關,是“研究所有能夠改善人種先天素質(the inborn qualities of a race)”(43)Charles Benedict Davenport,Heredity in Relation to Eugenics,New York:Holt,1923,p.1.的科學。人種先天素質的差異可以后天彌補,似乎為急于找到“治病良方”的知識分子提供了加速國族“現代化”的靈感,除了周氏兄弟三人,嚴復、章太炎、陳獨秀、胡適、陳長蘅等人都發表過優生優育以實現人種改良的言論。
但并非所有人都對“人種進化”“疾病治愈”的“黃金未來”心馳神往。值得一提的是,比起魯譯后按語對“人芽”的接受,包譯版本后自加的按語則態度微妙。“發明造人術后,更當發明造魂術,不然,是蠕蠕者縱能運動,世界亦奚用此行尸走肉為?”(44)笑:《造人術》,《時報》,1904年4月26日。即便人種完成了“新陳代謝”,后來者若是沒有精神世界的革新,便也是無用的行尸走肉,這是對科學幻想中“少年中國”的警示。1910年,包天笑譯作《新造人術》在《小說時報》面世,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個已然全新的世界。有一博士造出腦力體力均優于人類的超級物種,不料實驗品從實驗室逃出,躲藏在一位作家家中。作家見其打字迅捷,博學多才,便也默許這只半人半羊的物種留下,幫他一起寫歷史小說。但是博士終究找到作家,用電擊脅迫實驗品回到實驗室,作家斥責博士殘酷至極,卻也被電擊威脅。包天笑譯罷,嘆曰:“嗚呼!創造生物,創造生物,果人間社會之幸乎?”(45)笑:《造人術》,《時報》,1904年4月26日。其實包天笑前后兩次翻譯不同的“造人術”,他的態度并未改變,病態中孕育出的新生命,不一定是治病良方,可能是惡劣“原質”的延伸,何來“治愈”的功用?
清末民初文學實踐場域中,隱藏在文本之下的“疾病”自指已經成為蘇珊·桑塔格所說的“疾病的隱喻”,“在現代政治話語中,疾病隱喻的夸張透露出一種懲罰性的觀念:這并不是說疾病是一種懲罰,而是疾病被當作了邪惡的標志,某種將被懲罰的東西的標志”。(46)[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第89頁。古老的國度及其子民在肉體和精神上被發現的“疾病”,變成一種虛弱的疲態,一種現代化過程中落后于他國的內在原因。原本天人合一的個體養生觀念,終究被民族“疾病”“診療”的話語實踐取代。而無論是中西醫論爭映射在作品中的困頓,抑或是新生“人芽”的狂想,都試圖在文字中“治愈”“頑疾”,讓積貧積弱的中國在象征層面“煥然一新”。從“醫人”到“醫國”乃至“造人”,疾病隱喻引發的“療救焦慮”,最終成為一種“尋求富強”的現代性探索。清末民初的文學實踐場域,見證了“國族之病”的發現與療救,也見證了“進化論”與“優生學”在科幻敘述中完成的“人種改良”。人文傳統與科學話語的交織并行,共同構成了“五四”文學的先聲。在“救亡”與“啟蒙”的延長線上,注定伴隨著矯枉過正式的文字“猛藥”,清末民初文學只記錄下一部分時代轉型的陣痛,而相關的探索、闡釋與反思永遠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