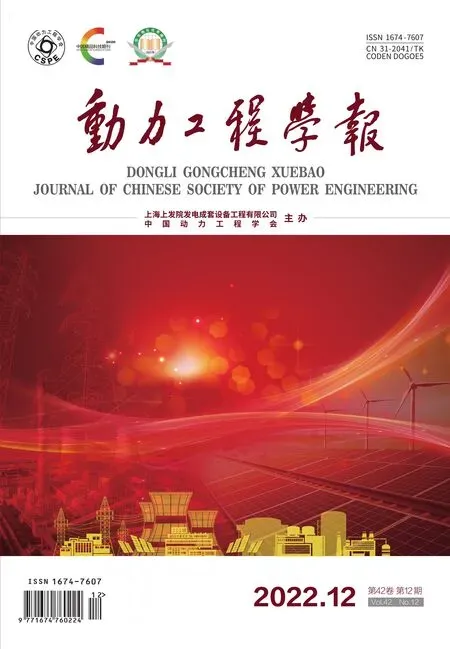表面微溝槽對風力機翼型氣動性能的影響研究
牛志罡, 羅大海, 王子堯
(1.上海理工大學 能源與動力工程學院,上海 200093; 2.上海市動力工程多相流動與傳熱重點實驗室,上海 200093)
風力機風能利用效率與其翼型的氣動性能密切相關,研究風力機翼型的減阻特性對增大風力機的輸出功率具有重要意義[1]。傳統觀念認為阻力大小一般與物體表面的粗糙度成正比,但隨著湍流理論的蓬勃發展,這一傳統認知被打破,仿生減阻展現出極大的優勢[2]。仿生減阻是指研究鯊魚、海豚等運動較快動物的表面結構,從而設計表面溝槽幾何特征,使壁面流場重新分布,達到減小摩擦阻力的目的[3-4]。
王晉軍[5]開展了不同粗糙度溝槽的試驗研究,結果發現減阻大小與溝槽深度和寬度有關。陳瑩等[6]在旋成體模型表面粘貼鋁基溝槽蒙皮,選定3種尺寸的溝槽進行減阻試驗,發現與光滑表面相比可減小約3%~4%的阻力,并得出計算溝槽無量綱高度和寬度的公式。張子良[7]提出了溝槽模化方法,探索二維V型溝槽表面的流場特性及其減阻機理,研究表明最大減阻率可達3.07%。徐琰等[8]利用邊界層理論提出一套減阻微溝槽的高度設計方法,得出三角形鋸齒微溝槽的減阻率達5.5%;進行減阻溝槽設計時深度為主要因素,保持在y+=14左右具有較好的減阻效果。葉學民等[9]對鋸齒尾緣葉片進行數值模擬,探究了3種不同長度的鋸齒尾緣對風機的性能影響,在小流量工況下提高了風機的效率也改變了動葉尾緣脫落渦的結構。陳璠等[10]基于仿生學結構對不同溝槽布局形式在不同雷諾數下的減阻效果開展了對比研究,結果顯示,橫向和縱向布局時溝槽減阻率均隨雷諾數增大而減小,且雷諾數影響占主導地位。國外對溝槽減阻技術的研究起步較早,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蘭利研究中心發現順流向的微小溝槽表面能有效地降低壁面摩阻,由此引發了表面溝槽減阻技術的研究熱潮。早期開展的是溝槽平板湍流減阻研究,研究人員發現最佳的溝槽設計形式為對稱的V型溝槽,且當其溝槽深度h和溝槽間距s的無量綱尺寸h+≤25和s+≤30時具有減阻效果[11-12]。Chamorro等[13]將不同形式和尺寸的溝槽布置在機翼表面并分析得出溝槽尺寸的無量綱值對阻力系數的影響,溝槽的尺寸h+=8和s+=15時減阻效果最佳。Timmer等[14]對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設計的翼型進行了氣動分析,并研究了Z字型溝槽對DU96-W-180翼型升阻力特性的影響。Sareen等[15]在3種雷諾數情況下對DU96-W-180翼型表面V型溝槽進行了減阻實驗,測得最優溝槽尺寸為62 μm時可以達到5%的減阻效果。Radmanesh等[16]在NACA S5020翼型表面布置矩形溝槽,進行了數值模擬研究,發現減阻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攻角,非優化的溝槽在某些攻角下反而增加了4%的阻力。
目前,國內外關于翼型表面仿生溝槽的研究主要采取實驗和二維數值模擬的形式,而較少采用三維模型通過數值模擬來研究表面溝槽的減阻效應。在以往針對翼型的數值模擬中,溝槽大多采用垂直來流方向的橫向布局形式,為了減少計算量,往往采用二維數值模擬,這種簡化模擬得到的研究結論并不適用于溝槽順來流方向的縱向布局情形。筆者采用三維數值模擬來研究溝槽縱向布局時對風力機翼型氣動性能的影響,通過系統分析不同工況下翼型的升阻力特性及表面摩擦力系數來闡述表面溝槽的減阻機理。
1 數值方法和幾何模型
基于Ansys Fluent商用計算流體動力學(CFD)軟件對風力機翼型繞流流場進行三維定常不可壓雷諾平均方法(RANS)模擬。速度壓力耦合采用SIMPLE算法,壓力項和動量項空間離散采用二階迎風格式,同時考慮翼型表面的流動轉捩,選用基于γ-Reθ t模型[17]的四方程Transition SST模型。3種不同翼型的幾何輪廓對比如圖1所示,其中x、y分別為弦向和縱向坐標,c為翼型弦長。

圖1 翼型幾何輪廓對比
本文重點考慮DU96-W-180翼型,并選用相對厚度接近的S809翼型及同等厚度的NACA0018翼型進行對比。對于翼型表面微溝槽,考慮L型和V型2種幾何形式,如圖2所示。其中,w為L型溝槽寬度。

(a) L型溝槽

(b) V型溝槽
溝槽深度和間隔對應的無量綱幾何參數[11-12]定義如下:
h+=h·u*/ν
(1)
s+=s·u*/ν
(2)
(3)
式中:τω為壁面剪切應力;ν為流體運動黏度;ρ為流體密度。根據文獻[18],表面溝槽減阻特性曲線可分為黏性區(h+=0~<11)、減阻效果惡化區(h+=11~25)和粗糙表面區(h+>25),應盡量確保溝槽在最佳減阻點(h+=11)附近。本研究中僅改變h和s,溝槽幾何特征保持不變,計算公式詳見文獻[6]。
布置表面微溝槽的仿生翼型三維幾何模型、L型和V型溝槽三維模型,如圖3所示。溝槽順流向縱向布置,覆蓋翼型的上下表面。由于溝槽非常微小,內部的網格尺度也很微小,考慮到計算量,沿翼型展向均勻布置10個溝槽。

(a) 仿生翼型三維幾何模型
計算域和網格分布如圖4所示,其中α為來流攻角。遠離翼型的計算域采用O型網格,如圖4(a)所示;翼型附近的計算域采用C型網格,如圖4(b)所示。外邊界距翼型表面約為60倍翼型弦長,盡量減小外邊界對內部流場的影響。外邊界左側為速度進口邊界,右側為壓力出口邊界,計算域展向兩側設為對稱邊界條件,翼型表面設置為無滑移絕熱固壁。

(a) 全局網格
溝槽附近的網格分布如圖5所示。L型溝槽內部設置至少4個網格單元,V型溝槽內部設置至少8個網格單元。從溝槽內部區域到邊界層外部流場區域,采用多塊結構化搭接網格,網格分布由密到疏,以保證溝槽附近流場求解精度,同時減少總體計算網格數。
想困惑,從十個方面揭示出《共產黨宣言》的時代價值和當代生命力,力圖幫助讀者特別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牢固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補足“精神之鈣”。

(a) L型溝槽
為了檢驗計算結果的精度,首先進行網格無關性驗證,并與實驗數據[15]進行對比。雷諾數Re=1×106條件下原始DU96-W-180光滑翼型升、阻力系數Cl和Cd隨攻角變化的計算結果如圖6所示。從圖6可以看出,當網格數量增加到168.8萬以后,繼續加密對升、阻力系數的計算結果影響極小,本文中等網格、密網格得到的計算結果、實驗結果[15]以及XFOIL程序的計算結果[15]吻合較好。出于計算精度和資源的考慮,本文選用中等網格作為后續研究的基準網格。

(a) 升力系數
4°攻角下原始DU96-W-180光滑翼型表面壓力系數分布的對比如圖7所示。從圖7可以看出,所計算的表面壓力系數Cp分布與文獻[15]的計算結果吻合,也驗證了本文數值方法的可靠性。

圖7 表面壓力系數分布結果對比
2 計算結果與分析
2.1 溝槽尺寸對表面溝槽減阻效應的影響
溝槽深度對風力機翼型氣動性能有顯著影響,此外,溝槽寬度和間隔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素。在雷諾數Re=1×106條件下,根據最佳減阻點h+=11估算出h約為0.000 25 m。對于DU96-W-180翼型,光滑翼型和表面布置溝槽的仿生翼型阻力系數對比如圖8所示。

(a) L型溝槽
總體上,L型溝槽的減阻效果要優于V型溝槽。當s=0.000 25 m,w=0.000 50 m,h=0.000 25 m時,L型溝槽具有最佳減阻效果;在4°攻角下,該仿生翼型的升力系數提升1.67%,阻力系數降低5.60%,升阻比提升7.70%。對于V型溝槽,當s=0.000 4 m,h=0.000 25 m時,表面溝槽具有最佳減阻效果;在4°攻角下,升力系數提升1.60%,阻力系數降低3.70%,升阻比提升5.50%。
4°攻角下表面布置最優L型溝槽的仿生翼型與原始光滑翼型表面壓力系數分布的對比如圖9所示。可以看出,表面布置溝槽后,翼型的壓力系數分布相比原始光滑翼型變化很小。在x方向和y方向上,光滑翼型和仿生翼型對應的Cp曲線圍成的圖形面積幾乎相等,這也說明,仿生溝槽幾乎不會提升翼型的升力,也幾乎不會增加翼型的壓差阻力。

(a)
光滑翼型和表面布置最優L型溝槽的仿生翼型展向平均后全流場的間歇因子分布如圖10所示。從圖10可以看出,仿生翼型表面流動轉捩位置相比光滑翼型要略微靠后。布置溝槽后,吸力面轉捩位置大約從x/c=0.472往后推移至x/c=0.485,壓力面轉捩位置大約從x/c=0.73往后推移至x/c=0.75。在翼型表面布置仿生溝槽可以極小地延遲邊界層內的流動轉捩,而流動轉捩帶來的摩擦阻力系數的減小是可以忽略的。

翼型的壁面摩擦力系數Cf反映了摩擦阻力的大小,表面布置最優L型溝槽的仿生翼型前緣處壁面摩擦力系數分布如圖11所示。溝槽底部近乎為“死水”區,摩擦力系數很小,溝槽頂部的摩擦力系數遠遠大于底部。在溝槽的側壁面,摩擦力系數從溝槽底部接近于零急劇增大到溝槽端口處的極大值。

(a) 光滑翼型
圖12給出了4°攻角下光滑翼型和表面布置最優L型溝槽的仿生翼型壁面摩擦力系數沿翼型展向的對比,其中z為翼型展向坐標。在4個不同流向站位處(x/c=0.2、0.4、0.6和0.8),仿生翼型的壁面摩擦力系數沿展向呈現規律變化,總體上仿生翼型壁面摩擦力系數峰值要略高于光滑翼型,但其壁面摩擦力系數展向均值要低于光滑翼型。在翼型壓力面x/c=0.4處,壁面摩擦力系數有極小值,光滑翼型和仿生翼型兩者的壁面摩擦力系數值都很小,但仿生翼型壁面摩擦力系數的峰值和展向均值都小于光滑翼型。布置表面溝槽后,兩溝槽之間的翼型表面附近流速加快,摩擦力系數也隨之增大,在溝槽端口處壁面摩擦力系數達到最大(峰值比光滑翼型高約30%)。同時,溝槽底部流體受壁面約束的影響,流速很小,相比頂部,溝槽底部壁面摩擦力系數要小一個量級。在這4個不同流向站位處(除了壓力面x/c=0.4),仿生翼型壁面摩擦力系數均值相比光滑翼型要低30%~40%。布置表面溝槽后,仿生翼型的壁面摩擦力系數總體上是降低了,表面溝槽對翼型的減阻效應取決于摩擦阻力的減小。

2.2 雷諾數對表面溝槽減阻效應的影響

當雷諾數Re=1×105時,h=0.000 25 m對應的無量綱溝槽深度h+≈2,此時溝槽深度處于黏性區,4°攻角下表面溝槽減阻效果達到最佳,相比光滑翼型,仿生翼型的阻力系數降低了3.46%。溝槽深度h=0.002 m (h+≈11)處于最佳減阻點附近,此時4°攻角下翼型的阻力系數最大降幅達到14.06%。隨著溝槽深度進一步增大,當h=0.003 m (h+≈16)時,溝槽的減阻效果有所降低,最大減阻率降為9.78%。
當雷諾數Re=3×105時,h=0.000 25 m對應的無量綱溝槽深度h+≈5,最大減阻率為2.70%。h=0.000 78 m (h+≈11)處于最佳減阻點附近,在該雷諾數下仿生翼型的阻力系數相比光滑翼型最大可降低5.54%。隨著溝槽深度進一步增大,h=0.001 14 m (h+≈16)時,最大減阻率降為4.08%。與Re=1×105的低雷諾數工況相比,在該雷諾數條件下,整體上表面溝槽的減阻效果有所減弱。
當雷諾數Re=3×106時,因溝槽建模時存在困難無法實現最佳無量綱參數對應工況的模擬,故只能將h=0.000 25 m應用于模型中,所對應的無量綱h+≈25,在α=2°~6°依然有減阻效果,但升力系數均有所降低,最大減阻發生在6°攻角時,阻力系數可降低3.86%,升力系數降低1.86%。進行無量綱參數h+≈27的計算,發現全攻角的氣動特性均惡化。上述算例說明在不同雷諾數下,h=0.000 25 m溝槽均具有優化翼型氣動特性的效果。
2.3 表面溝槽對不同翼型氣動性能的影響
為驗證仿生溝槽對其他翼型也有氣動優化效果,將h=0.000 25 m應用于厚度接近的S809翼型及NACA0018翼型,來流雷諾數Re=1×106。不同翼型對應的阻力系數如圖14所示。

(a) S809翼型
對于S809仿生翼型,最大提升和減阻均發生在4°攻角時,升力系數提升約為3.7%,阻力系數可降低12.6%。對于NACA0018仿生翼型,最大提升和減阻也均發生在4°攻角時,升力系數提升約為1.0%,阻力系數可降低8.3%,表明這兩款不同厚度的翼型對溝槽的敏感度要高于DU96-W-180翼型,有更明顯的減阻效果。S809、NACA0018翼型表面布置最優L型溝槽的仿生翼型前緣處壁面摩擦力系數分布如圖15和圖16所示,可以看出二者的摩擦力系數峰值高于DU96-W-180翼型。溝槽底部近乎為“死水”區,摩擦力系數很小,溝槽頂部的摩擦力系數值遠遠大于底部。在溝槽的側壁面,摩擦力系數從溝槽底部接近于零急劇增大到溝槽端口處的極大值。仿生翼型峰值處的摩擦力系數高于原始翼型,但考慮到底部的低摩擦力區,沿展向的壁面摩擦力系數均值要低于原始翼型。

(a) 光滑翼型

(a) 光滑翼型
3 結 論
(1) 在翼型表面布置微型溝槽可以有效降低阻力。當來流雷諾數Re=1×106,攻角為4°時,布置h=0.000 25 m的L型溝槽,對于DU96-W-180翼型可使阻力系數降低5.6%;同等條件下S809翼型可降低12.6%,NACA0018翼型可降低8.3%。
(2) 表面溝槽的減阻效果受來流雷諾數、溝槽尺寸、溝槽類型以及翼型的影響。隨著來流雷諾數的增大,減阻效果有所降低。隨著溝槽深度的增加,減阻率先增大后減小,最佳減阻點位于h+≈11。L型溝槽的減阻效果普遍優于V型溝槽;S809、NACA0018翼型對表面L型溝槽的敏感度高于DU96-W-180翼型。
(3) 在翼型表面布置微型溝槽可以略微延后轉捩的發生,對3款翼型壓差阻力和升力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壁面摩擦力系數的減小是翼型減阻的主要原因,雖然仿生翼型在部分站位槽口處的摩擦力系數高于光滑翼型,但是在展向上仿生翼型從槽底到槽口的平均值都小于光滑翼型,因此總體摩擦力系數減小,阻力也隨之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