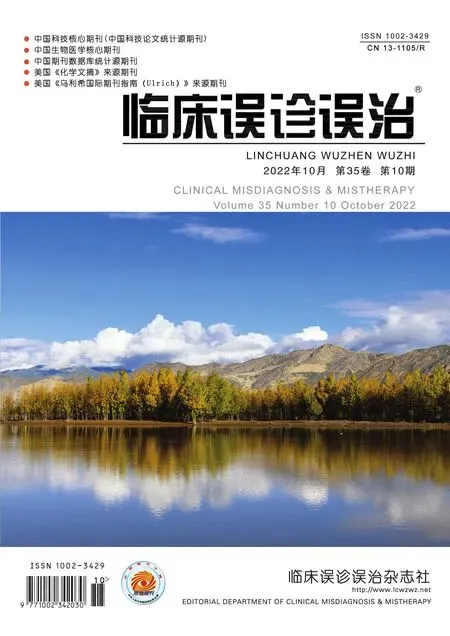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情況及其影響因素預測模型的建立與驗證
唐齊兵,楊 梅,董瓊蘭,楊雨欣
ICU是危重癥患者病情監護和治療的重要場所。在ICU中氣管插管是搶救呼吸衰竭及各種呼吸暫停患者的常用手段,但氣管插管為侵入性療法,在搶救患者的同時也可能將致病菌帶入患者肺內,引起肺內感染,甚至可導致患者死亡[1-2]。預測ICU患者氣管插管并發肺內感染風險是降低肺內感染風險的前提。雖然關于ICU患者氣管插管并發肺內感染影響因素方面的研究已有一定報道[3-4],但多為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預測計算復雜,對臨床的指導價值不大。列線圖預測模型為近年常用的可視化預測模型,可將多因素分析結果進行可視化處理而簡化預測操作。目前,關于列線圖預測模型在ICU患者氣管插管并發肺內感染風險預測方面的研究少見報道。本研究分析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病原菌分布情況并建立影響因素列線圖預測模型,以期為臨床上ICU患者氣管插管后肺內感染的預防控制措施制訂提供參考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選取2018年2月—2020年12月在我院ICU行氣管插管 213例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行氣管插管治療;②氣管插管治療前無肺部感染;③氣管插管時間在48 h以上;④患者和(或)其家屬對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簽署相關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入院48 h內轉院或因病情嚴重在入ICU后48 h內死亡者;②合并肺部嚴重創傷者;③妊娠期及哺乳期婦女。
1.2研究方法 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可能影響因素收集,內容包括:①人口學特征:性別、年齡、體質量指數、吸煙史、飲酒史;②身體狀況: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史、肺部基礎病史(肺氣腫、支氣管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評分、ICU入住時間;③疾病治療相關因素:糖皮質激素使用、抗生素使用、氣管插管時間、氣道濕化、營養支持途徑、急診手術、全身麻醉和腦胸腹部手術。
肺內感染診斷:參照《中國成人醫院獲得性肺炎與呼吸機相關性肺炎診斷和治療指南(2018年版)》[5],根據臨床表現、影像學檢查及血、尿常規綜合判斷患者是否出現肺內感染,標準如下:①體溫高于基礎體溫1 ℃以上或超過38 ℃;②外周血白細胞計數>10×109/L或<4×109/L;③呼吸道膿性分泌物鏡檢在低倍鏡下顯示白細胞計數>25個或膿性分泌物培養出潛在呼吸道病原菌;④CT等影像學檢查提示肺部出現新發或進展期浸潤灶,查體有啰音。根據診斷結果將氣管插管213例分為肺內感染組和非肺內感染組2組,比較2組上述各因素,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判斷各因素對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的影響。
致病菌群感染情況檢測:對確診為肺內感染的患者,經人工氣道以一次性滅菌吸痰管吸取呼吸道痰液標本,置無菌杯中,先對標本進行涂片鏡檢,對于白細胞>25/HP,鱗狀細胞<10/HP者進行病原菌分離及鑒定。采用法國梅里埃公司生產的ATB Expresin型全自動細菌鑒定儀進行細菌鑒定,質控菌均購于中國微生物菌種保藏中心,分別為金黃色葡萄球菌ATCC 29213、大腸埃希菌 ATCC 35218及銅綠假單胞菌ATCC 27853。
1.3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 22.0統計學軟件對所有數據進行處理分析,病原菌分布情況采用描述性統計,單因素分析行χ2檢驗,多因素分析行Logistic回歸分析;應用R4.1.2軟件的RMS包構建列線圖預測模型,以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分析該預測模型預測價值,并以計算機模擬充分采樣(Bootstrap)法對該預測模型進行內部驗證,α=0.05為檢驗水準。
2 結果
2.1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病原菌分布情況 本研究納入的ICU行氣管插管213例中共51例確診為肺內感染,共培養出病原菌63株,其中革蘭陰性菌最多,共40株(63.49%),革蘭陽性菌19株(30.16%),真菌4株(6.35%),各病原菌分布情況見表1。

表1 ICU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51例病原菌分布情況
2.2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肺內感染組與非肺內感染組年齡、體質量指數、吸煙史、糖尿病史、肺部基礎病史、GCS評分、ICU入住時間、糖皮質激素使用、抗生素使用、氣管插管時間、營養支持途徑、急診手術、全身麻醉和腦胸腹部手術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P<0.01),見表2。

表2 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單因素分析
2.3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的各因素賦值,年齡<60歲=0,≥60歲=1;體質量指數<25 kg/m2=0,≥25 kg/m2=1;吸煙史無=0,有=1;糖尿病史無=0,有=1;肺部基礎病史無=0,有=1;GCS評分≤8分=0,>8分=1;ICU入住時間≤7 d=0,>7 d=1;糖皮質激素使用無=0,有=1;抗生素使用無=0,有=1;氣管插管時間≤7 d=0,>7 d=1;營養支持途徑腸內=0,全靜脈=1;急診手術無=0,有=1;全身麻醉無=0,有=1;腦胸腹部手術無=0,有=1。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年齡≥60歲、有吸煙史、有糖尿病史、使用糖皮質激素、氣管插管時間>7 d及急診手術為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的危險因素(P<0.05,P<0.01),GCS評分>8分為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的保護因素(P<0.05),見表3。

表3 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2.4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列線圖預測模型建立 根據表3中多因素Logistic分析結果以R4.1.2軟件的RMS包構建列線圖預測模型,該預測模型包括年齡、吸煙史、糖尿病史等7個因素,使用時根據患者各因素向上做垂直線后獲得各因素的分值,將各因素累加后得到總分,向下做垂直線即可得到肺內感染風險發生率,見圖1。

圖1 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列線圖預測模型
2.5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列線圖預測模型驗證 以ROC曲線評估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列線圖模型的預測價值,結果顯示曲線下面積為0.829,95%CI為0.768,0.889,說明該預測模型區分度較好;再以Bootstrap法對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列線圖預測模型進行內部驗證,以原始數據重復抽樣1000次,結果顯示平均絕對誤差為0.033,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列線圖預測模型與理想模型基本擬合,提示該預測模型預測準確度較高,見圖2和圖3。

圖2 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列線圖預測模型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

圖3 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列線圖預測模型內部驗證圖
3 討論
正常情況下人體口腔中寄生著數十種正常菌群與致病菌群,在健康人群中2種菌群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可免受感染[6-7]。然而,ICU患者病情嚴重,免疫功能降低,正常生理活動減弱,易出現菌群失調而使大量致病菌繁殖[8]。本研究納入的ICU行氣管插管213例中共51例確診為肺內感染,與以往研究結果基本一致[9]。氣管插管為臨床常用的搶救技術,在降低病死率和挽救患者生命方面起著關鍵作用,但氣管插管為侵入性治療技術,可使患者咳嗽反射和纖毛清除運動等呼吸道防御功能被削弱,易致口腔和鼻咽部的細菌隨導管侵入肺部[10]。
本研究肺內感染51例中共培養出病原菌63株,其中革蘭陰性菌最多,共40株(63.49%),革蘭陽性菌19株(30.16%),真菌4株(6.35%),與相關研究結果一致[11]。本研究肺內感染51例從致病菌種類來看鮑曼不動桿菌占比最高,占23.81%。鮑曼不動桿菌為嚴格需氧的非乳糖發酵條件致病菌,該菌感染后可引起膿毒癥等嚴重疾病,近年隨著抗生素的應用增多已有多篇關于多重抗藥鮑曼不動桿菌感染的報道[12-13]。另外,本研究肺內感染51例中肺炎克雷伯菌的感染率也較高,占比為20.63%。肺炎克雷伯菌常見于呼吸道及胃腸道感染性疾病,也為條件致病菌的一種,免疫功能低下者可經呼吸道吸入肺內而引起肺大葉或小葉出現融合性實變,肺炎克雷伯菌亦容易出現耐藥性,故臨床上對肺炎克雷伯菌感染在選擇藥物時應注意考慮是否存在耐藥的問題[14]。本研究肺內感染51例中革蘭陽性菌及真菌感染占比雖不高,但治療時同樣需引起重視,并注意抗菌藥物的選擇。
本研究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年齡≥60歲、有吸煙史、有糖尿病史、使用糖皮質激素、氣管插管時間>7 d及急診手術為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的危險因素,GCS評分>8分為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的保護因素。分析該結果原因如下:①在年齡方面,隨著患者年齡增長,各臟器功能逐漸衰退,免疫功能也隨之下降。前文已述ICU患者氣管插管后肺內感染主要以感染條件致病菌為主,免疫功能低下者更容易感染。另外,老年患者氣道纖毛運動能力下降,咳嗽反應也較遲緩,導致痰液難以排出,這也是出現肺內感染的一個重要原因[15]。②因煙草中含有大量尼古丁和焦油等刺激性大、毒性強的物質,有吸煙史患者長期接觸此類物質可致氣道表皮細胞受損而影響氣道防御機制,增加機會感染的風險。另有報道顯示,長期吸煙可改變氣道內細菌的種類、數量及密度,增加呼吸系統致病菌感染的風險[16]。③糖尿病為臨床常見的代謝紊亂性疾病,此類患者在入住ICU后易出現肺內感染的原因可能與患者長期高血糖使血漿滲透壓升高,導致白細胞的吞噬能力受抑制而降低免疫力有關;并且血糖濃度升高至一定水平時可使肺炎克雷伯菌等條件致病菌的繁殖加速;另外,糖尿病患者還可能出現T淋巴細胞及B淋巴細胞數量減少,使細胞調節免疫功能下降而增加肺內感染的風險[17]。④糖皮質激素為臨床常用的免疫抑制劑,抗炎作用顯著,ICU患者多有嚴重的炎癥反應,糖皮質激素的使用率也較高。全身糖皮質激素的使用在減輕患者炎癥癥狀的同時,還可導致機體免疫功能下降而增加氣管插管患者肺內感染的風險[18]。⑤一般情況下氣管插管后1或2 d即可在其周圍出現纖維蛋白鞘的包繞,為細菌在其表面的繁殖提供便利;氣管插管還可使上呼吸道過濾、凈化空氣的功能受損,使氣道的自然防御屏障被破壞而增加病原菌侵入的風險,隨著氣管插管時間的延長病原菌感染的風險明顯增加[19]。⑥急診手術也是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的危險因素。行急診手術者多為嚴重創傷、心腦血管疾病、急腹癥和大出血等危重癥患者。此類患者自身免疫力本就較低,在手術與氣管插管的雙重打擊下,可使機體抵御細菌侵入的屏障功能進一步受損而出現肺內感染。⑦GCS評分為臨床常用的昏迷評估方法,<8分者為重度昏迷狀態,此類患者無氣道自凈的能力,加上此類患者氣道內纖毛運動能力下降,支氣管與肺泡功能均低下,容易使氣道內積聚大量的分泌物而使病原微生物快速繁殖,在進行氣管插管時病原微生物容易隨導管進入肺內而出現肺內感染[20]。
多因素Logistic回歸預測模型計算復雜,在臨床上應用較困難。因此,本研究采取目前常用的列線圖預測模型建立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的預測模型,并以ROC曲線評估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列線圖預測模型的預測價值,結果顯示曲線下面積為0.829,95%CI為0.768,0.889,說明該預測模型區分度較好;再以Bootstrap法對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列線圖預測模型進行內部驗證,以原始數據重復抽樣1000次,結果顯示平均絕對誤差為0.033,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列線圖預測模型與理想模型基本擬合,提示該預測模型預測準確度較高。臨床上醫護人員可使用本研究建立的列線圖預測模型預測ICU患者氣管插管后肺內感染發生風險,對于風險較高者可針對性地給予預防干預措施以降低肺內感染發生率。
綜上所述,ICU患者氣管插管后并發肺內感染率較高,以革蘭陰性菌感染為主,其并發肺內感染與年齡、吸煙史和糖尿病史等因素有關,以上述因素建立的列線圖預測模型具有較高的區分度與準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