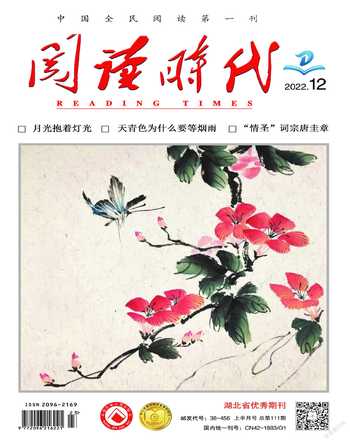我的“圖書館”
沈嘉祿
上初一的時候,我在閣樓上發現了一個秘密:二哥留下的兩本日記。日記的最后一頁記錄了他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前夕的心情:“路途遙遠,可惜行囊里的書太少,也許我可以跟同伴交換著讀。沒能建立起個人的藏書,是青春的遺憾。”
不過在一口紅漆衣箱底層,我摸到了二哥留下的幾本書,托爾斯泰的《哈澤·穆拉特》、巴爾扎克的《家族復仇》、柯切托夫的《葉爾紹夫兄弟》,盡管有些破舊,仍讓我欣喜若狂。
那是一個文化荒蕪的年代,多少個冷風凄雨的夜晚,一盞黃燈映照著慘綠的臉,家里可讀的書所剩無幾。精神饑渴引起的焦慮非常折磨人,所幸我很快在年級里建立起一個小圈子,可以交換余存的圖書,記得有《野火春風斗古城》《粉飾的墳墓》《紅巖》《多浪河邊》《金星英雄》等等,我那本薄薄的《家族復仇》至少出借二十次,后來不知所終。
學校圖書館處于“冰封”狀態,但有同學從氣窗翻進去,弄出一兩本翻譯小說在同學間流傳。偷書的同學對閱讀并不感興趣,他們以此為餌“釣魚”,借一本書得給一角錢,外國名著收費加倍。
為了讀書,我將吃早點的錢去支付借書的費用。整個上午我在饑腸轆轆中度過,最可怕的,肚子里突然發出不雅之聲,引得同學哄堂大笑。我還將家里的肉骨頭、雞毛、老酒瓶、雞肫皮賣給廢品回收站,換來三五天的閱讀權。
后來我意識到,不能這樣一直被小混混“剝削”下去,必須建立自己的藏書。我干脆向他們購買。有一次我“懸賞”五角錢讓他們去庫房尋找《基督山伯爵》,但他們只找到一本“賣相老好”的書——精裝本《物種起源》,敲了我七角錢的竹杠。到初二時,我已經擁有三十多本圖書了,從理論上說,與四五個同學交換,便可實現一百本的閱讀量。
等到學校圖書館“解凍”后,我每周都去借書。班里的鐵哥們也用各自的借閱證幫我借書,滿足我的貪欲。
等我積攢了一百來本圖書后,就想建一個小小圖書館。關鍵時刻媽媽將一具從老家紹興帶來的被頭柜給我瞎弄,一分為二,再買一張三夾板,洋釘膠水,豬血老粉,油漆一刷,兩口書柜并肩登場。有些翻譯小說已經破爛,封面也掉了,不知道作者是誰,我就用兩層牛皮紙做一個封面,再用舊畫報包得服服帖帖。我還專門跑到福州路,在一條弄堂口的攤頭上偷學老師傅的圖書修理技術。
同學們知道我有一個小小圖書館,走動更勤了,關系最鐵的同學來,我就拿出三哥留在上海的美術資料讓他們大飽眼福。借出去的書最怕人家不還,更怕自己忘記,所以我專門做了借閱記錄本,還刻了一方小印章,一個字:“還”。
閱讀讓我體驗豐富的生命,幫助我認識世界、觸摸靈魂,我矢志不渝地愛上了文學。考大學時我想報考圖書館專業,但最后一刻我聽到了魯迅先生的召喚。
這段經歷也讓我懂得了分享的原則,這大概也是公共圖書館的價值。喬遷新居后,有位朋友動員我向一家新建圖書館捐點舊書,我立馬裝了兩大箱送過去。后來我還向多家圖書館捐過圖書和手稿,以至于有人想收藏我的手稿,可我連一張草稿都拿不出來了。
(源自《新民晚報》,有刪節)責編: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