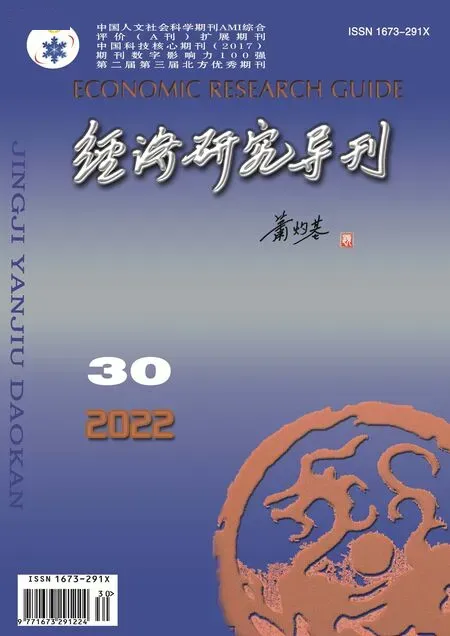鄉村振興視域下農村家庭養老的多維度發展與完善
曹汝朵
(上海工程技術大學 管理學院,上海 201620)
長久以來,家庭養老是人類社會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養老方式[1]。在農村青壯年向城市大批流動的背景下,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難以為繼,而我國目前依舊處于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農村的社區養老、機構養老等社會養老方式發展得并不完善。加之農村老年人“養兒防老”的觀念根深蒂固,有調查數據顯示,占81.3%的受訪老年人認為“家庭養老”仍是當下最理想的養老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有98.7%的農村地區老年人對“家庭養老”更加青睞[2]。因此就當前而言,家庭養老依舊是農村地區最主要的養老方式,但卻因缺乏足夠的現實支持而難以滿足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十四五”規劃中提出,要落實鄉村振興戰略,大力發展新農村建設,而這一政策的實施需要大量年輕勞動力的支持。值此契機,鼓勵一部分進城務工的青壯年返鄉就業或創辦養老服務機構,不僅能夠為鄉村振興注入可持續的內生動力,而且能夠緩解一直以來農村家庭養老方面無子女在旁給予老人生活照料與精神慰藉的難題,對農村在經濟與人文建設方面具有雙重正向效應。
一、當前農村家庭養老面臨的困境
(一)空巢老人數量不斷激增
隨著我國生活水平、醫療水平及國民健康意識的顯著提高,老人的平均壽命也有所延長,所以無論在城市地區還是農村地區,高齡老人的數量呈明顯增長的趨勢,這就導致我國老人撫養比逐年遞增,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在人口社會特征中,老年人隨著年齡的增大,不僅更需要家人的照料,并且照料需求的強度也會增強[3]。但是由于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流出,使得農村子女與父母在空間上隔離,老人們被迫成為空巢老人,無法獲得子女對自己正常的生活照料與精神慰藉。
(二)家庭養老功能持續弱化
學界大多數觀點皆認為:當前農村家庭養老功能在生活照料與精神慰藉方面存在弱化趨勢。首先在家庭結構方面,相較于傳統多子化社會中一對父母生有多個子女的情況,由于計劃生育的實施,現代社會的家庭呈現“4+2+1”的核心模式,在當今人們日益繁忙且精神壓力倍增的背景下,一對夫妻除了要撫養一個或幾個子女,還要供養四位老人,所以均分到單個老人的生活照料與精神慰藉顯得極為有限,其次在空間距離方面,農村子女外出務工從空間上與父母隔絕,在很多時刻,遠水難救近火,子女無法照護到父母的大小疾病、心理變化以及細微的生活需求等。
黃健元指出,許多學者只重點關注精神慰藉與生活照料這兩個方面,而忽視了經濟支持方面的強化。但就目前中國農村而言,許多老人即使沒有退休工資,也極少使用兒女的錢用于自身養老,相反的,由于老人一貫以來的勤儉作風與濃厚的家庭觀念,他們往往會幫助自己的兒女照看孫輩,以減輕他們的育兒負擔。所以筆者認為從經濟支持方面來看,外出務工的子女也并未為父母提供更優質的物質生活,一是由于進城務工的青壯年本身在城市的個人消費水平會比在老家有所上升,且即使有物質結余,擁有家庭資源優先享用權的也是他們的子女而非父母,即農村老人這一群體。
(三)尊老敬老的風氣逐漸消失
在我國古代小農經濟的背景下,皇權不下縣,鄰里關系緊密,彼此間在物質與精神上互幫互助的情況尤為普遍,由于家長制占據主導地位,所以尊老敬老的風氣盛行,鄉紳多由當地具有實質權威性的德高望重之人擔任,他們扮演著主持公道、伸張正義、維護村落和平及調節家庭內部或家庭與家庭之間大大小小的矛盾的角色,具有一定的公信力。一般來講,對于個別家庭子女的不孝行為會給予一定的批評教育甚至懲戒措施,這些皆是為政府所默許的行為,也是村民們所信服的評判,雖然這一約定俗成的鄉俗其合理性和科學性還有待商榷,但不可否認,在一定意義上,確實緩解了政府權力所管轄不到的一些家庭糾紛,維護了小范圍內的仁孝正義及老人的合法權益。
現代家庭中“養老不足,愛子有余”的代際重心下移的現象比較普遍,在農村,這種“重幼輕老”的現象更為明顯,一些家庭一切以孩子為中心,一切圍著孩子轉。這種“重幼輕老”的現象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長,也不利于老人的幸福養老[4]。
(四)農村老人的資源稟賦不高
個人稟賦主要是指個人所擁有的資源、素質或所表現出的個人特征[5]。從經濟資源的稟賦來看,相較于城市老人的經濟資源稟賦,農村老人明顯勢弱,大部分城市老人都享有退休金待遇,能夠更好地提升生活的品質,而農村老人經濟來源較為有限,尤其是部分女性老人,從未有過就業經歷,缺乏一定的就業技能,一直以來,都是依靠配偶賺取生活費用,到年老的時候,養老就顯得更加的被動;從人力資源的稟賦來看,由于農村人口的總體受教育程度不高,健康意識較為淡薄,精神生活的缺乏與急救常識的匱乏導致農村老人所占有的高質量的人力資源稟賦與城市老人之間還有一定的差距;從公共設施資源的稟賦來看,對于退出勞動力市場且身體機能不斷衰退的老人而言,豐富的基礎公共設施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緩解衰老焦慮,增添晚年生活的樂趣,城市老人所占有的資源就較為豐富,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諸如醫院、小區健身器材、商場、老年大學等應有盡有,城市老人無論是從物質生活還是精神生活來看都豐富多彩。相比之下,雖然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加速,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也逐步發展起來,但依舊存在諸多局限性甚至區域空白。
二、農村家庭養老面臨困境的原因
(一)現代化進程中計生政策實施的歷史結果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史上最為嚴格計生政策的實施以及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中國城鄉社會的家庭結構發生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傳統的大家庭模式逐漸被小家庭模式所取代[6]。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家庭戶平均人口為2.62人,較2010年的3.10人減少0.48人[7]。從家庭結構層面來看,與古代子女眾多情況相比,我國目前主要的家庭模式為“4+2+1”,人員單薄,且可利用的家庭內部人力資本極為有限,而中年人作為家庭的中流砥柱肩負著養老與養小的雙重責任,在市場競爭極為激烈的社會環境下,物價飛速上漲、育兒壓力等使得他們陷入即使孝心有余,而人力、財力、精力不足的窘境。
(二)傳統孝道宗親倫理的嚴重滑坡
從社會文化方面來看,自中國古代便有“百善孝為先”的優良文化,表現為封建時代將“忠與孝”作為判定人才德行的重要標準,在隋朝更有舉孝廉的人才選拔制度,在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中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生于斯長于斯”封閉性的社會共同體,共同體的穩定是由內在深層次的機理維系著,這當中最為重要的體現,正是“長老統治”[8],而近代以來,由于受到新文化運動與西方外來文化的影響與沖擊,孝道倫理意識逐步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經濟逐利意識與理性的自我發展意識占據思想的主導地位,加之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中,老年人的競爭力遠不如能更好地適應日新月異市場社會的年輕人,進而極大地削弱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權威性與地位,隨著家庭收入來源中農業收入比重下降,老年人的傳統種植經驗相對貶值,削弱了其家庭權威,造成老年人家庭地位下降[9]。甚至許多人將老人冠以“落后”“無用”之名,將老人的家庭價值與社會價值污名化。
(三)社會結構的變遷與傳統養老模式的失調
傳統社會中家庭存續的基礎就在于各成員對家庭的責任。與之相對,市場經濟運行的基礎則在于“經濟人”理性和利益最大化[10],在工業化、市場化進程中,家庭日益核心化,小型化,且社會的整體流動性不斷增強,很少有年輕人能在整個生命周期內從始至終生活在自己的家鄉,于是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具有滯后性,已不再適用于當前的社會結構,而新的養老方式又沒有應時而出,農村配套的社會化養老服務以及公共基礎設施缺失,導致農村家庭養老問題成為一直以來亟待解決的難題。
(四)鄰里之間的關系不斷疏遠
農村社會中,鄰里互助的風氣之所以不斷衰弱,原因在于農村三緣體系中的地緣關系衰弱,鄰里互助的和諧局面被打破,倫理關系瓦解。一方面,由于工業化發展使得遷徙或進城務工的現象越來越普遍,鄰居變動的可能性遠大于中國古代,導致鄰里之間的親密關系很難被構建;另一方面,目前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生活節奏都不斷加快,使得大多數人每天都過著忙碌的生活,無暇顧及周圍的人,互助意識便逐漸消退,加之隨著社會私有化的不斷發展與物質生活的不斷豐富,許多家庭能夠在各個方面自給自足,不再與周圍鄰居在平常有緊密的聯系與頻繁的往來,久而久之,導致鄰里互助的風氣不斷消逝。
三、鄉村振興視域下農村家庭養老的多維度思考
(一)政府層面:根據社會結構合理匹配公共服務
興建公共基礎設施,對基礎設施進行適老化改造。隨著農村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在人口基數難以在短期內發生改變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失能率水平[11],不僅能夠為返鄉勞動力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就業崗位,同時還能提升老年人生活水平,減輕家庭負擔,同時給予返鄉人員一定的遷回政策鼓勵如對有返鄉勞動力且子女與父母同住的家庭給予一次性小額補貼、給予返鄉勞動力就業優先的政策等,不僅能從現實意義上推動更多勞動力的回流,也體現國家對“三農”問題的重視以及對農村人口的人文關懷。
(二)社區層面:營造新型村民互助的良好氛圍
新時代應該賦予家庭養老在鄰里互助方面新的定義,旨在重構一套符合當前制度體系與現實需求的方法論,首先在每個村選舉一名德高望重的人輔助村支部協調村里內部關系,舉辦一些促進老人身心健康的親子活動以增進子女與老人之間的情感交流,其次可以設立一套獎勵機制,對村里在平時生活中經常照料或幫扶老人的村民給予表彰或一定的物質與精神獎勵,再則,組建一支訓練有素的中老年志愿者隊伍,由于中老年身體狀況良好,還未處于需要被照料的人生階段,且他們空余時間較之年輕人較多,在年齡方面由于跟老人較為接近,共情能力強,能夠更貼心地照顧老人。同時,由于青壯年返鄉,村里可以從每家挑選一名青壯年作為志愿隊后備軍,以應對一些突發緊急情況或解決特殊的技術性問題。
(三)工作單位層面:獎懲措施與道德教育并舉
一般來說,一個人求學生涯結束后至退休前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于工作,故一個企業的文化環境對員工個人人格價值觀的養成與塑造具有重要影響。因此,返鄉勞動力在進入當地企業就職以后,企業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去影響員工的盡孝思想與行為。
中國自古便有百善孝為先的傳統,時至今日,雖然時代的改變致使孝道倫理在不斷弱化,然而在整個社會價值體系中,孝順父母仍然是為人所稱贊的美德,孝順的子女總會更容易受到別人的尊重與信任,在工作單位這一復雜的集體中,受到尊重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人的尊重需要與自我實現需要是個人在滿足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后不懈追求的目標,獎勵孝行,在一定程度上不僅能夠為公司打造優良的企業文化,也能滿足子女的尊重需要與自我實現需要,還能切實地提升家庭養老的品質,可謂一舉三得。
(四)家庭層面:重塑新型家族孝道倫理
傳統的家庭生活方式是父輩與子輩、孫輩共同生活,子女有在年邁的父母身側照護日常起居的責任與倫理約束。《論語·里仁》有云:父母在,不遠游,也揭示了傳統家庭養老的模式。當前社會,要使所有子女都留在父母身邊盡孝已不再可能,而這時,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內部之間的宗親照護便不失為一種具有人情味的輔助養老方式,雙方可就照護方面的各個細則進行協商,達成一致,如此既能夠緩解遠在外地的子女的后顧之憂與心理負擔,也能夠讓老人感受到親情式的關懷與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