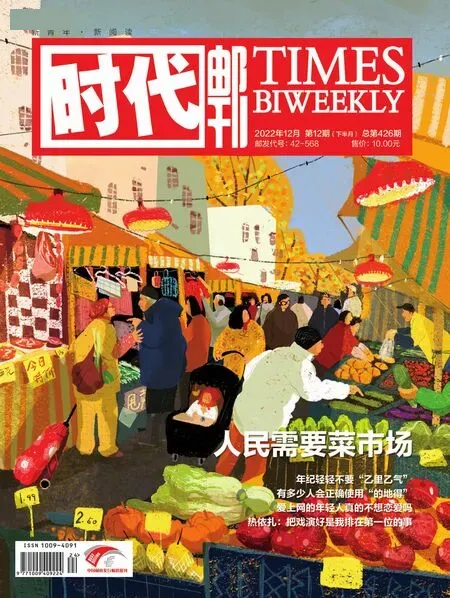《三悅有了新工作》:一堂珍貴的生死課
文于理

“小破站”出品、沒有流量明星,《三悅有了新工作》(以下簡稱《三悅》)意外成為今年國產網劇的一匹黑馬,在年輕人中收獲了高口碑和高人氣。
劇中的主人公名叫三悅,是一名95后,舞臺設計專業畢業,明明很優秀卻處處碰壁,再加上一直經受母親的言語打壓,內心不免受挫,于是不思進取地在家“躺平”了一年。
陰差陽錯之下,三悅去了殯儀館當遺體化妝師。三悅起初對這份工作充滿排斥,但她還是接受了,理由是可以氣到母親 — 最后果真得逞。這似乎是很多年輕人與父母“相愛相殺”關系的縮影:你不喜歡我干什么,我偏要干什么。
殯儀館每日為各種各樣的逝者送行,劇集以單元劇的敘事結構呈現,每集講述一個逝者的故事。貫穿整部劇的第一主題,就打消了觀眾對于殯葬從業人員的誤解與歧視。在這一點上,《三悅》與今年的熱門電影《人生大事》異曲同工。劇中有句臺詞說得很好,醫生是“生的守門員”,殯葬從業者是“死的擺渡人”,他們消除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幫助逝者更有尊嚴地離開。
《三悅》的另一個核心主題,與年輕人息息相關,它試圖幫助那些覺得生活很沒勁、一心想“躺平”的年輕人思考這么一個問題:我們該如何更好地、有所眷戀地活下去?由此,一個個逝者的故事,其實是這一堂生死課方方面面的案例,意圖讓觀眾對生與死有更深刻、更立體的思考。
有些人每當受挫了,就愛把“死”掛在嘴邊,好像這樣就徹底解脫了。三悅最初也是這么想的,她對于活著本就是厭煩的,她甚至羨慕一個罹患肺癌晚期的同齡人,她認為如果她有絕癥,就可以沒什么負擔地等死了。
人總是容易輕視自己擁有的珍寶。當三悅送走了一個個逝者,她漸漸發現手中就攥著珍寶:自己所厭棄的活著,是多少人所眷戀和渴望的東西。就像那個為了讓家人過上更好生活的修手機小哥,他活得那么用力那么無私,可死神還是不由分說奪走了他活著的權利;抑或是那個罹患白血病的孩童,他還有那么美好的航天夢要去實現,但命運沒有給他機會。
活著的意義,其實就在于活著本身,活著已經是莫大的勝利,哪怕暫時困頓,活著就意味擁有逆風翻盤的可能。就像殯儀館的老高說的,“活著是一輩子的事,死是一下子的事。”漫長的一輩子總會迎來柳暗花明,而“一下子”就意味著徹底地一了百了,所有的希冀、美好、奇跡都沒了,所有的日出日落、風輕云淡、碧海藍天都沒了。
年輕的觀眾很難擁有與三悅一樣的經歷,但經由三悅的視角,觀眾與她一起上了這一堂珍貴的生死課 — 以死亡為媒介,通往的是活著的大道。《三悅》沒有否定年輕人或喪或躺平的心態,而是共情他們的處境,給予他們一點積極的暗示與溫暖的鼓勵,讓他們“一百次說著要放棄,又一百零一次迎著太陽擠公車、擠地鐵、擠進生活風暴的縫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