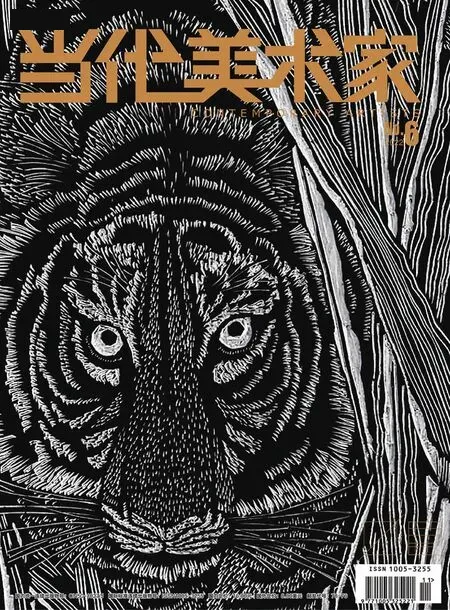現代主義視角的社會主義
——1949-1966年新中國美術的另類路徑
劉斯博 Liu Sibo
鄭勝天曾在《“社會主義現代主義”》一文中引用西爾弗伯格(Laura Silverberg)對這一現象的描述:“社會主義者將現代主義技巧與他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相結合的努力,打破了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參與共事與持不同政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西方現代主義之間的分界。”[1]并在文末提出疑問: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中國是否也有一種可被稱作“社會主義現代主義”的藝術現象?[2]這或許可以從1949—1966這17年間,在“蘇派”獨大的語境下,依舊秉持現代藝術觀念的藝術家們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描繪中獲得回應。
一、新中國社會主義美術的時代語境
1949年后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美術在指導思想上延續了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要求藝術為無產階級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大眾服務。[3]在創作方法上,受到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影響,盡管在1956年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1957年后又提出了民族化的“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相結合”的口號,但依舊沒有跳出蘇聯模式。
在1949—1966年這17年間,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成為新中國美術創作的主流范式。它在內容上要求樹立新中國形象,表現昂揚、光明、樂觀、團結的社會主義精神。在題材上以正面歌頌為主:一是展現黨的革命斗爭歷程,二是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成就和人民群眾的新氣象,三是塑造領袖和英雄人物,四是描繪富有政治寓意的山河風貌。美術界的創作面貌發生根本轉變,無論哪種派系的藝術家都迅速匯集到這些命題上來,產生了諸如胡一川的《開鐐》(1950)、董希文的《開國大典》(1953)、吳作人的《黃河三門峽·中流砥柱》(1955—1956)等經典主旋律作品。
此時“現代派”的藝術家也在竭力適應新時代的要求,他們對描繪社會主義中國是積極的。劉海粟在一次會議上就發表了慷慨的陳詞:“是什么力量支持著我這樣頑強地進行工作呢?是建設中的偉大祖國,是工人們的忘我勞動深深感染著我。”“我力求創造出具有鮮明思想內容的作品來,描寫人民在改造大地、改變自然風景中所起的作用。”“我相信在我的油畫創作里不僅僅只是發揚傳統,還表現了時代氣息。覺得自己畫的情調已經有所改變,表現了一種樂觀的情調。”[4]林風眠也曾表示:“因為常去工廠、農村走走,可以創作的題材也就很多,而且內容也都更接近現實。”“看看祖國的建設一日千里,面貌日新月異,加上那多嬌的江山,我的創作型興致越來越好了。”[5]
在形式技法上,1953年后中國的現實主義美術完全沿襲了蘇聯式的寫實風格,俗稱“蘇派”,尤其在1955—1957年蘇聯專家馬克西莫夫來華舉辦培訓班及20世紀60年代留蘇學員歸國后被普及化與正規化,影響至今。蘇聯現代繪畫的技術樣式以契斯恰科夫素描體系為造型基礎,繼承了“巡回展覽畫派”的傳統,尋求虛與實、整體與局部的辯證統一;輪廓清晰,塑造結實,強調立體感;同時注重塊面化的筆觸以及外光化、灰色調的色彩。在敘事手法上具有典型性和紀念碑性的特征。像王誠一的《信》(1957)、馮法祀的《劉胡蘭就義》(1957)、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壯士》(1959)、劉國樞的《飛奪瀘定橋》(1959)等美術創作都打上了濃郁的“蘇派”烙印。但這種照相般的寫實風格無疑造成了藝術樣式的單一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藝術個性的展開。
藝術個性必須服從于集體主義美學倫理,構建社會主義的文化視覺系統必然要對資產階級的藝術形式進行限制和批判,蘇派寫實主義一家獨大,現代主義藝術由顯學變為隱學,這是“十七年”時期社會主義美術的時代特征。在蘇聯沙文主義的影響下,印象派和印象派之后的美術被基本否定。[6]中國美術界從1951年開始對各種非現實主義進行清理,將一切非現實主義都歸于形式主義之中。例如1951年江豐對以林風眠為代表的“新畫派”發動批判,在師生中清除與現實主義藝術觀相對立的所謂“形式主義”的創作思想。[7]20世紀50年代后期,印象派亦被作為非現實主義、頹廢形式主義的代表,繼而成為腐朽反動、鴉片煙、怪畫等的代名詞。[8]
經過建國初期的整頓,現代主義藝術和藝術家逐步被邊緣化而淡出了官方系統。但在一些政治氛圍相對寬松的節點,一些“現代派”藝術家針對當時的現實主義藝術方法曾提出意見和批評。在1956年全國油畫教學會議上,美術家們就圍繞“風格”問題展開討論。如倪貽德發言說:“從人民對于藝術作品的要求和喜愛的復雜多樣化來說,都要求我們創作上風格多樣化。”“不能看到有些夸張、變形,或色彩強烈,筆觸粗放一點的畫就說是形式主義。”[9]1957年林風眠在《美術界的兩個問題》一文中指出:“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道路看得太狹小。”“尤其是以自然主義和學院派替代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美術創作,成為清規戒律。不同于他們的就扣上形式主義的大帽子,一棒打死。”“千篇一律、公式化、概念化的產品就大量出爐,霸占藝壇。”[10]不過1966年后,隨著這些“現代派”藝術家被徹底否定,現代主義的聲音在中國美術界也就銷聲匿跡了,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
二、社會主義美術中的現代主義藝術與藝術家
1949—1966年間以現代主義視角表現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藝術實踐主要從印象主義、表現主義、形式主義等不同維度展開,并結合了民族化的修辭手法。這些“現代派”的藝術家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部分是在20世紀前期就赴海外留學接受現代美術教育,并在1949年后長居新中國的老一輩畫家及其學生,如去歐洲的劉海粟、林風眠、顏文樑、周碧初、符羅飛、胡善馀,去日本的關良、倪貽德、譚華牧、衛天霖等,他們的風格深受西方現代主義藝術的熏陶。另一部分是建國后接受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培養的青年畫家,其中有20世紀50年代公派去東德學習的梁運清等人;也包括參加浙江美術學院“羅訓班”的金一德、夏培耀等人。這些東歐國家雖然處在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下,但他們的藝術風格卻沿襲了歐洲早期現代主義的傳統。還有一些是此間來華的外國藝術家,如羅馬尼亞的博巴和比利時的麥綏萊勒,為描繪新中國提供了現代主義的他者視角。
(一)印象主義的視角
印象主義作為現代藝術的先聲與“現代派”存在著親緣關系。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一批畫家經過民國時期的留學生涯或多或少都受到印象派的影響,無論是偏向自然主義學院派的吳作人、秦宣夫,還是后來走向表現主義或形式主義的劉海粟、關良、林風眠等。因此本節論述的藝術家和作品,一直在相對穩定的印象派范疇內,將豐富的色光關系、輕松細碎的筆觸等典型特征融進寫實技巧。正如林文錚所言:“印象主義介乎最精確之寫實和最浪漫的放肆之間。”[11]因此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語境下,印象派容易達成現實與個性間的平衡。
被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稱為“合格但保守的印象派畫家”[12]的顏文樑(1893-1988)在1964年創作了反映嘉興一大會址的經典之作《南湖》(圖1),表現出“旭日東方照耀紅,煙迷雨濛盡消空,燎原火自星星始,革命洪流起涌中”[13]的意境。這是一幅嚴謹又寫實的油畫,但印象派的格調令其在同類作品中亦顯得出挑并精彩:畫面光色處理得鮮亮通透,注重空氣透視與冷暖對比,筆觸細膩醇厚,整體氣氛溫潤又寧遠,平和且崇高。既在內容上以紅日點明了政治隱喻,又在形式上附和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欣欣向榮的基調。顏文樑以印象派技巧創作的反映新中國社會新象的油畫還包括《北京人民大會堂》(1953)、《人民大道》(1960)、《虹口公園人造山》(1962)等諸多作品。

1.顏文樑,《南湖》,布面油畫,35×69cm,1964
周碧初(1903—1995)早年受業于法國印象派畫家、修拉的好友歐內斯特·洛朗(Ernest Laurent)。1959年自印度尼西亞歸國后,始終在印象派的形態中描繪新中國的風貌。其中既有表現新社會山鄉巨變的《龍潭水電站》(1961)、《新安江水電站》(1963)、《農民新居》(1963)、《盛日新生活(曹陽新村)》(1964),也有取材于革命圣地的《茨坪》(1960)、《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1961)、《龍江書院》(1965)、《井岡山》(1966)《井岡山-黃洋界》(1966)等。但這些作品主要是從自身的人文角度出發來反映視覺性的風景,政治宣傳性較弱。如《井岡山-黃洋界》(圖2)就以一覽眾山小的氣勢描繪了蒼翠雄峻的自然云山,而時代主題則以紅旗等細節作點綴。周氏畫風在新印象派式的點彩樣式中融入了傳統“米氏山水”點苔的意蘊,筆觸短簇,疏落有序;其色彩純粹自然,變化豐富微妙,弱化色階而強調補色關系,從而使畫面充滿裝飾意味。

2.周碧初,《井岡山-黃洋界》,布面油畫,82×131cm,1966
胡善馀(1909—1993)的作品也在寫實主義中葆有強烈的印象派和后印象派風味。他早期在杭州藝專師從林風眠、蔡威廉,就對印象主義產生興趣,后又留學法國,更鐘情于畢沙羅、西斯萊、莫利索等大師的技法。其畫作顏色燦爛、筆觸雅拙、輪廓松散,又聚合了東方線條的酣暢,折射出虛靜脫俗的寫意之趣。胡善馀的風格與當時的蘇派畫法顯然格格不入,但他依舊泰然自若地繼續著自己的藝術追求,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達到了創作高峰,筆耕不輟地描繪了大量關注祖國風物、社會主義建設的作品。例如他的《新安江水庫夜景》(1959)(圖3)以深湖藍色鋪滿夜空和水面,再疊加檸檬黃色的燈光和倒影,筆法概括輕松,和凡·高的《羅納河上的星夜》(1888)在色彩、構圖等方面都頗有相似之處。潘耀昌評價胡善馀的畫在蘇派氛圍中“好像一顆閃閃發光的鉆石,以一種迥然不同的面貌呈現出來。”[14]

3.胡善馀,《新安江水庫夜景》,紙板油畫,36×60cm,1959
此外,以印象派畫風融合中國民間藝術語言而著稱的衛天霖(1898—1977)也創作過《礦區小景》(1958)、《土火車》(1959)、《礦工》(1963)等現實題材作品。許幸之(1904—1911)的《打場》(1955),唐蘊玉(1906—1992)的《農閑》、《學習小組》(1950)、《古麗雅的道路》(1956),方干民(1906—1984)的《農場》(1962),林達川(1912—1985)的《水庫》(1957)等作品也均帶有印象主義的余韻,此處不再贅述。
(二)表現主義的視角
中國現代藝術中的表現主義傾向在借鑒了后印象主義、野獸派、北歐表現主義等西方現代流派手法的同時,又混雜了傳統文人畫中的寫意甚至抽象的語法,具有熱情的繪畫精神。
作為“藝術叛徒”的劉海粟(1896—1994)本不敢也無法涉足主題性創作,[15]但身處時代洪流中的他亦于1956年創作了油畫《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圖4)。這幅作品直接、正面地描繪了是年上海群眾游行時喜慶熱烈的現實場面,畫中充滿了紅色元素——條幅、標語、旗幟,加之全景式的宏大構局,與費以復于1954年作的《五一節上海大游行》有異曲同工之處,后者是典型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然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在形式上更像是一張后印象主義十足的風景畫:遒勁松動的筆觸與較為稀薄的顏料使畫面充滿寫生感,高飽和的色彩與勾勒物像的黑線又使圖像趨于平面化。而在《打鐵》(1950)、《佛子嶺水庫》(1954)、《農村風景》(1963)、《挑河泥》、《打夯》(“十七年”時期)等深入工農生活采風的作品中,劉海粟偏向于凡·高和野獸派的表現性風格則更為顯現。對比劉海粟的《打夯》與王文彬同題材的《夯歌》(1962),可以直觀感受到他與流行風格的差異。

4.劉海粟,《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布面油畫,94×94cm,1956
關良(1900—1986)曾求學于日本,在那里他接觸到高更、塞尚、馬蒂斯等歐洲現代藝術家的作品,深受啟發。他將現代風格的“粗糙美”與八大山人、石濤等中國畫家強調的“逸筆草草”結合起來,畫風似兒童般稚拙。“十七年”時期關良創作的社會主義題材作品比較豐富,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類型:一類是少量的敘事性主題創作,如《中朝友誼》(1950)、《學生下鄉訪農記》(1953);其次以人物為主表現工農群眾的勞作場景,如《火紅的年代》(20世紀50年代)、《山鄉農忙》(1958)、《豐收的季節》、《除蟲》(圖5)、《養豬人家》(20世紀60年代)等;第三類以景物為主表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建設,如《高爐》(1950)、《軋鋼廠》(圖6)、《煉鋼廠》、《廣州造船廠》(20世紀50年代)、《新安江大壩》(“十七年”時期)等。在這些作品中,關良以灑脫渾厚的用筆、弗拉芒克式的色彩、單純生動的造型消解了主旋律視覺的嚴肅與崇高,更多地讓觀者感受到了畫家在作畫時恣意涂抹油彩時的快感,以及他恬然平和的心境。

5.關良,《除蟲》,油畫,30.2×35cm,1960

6.關良,《軋鋼廠》,布面油畫,39×52cm,1950
與關良同期留學日本的譚華牧(1896—1976)常被稱為中國現代美術的“失蹤者”,是一位游離于主流視域之外的畫家。譚氏1956年自澳門回廣州定居后以表現性的現代主義風尚創作了大量反映時代新象的日記般的作品。從游園的紅領巾到集體訓練的隊列再到赤腳下田的農婦,這些主旋律的元素雜糅了盧梭式的疏離感以及宋元繪畫的空靈感,點綴進畫家詩意又摩登、顛覆又內斂的視覺空間,顯示出一種孤寂但溫柔的拙趣。李偉銘將其形容為在高亢激越的“大合唱”時代中以一支貼身拐杖為伴自憐自惜地游吟。[16]《春耕》《和風》《爐》《推一把》《收獲》《隊列》(20世紀50—60年代)等作品就是他這一時期以小我抵抗喧囂的寫照。
符羅飛(1897—1971)很早就成為了一名共產主義者,他的藝術底色充盈著戈雅式的革命浪漫主義精神,游藝歐洲回國后,在對現實的悲憫與觀照中又展露出德國表現主義的自由不羈、渾厚深沉。他曾表示“我們的主題必須正確而明顯,但我們的技巧卻應該有高度的藝術價值。為了表現得強烈,我們不妨用浪漫的作風。”[17]又說道:“現實主義,不是如實地寫生,而是畫家的主觀表現,要求通過對象的客觀形象,藝術地再現。”[18]解放后符羅飛畫了很多表現土改運動和日常勞作的素描、粉畫、水粉畫和彩墨畫。如他與王式廓在20世紀50年代都創作過表現憤怒的人群控訴剝削階級情節的素描,但不同于《血衣》經典的“蘇派”風格,符羅飛在《訴苦會》(1951)中那珂勒惠支式的處理則更具視覺感官上的壓迫與張力,粗黑的線條洋溢著對時代不加修飾的個人激情。
(三)形式主義的視角
中國現代藝術中的形式主義受到西方后印象主義、立體主義、新藝術運動等現代思潮的影響,并力求嫁接中西,強調藝術語言本身的獨立審美價值,以理性的結構分析和感性的自由表達為特征,[19]追求形式美感。
林風眠(1900—1991)的藝術實踐以形式主義為出發點,在審美現代性、繪畫本體性、中西融合的實驗中進行了極富開創性的探索,并在20世紀50年代后愈發成熟。他在《跨入一個新的時代》中寫道:“尤其是許多油畫工作者,不但要學習工農群眾的優良品質來改造自己,就是在他們的美術創作表達的方法上,也要去學習,成為自己新的推動力量去掌握自己的技術。”[20]這一時期,林風眠吸收了當時流行的年畫、農民畫中樸素爛漫的造型特點,創作了一系列“豐收”“漁獲”等表現婦女群眾的作品,人物形象充滿童真稚趣。如《兩個女民兵》(1958)(圖7)中他用黝黑極簡的線條勾畫出如仕女般的女民兵形象,沒有刻意展現她們政治化的昂揚英姿,而是以悠然含蓄的情緒表現了其生活化的一面。在《漁村豐收》(約1950—1960)(圖8)中,林風眠以飛動銳利的弧弦分割構圖,將富有時代特征的東方捕魚人刻畫得猶如“亞威農少女”,極具主觀性和辨識度。在這些濃墨重彩、方圓有序的畫作里,他把自己創立的中國式立體主義手法運用到適合中國現實生活的題材中,并在一定程度上理想化、浪漫化。[21]這些與“正統風格”截然不同的現實主義作品在“十七年”時期注定是被冷落的,但卻遮蔽不了林風眠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美術邊界的多元化拓展。

7.林風眠,《兩個女民兵》,紙本彩墨, 51×52cm,1958

8.林風眠,《漁村豐收》,布面油畫,78×80cm,約1950-1960
同樣注重形式美與中西調和的畫家還有倪貽德(1901—1970)。他早期的藝術思想在1932年由其執筆的決瀾社宣言中便展現得直接而熱烈——“用狂風一樣的激情,鐵一般的理智,來創造色、線、形交錯的世界……要自由地,綜合地構成純造型的世界。”[22]抗戰之后,倪貽德受時局感召,并接觸到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著作,政治上貼近左翼,藝術觀念也發生較大轉變,提倡新寫實主義,主張“藝術為人民”,但在形式風格上依舊保有現代主義的余溫。他認為“舊的寫實只是照相式的羅列與堆積,這種新的寫實是經過主觀的選擇取舍,經過20世紀初期繪畫技法的洗禮,采取一種著重效果的表現法,強化事實的表現,同時形成繪畫本身的造型體系。”[23]從1950年倪貽德創作的兩幅罕見的主題性油畫《修好汽車,支援前線》和《骨干會議》中可以看出,盡管畫家對“典型性”的理解還不成熟,但在人物的變形和對邊緣線的處理上卻也個人風格明顯。在《建設中的長江大橋》(1956)、《杭州煉油廠》(1958)、《建設工地》(1960)等建設題材作品中,倪式語言則更為鮮明:強調畫面的構成感,善于運用濃重堅實的直線來組成幾何化的形體,以簡馭繁,筆觸粗放果斷,色彩明快沉著,洗練準確地刻畫出物質的內在精神。
(四)“德派”“羅派”與他者視角
1955年后,中國開始實施“請進來,派出去”政策,加之中蘇關系趨緊,中國與東歐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間的文化往來愈發緊密。1956—1961年,中國公派了一批留學生赴民主德國。1960—1962年,中國邀請羅馬尼亞專家埃烏琴·博巴(Eugen Popa1919-1996)在浙江美術學院開辦油畫培訓班,即“博巴班”或“羅訓班”。這些東歐國家提供了更接近現代主義的美術教學方式,對應于主流的“蘇派”,俗稱“德派”和“羅派”。與此同時,在“十七年”時期,亦有許多來自波蘭、民主德國、比利時、英國、墨西哥等國的藝術家來華交流參訪,并以他者視角表達了對新中國的理解。
今天中國語境里的“德國學派”依舊鮮有耳聞,在當年“蘇派”一統江湖的時代里更是被歸作異聲。1956年,梁運清(1934—)、全顯光(1931—)、舒傳曦(1932—)等人前往不同于蘇聯美育系統的民主德國學習,并帶回了一套教學方法。“德派”風格受到德國表現主義的影響,且崇尚理性精神。在造型上,以線條和結構為主,而非明暗調子;在藝術效果上,概括、拙厚、大刀闊斧而非繁復雕琢。[24]梁運清1961年在德累斯頓造型藝術大學的畢業創作是壁畫《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盡管內容主題性十足,但從其堅實硬朗的線稿中就可看出他對結構的深入理解和強調。他20世紀60年代回國后創作的《陜北漢》《廣東海陵島》(1964)等油畫也帶有明顯的“德派”韻味。
博巴的文藝觀雖然是現實主義的,但他的學術思想、繪畫風格、教學觀念卻是迥異于“蘇派”的全新模式。博巴強調造型本質,注重結構和線的表現性,色彩上以固有色和裝飾色為主,反對機械似地照抄對象的光影、畫得面面俱到。他認為應更為關心藝術的個性和感染力,主張釋放主觀的藝術激情。博巴曾講道:“在統一的政治目標下,應該在藝術風格和藝術表現上做出多種多樣的探討,堅持同一藝術潮流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應有不同的風格和面貌。”[25]經過“博巴班”的培訓,學員們的作品形態發生了較大轉變。例如夏培耀(1934—)創作的《擴建中的502電廠》(1962)(圖9)以厚重的黑線提煉出物象的結構,筆法肆意松弛,表現主義風格濃烈。而金一德(1935—)在1959年創作《爐前入黨》時還是鮮明的蘇聯式畫風,但到了1964年創作《農村支部》時,人物造型就強化了線的作用,對結構的歸納也更顯概括和肯定。

9.夏培耀,《擴建中的502電廠》,46×71cm,布面油畫,1962
博巴和他的妻子在華兩年非常勤奮,以另類的他者視角創作了大量表現中國風土人情的油畫、速寫以及水墨作品。“他者”的差異不僅反映在現代性的藝術風格上,也體現在對具體描繪對象的選擇上。《博巴油畫訓練班專家活動簡報》中曾記載:“(專家和夫人)比較愿意到偏僻的地方畫畫,本周到郊區去過兩次,那個地方房屋矮小、大小帆船也很舊,但他們說很美,對我們的西湖反而沒有畫。”[26]他的現實題材油畫《出工》《建筑工人》(20世紀60年代)(圖10)等被官方評價為“藝術形式方面受現代派的影響,反映在刻畫工人的精神面貌方面不是很強。”[27]像博巴這樣,在以異域目光表達新中國印象的外國藝術家中,比利時著名版畫家法朗士·麥綏萊勒(Franz Masereel)(1889—1972)也是比較突出的一位。他是進步的左翼人士,早在20世紀30年代即被魯迅介紹到中國,1958年受邀訪華,參觀了北京、武漢、上海等地。麥綏萊勒以冷峻的現代主義視角畫了若干幅描繪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以及大煉鋼鐵場景的素描(圖11),并在之后創作了《回憶中國》系列版畫。這批作品運用擦拭涂抹等手法,筆力簡潔而生猛,黑白對比強烈,造型異質渾拙,具有詭秘而壓迫的氣氛。

10.埃烏琴·博巴,《建筑工人》,布面油畫,90×120cm,1960

11.法朗士·麥綏萊勒,《熱火朝天的北京》,素描,31.5×48cm,1959
余論
當然在前述這些“正統”的現代主義畫家之外,還有一些藝術家的實踐則更具復雜性、多樣性。例如胡一川本是傳統意義上的革命美術家,但其藝術創作亦包含了對現代主義語言的某種轉譯。據蔡濤考證,胡一川1961年創作的《前夜》就與凡·高的《吃土豆的人》和塞尚的《玩紙牌者》存在著關聯性。[28]由于歷史的局限性,“現代派”藝術和藝術家在這一時期大多被孤立和否定,現代主義風格的社會主義題材作品被長期埋沒、忽略,知名度和認可度相對較低。但一些畫作在當時也并不都是“在野”的與“不可見”的,如劉海粟的《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不僅登上了上海作協刊物《文藝月報》1956年3月的封面,還被印成了宣傳畫而發行全國;倪貽德的《建設中的長江大橋》收錄于《美術》雜志1956年12月號;譚華牧1958年作的《春耕》亦被中國美術館收藏。這也表明在1949—1966年期間,一些折衷主義的現代藝術形式在社會主義語境里尚有緩存空間。
通過對“十七年”時期社會主義美術中現代主義視角創作的梳理,或許可以呈現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主義”現象的一個側面。“現代派”藝術家在構建新中國的圖景上為我們探索出一條有別于“蘇派”的另類路徑:在內容上,雖然圍繞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展開,但基本看不到表現重大革命歷史主題的作品,英雄和領袖肖像也鮮有涉及,而多以表現新中國的群眾面貌、建設場景和紅色名勝為主。貼近生活的人物和風景題材更易使他們原有的藝術方法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語境里轉化,因此也更易獲得“現代派”藝術家的青睞。在風格上,將多維并蓄的西方現代藝術形式與民族性的傳統藝術語言廣泛結合,強調藝術個性與繪畫語言本身的表現張力,大多充滿人文關切,為嚴肅的政治宣教情境注入了藝術的柔化劑。
以現代主義風格表現社會主義不甚符合當時中國民眾的觀看經驗,以及體制的宣傳話語。但如今來看,這些樣式與時代相左的作品作為“十七年”時期社會主義美術的一種旁注和副本,突破了對特定時期風格表征的程式化印象,更凸顯其藝術史價值。在圖像上,這些作品為我們提供了在主題先行的現實主義作品之外更加接近日常的歷史文本,以人性化的視角讓人們能夠更加真切地體悟到當時的時代風貌。在藝術上,鮮活的現代主義形式為觀者帶來了更為感性和多元的審美判斷,豐富了新中國社會主義美術的表現語言。諸位“現代派”藝術家前輩們在面對主題性創作時大多沒有做流于表面的粉飾,而是在肉身與時代的糾纏中尊重了內心的自我選擇,實踐了藝術自覺,保留了藝術家的執著堅守和不卑不亢,更延續了新中國美術的現代性火種。在形塑新中國的過程中,現代主義并沒有缺席,它作為對社會主義美學的反叛和補位,也成為歷史的一種證據。
注釋
[1]鄭勝天:《“社會主義現代主義”》,《油畫藝術》,2014年第2期,第84—85頁。
[2]同上。
[3]鄭工:《演進與運動:中國美術的現代化(1875—1976)》,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02年,第266頁。
[4]劉海粟:《在政協上海市三屆委員會大會上的發言》,1962年7月,載于《劉海粟藝術文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年,第183—184頁。
[5]林風眠:《老年欣逢盛世》,《文匯報》,1959年9月8日。
[6]王鏞:《中外美術交流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67頁。
[7]同[3]。
[8]顏榴:《印象派與20世紀中國藝術》,中央美術學院,2007年,第81頁。
[9]《關于油畫教學、技法和風格等問題—全國油畫教學會議的若干問題討論紀要》,《美術》,1956年12期,第8頁。
[10]林風眠:《美術界的兩個問題》,《文匯報》,1957年5月20日。
[11]林文錚:《由藝術之循環規律而探討現代藝術之趨勢》,1928年,載于鄭朝:《西湖論藝》,浙江: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9年,第106頁。
[12][英]蘇立文:《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上)》,譯者:陳衛和、錢崗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2頁。
[13]顏文樑為畫作的題詩《南湖旭日》。
[14]潘耀昌:《緣而葆真 清而容物—評胡善馀油畫的風格特性》,《新美術》,1993年第1期,第27頁。
[15]同[3]。
[16]李偉銘:《尋找“失蹤者”的蹤跡:譚華牧(1898—1976)及其繪畫—兼論現代主義在20世紀中國美術歷史中的命運》,《美術研究》,2004年第4期,第27頁。
[17]《我們需要有血有肉的藝術——符羅飛教授訪問記》,《建國日報》,1946年8月22日。
[18]董丹東:《與人民同心 與時代同步——符羅飛評傳》,載于《華南理工大學名師——符羅飛》,廣州 :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80頁。
[19]同[3]。
[20]林風眠:《跨入一個新的時代》,《文匯報》,1959年1月1日。
[21]汪滌:《林風眠之路——林風眠生平、創作及藝術思想評述(1937—1977)》,《林風眠之路——林風眠百歲誕辰紀念》,浙江: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9年,第67頁。
[22]決瀾社:《決瀾社宣言》,《藝術旬刊》,1932年第1卷第5期。
[23]倪貽德:《戰后世界繪畫的新趨勢》,1947-1948年,載于林文霞主編《倪貽德美術論集》,浙江: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1993年,第64頁。
[24]詳見王新:《孤往雄心——發現“德國學派”藝術大師全顯光》,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83頁。
[25]徐君萱、金一德:《博巴油畫示范教學筆記》,《新美術》,1981年第3期,第9頁。
[26]陳琦:《江水如藍——博巴油畫訓練班研究》,浙江: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8年,第14頁。
[27]同上。
[28]詳見蔡濤:《塞尚、街頭劇和“土油畫”——藝術家胡一川的跨媒介實踐(下)》,《美術學報》,2018年第5期,第70—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