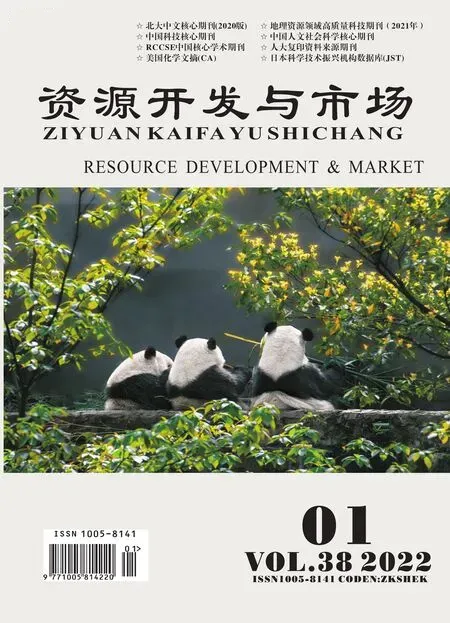交通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研究
——基于成渝雙城經濟圈的時空數據分析
潘林偉,林子雄
(重慶交通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重慶 400074)
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交通基礎設施通過加速生產要素在市場上的流通,有效地降低運輸成本,以促進經濟要素的集聚或擴散,最終達到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目的[1,2]。“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統籌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加快建設交通強國”,從國家宏觀政策層面體現了交通基礎設施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已有研究在全國、省域層面證明了交通基礎設施對經濟發展的有效促進作用,但如果考慮到不同區域地理條件和資源稟賦的差異性,交通基礎設施對各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是不盡相同的。此外,交通基礎設施網絡狀的分布特征決定了其空間上存在相互依賴關系,而以往較多計量研究在模型中忽略了空間因素,且未深入探討交通基礎設施對經濟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使分析結果存在一定的偏差[3]。基于此,本文以成渝雙城經濟圈為研究對象,選取2003—2019 年的城市時空面板數據,在4 種空間權重矩陣下,實證檢驗和分析了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自相關性和交通基礎設施對經濟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并據此提出政策建議,以期豐富和拓展相關研究,為推動成渝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與協調發展提供參考。
交通基礎設施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一直是國內外學者的關注熱點,已有文獻的研究方法從發展歷程上來看大致為:時間序列→面板數據→空間計量。Aschauer[4]利用時間序列模型對美國核心基礎設施的產出彈性進行了研究,發現交通基礎設施具有顯著的生產率效應;宗剛、黃壽峰等[5,6]通過對我國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得出交通基礎設施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鑒于時間序列數據可能會帶來“偽相關”問題,后續研究轉向了面板數據分析。如,劉生龍、徐瑾等[7,8]基于我國省域面板數據,得出交通基礎設施對經濟發展有顯著的拉動作用,但由于時空異質性的存在,作用程度存在差異;趙春娟[9]對“21 世紀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13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發現交通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起抑制作用。隨著新經濟地理學和空間計量經濟學的發展,空間因素被納入到交通基礎設施對經濟發展的溢出效應研究中。如,Douglas、Amy[10]基于空間計量方法對美國高速公路的溢出進行了研究,未發現顯著的正向地理溢出效應;Boarnet[11]在美國加尼福利亞州1969—1988 年所轄各縣面板數據的空間回歸結果中發現,公路交通基礎設施的溢出效應顯著為負;李慧玲、陳軍[12]對我國1995—2015 年省級面板數據進行了空間計量回歸,得出交通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發展呈現出顯著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樊建強、李璐[13]基于陜西省各市的相關數據,在不同空間計量模型下,通過效應分解發現該省交通基礎設施存在負向空間溢出。
綜上,基于空間計量方法探討交通基礎設施對經濟發展的溢出效應成為重要的研究趨勢,但溢出效應的方向尚無定論,主要分為正效應、負效應和不顯著3 種情況,這與研究對象和研究尺度的選擇有關,需根據實際情況,采用相應空間計量模型進行分析。同時,部分空間計量研究僅采用單一空間權重矩陣,未在多種權重矩陣下進行對比分析,導致研究結果缺乏穩健性和可靠性。此外,一些研究未將交通基礎設施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進行效應分解,得到的空間溢出效應也存在偏差。本文的貢獻在于:①聚焦成渝雙城經濟圈,將考察期向后推進,豐富了特定區域視角下交通基礎設施對經濟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研究。②設定并基于4 種空間權重矩陣,通過系列檢驗,確定各權重矩陣下合適的空間計量模型,提高了實證結果的穩健性和可靠性。③通過效應分解,準確地分析交通基礎設施對成渝雙城經濟圈經濟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提高了建議的針對性。
1 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1.1 變量選取
經濟發展水平(PGDP)是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了消除價格因素的影響,本文以2003 年為基期對原始數據進行了平減處理,得到實際人均GDP 以衡量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交通基礎設施水平(TRAN)是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鑒于市級層面的鐵路和水運等交通工具數據難以獲取,本文以公路密度作為基礎,通過間接折算的方式,把鐵路、水運、航空等交通運輸方式的影響全部反映到公路密度中,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i 和t 分別為城市和年份;road 和S 分別為公路里程和土地面積;pt 和gt 分別為總客運量和總貨運量;roadpt和roadgt分別為公路客運量和公路貨運量。
綜合已有研究,本文從區域內部現狀、對外交流和政府效能3 個角度出發,加入以下6 個控制變量:①人力資本水平(HC)。人力資本水平通過影響城市的創新發展,進而影響城市的經濟發展,本文以城市當年高等學校在校學生總人數占全市年末常住人口數的比重來表示人力資本水平。②工資水平(WAGE)。工資水平通過影響城市居民的支出,進而影響城市的經濟發展,本文選取城市在崗職工的年平均工資來表示工資水平。③市場內部潛力(IMP)。本文采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城市內部距離(城市行政區劃半徑的三分之二)的比值來衡量市場內部潛力。④產業結構(TIND)。城市的產業結構也影響著經濟的發展,本文以第三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來表示產業結構。⑤對外開放水平(DWKF)。地區對外開放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影響生產效率來影響城市經濟的發展,本文以各市當年實際利用外資額占名義GDP 的比重來衡量對外開放水平。⑥政府參與程度(GOV)。地方政府在宏觀調控、資源配置和體制機制建設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本文采用財政支出占名義GDP 的比重來表示政府參與程度。
1.2 數據說明
為了便于數據的統計,本文研究涉及成渝雙城經濟圈的16 個城市,分別為:重慶市、成都市、自貢市、瀘州市、德陽市、綿陽市、遂寧市、內江市、樂山市、南充市、眉山市、宜賓市、廣安市、達州市、雅安市和資陽市。原始數據于2004—2020 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重慶市統計年鑒》《四川省統計年鑒》和區域內其他各市的統計年鑒,對個別缺失數據,本文進行了線性插值處理;構建空間權重矩陣所需的經緯度坐標來源于國家地理信息中心發布的中國基礎地理信息數據。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2 研究方法
2.1 空間權重矩陣
作為空間計量研究的核心部分,空間權重矩陣W的基本形式如下:

式中,n 為空間單元數;wij為單元i 和單元j 之間的空間權重。
為了避免單一空間權重矩陣的局限性和對結論的影響,本文在王磊、曾剛[14,15]的研究基礎之上拓展設定了4 種空間權重矩陣,以此作為空間計量分析的基礎。
簡單0—1 權重矩陣(W- 0-1):采用Queen 相鄰的方式設定簡單0—1 權重矩陣,wij-0-1為:

地理距離權重矩陣(W- dis)。采用經緯度距離平方的倒數設定地理距離權重矩陣,wij-dis為:

K最近鄰權重矩陣(W- kn):根據經驗規則,本文將K值設置為3,構建3-最近鄰權重矩陣,wij-kn為:

新經濟距離權重矩陣(W- eco):本文以城市間人均生產總值差額的絕對值代表“經濟距離”(由于人均生產總值這一指標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因此本文選取每個城市考察期內的平均人均生產總值來進行計算),同時考慮地理距離,得到新經濟距離權重矩陣,wij-eco為:
2.2 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
區域內存在空間自相關性是進行空間計量分析的先決條件,本文引入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ESDA)方法,通過描述樣本數據的空間分布,以探索樣本在研究區域范圍內是否存在空間自相關性,為后續使用空間計量模型提供了依據。具體而言,本文采用全局莫蘭指數和莫蘭散點圖從全局和局部兩個維度對成渝雙城經濟圈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自相關性進行了探索,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n表示城市數;xi和xj分別表示城市i 和j經濟發展水平的觀測值和S2分別表示各觀測值的均值和方差;IG表示整個區域的全局莫蘭指數,IG∈[-1,1]。IG>0,為正向空間自相關,即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城市呈現集聚分布狀態;IG<0,為負向空間自相關,即經濟發展水平相異的城市呈現集聚分布狀態;IG=0,為無空間自相關,呈現隨機分布狀態。Ii表示i 城市的局部莫蘭指數,其判定方式與IG相似,將其進行可視化呈現,可得到莫蘭散點圖。
2.3 空間計量模型
遵循空間計量研究的思路,本文先設定不考慮空間因素的交通基礎設施對經濟發展影響的普通面板計量模型:

式中,i和t 分別為城市和年份;PGDP 和TRAN分別為經濟發展水平與交通基礎設施水平;X 為控制變量組;β0為常數項;β1、β2為待估參數;ui、δi分別用來控制地區和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誤差項,且服從正態分布。
地理學第一定律(Tobler′s First Law)指出,任何事物都與其他事物相關,只是相近的事物關聯更緊密[16]。普通面板計量模型并沒有考慮到地區之間也會存在相互影響,因此本文在公式(9)中分別加入不同地理單元之間的空間依賴變量,得到以下空間面板計量模型。公式(10)—(12)分別表示空間誤差模型(SEM)、空間滯后模型(SAR)和空間杜賓模型(SDM):

式(10)—(12)中,W 為空間權重矩陣;Wσit、WlnPGDPit、WlnTRANit和WlnXit分別為隨機誤差項、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空間交互項;ρ、λ、θ、η為待估參數。
3 成渝雙城經濟圈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
3.1 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
本文根據公式(7)計算了2003—2019 年成渝雙城經濟圈經濟發展水平的全局莫蘭指數,結果見表2。由表2 可知,W-0-1 矩陣下各年份的全局莫蘭指數值均為負但不顯著,而在另外3 種空間權重矩陣下,其值都至少在10%水平上顯著為正。且明顯可以看出,W- kn 矩陣下的全局莫蘭指數值最大且最顯著,即在考慮經濟與地理雙重因素下,成渝雙城經濟圈內部經濟發展水平的正向空間自相關性最強。不同的空間權重矩陣選取會影響結果,故本文設定多種空間權重矩陣。在后3 種空間權重矩陣顯著性的保證下,成渝雙城經濟圈內部經濟發展存在較為穩定的正向空間自相關性。

表2 2003—2019 年成渝雙城經濟圈經濟發展水平的全局莫蘭指數Table 2 Global Moran′s I index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Chengdu- 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from 2003to 2019
3.2 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
為了進一步觀察區域局部經濟發展的空間集聚特征,本文以W- eco矩陣為例,根據公式(8)計算了2003年和2019 年的局部莫蘭指數,并將其可視化得到莫蘭散點圖(圖1)。總體上看,位于第一象限、第三象限的城市數量明顯多于第二象限,第四象限無城市樣本點,即區域內各城市間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自相關模式以H- H(高—高)集聚和L- L(低—低)集聚為主,極少部分是L- H(低—高)集聚,不存在H- L(高—低)集聚。從年份的對比來看,各象限所分布的城市數量變化不大,表現出較為穩定的分布特征,這說明區域內部經濟發展呈現出較為穩定的正向空間自相關性,與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中得出的結論相契合。綜合全局和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的結果可知,成渝雙城經濟圈的經濟發展存在顯著且穩定的空間自相關性,具備研究空間溢出效應的基礎,可進行空間計量分析。

圖1 成渝雙城經濟圈2003 年、2019 年經濟發展水平的莫蘭散點圖Figure 1 Moran scatter char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Chengdu- 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in 2003 and 2019
4 空間計量實證與分析
4.1 模型檢驗與選擇
在進行空間回歸前,需要在前文設定的SEM、SAR和SDM共3 種空間計量模型中進行具體選擇。遵循模型選擇流程(圖2),得到拉格朗日乘數(LM)檢驗結果(表3)。

圖2 空間計量模型的選擇流程Figure 2 Selection process of spatial measurement model

表3 拉格朗日乘數檢驗結果Table 3 Lagrange multiplier test results
從表3 可見,W-0-1、W- dis 和W- kn 矩陣下,誤差拉格朗日乘數(LM-error)的穩健形式均不顯著,因此應選擇SAR;而在W- eco 矩陣下,滯后拉格朗日乘數(LM-lag)和誤差拉格朗日乘數(LM-error),以及它們的穩健形式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因此應選擇SDM。
在確定具體模型后,本文按照圖3 所示流程進行了效應識別的Hausman 檢驗和SDM 穩健性的LR檢驗,得到表4 所示的結果。由表4 可知,Hausman檢驗的統計量均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即模型應采用固定效應。固定效應的LR 檢驗中LR(both-ind)和LR(both-time)統計量均在1%水平上顯著,進一步表明模型應采用雙向固定效應。SDM 穩健性的LR 檢驗中LR(SDM-SAR)和LR(SDM-SEM)統計量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即W- eco矩陣下選擇SDM是穩健的。綜上所述,本文最終的模型選擇方案為:W- 0-1、W- dis 和W- kn 矩陣下采用帶雙向固定效應的SAR;W- eco 矩陣下采用帶雙向固定效應的SDM。

表4 模型效應識別和穩健性檢驗結果Table 4 Model effect indentification and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圖3 模型效應識別和穩健性檢驗流程Figure 3 Model effect indentification and robustness test process
4.2 實證結果與分析
為避免實證結果的有偏或無效,本文采用準極大似然估計法(QLME),在4 種空間權重矩陣下根據相應模型分別進行了空間回歸,回歸結果表5。

表5 4 種空間權重矩陣下各模型回歸結果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each model under four spatial weight matrices
表5 的回歸結果顯示:空間自相關系數rho 均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成渝雙城經濟圈內部經濟發展存在著空間依賴性,即其中某一城市的經濟發展會受到其他城市經濟活動的影響,也再次驗證了本文采用空間計量模型的合理性;核心解釋變量lnTRAN均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控制變量除了lnWAGE 和lnDWKF 外也都有較好的顯著性;R-sq和Log- L 值較理想,表明模型整體解釋性較強。總的來說,4 種空間權重矩陣下各模型的回歸結果都較理想。
在空間計量模型中,解釋變量的變動在對本地產生影響的同時,還會影響其他地區,故不能直接把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參數估計結果作為影響效應[17]。參考Lesage、Pace[18]的研究,本文基于偏微分的運算原理把交通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發展的總效應分解為直接效應(即本地效應)和間接效應(即溢出效應),得到效應分解結果(表6)。
由表6 的分解結果可知:①交通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發展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均為負,在W-0-1、W- kn 和W- eco 矩陣下都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表明成渝雙城經濟圈交通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的負向空間溢出效應。即本地交通基礎設施改善未能有效促進區域內其他城市的經濟發展。且在考慮經濟與地理雙重因素下,基于W- eco矩陣的負向溢出效應數值最大,顯著性最強。交通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為負,可能與成渝雙城經濟圈內部存在“中部塌陷”現象有關。即“雙核心城市”——重慶市和成都市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區域內其他城市差距較大,呈現出“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式”狀態。以2019 年為例,重慶市和成都市的生產總值分別是雅安市的32.614 倍和23.505 倍,即使與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靠前的綿陽市相比較,重慶市和成都市的經濟實力仍是其8.265 倍和5.956 倍。在成渝雙城經濟圈發展欠均衡的“中部塌陷”現狀下,重慶市和成都市作為核心城市,憑借優越的交通基礎設施條件和經濟和區位等稟賦優勢,吸引區域內其他城市的資金、技術和人才等資源不斷流入,經濟發展的集聚效應大于擴散效應,使得交通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發展產生負向空間溢出效應,削弱了其他城市特別是落后城市的經濟發展。②人力資本水平對區域經濟發展的直接效應均為正,且至少在5%水平上顯著,間接效應在W- 0-1 和W- kn 矩陣下顯著為正,表明提高人力資本水平有利于經濟發展,通過重視人才的培養和引進,發揮人才對社會經濟的支撐引領作用,可以有效推動成渝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③在W-0-1、W- dis 和W- kn 矩陣下,市場內部潛力對區域經濟發展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均至少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通過優化市場消費服務質量和市場結構以發揮市場內部潛力,可以有效拉動區域經濟。④產業結構升級對區域經濟發展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均至少在10%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單純擴大第三產業占比并不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途徑,成渝雙城經濟圈的建設還需要依靠各個產業的統籌協調發展。⑤在W- 0-1、W- dis 和W- kn矩陣下,政府參與程度對區域經濟發展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均至少在5%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成渝雙城經濟圈的各級政府應明確政府行為和市場主體的有效邊界,避免對經濟活動的過度參與。⑥工資水平和對外開放水平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均不顯著,這可能與本文選用的樣本數據有關。

表6 4 種空間權重矩陣下各模型效應分解結果Table 6 Effect decomposition results of each under four spatial weight matrices
5 結論與政策建議
5.1 結論
本文基于2003—2019 年成渝雙城經濟圈16 個城市的時空面板數據,在4 種空間權重矩陣下,實證探究了交通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主要結論如下:①隨著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成渝雙城經濟圈內部的傳統地理空間限制被逐步打破,原本地理空間相關性不強的城市之間的經濟聯系與交流得到加強,區域內存在顯著且穩定的空間自相關性,這得到了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的驗證。在考慮地理和經濟雙重因素下,空間自相關性與空間溢出效應的數值和顯著性最為突出,即采用新經濟距離權重矩陣進行空間計量分析更符合區域經濟實際情況。②成渝雙城經濟圈交通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為負,該結論在W-0-1、W- kn和W- eco 矩陣下都是穩健的,原因可能與區域內存在“中部塌陷”現象有關。“雙核心城市”——重慶和成都憑借自身的稟賦優勢,吸引區域內其他城市的資金、技術和人才等資源不斷流入,導致經濟發展的集聚效應大于擴散效應,使交通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發展產生負向空間溢出效應,削弱了其他城市特別是落后城市的經濟發展。③控制變量中,人力資本和市場內部潛力對成渝雙城經濟圈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政府參與程度和產業結構升級對區域經濟發展未發揮有利影響;工資水平和對外開放水平的作用不顯著。
5.2 建議
綜合以上結論分析,本文提出以下3 條政策建議:①深化交通基礎設施通聯,促進區域經濟要素的有效流動。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應充分考慮區域內經濟發展的顯著空間關聯特征,重視各城市間的經濟活動聯系,在推動區域交通基礎設施協同發展的基礎上,合理制定各城市的交通運輸規劃,深化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進一步突破區域內的空間地理壁壘,依托成渝北線、中線和南線綜合運輸通道,促進區域經濟要素的有效流動,夯實成渝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協調發展的交通運輸基礎。②以改善“中部塌陷”現象為抓手,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協調發展。深化區域內的多層次合作,通過建立合作區、示范區等形式,促進成渝中部地區一體化發展,充分發揮成渝雙核的輻射帶動作用,加速中部地區崛起。在保證核心城市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注重發掘和培育非核心城市的經濟增長點,以堅持差異化發展戰略為導向,不斷提升非核心城市的可達度、吸引力、競爭力和承接力,形成比較優勢,支持綿陽、南充、德陽、內江等城市優先承接產業轉移和功能疏解,打造協同發展通道經濟和樞紐經濟,縮小核心城市與非核心城市間的經濟差距,促使交通基礎設施的空間溢出效應由負向正轉變,形成相互帶動的良性區域經濟生態。③合理發揮其他因素的促進作用,做好區域統籌規劃。加大人才的培養和引進力度,制定和完善有吸引力的人才政策,促使高端人才的扎根集聚;注重消費服務水平的提高和市場結構優化,但不能通過單純擴大第三產業占比來刺激經濟短期增長,需要考慮區域產業結構特征和經濟水平動態變化等因素,著眼區域長期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做好統籌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