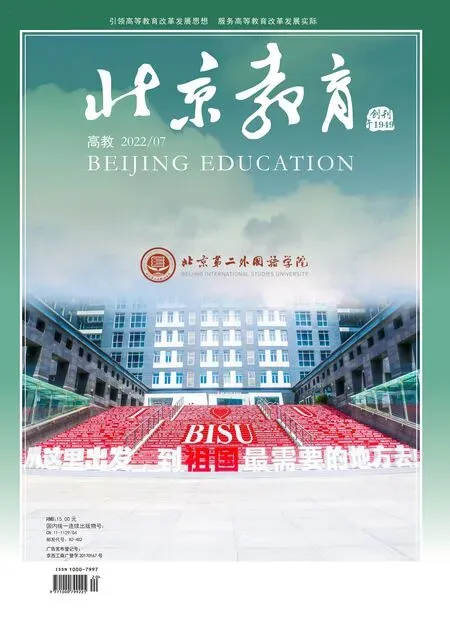高校青年教師職前發展的政策建議
□ 文/孫立會
無論是大學教育改革政策的推進還是大學高質量內涵式發展的迫切需要,教學之于大學的意義從未得到過如此重視,以本為本,全面提升大學教學質量的時代已來。大學教師作為一種職業,在高等教育政策中并未十分明確規定應先取得“高等學校教師資格認定”,然后才能從事大學教學的規定,以至于很多大學教師即便長期在課堂教學的一線也從未取得過或正在申請取得“高等學校教師資格認定”,相關資料也表明:入職后的大學教師90%未接受專門化的教育培訓或沒有教學經歷[1]。這也說明“能教”是大學教師隱藏的“默認”職業能力,但具有高深知識與“會教”完全是兩回事,教學是一門需要學習才能獲得的學問,不是伴隨知識獲得過程的“附加屬性”,所以除了具有天賦秉性的教學者之外,各個大學之間的教師教學能力差異“謬以千里”,甚至于同一個大學的同一個系所的教師之間的教學水平也差距十分明顯。雖然,這與現有的考核機制有關,但教學寫在考核指標中也僅僅是被描寫為“承擔幾門本科生課程”,至于是否有承擔的資格并未進行過充分的論述或者頒布過可以值得信賴的評價標準。但無論怎樣,教學是大學青年教師職業發展的起點,也是其職業生涯中的生命線,高等教育政策應將其起點前移,盡早將教學觀貫通學術研究的整個發展歷程之中。
一流的教師是大學教育質量的有效保障,而職前培養是教師發展的關鍵環節,但大學教師職前發展從未得到過足夠的重視,甚至于這個概念也是近幾年才出現在高等教育研究領域之中。大學教師專業發展(Faculty Development,簡稱FD)一般是指大學為教師提高教學能力而提供的實踐性方法,是大學教學改革的一種組織形式,重在大學教師的教學能力的提升[2]。大學教師職前發展(Pre-Faculty Development,簡稱Pre-FD)是FD 的衍生物,主要是面向以大學教師為職業取向但還未取得大學教師資格的博士生提供的一種職業化培養方式,在理解大學教師角色職業行為基礎上促進其教學能力的提升,未來進入大學能更好地承擔起大學教學的基本任務。FD 的意義在于喚起大學對教師教學能力的更多關注,Pre-FD 的意義是喚起以大學教師為職業取向的博士研究生對教學能力的關注,也是轉變大學高層次育人育才職業職能的訴求與期待。
大學應鼓勵與支持研究生院開設“大學教師職前教學模塊”必修課
青年教師進入大學后,通常都會接受崗前職業能力培訓,其中包含高等教育學、高等教育心理學等課程或專家講座,培訓之后撰寫一個“學習心得”便默認可以從事大學教學了,其后有的大學會通過教師發展中心為青年教師提供類似“午餐會”“青年教師教學大賽”等教學能力提升路徑。但因入職后的青年教師所需要承擔的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等各項工作集聚一身,雖有心參與相關教學能力提升工程,但也略顯“無力”。所以,大學在培養博士生時有責任與義務開設大學教師職前教育模塊課程,通過必修與選修相結合、大學教學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為未來可能成為大學教師的博士研究生提供2 學分~3 學分的課程,并且也可通過一些教學活動競賽激勵博士生積極參與職前教師培訓,以獲得對大學教師形象、教育理念及教學方式等大學教學基本能力的掌握。國內已有一些一流大學進行積極探索,如清華大學研究生教學能力提升項目、北京師范大學李芒教授為博士生開設的“大學教學能力提升”選修課程等,但還未形成一定的規模化、模式化與流程化,博士生們也并未深刻認識到教學之于未來大學教師職業生涯的重要意義,所以還未引發“蝴蝶效應”。
重新定義教學助教(TA)的職能
大學里的教學助教(Teaching Assistant,簡稱TA),通常指學校的在讀碩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協助某門任課教師從事教學的輔助性工作,在正式稱其為助教之前會參與學校的相關培訓,這是很難得的大學教師職前崗位培訓機會,正如近田政博教授所言,從長期培養未來大學教師的層面來看,大學教師職前培養與TA 定位基本相同[3]。但事實上,很多學生或是助教本身都將其視為一份勤工助學的崗位,以“勞務”式的“助”,而非以幫助或促進“教學”的“助”。因此,助教崗位的教育目標及意義經常被忽略,參與培訓時也僅僅是對其承擔任務性工作的描述而非進行聯接教師職能的闡述,進而忽視助教的真正教育教學價值,教育性應是其第一準繩。未來的大學在助教選拔過程中應盡可能充分以學生未來職業能力發展規劃為目的取向,并由大學的教務處、研究生院及教師發展中心共同承擔,選拔那些有志從事大學教學的學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擔任助教崗位,并通過“試講”“大學教學知識問答”等多種方式充分發揮助教的本真之意,不斷為其心中大學教師“畫像”。
大學教師招聘中應明確要求應聘者的教學能力
國外大學教師招聘中已明確規定應聘者應具有一定的教學能力。例如:日本的一些大學在教師招聘過程中會讓應聘者提供一份詳細的“教學計劃書”,教學計劃書簡單來講就是指每門學科的教學大綱,具體還包括教師教授科目的名稱、教學目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評價、參考書目、選修條件等,可謂是巨細無遺,涉及到課程的方方面面[4],如若不經過專門的職前教學訓練是沒辦法掌握撰寫教學計劃書技能的,因為這不是“模板化”的,而應在撰寫不同科目的教學計劃時盡可能展示出應聘者的教學基本素養;同時,如果應聘者的履歷中顯示參與過大學教師職前培訓,會相對來說更容易受應聘大學的垂青,所以日本大學教師職前發展非常受在讀博士生甚至于已畢業但還未找到大學教職的博士所歡迎,并且確實承擔起了促進大學教師專業發展的責任[5]。而我國現有大學教師招聘中對學歷、學術成果等的要求已十分具體,但對其教學能力的要求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即便是通過“試講”環節考察應聘教師必備的教學職業素養,有時也僅僅通過應聘者的學術介紹一筆帶過,并未成為其面試錄用考核的決定因素,這與不斷重視大學教學的呼聲相距甚遠。
“高等學校教師資格認定”是嚴控大學教學質量的關鍵
雖然,目前高等學校教師資格認定無法與中小學教師資格認定一樣實行社會化改革,也不可能進行大學教師職前專業化認證改革,先入職后進行教學培訓的既定邏輯順序很難改變。所以,各個大學要嚴格控制教學質量底線,不能因任何原因在新入職教師還未取得高等學校教師資格認定之前進行課堂教學。同時,要將更能體現大學教師角色的教學實踐性知識融入高等學校教師資格認定筆試考核之中,從理論上認識“教”的重要性也是其走向教學實踐的基本前提。當然,在獲得高等學校教師資格認定之前,青年教師也可通過“師徒制”的方式,跟從具有豐富教學經驗的教師進行課堂教學實踐觀摩,以及青年教師之間通過“教學工作坊”“集體備課”“磨課”等方式進行教學能力水平的自我提升,了解大學教學的基本規律。
大學教師職前培養的質量是大學教學質量提升的源頭,不把握好這個源頭,大學教學質量提升很難一蹴而就,“口號”式的呼聲無法起到長遠的激勵作用。雖然很多大學通過評選“教學型教授”或給予在教學中作出突出貢獻的教師進行高額獎勵,但無論是教學型教授數量少的可以基本忽略不計(一般一所大學一年為1個名額左右),還是教學獎勵的獎金再高僅獎勵全校的一個人,如此這樣通過教學的通道獲得提升對于青年教師來講可以說是相當渺茫的。所以,并非是設置教學型教授而是更應設置大量的教學型副教授,以此激活整個大學熱愛教學的浪潮,把類似于一種“噱頭”式的高額獎金分成若干等份,盡可能多地獎勵青年教師,鼓勵其不斷迭代教學實施、總結、提升,將自己的教學形成一種模式進而上升為一種“理論”,然后賦能未來青年教師的教學發展,以此形成一個大學教學質量保障的良性循環發展。雖然不同的青年教師的研究“隔行如隔山”,但教學是有共通性的,而這正是聯結一個大學所有教師的“節點”。
當然,青年教師的教學能力發展除外部驅動力驅動外,重要的還是在外部驅動的過程中形成自我內驅力。歸根結底,大學教學更多需要教師的“自治”,這需要源于教師對教學的本源性熱愛,而不僅僅是因為評聘的需要,教師要在教學的過程中保有一種持續的激情,學會在教學中“自我感動”,無關乎任何榮譽。雖然科學研究是知識生產的主要方式,但很多創新性知識并不僅僅是產生于象牙塔里的實驗室,也可能是一個“不經意”的觀察或沉思后的“夢境”,更可能是在教學過程中。例如: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物理系教授奧斯特在1820 年給學生授課過程中演示物理實驗時,突然發現一根通電導線放在磁針上方時會發生偏轉,并最終垂直于導線的方向停下來,這是其在之前的研究過程中所沒有發現過的科學現象。下課后,奧斯特通過反復實驗證明了通電導線周圍存在磁場,即電流的磁效應,這完全可以說明通過教學也可以生產知識。雖然,很多人認為奧斯特在教學中的這一知識發現純屬一種偶然,但往往所謂的偶然,其實是偶然中的必然,很多重大科學發現都是一種執著努力后的“偶然”。所以,理解大學教學不能僅僅從中小學的教學建立聯想點,大學教學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授,更應是一種“生成性”的創造活動,在這個創造性的活動中必然會有思想在人與人之間進行流動,而在這一過程中就一定會產生知識。大學教師不能僅用非此即彼的簡單二元對立哲學的視角去看待教學與科學研究之間的關系,教學與科學研究之間是有很強的聯接紐帶,如果不在教學中進行研究或不在研究中進行教學,都不能稱其為一名合格的大學教師。當然,重視教學并不代表輕視科學研究,沒有持續更新的科學研究的教師的教學也不是真的好的教學,研究與教學是大學教師的手心手背,缺少哪一部分都將失去這一個崗位的職責屬性。
青年教師教學發展的高度取決于其對大學教學的認識高度,這個高度是無止境的,教無止境也是教學藝術的真實體現。大學教師職前發展的意義就在于給未來的青年教師攀登教學高峰搭建一個“扶梯”,以免在實踐教學過程中產生“斷裂”。
本文系全國教育科學“十三五”規劃國家一般課題“大學教學現代化的戰略愿景與理論創新研究”(項目編號:BCA180085)階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