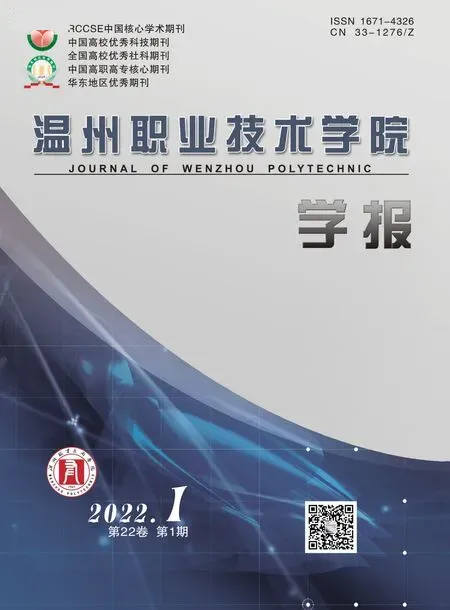劉基對柳宗元《天說》中“天人說”的接受
周玉華
(湖南科技學院,湖南 永州 425199)
一、柳宗元《天說》及“天人說”溯源
《天說》乃唐代文學家柳宗元(773—819)的散文名篇之一,也是表達其哲學思想的重要作品,文章被收入《柳河東集》和《柳宗元集》第十六卷。在《天說》中,柳宗元針對韓愈的“天命說”闡述了“天人說”。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柳宗元、劉禹錫等參與王叔文、王伾為首發起的“永貞革新”,改革以抑制藩鎮割據、削弱宦官勢力、加強中央集權、革除政治弊端為主要目的,最后在宦官勢力反撲下,王伾、王叔文被貶為開州和渝州司馬(王伾不久死于貶所,王叔文翌年亦被賜死)。后柳宗元、劉禹錫等八人先后被貶為遠州司馬,史稱“二王八司馬”。永貞革新僅歷時100多天就宣告失敗。對于這次革新,韓愈大加貶斥。雖然他與柳宗元、劉禹錫等交好,同情其貶謫遭際,稱“郎官清要為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湖波連天日相騰,蠻俗生梗瘴癘烝”[1]10,但在《永貞行》中,他仍稱革新派為“小人乘時偷國柄”,曰“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認為其遭貶乃應受的懲罰,“嗟爾既往宜為懲”。
在修撰《順宗實錄》中,韓愈也表達了對革新派的不滿,正如其《答劉秀才論史書》所言:“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1]70韓愈對革新派的態度也引發了后世爭議。韓愈“不有人禍,則有天刑”之說,實則暗指“永貞革新”失敗乃遭受天的懲罰。對于這一說法,柳宗元是極不滿意的,“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故而他撰文《與韓愈論史官書》加以反駁,認為做官要“中道”,辦事要不偏不倚,不要畏懼而輕為之。即“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茍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2]807,稱“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認為只有愚昧無知者才會對天感到迷惑,而明白事理者是不言鬼神之事的,從而有力反駁了韓愈的鬼神“禍人”“福人”論。
可是韓愈并沒有就此罷休,將爭論的焦點又從“說史”轉到“說天”,提出了“天命說”,責備柳宗元“不知天”。從現實生活事例出發,韓愈以“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舉例果蓏、飲食壞而蟲生,元氣陰陽之壞而人由之生,然后加以闡發,引出天命說,認為“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從而提出天能賞功罰禍的“天命說”,并且還稱“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由此可見韓愈“天命說”屬于典型的唯心論,自然遭到了柳宗元的批駁。
柳宗元站在樸素唯物論的角度提出了“天人說”。稱“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2]442-443,認為天、地、陰陽與果蓏、草木一樣皆為物,作為自然現象肯定沒有意志,又怎么能賞功罰禍呢?“功者自功,禍者自禍”,希望天能賞功罰禍可謂無比荒謬,而向天呼喊埋怨,希望天能發善心可憐他,那就更加荒謬可笑了。柳宗元合理論證了“天人說”,強調天為物質,天無意志,從而筆鋒犀利地批判了韓愈所持天能賞罰的“天命論”。由此可見,在天有無意志問題上,柳宗元與韓愈是根本對立的。
劉禹錫作為柳宗元好友,大為贊同柳的“天人說”,在《天說》的基礎上寫了《天論》上、中、下三篇來闡發天與人關系,進一步批駁韓愈的“天命論”。他在《天論》上篇明確交代了寫作原因,稱“余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3]291。
在文中,劉禹錫先是表明自己的唯物論立場,認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與人都有能與不能,“天與人交相勝”,提出“人能勝乎天者,法也”。他認為福禍皆由自取,非天預人也,論述了“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非天預乎人爾”“人不幸則歸乎天”等一系列說法,進一步闡釋了人們對天迷信是因為政治腐敗、法制松弛,“法大馳,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他還認為事物發展是客觀規律的必然性和發展趨勢的偶然性的結合。劉禹錫“天人交相勝”及“人能勝乎天”的推論可謂柳宗元“天人說”的進一步深化,從而將唯物思想推向了新高度。
作為樸素的唯物論思想,柳宗元“天人說”并不是其獨創,而是在前人唯物思想基礎上的闡發。源頭往前可以追溯到屈原《天問》以及荀子《天論》。《天問》為戰國時期偉大詩人屈原(約前340—約前278)所作的一首長詩,全詩三百七十多句一千五百多字,一共提出了一百七十多個問題,從天文地理到政治歷史,涉及內容可謂精深豐富。其中,對天地、自然的提問,對傳說的懷疑,集中反映了屈原對宇宙的探索,展示其非凡的學識和超越時代的宇宙認識。《天問》可謂屈原思想學說的精粹,被譽為“千古萬古至奇之作”,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價值,對后世文學創作影響頗為深遠,從而引出了諸多模擬之作。
荀子(約前313—約前238 年),戰國末期思想家,比屈原出生略晚,其《天論》中唯物思想表達比屈原更為直接大膽。《天論》開篇即提出鮮明觀點,曰“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4]192,明確表示自然界變化有其客觀規律,與人事沒有什么關系。在這一觀點引領下,他提出“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這就需要各司其職,“不與天爭職”。進而還明確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論點,可謂對當時各種迷信的極力否定,大力強調了人力的積極作用。由此可見荀子思想頗具時代先進性。
柳宗元、劉禹錫在與韓愈爭論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了屈原、荀子等人的唯物論思想,加以吸收消化,進而提出了更為具體明確的“天人說”,受到后世關注,也推動了《天問》的擬寫之風,明代劉基就是其中之一。
二、劉基對柳宗元的接受
劉基(1311—1375),字伯溫,元末明初的著名政治家,他精通天文、兵法和數理,號稱大明王朝第一謀臣,多次被朱元璋稱為“吾之子房”,輔佐朱元璋平定天下。民間將其與張良、諸葛亮并稱,說“三分天下諸葛亮,一統江山劉伯溫;前朝軍師諸葛亮,后朝軍師劉伯溫”。同時,他還是一位在文學史上具有一定影響的文學家。其詩文理論力主教化諷諭、“美刺風戒”,講求經世致用。內容多關注現實、同情民生疾苦,抨擊腐朽統治者。風格古樸奔放,與宋濂、高啟并稱“明初詩文三大家”。其著作頗豐,由其子孫分別編為《郁離子》五卷、《覆瓿集》并拾遺二十卷、《寫情集》四卷、《春秋明經》四卷、《犁眉公集》五卷,后被編為《誠意伯劉先生文集》。劉基博覽群書,他很好地借鑒吸收了前人思想,其中就包括柳宗元的政治文學思想。仔細研讀其作品,我們會找到許多相似之處。
第一,劉基秉持儒家詩教觀,提倡理氣并重,強調詩歌的教化諷諭作用,學習司馬遷、陳子昂、韓愈、柳宗元等的文學創作,從而恢復漢唐文學傳統。他在《蘇平仲文集序》中表述十分明確,文曰:“文以理為主,而氣以據之。理不明,為虛文;氣不足,則理無所駕。文之盛衰,實關時之泰否。”[5]117贊唐虞三代、漢唐之文,曰:“唐虞三代之文,誠于中而形為言,不矯揉以為工,不虛聲而強聒也,故理明而氣昌。……漢興,一掃衰周之文敝而返諸樸。豐沛之歌,雄杰不飾,移風易尚之機,實肇于此。……繼漢而有九有,享國延祚最久者,唐也。故其詩文有陳子昂,而繼以李、杜;有韓退之,而和以柳。于是唐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5]118由此可見,劉基以李杜、韓柳為效法對象,提倡文學復古,注重詩文思想內容。
第二,劉基的治國思想核心為得民心、施德政,劉基德政的出發點亦為儒家的民本思想。柳宗元民本思想受儒家愛民、仁政思想影響極大。生活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時代,藩鎮割據、政局不穩,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柳宗元從少年時期就開始了解民間百姓疾苦,尤其在參與“永貞革新”失敗,被貶永州司馬之后,他深入民間,對百姓生活困苦、統治者酷政暴行有更加切身的感受。于是,其民本思想更加充實,在《送范明府詩序》中首提“吏為民役”說,文曰:“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2]593在《送薛存義之任序》中又加以完善,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于我也。”[2]616這樣,“吏為民役”“民可黜罰”思想,明確指出官吏為百姓的仆役,就應該為百姓服務辦事,百姓也有權利對其罷黜懲罰。他還進一步提出為政者要“利民”,即施行仁政,與民休養。在《種樹郭橐駝傳》中曰:“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提出為政者當“順人之欲,遂人之性”[2]473,即遵從百姓意愿,遵循生產生活規律,讓百姓能夠安居樂業。針對現實的苛政暴政現象,他寫作了大量作品以鳴不平,如《捕蛇者說》《田家三首》等就是這一時期創作的。
劉基生活在元末明初,當時,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集,突出尖銳,戰亂頻發,社會動蕩,百姓流離失所,生活艱辛。他從小就關心社會,同情百姓疾苦。再加上仕宦失意,使得他對社會艱難狀況了解更多,尤其對民生多艱和官吏暴政的認識更深,也使得其民本思想逐漸成熟,形成了以愛民、保民、養民為核心的德政思想,即執政為民、執法為民。劉基在其寓言集《郁離子》中,頗多論述其德政思想。如在《天道》中提出要愛民,文曰:“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為之求善牧矣。”[5]54
在《天地之盜》中提出對百姓要因循善誘,曰:“故上古之善盜者,莫伏羲、神農氏若也。惇其典,庸其禮,操天地之心以作之君,則既奪其權而執之矣,于是教民以盜其力,以為吾用。春而種,秋而收,逐其時而利其生,高而宮,卑而池,水而舟,風而帆,曲取之無遺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5]40并以種菜為喻,讓統治者善于管理百姓,曰:“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藝植焉。窊隆干濕,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后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根。擷已而溉,蔬忘其擷。于是庖日充而圃不匱。”[5]41
同時,劉基還創作了許多同情農民不幸遭際的詩文,表達對統治者殘酷剝削、壓迫百姓的不滿。其《野田黃雀行》詩云:“農夫力田望秋至,沐雨梳風盡勞瘁。王租未了私債多,況復爾輩頻經過!野田雀,鷹隼高翔不汝擊,農夫田父愁何極!”[5]322其《畦桑詞》云:“君不見古人樹桑在墻下,五十衣帛無凍者。今日路傍桑滿畦,茅屋苦寒中夜啼。”[5]337這些詩文反映的都是農民承受沉重的地租王稅。《雨雪曲》詩云“平民避亂入山谷,編蓬作屋無環堵。回看故里盡荊榛,野烏爭食聲怒嗔。盜賊官軍齊劫掠,去住無所容其身。”[5]338《苦寒行》詩云:“去年苦寒猶自可,今年苦寒愁殺我。去年苦寒凍裂唇,猶有草茅堪蔽身。今年苦寒凍入髓,妻啼子哭空山里。空山日夜望官軍,燕頷虎頭聞不聞?”[5]338這些詩則是描寫了農民在連年戰亂中被迫流離失所,饑寒交加,還要遭受盜賊、官兵劫掠的悲慘景象。
第三,從劉基寓言中我們可以感受其寓意深刻、諷刺辛辣的鮮明特征,這也與柳宗元的寓言創作情形有相似之處。寓言通過淺顯明白的語言、通俗易懂的故事講述深刻的道理,在中國古代頗受歡迎。尤其在時局不穩定,不便直接表明觀點的情況下,文士在說理、論證、諷諭中便多采用寓言闡明自己的社會見解、政治主張或愛憎態度。如春秋戰國時期就是寓言形成的重要時期,在《莊子》《孟子》《呂氏春秋》《戰國策》等諸子散文和歷史散文中,就出現了大量的寓言故事。唐代柳宗元則開啟了寓言創作的新階段,他在繼承先秦寓言的基礎上,在藝術形式、思想內容等多方面都達到了新的高度,不僅體裁形式多樣,有散文體、詩體、傳記體,以便于闡述,還在寓言中塑造了尸蟲、王孫、驢、鼠等多種生動豐滿的形象。另外,其用語更精練簡潔,筆鋒更犀利,因而其批判也更具鮮明說服力。
如其《三戒》的《永某氏之鼠》這則寓言就頗具代表性,其文曰:“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余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嚙斗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2]535寓言所述之事頗具諷刺性,由于主人生肖屬鼠,故迷信不準養貓狗捉拿老鼠,導致老鼠越聚越多,越加肆意妄為。后換一憎惡老鼠的新主人,采取多種措施,結果老鼠全部被消滅。寓言以鼠喻人,影射那些仗勢欺人、貪婪殘暴的奸佞小人,即使他們依附昏君能僥幸逞兇一時,但終將遭受“永某氏之鼠”的可恥結局。文中對永某氏的迷信縱容和姑息養奸進行了辛辣諷刺,對仗勢欺人的鼠進行了無情鞭撻。
劉基寓言集《郁離子》,則更多批判元末黑暗政治,揭露統治者的昏庸愚昧、貪婪自私,諷諫統治者能夠警醒,以此讓其施德政愛百姓。如《靈丘丈人》諷刺頗為辛辣,文曰:“晉靈公好狗,筑狗圈于曲沃,衣之繡。嬖人屠岸賈因公之好也,則夸狗以悅公,公益尚狗。一夕,狐入于絳宮,驚襄夫人,襄夫人怒,公使狗搏狐,弗勝。屠岸賈命虞人取他狐以獻。曰:‘狗實獲狐。’公大喜,食狗以大夫之俎,下令國人曰:‘有犯吾狗者,刖之。’于是國人皆畏狗。狗入市,取羊豕以食,飽則曳以歸屠岸賈氏,屠岸賈大獲。大夫有欲言事者,不因屠岸賈,則狗群噬之。趙宣子將諫,狗逆而拒諸門,弗克入。他日,狗入苑食公羊,屠岸賈欺曰:‘趙盾之狗也。’公怒,使殺趙盾。國人救之。宣子出奔秦。趙穿因眾怒,攻屠岸賈,殺之,遂弒靈公于桃園。狗散走國中,國人悉禽而烹之。君子曰:‘甚矣!屠岸賈之為小人也,譝狗以蠱君,卒亡其身,以及其君,寵安足恃哉!’人之言曰:‘蠹蟲食木,木盡則蟲死,其如晉靈公之狗矣!’”[5]20-21
此寓言故事,鮮活地刻畫出了昏君的荒淫愚昧,受到臣子欺騙愚弄而毫不知情,受臣子的阿諛奉承、欺上瞞下,爪牙走狗的仗勢欺人,失勢后的可憐恓惶,辛辣諷刺了從上到下的社會丑態。仔細研讀,不難發現劉基寓言作品借鑒柳宗元之處頗多,這里點到為止,留待后續進一步深入探究。
三、劉基《天說》繼承并發展了柳宗元的“天人說”
劉基的《天說》分為上、下兩篇,字數不到一千五百字,但其內涵豐富,論述精辟,頗具思想性。通過研讀,我們發現劉基《天說》篇與柳宗元的《天說》篇一樣,都是繼承和發展了屈原《天問》、荀子《天論》中的“天人說”思想。我們已說過柳宗元《天說》中“天人說”強調天地與草木萬物一樣是自然存在物,沒有意志,故而與人的賞罰福禍沒有關系。劉基《天說》上篇就繼承和發展了柳宗元的“天人說”,對“天能賞善罰惡”的“天命論”進行了批駁,他以“天之降禍福于人也,有諸”設問,明確否定,反問“否,天烏能降禍福于人哉”,如果“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為善者不必福,為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那么“使天而能降禍福于人也,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5]186。假設天能夠降福禍于人的話,那按照天之道則應是獎善罰惡,可現實情況卻是為善者不一定有福,為惡者不一定有禍,這就成了“自戾其心”了。故而劉基明確表達曰:“天之不能降福禍于人亦明矣。”由此可見,劉基的“天之不能降福禍于人”可歸納為“福禍說”,乃是接受繼承了柳宗元“天人說”觀點。
劉基還在柳宗元“天人說”基礎上進一步加以闡述,認為“禍福為氣所為”,從“氣”的角度對古代長期以來的疑惑爭論進行了解答。文曰:“氣有陰陽,邪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于為之也。是故朝菌得濕而生,晞陽而死;靡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氣有心于生死之也,生于其所相得,而死于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于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不能御也。”[5]186劉基認為氣有陰陽,陰為邪,陽為正。陰陽交錯,邪正互有勝負,無方也無常,只要萬物遭受了陰陽,就形成了禍福,并不是氣“有心為之”。這樣,善惡、福禍就因所遇不同而有別,且氣有偏勝,人無法抵御抗拒。總之,無論是“天”,還是“人”都沒有決定社會現實中出現的善惡、福禍的能力,只有陰陽、邪正之“氣”才起決定性作用。
劉基的這一論述可謂進一步闡釋了柳宗元的“天人說”,并且他還回答了“天聽于氣乎”的問題。他以“天”“人”皆為氣,反駁了“天聽于氣”和“天果聽于氣”的觀點,說“天之質,茫茫然氣也”,又說“人也者,天之子也,善假于氣以生之”。既然“天”和“人”都是物質性的“氣”所生成的,那么“天”就不一定要順從“氣”的支配,即“天不聽于氣”。
劉基又以“元氣”說來佐證,也是繼承和發展了柳宗元等前人的理論。曰:“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于一時,必有復也。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于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又稱“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在這里,他指出“元氣”是“不息”“可復”的,是“正氣”最終戰勝“邪氣”的“天理”。柳宗元回應屈原《天問》寫成《天對》,認為“元氣”是宇宙萬物生成的起源,曰:“往來屯屯,龐昧革化,惟元氣存。”在《非國語·三川震》中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游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又況天地之無倪,陰陽之無窮。”[2]1269而山崩地震則是“元氣”“自動自休,自峙自流”的結果。
以“元氣”論為基礎,劉基在《天說》下篇還對風雨、雷電、晦明、寒暑等自然現象進行了解釋,從而反駁了“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警于人”的觀點,這也是傳統社會的主流觀點。劉基稱“天以氣為質。氣失其平則變”,明確以“元氣”論為前提解釋自然現象。曰:“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噓、動息、啟閉收發也。”指出風雨等自然現象為“天”的啟閉收發等行為,而“天”的如此行為又是怎么產生的呢?于是劉基再復歸到“元氣”來,分析“氣”運行通暢與否出現的后果,曰:“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并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后病生焉。”[5]187然后再具體描寫“天之病”的表現,曰:“故吼而為暴風,郁而為虹霓,不平之氣見也。抑拗憤結,回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蕩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祲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5]187-188氣不平則天病,表現為驟雨疾風、冬雷夏霜、水旱愆殃、瘴疫流行等等“天之病狀”。作為“天之氣以生者”的萬物自然也就出現病狀了,表現為“瘥癘夭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為也”。如此解釋可謂順序合理,頗具邏輯性和說服力。
在“元氣”說前提下,設若“天之氣以生者”萬物有病,天都不知怎么辦,“天亦無如之何”,那還有誰為“善醫者”。劉基提出了惟有“圣人”有神道,這是對其信奉的傳統儒家“圣人”歷史觀的闡發,認為“惟圣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于未形,不待其機之發”。圣人能夠先知先覺,防患未形。還以歷史上的典型事件證明:“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為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之。”正是因為圣人的作為,元氣才源源不斷,“元氣之不沽,圣人為之也”。
并以“醫者”為喻,指出“圣人”即“良醫”,“天有所不能”乃因“病于氣”,只有圣人能治病,“惟圣人能救之,是故圣人猶良醫也”。舉例強調古代“圣人”及其“醫世”作用,曰:“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圣人“孔子”則是“時不用,著其方”,曰:“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5]188再舉例兩漢雖有能醫者,然不能稱為圣人,故而天道漸窮,文曰:“高、文、光武能于醫而未圣,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鉤吻為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是病入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6]188可以說這也是劉基對“人定勝天”論的理性認識。
這樣,我們再回頭看劉基關于“人”的福禍觀,就容易理解了。“圣人”能醫天之病,因而能得福,而“為惡之人”自當得禍。因為“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為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逢其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并且還以曹操和司馬懿等人為例加以解釋,曰:“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于其身,而于其后昆。”這并不是“天有所私”,而是來自佛教中的“因果報應”論,這就是“天知地知神知鬼知,何謂無知;善報惡報速報遲報,終須有報”的道理。如此解釋雖可通,但劉基并非佛教人士,因此他又回歸儒家觀點,主張“修身以俟命”:“不怨天,不尤人,夭壽不二,修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5]187
綜上所述,劉基的《天說》上下篇所述觀點是在繼承前人,尤其是柳宗元“天人說”的基礎上,結合社會時代背景,對其進行了新的闡發,從而對這一理論闡述更為全面,也更具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