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圍“中年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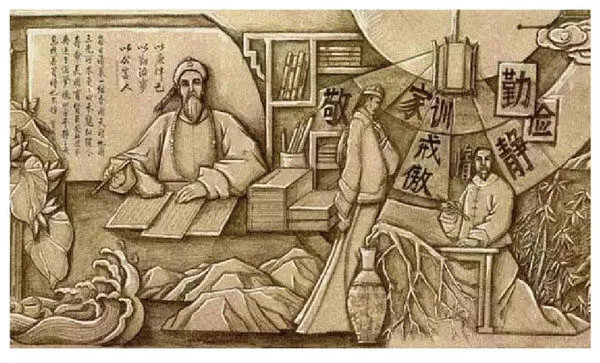
清咸豐七年(1857),盛夏的熱浪蒸騰著湖南長沙府湘鄉荷葉塘白楊坪,四十六歲的曾國藩站在老柏樹下沉默不語。出湘三載,征戰不休,卻帶著半頭風霜和一身火氣歸來;數年努力之經營,在炎炎烈日的炙烤下如露消逝,他眼中透著兩個字——“不甘”。勇猛精進的剛介儒生遭遇中年危機,自然抑郁苦悶。上司的猜忌,同僚的中傷,友朋的死難,凡此種種,與壯志難酬的憂愁纏繞在一起,灼燒著曾國藩的神魂,令其寢食難安。
他常在老家屋前靜坐,仰觀高嵋山上陽春煙霞,俯瞰白楊坪前翠竹松濤,情郁于中,不能釋懷。好友歐陽兆熊得知后,推薦長沙名醫曹耀湘(字鏡初)為曾國藩治療失眠癥,又勸諫說:“曹鏡初的醫術可以治你的身病,而黃老道之書,可以醫你的心病。”經歐陽兆熊和曹耀湘推薦,曾國藩開始讀老莊等道家著作,早年匆忙一過的名言如“大象無形”“大巧若拙”“強大處下,柔弱處上”“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此時再讀真如一縷春光,照到他被黑暗重重包圍的心上。
夏日過后,天氣漸涼,身心稍有恢復的曾國藩走出白楊坪,四處訪友。看到湘水潮起潮落,不舍晝夜;江上往來的輕舟順流而下,倏忽之間,已越十里,曾國藩忽然領略到“上善若水”的境界,明悟了“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的道理。
曾國藩最崇拜的祖父曾玉屏,留下祖訓“男兒以懦弱無剛為恥”,母親也是倔強剛強之人,他自述“吾兄弟皆稟母德居多,其好處亦正在倔強”。受家庭的影響,曾氏的個性剛強,這也符合湖南人霸蠻(堅決、執拗)的風格。曾國藩到京師讀書后以程朱為宗,常年帶兵打仗,以申韓之術治兵,又學到了法家的霸道。他以剛強、迂闊、自戀、霸道的態度周旋于晚清陳腐的官場,當然不免四處碰壁,待碰壁之后再用這套觀念去反思,不但不得要領,反而如火上澆油,越烹越燙。得歐陽兆熊提醒后再讀老莊,受“中年危機”困擾的曾國藩才算是找到了突圍的辦法。
道家人生觀的要義,首先在“順其自然”4個字上。自然規律不可抗拒,天命不可揣測,人力終究有限,歷史的大勢往往不受個人的意志和努力而轉移。儒家強調遇事當仁不讓,舍我其誰,知其不可而為,總想以一己之力撼動大勢,往往徒勞無功。曾國藩受老莊的啟發,感悟到在浩瀚的宇宙里個人的渺小,繼而又認識到在浩浩蕩蕩的歷史浪潮中,個人只能努力實踐而不能妄求一定成功的道理:人生在世,做事只求盡心,而成敗不必強求。如果大事有成,那也是個人的努力符合了自然規律或者天命,不必把功勞都當作自己的;若大事無成,也不必沮喪,因為世事的發展本就不受個人掌控,“盡其在我,聽之在天”。一旦看破這個道理,不再執著于成敗,不再汲汲于功名,那之前所遭受的各種挫折,也就不必時時掛念在心了。
所謂中年危機,無非就是人到中年因事業無成而產生的焦慮和惶恐,一旦跳出功名利祿的圈子,從宇宙的維度來看待世事,以恬淡沖融的態度來重新看待人生,危機帶來的抑郁也就消泯了。
丁憂守制前,曾國藩的學問,是以程朱理學為統攝的,而程朱理學,是儒學中的激進派。理學家講求天理道德,認為個人通過格物致知、存天理滅人欲,就會掌握天理,最終與天理同在。天理在手,我就可以匡扶正義,改造社會,最后化成天下。其流弊大致有兩端:一是空疏不實,知道要格物致知,卻不知道“物”應當如何去“格”,欲求道,卻無求道的方法和工具;二是處處誅心,自視過高,為人極端。曾國藩自認笨拙無才,后世也多稱他為笨人,然而曾雖然不夠聰明機巧,卻有穿透歷史迷霧的悟性。他雖未接觸過近代科學,卻從考據求實的漢學里得到啟發,無師自通地開創出與近代實證主義接近的科學思辨方法,講求從實際中去驗證知識,從經驗中去總結規律,把充斥著玄學的古代兵法,變成以實證經驗為基礎的軍事工程學、軍事運籌學。理學空疏不實的弊端,被曾國藩突破了,這是曾氏遠超同時代人的地方。
曾國藩的上司和同僚,如咸豐、駱秉章,有的好名虛偽,有的貪權懦弱,但總有幾分精明能干,是可以共謀大業之人。即便如陳啟邁、官文,雖政見不合,官聲不佳,也未必見得就無可救藥。古往今來的大事業,都是少數英雄帶著大多數凡人做成的。君子之間也常政見不合,也需要相互妥協、調和矛盾,才能共舉大事。哪能遇事不順,就剛強到底,寸步不讓呢?道德教化,律己可以昭昭如烈日,律他卻只能浸潤如春雨。自讀老莊悟道,曾國藩懂得了在官場上“知雄守雌,卑弱自持”。第一個改變,就是懂得自省和謙虛,凡事先找自己的不足,而不再一味抱怨他人無理。他反省自身,了解了自己“長傲”和多言的缺點。以前與人沖突,都以為自己必然正確,但回頭反思,自己又真的事事占理嗎?在湖南練兵打仗,自己暗示下屬不必聽從駱秉章的調遣,因為駱秉章毫無才能,只會壞事;與駱秉章文書往來,也只有簡單粗暴的通報,而無請教、商榷的口吻,只因為看不起駱秉章的才干。然而駱秉章在曾國藩出省后,把湖南的財政收入提高了三四倍,練出了四五萬精兵支援各地作戰,又哪里顢頇昏庸呢?咸豐多次強令曾國藩出省救援,曾國藩把咸豐的上諭當作亂命不從,結果是江忠源、吳文镕敗亡,廬州、武昌兩城丟失,局面為之大壞,損失又豈是幾千湘軍可比?縱然陳啟邁在江西克扣湘軍的軍餉,除了限制湘軍發展之外,他也是想籌餉自練一軍。陳啟邁最后沒來得及練成贛軍就被撤職,但曾國藩何以知陳啟邁就一定不行呢?
此前種種沖突,固然因為湘軍的存在觸動了官場原有的利益格局,但與曾國藩的桀驁孤僻又何嘗無關?出江西后,其他湘軍統領和駱秉章相處甚得,曾與陳啟邁不和,而胡林翼卻能與官文共事。如果把晚清的局勢比喻成黑夜,曾國藩是想化身太陽,驅散黑暗,然而他終究把自己燒得油枯燈滅而徒勞無功。胡林翼則更像是黑夜中的舞者,在黑夜中小心翼翼地游走,與黑暗虛與委蛇、若即若離,尋找著還能點燃的燈芯,把它們一一點燃,最終匯成萬家燈火。
曾國藩懂得謙虛自省后,說“反躬自省,全無是處”,以前總自負本領大,總去看別人的不是,自從悟道后,才知道自己并無什么特別的本領,凡事也能看到別人有幾分長處。知道自己不足,而能看到他人長于己處,道德文章方能因此長進,人際關系方可改善。道家的柔術啟迪了曾國藩,讓他知道如何在顢頇、瑣屑的官場中尋求出路:暫時無力改變政治環境,那就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先以謙卑的態度獲得上司、同僚的好感,再積極參與官場的應酬,和光同塵,把自己融入官僚之中。這樣自己就不再是他人眼中剛介古怪、難于共事的酷吏,不再是黑天鵝中的白天鵝。磨去棱角就不再容易被他人攻擊,成為官僚們的自己人,行事就會容易。
曾國藩過去辦事,總想把無能的庸官一腳踢開,然后換上自己信任的正人君子,同心同德改易風氣,共創大業。經過屢屢挫折,他也開始熟知人性的弱點和社會的復雜,知道自己究竟不能隔絕所有不一心的人,何況他所信任的“正人君子”,又何嘗沒有私心雜念?
老子講求君子行事如水,因勢利導,不與人欲對抗,而以柔術馴人性濟功業,以共同的利害關系,循循善誘,引導他人順遂自己的意圖。清高好名之人恭維之,退讓瑣屑之人安撫之,貪婪好貨之人利誘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之人,把自己的事業變成大多數人的利害所在,辦事自然無往不利。曾國藩過去很討厭官場應酬,不喜歡與人客套交往,只喜歡公事公辦,認為官場往來是浪費時間。但在咸豐八年(1858)復出后,他積極參與官場的應酬,左宗棠清高、自大、好名,曾國藩就在日常交往中時時恭維,把他捧成天下第一能臣;官文貪權好利,曾國藩就推功相讓,每次獲得戰功,都分潤官文,每次攻破城池的奏折,都請官文領銜;駱秉章以老前輩自居,曾國藩就日常請教、咨詢、問候;基層官員缺乏認同感,曾國藩就謙卑以待,召見下屬不坐中堂,不讓他們站立,每逢節日還貼心問候;幕僚、弟子都懼怕他嚴厲、刻薄,他就每天和弟子一起吃早飯,講學問、說笑話,到李鴻章入曾國藩幕府時,往日刻薄迂闊的恩師已經是一位每天給下屬講段子,讓人如沐春風的長者了。
江南大營被攻破后,原不打算授予曾國藩地方實權的咸豐,任命他為兩江總督,究其原因,雖是形勢危急無人可用,但也有曾國藩變得更加深沉老辣,讓皇帝覺得可以信任了。
友人歐陽兆熊說曾國藩一生三變,在京師求學從詞臣變為程朱理學的門人,到長沙練兵從理學家變成申韓之徒,咸豐八年守制悟道后最終變成了道家門人。這個解讀,雖出自友人觀察,卻是對他的誤讀。曾國藩一生三變,變的只是做事的手段,變的只是術,而他一生的根本,仍是程朱理學,他的道,始終未變。
曾國藩在創辦湘軍時,確實用嚴刑峻法,但嚴刑峻法只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非目標。他帶湘軍打仗,還是為了捍衛儒家文化,捍衛儒家文化影響下的社會。他打這場仗,還是為了天下太平之后,移風易俗,讓天下變成儒家理想中那個人人有德的社會,其根本目的并沒有變。而且在創辦湘軍時,曾國藩讓自己手下的將領,按時到軍營里給士兵講儒家的道理,教士兵唱《愛民歌》,把士兵當成儒家門徒來訓導。他招募將領,也只招募道德出眾、才堪治民的書生,并不招殺人狂魔。可見曾氏仍是一介儒生,只是這個儒生懂得用一些法家剛強的手段,來彌補儒家的平和,以適應現實需要。
而他晚年,為了和官場上各種官僚打交道,確實用了道家的柔術,和皇帝、同僚“打太極拳”。但曾國藩這樣做,也是為了協調各種關系,以實現儒家理想。如果他成了道家門徒,那還辦什么大事呢?道家講究的是小國寡民,無為而治,圣人不作為最好,還打什么仗呢?如果太平天國當興,那就順其自然吧。可曾國藩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還想做大事業,想改造社會風俗。他在給弟弟曾國荃的信中也說,人力可奪氣數,努力能克天命,可見他始終都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儒生。只是用了道家的柔術,來彌補儒家的剛強。
那曾國藩真正的處事方略是什么呢?其實就是儒家提倡的“中庸”。
儒家思想認為,萬事萬物中都存在著一組對立的矛盾,如陰陽、剛柔、存滅、明暗。中庸就是取矛盾的中端,不偏向任何一方。后人對中庸有誤會,認為中庸就是不偏向左,也不偏向右,站在中間;遇到事情,我不說對,也不說不對,模棱兩可,誰也不得罪。這是把中庸思想庸俗化的理解,本質是膽小怕事,做騎墻派,當好好先生。那么中庸是什么呢?中庸是指,由于我站在矛盾的中間,所以我守住了事物的本質。守住中庸,就能“執兩用中”,是因為我拿住了事物兩極變化的中端,所以對立的兩邊都可以為己所用。
也就是說,中庸是平等看待事物兩面,根據形勢的需要,該左就左,該右就右,該強則強,該弱則弱。不是剛柔兼具,而是時而剛時而柔,根據時勢的發展靈活選擇。但不管選哪一邊,都要守住本心,也就是“執中”。
曾國藩守住自己的本心,守住儒家理想的同時,根據時勢選擇手段:帶兵打仗,需要剛強,就用一下法家的手段;官場斗爭,需要柔弱,就用一下道家的手段。無論道家和法家,都是達成目標的手段,是拿來用的“術”,而程朱理學,則是不變的“道”。用一句時下流行的歌詞來說,曾國藩是“做了那么多改變,只是為了我心中不變”。
(摘自岳麓書社《戰安慶:曾國藩的中年突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