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為什么沒帶來男女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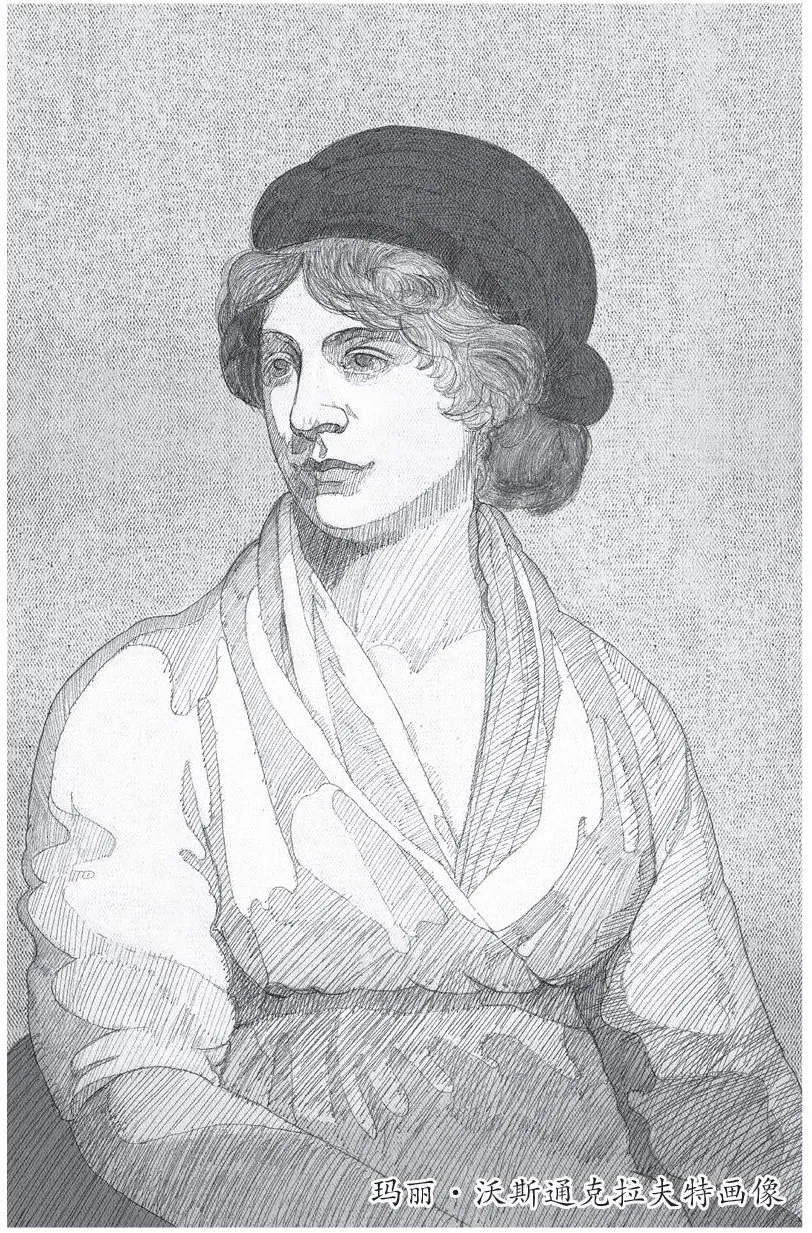
這是一個好問題,因為聯合國的研究表明,盡管女性主義已經掀起了4波“浪潮”,但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女性實現了與男性的社會平等、經濟平等和政治平等。然而在2017年,法國益普索公司在23個國家開展調查,卻發現約45%的女性認為自己已經實現了完全平等。這是怎么回事?
2017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根據從23個國家收集的信息,發布了《性別平等指數》,表明認為女性享有平等機會的男性在美國占72%,在印度和加拿大均占76%,在英國占67%。而或許讓人并不奇怪的是,在接受調查的女性中,認為自己擁有平等權利的人數比例要小得多(約占45%)。也就是說,男性和女性的觀點都無法準確地反映現實。美國作家蘇珊·法魯迪在20世紀90年代初對這種差異進行了研究,并意識到這種對于現實的扭曲是一種更為宏觀的現象的組成部分,它最終將導致每一波女性主義浪潮的失敗。她將這種現象稱為“反沖”。
法魯迪將這個詞用作《反沖:對美國女性的未宣之戰》的書名,并且詳細地探討了女性主義的每項成果是如何迅速地被社會上的反對者(特別是通過媒體)破壞的。她說,逆轉女性主義多年努力成果的手段每次都是一樣的,總是把女性主義歸結為傷害女性的因素,認為女性主義本身(而不是不平等或父權制)才是所有女性問題的根源。
法魯迪發現,無數頭條新聞在宣稱:職業女性“過度勞累”,年紀輕輕就突發心臟病,同時也成為“不孕不育流行病”的受害者。據說,單身女性因“缺少男性”而感到悲傷,對自己的處境感到“沮喪和困惑”。法魯迪說,在報攤上,在電視上,在電影里,在廣告里,甚至在學術期刊上和醫生的辦公室里,到處都能聽到這樣的呼喊。《紐約時報》稱未婚女性“歇斯底里”,她們由于“深層的信心危機”而精神崩潰。這些紛紛擾擾的訊息足以讓任何理智的人大喊:“夠了!無論是什么東西導致了這場噩夢,都必須被阻止!”當然,這正是他們想要的效果——因為他們所謂的這個“東西”就是女性主義。
妓女和污名
西方第一本重要的女性主義理論著作是英國政論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92年出版的《為女權辯護》。沃斯通克拉夫特被公認為是女性主義的鼻祖,正如英國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所說:“即使是現在,我們也能聽到她的聲音,追溯她對世人的影響。”沃斯通克拉夫特呼吁人們采取行動,反對女孩和成年女性缺乏教育和經濟獨立的現狀。然而在此之后的一個世紀里,她的名字幾乎被無可挽回地抹黑了。她說,她為之奮斗的目標不是讓女性“擁有主宰男性的力量,而是擁有主宰她們自己的力量”。
按照現在的觀念,這話聽起來一點都不激進,但事實上,它卻提前67年為英國哲學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的“經典”原則鋪平了道路:“個人擁有主宰自己、主宰自己身心的至高無上的權利。”密爾的版本自其著作《論自由》發表之后,就受到了哲學家的追捧,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版本——闡明女性擁有主宰自身的權利——卻遭遇了混合著困惑、贊同和敵視的目光。
到她38歲去世時,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已經在當時的媒體和知識分子中遭到了徹底的抨擊。他們還大聲指責她是個可恥之人:因為她生了個私生子,接著又對一位挪威船長一見鐘情,滿世界地追隨著這位船長,并且沿途寫了一本暢銷書。由其丈夫威廉·戈德文撰寫并在她身后出版的傳記無意中揭示了她是一個思想多么自由的女人,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連同她的思想)卻因此被斥為“可憐的瘋子”和有悖自然的人:一只“穿襯裙的鬣狗”。她年紀輕輕就死于難產,他們說這正是她應得的下場。
維多利亞時代的反沖
沃斯通克拉夫特因公眾對她的反感而遭到摒棄,甚至連她最熱切的讀者也被說服放棄了她的思想。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大英帝國,白人男性至上、制度化厭女癥和對性事的拘謹(以及私人性暴力)蔚然成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早期女性主義觀點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強烈反沖。中上層階級女性的主流意識形態(或規范)強調純潔、虔誠和家庭生活(也被稱為“真正的女性時尚”)。人們期望女性對生活采取被動的態度,同時贊揚她們的丈夫和父親利用世界各地“未被發現”的資源來發財致富。
現代女性主義者注意到,即便時至今日,針對女性主義的反沖仍然充斥著相同的概念:性、剝削、厭女和男性的“自然”霸權。
然而婦女參政論者挺身而出,反對這種論調,并開始為婦女爭取合法權利和代表權,此乃廣大女性之幸事。在這場運動中,少數人還積極為女性爭取性和生育的權利,例如美國的伏爾泰琳·德·克蕾和瑪AMQoa4E6pEplEysQ3XqQiA==格麗特·桑格。
所有這些女性和團體都被指責為“歇斯底里”和“瘋癲”,像貪婪的老巫婆,試圖奪走長期受苦的男人所擁有的一切。那時的一款明信片上有這樣一首詩,題為《這是男人建造的房子》。它如此描繪希望獲得選舉權的婦女:“狡猾的婦女參政論者,在男人建造的房子里,不擇手段想要擁有一切。”爭取平等的婦女參政論者被說成搶奪男人權力的人,她們穿著男人的衣服,干起“男人的工作”。由于那時男人比女人有權勢,他們的邏輯大行其道,惡猜女性主義者想要扭轉乾坤,讓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當家做主”。因此,自20世紀以來,每一次當女性主義遭受反沖時,“女性追求的不是平等,而是主宰男性”的論調都會故技重施。
被迫回歸家庭
20世紀60和7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打破了50年代西方有關家庭主婦的理念,因此不可避免地引發了針對女性主義的強烈反沖,其中包括這樣的疾呼:女性主義正在摧毀女性作為家庭主婦和母親的“天生”才能。報紙上高喊女性主義者正試圖消除女性氣質,以一種毫無吸引力的中性風格取而代之(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如此)。
在20世紀70和80年代,女性和男性都穿著更為中性化的服裝,愛美的男女都會化妝。女性開始在職場占據一席之地,并進入為男性所主導的機構。據法魯迪說,隨之而來的反沖便圍繞著“不孕不育”、缺男人和壓抑的單身生活等廣為流傳的“神話”。她發現,這些“神話”都是對事實的歪曲。正如法魯迪在《反沖》中所言,反女性主義的信息都是這樣的:“你現在可能自由平等了,但你從未像現在這樣痛苦。”你的處境是拜女性主義所賜,但幸運的是,我們有一些(昂貴的)方法(時尚、節食和化妝品行業),可以讓你重新變得美麗和女性化。“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法魯迪說,“女性運動……是女性最大的敵人。”
如今,隨著女性主義的再次興起,2012年發端于印度的反強奸、反性騷擾運動勢頭迅猛,并于2017年在美國得到強力推動。然而一些女性主義者認為,反沖會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現。法魯迪表示,到2017年12月,社交網上充滿了各種活躍的推文信息,暗示事情可能已經“走過頭了”。在法魯迪看來,依照20世紀80年代的歷史經驗,這正是反沖即將到來的信號。
(摘自譯林出版社《女性主義有什么用?》)(圖注: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畫像;1920年,美國女性爭取投票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