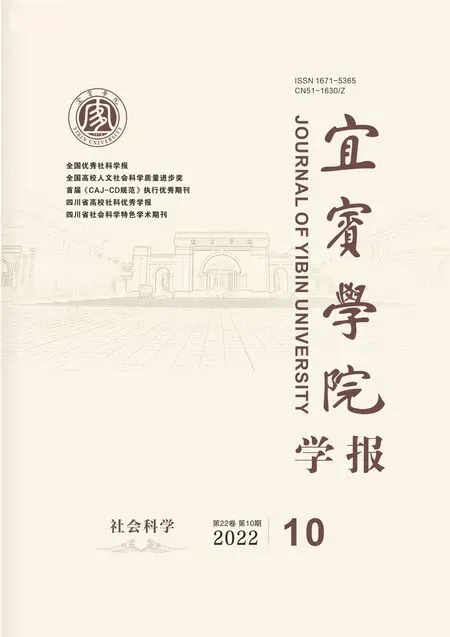中外酒稅史料略考及其得失評析
姚軒鴿
(三亞學院國家治理研究院,海南 三亞 572002)
酒稅作為古今中外王朝或政府對酒消費品所征收的一個稅種,和一切賦稅一樣,其優劣得失,都與國運興衰和王朝更替,特別是社會發展的文明進程緊密相關。亞當斯指出:“國家的繁榮與衰落經常有稅收因素,這一點我們在整個歷史中可以經常看到”[1]8。同樣酒稅的開征與禁止以及征收之多少,向誰征,在哪里征,如何獎懲等理由或許形形色色,但其倫理根據卻具有基礎性、穩定性與可持續性等特征,居于賦稅理財的核心位置。本文不揣冒昧,嘗試通過對中外酒稅史實的倫理回望與考析,以期能為當代中國酒稅及其賦稅治理體系的優化,汲取理性的智識,避免重蹈歷史上酒稅教訓的覆轍。
一、中西酒稅史實概述
(一)中國酒稅史實概述
酒這種消費品之所以能介入人類生活,并被古今中外的消費者所癡迷和沉醉,或是因為它不僅具有滿足人們物質生活需求的生存效應,也具有滿足人們精神生活需求的文化效應等。關于酒最早產生于何時的問題,中外歷史學家從來沒有放棄過探求,遺憾的是,至今尚未獲得精確的史料支持,并形成定論與共識。就本文的探討目的與重點而言,酒稅究竟誕生于何年何月何日并不是特別重要,可留給稅史專家們去考證。如同日本稅史專家朝倉弘教所言,為了解世界關稅歷史,知道某個史料是在公元前400年到公元400年間在何處“就已經足夠了”[2]57。據史料記載,中國開始制酒應該始于大禹時代。《呂氏春秋》:“儀狄作醉”;《戰國策》:“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而且酒既肩負“合歡成禮,祭祀宴賓,皆所必需”的政治職責,也具有滿足人們物質與精神需求等多重功用。諸如“何以解優,唯有杜康”的心理功能;“酒逢知己千杯少”的交流功能,以及“李白斗酒詩百篇”的“藝術”功能等。事實上,“酒作為日常重要飲品,歷來在社會習俗和消費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3]133。邏輯上,有酒便會有王朝或政府對酒的管理——酒政,也會有酒稅。因此,中國酒稅應始于西周時期無疑。因為“酒政,是國家對酒的生產、流通、銷售和使用而制定實施的制度政策的總和”[4]823。史載西周時期就已經有了關市稅。盡管就關市稅的理解上存在不同觀點,因為“‘關市稅’的確切含義并不明確,是指單一的一種賦稅較‘關市稅’,還是指兩種不同的稅,即關稅和市場稅呢?盡管許多研究者傾向于后一種觀點,即是指兩種不同的賦稅”[2]66。但這也說明,西周時期就已經有了酒稅。因此有研究者認為:中國酒稅始于戰國時期,其依據是《商君書·墾令篇》的文字記載,即“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具樸”[5]。但當時中國的關稅收入,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相較于中東和歐洲小得多而已[2]68。因此,不論關市稅是指單一稅,還是兩種稅,即關稅和市場稅?從那時起,酒顯而易見已經作為一種貿易商品開始交易和消費,既有酒政的史實支持,又有關稅貿易的史料佐證,憑此或可判定中國酒稅誕生于西周時期,即“西周說”是有一定道理的。
問題是,國內不少專家認為,中國酒稅始于西漢武帝時的行“榷酒酤”,即由朝廷經營,昭帝時才改專賣為征稅,即主張“漢代說”。《煙酒稅史》就認為:“夫榷酤昉自漢代,煙稅始于盛清,在昔國家僅視為無足輕重之數。未嘗設有專官。今則為國稅入大宗。歲額數以千萬計”[6]1。學者翁禮華也持同論。當然也有學者認為,漢武帝天漢三年實行酒專賣,官釀官銷,“不存在征酒稅問題”。直至漢昭帝時,即于始元六年(前81年)才罷榷酤,實行酒稅制等。或者認為,繼西周創立酒政之后,直至唐宋才在借鑒前朝酒政的基礎上,逐步完善和成熟,才為“酒稅最終成為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奠定了基礎,直至宋代,才“建立了一個更為穩定健全的酒政制度,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7]72。因此認為,中國酒稅應該始于宋代,即主張“宋代說”。學者李華瑞就持此論[8]1。因為“前此(指漢武帝天漢三年前)有無酒稅,未見明文;惟在市區內營業者,既須納市租,則在市內酩酒者納稅無疑”[9]。
此后歷朝歷代,大多根據當時的國運與情勢,有征收也有禁止,稅負有高也有低,征稅方式或寬嚴不一等。即或“榷酤”或開征“酒稅”,或禁酒停征酒稅;或遇災荒,則以榷酤取代稅酒制等。比如咸亨元年七月,唐高宗也因谷貴“斷酤酒”[10]6042。乾元元年二月,“聞京城之中,酒價尤貴,但以曲蘗之費,有損國儲,游惰之徒,益資廢業,其京城內酤酒,即宜禁斷,麥熟之后,任依常式”[11]482。唐代宗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12]1381。此后,稅酒戶制一直持續到大歷十四年。德宗建中年間,則因朝廷出兵平亂,導致國庫空虛,朝廷在建中三年下令“天下悉令官釀”[13]2130,即把酒的專賣權收歸國有。當然,歷史上酒稅的開停與榷酤形式有時也會交錯并行,主要是因為酒政不完備或監管混亂等原因。比如東漢時期,國家只在災荒缺糧時才偶行禁酒,“對酒不收專稅,只收市稅”[7]72。唐穆宗長慶元年出現的榷酒錢與官酤并行就是一例。對此《全唐文》有記載:“榷酒錢有已分配百姓處又置酒店官酤,并諸色榷率,切宜禁斷”①。太和五年,江西洪州也發生過榷酒錢與稅酒戶重疊的事情[14]6043。即認為中國酒稅直到晚清,才實現了從以禁為主,走向以稅為主的重大轉折,開始順應現代國家形成的潮流②。
簡而言之,中國歷代王朝,關于酒稅理財,或因財政需求,或因災疫所迫,或因戰亂窘迫等因素而有所權變,或者開停酒稅,或者官營、民營,或者采取不同的征稅管理方式等。唯一不變的是,酒稅權始終由皇帝一人獨掌,官吏們只是負責具體征收入庫而已。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毋庸諱言,中國古代酒稅因之天然帶有主觀隨意性、相對性與特殊性等特征。就是因為,酒稅及其賦稅權力既缺乏合法性,也缺乏有效的監督,容易背離賦稅理財的終極目的,從而對百姓利益構成大面積侵害,因此老子認為,“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二)國外酒稅史實述略
相對國內酒稅史料而言,國外酒稅史料比較少,本節主要受益于日本關稅史學者朝倉弘教的《世界海關和關稅史》。據考證,國外酒稅最早始于古埃及新國王時期(即公元前609年至公元前594年)。據尼克國王的墓志銘記載,當時征收的關稅(包括酒稅),主要是對葡萄酒和啤酒征收消費稅,稅率10%[2]15。而且在托勒密王朝時代定居于埃及的希臘人,剛剛建立起葡萄園就開始釀酒,埃及國王則毫不猶豫地“開始征收葡萄園稅和釀酒稅,以及巧立名目對葡萄酒征收各種稅。”當然由于稅賦繁重,曾導致國內葡萄酒的價格大幅上升。但埃及國王為了保護釀酒商的利益,也對受到補貼或者保護的進口葡萄稅征收重稅。或許這是“保護性稅收”開征的較早記錄,開始注意酒稅調節產業平衡發展功能的發揮。即征收進出口酒稅,為了保護埃及國內的葡萄酒產業,保證酒稅稅源。另有史料記載,早在古希臘時期(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146年),就已征收葡萄酒銷售稅,而且是“古希臘非常重要的稅收”,主要征收方式是包稅制。但在羅馬時代(公元1世紀至公元2世紀),對葡萄酒稅的征收則采用從量稅方式,即對每壇(大約19升)征收固定的關稅。但關稅的征收方式,則開始由包稅制轉變為由政府官員直接征收。而這一轉變,“對羅馬帝國的政治、經濟和財政體系產生相當影響。”且當時海關葡萄酒稅征收的具體標準是“每駱駝馭每趟1個迪納里厄斯的”[2]36。
直至到了中世紀的歐洲,酒稅征收已經自成體系。因為那時已經“具有按桶、餅,即按計量單位征稅,對酒店里酒的銷售征稅。”而且和其他時間、空間的酒稅一樣,歐洲酒稅征收目的,“都是為了滿足統治者個人的消費,以后有轉變為現金交易的方式。”而英國最早開征的酒稅,應是11世紀的比林斯格特通行稅,即對酒征收貨物稅。在正常情況下,當貨船上共有不多于20桶酒、但至少20桶酒時,可從每10桶酒中拿走1桶酒作為關稅;當貨船上多于20桶酒時,則在桅桿前后各拿1桶酒;對于只載有10桶以下酒的貨船則實行免稅。
近代以來,各個國家幾乎都在征收酒稅。英國都鐸王朝時期,對酒消費品實行從量征收,并另有稅率。比如對其它過境的商品,一律按照每磅1先令或者貨物的5%征稅。法國則在大約1360年,就因為要向英國支付300萬埃居的贖金,便根據布雷蒂尼協定,對酒等商品征稅。而且1369年,就對所有沿盧瓦爾河上下游運輸的貨物,包括酒征稅。事實上,現代國家如美、日、德、澳大利亞等都在征收酒稅,差別僅在于各自的制度背景不同,主要是酒稅權的合法性及其監督的有效性不同,以及征稅方式的文明位階之高低不同而已。
二、酒稅的善惡
(一)酒稅之善
不論中外,自從酒稅開征以來,酒稅能為國民需要的公共產品生產和供給籌備資金,以便政府生產和供給一定的公共產品,滿足全社會和每個國民、每個納稅者的利益或福祉總量,從而成全酒稅及其賦稅的善。特別是在特定的歷史境遇下,酒稅也會肩負起不可推卸的歷史重任,諸如籌集資金,生產和供給保障社會生活與生產基本秩序的“稅富一致、稅福一致、稅道一致、稅識一致”等制度類公共產品,或者提供救災預災,保障人際安全等公共產品。具體說,酒稅功德,或者說酒稅之善如下:
第一,通過增加財政收入,提供保障經濟、文化生活正常運轉的公共產品,維護基本社會秩序。在《煙酒稅史》看來,酒稅“經制國用,視乎稅收。煙酒二者,列為專稅。消費普及編氓,品質屬于奢侈。揆諸利用厚生之旨”[12]9。比如宋天漢三年(前98年)之所以開征酒稅,便是為了擺脫軍費匱乏的困境。中國歷朝歷代酒稅的開征或停征,僅僅只有數量和方式的差異,并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始終不變的目的,都是酒稅的聚財斂財功能。而且,這是各個王朝都特別重視的理財核心問題。當然,和其它賦稅一樣,既是酒稅的功德所依,也是王朝興衰更替的主因之一。據呂夏卿《唐書直筆》卷四所載,唐時酒類專賣收入為138萬余緡,酒課收入占貨幣總收入的15%[15]4490-4491。學者周輝認為,當時“田畝種秫,三之一供釀財曲蘗,猶不充用”[16]47。足見酒稅在宋朝財政收入中的重要作用③。事實上,酒稅收入對宋朝政府的養兵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17]32。史載岳飛手下軍官李啟,就“有心計,能斡旋財賦,惟著布衣草鞋,雨中自執蓋步砌,佐飛軍用甚多”[18]。
就中國歷代王朝酒稅的基本特征而言,差異僅在于,“在不同時期酒稅占帝國收入的比重有增有減。”比如在帝國前中期,多因為“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有余糧可用來釀酒,國家也鼓勵,同時減免酒稅;但在帝國中后期,由于國力的衰弱,財政收入拮據,為了維持王朝統治便開征酒稅,或者增加賦稅,以便增加財政收入[19]133。事實上,即使到了民國時期,酒稅及其賦稅的基本功能還在于財政收入。以1943年為例,“酒稅占煙酒稅收入的59.71%”。就當下中國而言,酒稅收入在政府收入中仍然占據重要比重。比如白酒仍延續在生產(進口)環節征稅的政策,稅率為20%加0.5元/500克(或者500毫升,企業所得稅(25%)等。
在國外,通過酒稅及其賦稅聚財,也是歷代王朝和政府的首要目的。比如1894年以前,俄國就通過“國家壟斷、包稅制和消費稅”攫取酒稅收入。而這項收入在俄國財政收入中,酒稅收入歷來至關重要[20]126。又以法國酒稅為例,1995年間接稅的總收入為2 000億法郎,其中酒類間接稅收入就占其國家總收入的7.47%[21]。其實在當代,酒稅在其它國家和地區中的聚財地位,也很少被忽視,都在開征酒稅。
毋庸諱言,酒稅的財政收入功能與功德是超時空的,因之任何社會和政府都不可或缺和無視。當然也有論者認為,中國歷代朝廷開征稅酒而拋棄榷酒,是因為榷酒的管理成本很高,或者雖榷而私釀難止。特別是因為,據宋代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九《潭州奏復稅酒狀》所言,酒稅可以使“官無尺薪斗米之費,而坐獲利入,民無逮捕抑配之擾,而得飲醇美”。即酒稅既可以保證官家有額外收入可供其繼續奢侈性消費,同時又無虧本的風險,而且可以減少榷酒對百姓的騷擾,化解王朝傾覆的危機與風險。
第二,促進釀酒行業內外產業經濟發展的平衡。即國家可根據不同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情勢,通過酒稅征收,促進或者抑制酒業內外經濟的發展態勢,力爭平等和諧的發展。具體說,國家可通過酒稅的開征或停征,以及酒政的官辦與民營等手段,調節酒業行內行外的發展態勢,促進不同酒稅主體之間利益交換的公正,平衡社會秩序各要素。比如宋代酒政的穩定與健全,便促進了酒業及其它產業經濟的發展。據學者李華瑞研究,北宋初年的酒稅收入最低,在總收入中占比不足10%。但經北宋仁宗慶朝歷年努力才達到高峰,即酒稅收入共計1 710余萬貫,占總收入的38.9%左右。此后雖有下降,但酒稅收入僅占“貨幣總收入的20%左右”[22]192。在學者楊師群看來,就是因為酒業的發展,“為國家提供了巨大的酒課稅利,成為國家財政的重要支柱”[23]125。一句話,酒稅既是王朝的重要賦稅來源,或有功德于相關產業的發展。當然,元代江浙酒業在地區差異存在的前提下的相對、普遍繁榮,也反映出元朝在該地區賦役剝削的繁重[24]109。
但就酒稅對內外產業經濟效應重要性的深刻認知,或非曾歷任晚晴戶部郎中、刑部章京、軍機處章京的陳熾莫屬。陳熾針對當時中國酒業內外發展不公態勢,明確主張必須通過酒稅政策,調節酒業內外發展不公平、不平衡的問題,呼吁必須對外國商人也征收酒稅。具體說,“進口洋酒,僅納值百抽五之海關正稅,及值百抽二·五之子口半稅各一道,即可通行內地,沿途官卡,概免稅厘,其運銷租界商埠者,并子口稅亦于免征,稅率之輕,實近世各國所罕有”[12]1。而且“況自互市局開舶來煙酒,填塞市場。民性嗜奇。金錢外溢。不獨國家財政有關。即論國民經濟亦覺剝蝕靡遺。清季庫藏匱乏”[12]]9。同時,陳熾通過分析法國酒稅之利,主張發展中國本土的葡萄酒業并征酒稅,認為這是作為“開拓利源”的一大舉措。在他看來,“法國葡萄制酒之利,歲合華銀六萬萬兩,居全國出口貨物十分之七。而法之國用,全資酒稅,歲入約三萬萬兩,亦居全國賦稅十分之九。”因此,他援引外國旅游者對中國北方利于種植葡萄的說法大力呼吁,必須發展中國的葡萄酒業。同時認為,就其現實可操作性而言,“外洋酒稅甚重,酒價甚昂,酒之銷路甚廣,能仿造以分其利,固屬美舉”[25]。就是說,如果大力發展中國葡萄酒業,政府可通過征收葡萄酒稅而利國利民。
第三,振濟、救災和防疫。事實上,每當各個王朝遭遇饑荒災疫時,特別是遭遇饑荒時,大多數朝廷便會通過禁酒節糧,包括“寓禁于征”酒稅等舉措,及時發揮酒稅等賦稅振濟、救災和防疫的作用。一方面會通過酒稅的特別支出,向受災地區傾斜,即加大預災、救災和防疫等支出力度。另一方面則會通過直接禁酒或減免酒稅等措施,特別是減少釀酒,消減糧食消耗,紓解饑荒。比如隋代時一旦遇到饑荒缺糧,也會下禁酒令,對酒不收專稅,只收市稅[11]72。唐玄宗朝,唐肅宗朝也“以歲饑,禁酤酒,麥熟之后,任依常式”[13]251。元成宗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集賢學士劉敏中在中書省“陳十事”,其一就認為:“災傷闕食最甚去處,宜與放免酒課,止許窮民小戶造酒貨賣自養,諸有力之家不得造,違者準私酒法科斷。如此即與賑濟無異”[26]。在饑荒時,認為朝廷可通過鼓勵酒業民營,激活民間的自救力量。就是到了民國時期,一旦遇到饑荒,政府也注意運用酒稅工具紓解[27]3。問題在于,饑荒時的酒稅政策,大多缺乏統一法令,因此要求“禁酒之權應收歸中央,不得由各地方政府自行其是”[28]36。就是在中原解放區,酒稅的征收也不是簡單劃一,而是依據各地區條件征收,對于災荒區僅征收30%。
第四,通過為公共產品生產和供給提供資金支持,促進公共福祉的提升。與一切賦稅一樣,酒稅的本質就在于為政府生產和供給公共產品籌集資金。因此,酒稅的普遍功德自然在于,有助為每個國民或者百姓生產和供給所需求的公共產品與服務,從而滿足他們不斷增長的物質與精神需求。固然,不同朝廷和政府所提供之公共產品的類型,及其數量之多寡與質量之高低存在差異。因此,酒稅功德同樣有不同種類和層次。
從中國酒稅的起源看,酒稅為社會提供公共安全類公共產品籌集資金,比如為戰爭類公共產品的開支。當然,戰爭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別。舉例說,抗日戰爭期間,中國酒稅可謂居功至偉。據史料記載,抗戰爆發后,由于國民政府掌控的稅源受限,煙酒稅收入在貨物統稅中的地位更為突出[29]249-250。又據財政部統計,酒稅的作用更不可忽視,即酒稅在煙酒稅中的占比多超過50%,且有超過2/3者(1946年)[30]68。再以抗戰時的四川酒稅為例同樣,酒稅對抗戰社會經濟的貢獻非常大,以1943年為例,酒稅占全國收入的6.55%[30]97-98。
當然,酒稅還有其他功能,比如政治、道德、文化等。比如外國學者學者В.諾羅夫就認為,酒稅有促進國民身心健康的功能,但財政部在設計酒銷售壟斷方案時,認為酒“增強民眾健康是虛,讓國庫拿到更多收入是實。壟斷實踐常常完全將凈化民風拋向一邊”。
(二)酒稅之惡
酒稅之惡毋庸諱言。一方面是因為賦稅乃是必要之惡的本性,即酒稅天然帶有惡性。因為酒稅是對國民財富自由的一種剝奪與侵害,只是由于酒稅及其賦稅的結果可能給國民帶來“善”,所以酒稅也是一種“必要的惡”——善。另一方面是因為,酒稅能否結成善果,既取決于征收的正當性與征收方式的文明等要素,也取決于用稅的合意性與用稅方式的文明等要素。因此,有良知的中外學者總在追問:為何要對酒類消費品征稅?
事實上,與征收其他稅種一樣,“政府希望開源增收來維持其運轉”,也“可能希望人們減少對某種產品的消費,故設法使其變得更加昂貴。”或是因為“過度飲酒會導致各種社會問題,如醉酒駕駛、家庭及其他暴力事件、健康問題和生產率的降低等”[31]85。因此,當代自由派學者弗里德曼就一直反對酒壟斷,在他看來,“消費稅制度根本無力根除酗酒”。中外酒稅征收的啟示在于,酒稅征收正當性越充足,征收方式文明之位階越高,則酒稅的善性就越強,社會功德便越大。相反,酒稅征收正當性越欠缺,征收方式文明之位階越低,則酒稅的善性便越弱,其社會功德便越小。酒稅之惡與原因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酒稅之惡,是因為酒稅正當性不足,背離了酒稅征收的終極目的。由于酒稅正當性是基于酒稅權合法性之大小。因為最高稅權,包括酒稅權,是指諸如征多少,向誰征,在哪里征等重大涉稅事宜的決策權由誰掌握?即是由一人——君主獨掌,還是有全體國民共掌?毋庸置疑,酒稅權力的合法性大小,取決于被管理者——納稅者的同意及其人數之多少。因此,酒稅征收如果缺乏納稅者利益表達機制的支持,也就是未經納稅者同意的程序,其惡性便如定時炸彈。因為酒稅權力合法性的大小決定酒稅權利與義務交換公正性的大小,決定酒稅治理體系的結構性及其穩定程度。以此觀之,1911年以前的中國酒稅及其賦稅而言,其惡性顯而易見。就是因為,歷代百姓一直都被君主當作“資本”對待,而不是作為“根本”敬畏。就酒稅而言,同樣是將百姓當作斂財的對象和根據,而不是服務的對象和主人。
第二,酒稅之惡,是因為酒稅征稅數量的過度與方式的不當所致,加劇了酒稅的惡性,侵害庶民的利益和尊嚴。如酒稅是基于漢武帝劉徹迫于戰爭費用的需要而開征的,但最終釀成大面積民間的災難也是事實。既有酒稅正當性不足的問題(皇帝獨斷),也有征稅過度與征收方式粗暴的原因,致使在聚財斂財導向下的“告緡”等非道德征稅方式大肆泛濫。其危害可從漢武帝晚年頒布的《輪臺罪己詔》管窺一二:“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32]。直到北宋后期,朝廷才為了增加酒稅收入,便鼓勵“比較務”與原酒務之間進行競爭。
而酒稅之惡性,更多是因為酒稅征收過程缺乏監督,缺乏有效性。即由于對酒稅權監督制衡乏力,酒稅征收機構及其稅吏可利用手中的酒稅權,對納稅戶和庶民進行大面積的利益侵害,從而加劇納稅者的酒稅負擔,侵害納稅者和庶民的利益及其人格與尊嚴。一句話,酒稅的征收隨意性、主觀性、不確定性比較大。比如一會兒官辦官收,一會兒又民辦散辦。即就是散辦時,也會因為酒課標準和執行的不公平,引發諸多矛盾與沖突。據脫因,俞希魯所撰《至順鎮江志》卷一五:刺守太平記載,鎮江酒戶,曾因攤派的酒課稅額過高,引發“民愈困蹙,棄產業輟衣食以輸,甚者或逃亡焉”之惡果。更有甚者,官吏們會合謀聯手欺壓酒戶。具體說,有如下表現:
一是在不同地區、不同時間、不同社會背景下,酒稅政策經常變動,而且執行的稅率標準也會頻繁變動。而理由竟然是因為不同地區間的酒價不一,因此很快引發了朝廷及各級官吏們借酒稅斂財的沖動。又比如,宋時“舊四川酒課歲為錢一百四十萬絡,自是遵增至六百九十余萬緡”[33]。即一年左右時間,酒課即劇增至五倍。而夔州路,原來只有場店100余處,一年之內,也一下子增添至600余處[34]。邏輯上,稅吏們為了完成財政收入任務,如果酒戶限內納稅不足,就給隨意定罪,甚至“虛指債務,妄起訟端,郡縣急于官課,更不問有無通欠,遂使平人承認,械頸受墨,道路相望,因系坐獄,殊無虛日”[35]3533。甚至,即使發現了問題,甚至“怨譽四起,言者乞罷四川榷鹽、榷酷,以安遠民。”官吏們也不會認錯改錯,比如宋時川陜宣撫處置使張浚,便以“酒課已為軍食所仰”而不愿更改。更有甚者如南宋初期,因為戰局險惡、財政拮據,軍費開支捉襟見肘,竟然鼓勵和容忍,“八仙過海”斂財之能。
從表中可以看出,治療組顯效20例,有效12例,總有效率94.11%,對照組顯效14例,有效12例,總有效率76.47%,二者具有顯著性差異(P<0.05)。
二是由于朝廷各級官吏征收壓力的松緊不同,對具體酒稅的自由裁量尺度把握各異,加劇了酒稅之惡。比如元代酒課繁苛,就是因為對外大肆擴張,財政開支空前巨大。元人劉詵因此作萬戶酒歌正史:“城中禁釀五十年,目斷吹秫江東煙。務中稅增價愈貴,舉盞可盡官緡千”[36]。當然,官吏們的斂財積極性,主要是因為朝廷有鼓勵酒務增收課利的獎賞辦法——元豐賞格法,旨在從酒稅增收中抽一定比率,直接獎勵酒稅官吏,具體規定:“酒務監官,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二厘,酒務專匠,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一厘”[37]。因此官吏們便為了獲得獎賞,采用提高征稅機構稅入、多設征稅點等方式促使酒稅的增長,加劇酒稅之惡。而這種鼓勵征收機關多征稅收的舉措,國外也有,就是現代國家和政府同樣也有⑦。當然為了杜絕此種現象,一些朝廷和政府也頒布過一些法令進行監督和杜絕,比如規定征稅機構要將稅目、稅率張榜公布:“常稅名物,令有司件析揭榜頒行天下”[38]。問題是,由于酒稅權缺乏根本性的有效監督⑧。結果,有些酒稅征收者,便竭力搜刮,不惜竭澤而漁。
三是針對不同的酒稅繳納者,對酒稅政策的執行方式不同,也會加劇酒稅之惡,表現在標準不一,對有權有勢者是一個標準,對無權無勢者又是另一個要求。如在農村征收酒稅,竟以地畝多寡征收酒課,而且“酒課額有定,而民之貧富無常,貧或數贏,富或數縮,侯(江西靖安縣尹胡愿——引者)為均派,隨糧數之多寡定課數,貧民大便”[39]。寧宗時黃池鎮的官吏,酒課“日才一二百千,商旅如云,何患難辦?乃于官課之外,又多造白酒小酒,勒令行老,排擔抑依,立定額數,不容少虧,所得之錢,不知何用?”[40]難怪宋元時馬端臨認為,“酒政之為民害至此極矣,不可不稍寬也”[41]。
第三,酒稅之惡,是因為“用之于民”稅款數量不足或存在結構性不合理,以及用稅方式的不公平而加劇。即因為用稅環節的問題,背離了酒稅征收的終極目的,從而加劇了酒稅之惡。既不能造福于庶民,反倒侵害和打擾百姓的正常生活,百姓的基本生活秩序遭遇系統性風險沖擊,直至官逼民反。比如基于軍賦而征收的酒稅,就很容易異化為各級官吏橫征暴斂的借口,并將所征收上來的酒稅移作他用,不是被官吏們揮霍浪費,就是中包各級胥吏的私囊,完全背離征稅和用稅的初衷。或正因如此,理性的朝廷,為了家天下的江山永固,通常也會下詔糾弊,減少酒稅總額,防止管理腐敗尋租。比如南宋淳熙三年詔,“四川酒課折估困弊,可減額錢四十七萬三千五百余緡”。南宋中期,“今四川酒課累減之余,猶為絡錢四百一于余萬”。因此直到南宋后期,還在不斷減免四川酒課[42]。
中國如此,國外酒稅也是如此。或者充實國庫,增收公共資金,生產和提供高性價比的公共產品,促進經濟社會進步繁榮,增進全社會和每個國民的利益或福祉總量;或者引發社會危機,致使酒稅成為破壞社會生產和生活秩序的導火索。目前國外不少國家,酒稅還是重要財政收入來源,而且具有相對完備和優良的酒稅征收體系。比在西班牙就根據歐盟消費稅法的規定,酒稅屬于從量稅,高度酒的稅率一般按照酒精度設置。同時則在于發揮酒稅調節經濟,促進國民健康等功能,比如挪威人均飲酒量為6升,低于世界平均值,就是因為在其政府看來,酒價是影響酒消費水平和相關疾病的關鍵因素,因此便運用酒稅來干預價格,通過酒稅減少相關傷害實施公共健康策略。
當然,酒稅更多明顯之惡在于,因為酒稅征收缺乏正當性以及不公而引發納稅者抗議活動,甚至成為內亂、內戰的導火索。中外因稅收問題引發的系統性社會動亂,甚至王朝更替以及大規模戰爭的事例很多。比如宋時慶元府(浙江寧波市)翁山酒務下轄子坊十五所,宋理宗時官監酒務廢罷后由民戶買撲,即嘉熙四年(1240)“改坊為萬戶,任從民間醞造,卻將額錢攤抑一縣有物力之家”,致使有物力之家(鄉村主戶和城市坊郭戶),因稅負分配不公,“民被其害”而“詞訟紛紛”,此后便有了“坊場改萬戶,貧富齊受苦”的謠言[33]391。或正因如此,美國稅史學者亞當斯才一再告誡世人,重大歷史事件,“其根源都是稅收”。比如1635年,法國君主試圖在波爾多(Bordeaux)開征葡萄酒稅時,憤怒的納稅人怒吼道:“征稅官去死吧!殺死征稅官”[1]227。同時,酒稅也導致1851年法國外省的反波拿巴起義。再比如美國1791年3月通過的《國產酒稅法案》,就因為規定每加侖以國內原料釀造的酒征稅9~25美分,以國外原料釀造的酒要征稅11~30美分,從而引發大面積的抗稅事件。
結語
酒稅在各個國家都存在。就其表象而言,差別僅在于開征時間的早晚,稅率有高有低,征收方式繁簡,文明位階高低等。但稅收作為一種“必要的惡”,即就其“目的利己、手段利他,結果為善”而言,酒稅同樣具有“必要的惡”之性質。因為賦稅是對國民財富自由的一種消減或侵害,征稅是一種手段害。或如亞當斯所言,因為“稅收是強制性勒索”[1]456。但就征稅終極目的在于給國民生產和供給“高性價比”的公共產品,增進全社會和每個國民的利益或福祉總量看,酒稅作為一個稅種,也應該具備善之德性。問題是,由于酒稅征收的現實情境之復雜性,以及具體征收實踐的可操作性等因素,酒稅既可能為善,展示其“必要的惡”之善性,也可能為惡,展示其“必要的惡”之惡性。因此,從倫理視域回望中外酒稅歷史的天空,既有陰晴圓缺、波詭云譎的焦慮時日,也有云淡風輕、萬里晴空的愜意歲月。
①“榷酒錢有已分配百姓處又置酒店官酤,并諸色榷率,切宜禁斷。”見董誥等著《全唐文》(卷六十六),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03頁。
②見任紅壓《晚清四川酒稅的創征——以〈南部檔案〉為主的考察》,載于《西華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
③李華瑞認為,北宋慶歷年間,全國的酒稅收入曾經高達1 700萬貫,熙寧后則維持在1 300萬貫左右,南宋紹興有1 400萬貫。北宋熙寧時,東京、杭州和成都府一年的酒課,就達35萬貫以上。李華瑞《南宋的酒庫與軍費》,載于《人文雜志》,2016年第3期,第80頁。
④財政部財政年鑒編纂處:《財政年鑒三編》,下冊:第八篇“貨物稅”第十五章“國產煙酒類稅”,1948年,第68頁。
⑤“至外洋食物,照約免征,即以洋酒一宗,每歲入口,已及千萬,宜于十年換約,刪去此條。洋貨之入華者,設法以收利權;土貨之出洋者,減稅以輕成本,此將來之商務不可不開也。”轉引自楊自鵬《訪歐歸來話酒稅之二——法國的酒類稅收制度》,載于《中國酒》,1997年第4期。
⑥弗里德曼在其出版的《歐洲公報》上,他就一再抱怨,實行消費稅之后反導致酗酒泛濫,民眾酗酒愈演愈烈。因此主張有節制地提高消費稅,以避免私釀酒;可適當提高專賣稅;也應為地方自治機構和城市提供一部分收入。見弗里德曼《俄國酒壟斷》,第127頁。
⑦比如美國,也曾“為了強制執行這一稅收(指開征威士忌酒稅——筆者注),組建了國內收入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前身。全國被分成十四個地區,同時有十四個地區主管。每一位主管可以得到他所在地區所征稅款的1%;每一位稅務官員可以得到他所征稅款的4%。剩下的95%交給國庫。這種征管制度將消費稅變成了一種稅收承包制度——它將征稅官員置于納稅人的對立面。對于稅務官員而言,他們所征收的稅款越多,個人所獲得的利潤越多。”見查爾斯?亞當斯著,翟繼光譯《善與惡——稅收在文明進程中的影響》(第二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32頁。
⑧“其間課利雖不虧,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為少衰。詳究厥由,不獨以財用窘急,轉運司督迫所致,蓋緣上件給錢充賞條貫,故人人務為刻虐,以希歲終之賞。”蘇軾《東坡全集》(卷六十二),奏議八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