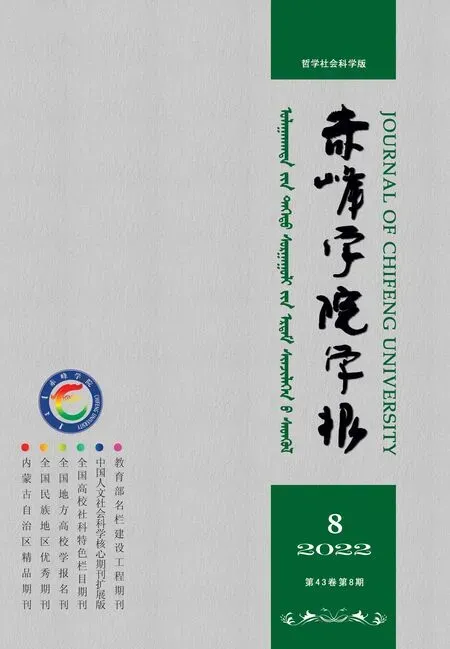接受美學視角下外國文學作品的漢譯研究
徐俊俊
(合肥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安徽 合肥 230011)
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既要在原文語境中利用關聯推理去理解原作意圖及意義,與原作在認知上趨同,又要通過譯文將自己理解的原作意圖及相關信息與譯文讀者進行交流,從而完成一次跨文化語言的交流活動。翻譯離不開讀者的參與:譯者閱讀原文時是源語文本讀者,表達譯文時要考慮譯文讀者,譯文質量的評定并不只是以源語文本作為唯一標準,也有賴于譯文讀者的接受程度;而接受美學正是以讀者為中心來研究文本的接受效果。要將外國優秀文學作品翻譯成漢語,不僅需要優秀的漢語譯者體會原文的內涵,更需要譯者將接受美學中的主張應用到翻譯過程中,凸顯漢語的魅力和美感。從這一角度看,接受美學視角下的漢譯研究頗具現實意義。
一、接受美學的理論基礎
(一)反對歷史客觀主義
認同接受美學理論的學家對歷史客觀主義理論持反對態度,即反對固定的文學作品只具備固定不變的內涵和意義。而隨著時間因素的影響和歷史經驗的積累,文學作品的內涵和意義會呈現出更新和發展的狀態,他們將這一理論指導下的研究視為一種經驗研究,并且接受歷史條件因素對研究工作開展所帶來的制約和影響。這一理論的確立者是H.G.加達默爾,后經P.里科爾從哲學維度進行了補充解釋,成為接受美學理論研究的重要基礎,也同步為這一理論的研究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1]。
(二)理論先驅
在不同的研究階段,不同的哲學家和美學家對于接受美學理論進行了不斷的更新和豐富。R.因加爾登(波蘭現象學美學家)認為,讀者在閱讀文學作品時應當首先重視作品的基本特征和結構形式,在此基礎上再本著一種具有創造性的態度對作品進行認知和了解。而結構主義美學之父J.穆卡洛夫斯基則認為文學作品的本質是一種物質成品,其審美價值具有隱蔽性,需要讀者通過自身的理解和分析體會其審美價值。另外,法國哲學家里科爾則以詩歌為切入點,提出詩歌在相關研究中對于認識和發現信息的價值有重要的意義。
二、接受美學的核心觀點分析
(一)讀者中心觀點
接受美學理論將讀者置于重要的地位上,將研究工作的側重點轉移到作品文本與讀者之間的關系研究上。文學作品的創作要首先做到為讀者所接受,隨后才能實現文學價值的體現。這里所指的“接受”非被動接受,而強調主動積極的接受。從某種程度上來講,讀者依托自身的文化背景、文學修養、理解能力對文學作品產生不同感受的過程,也是讀者參與文學作品價值再塑造的過程。只有讀者以一種主觀上積極的態度理解和接受文學作品,才能取得更好的閱讀參與價值再創造的效果,讀者帶給文學作品內涵的變化和文學價值的發展才更具備時代價值和先進價值。
(二)期待視野觀點
期待視野觀點側重于強調對接受者經驗的吸收和發展,其具體內涵是指作為讀者,在閱讀文學作品前都呈現一種先在知識的狀態。這是新事物被既往經驗理解和接受的關鍵要點,同時也是期待視野的體現。另外,期待視野還強調讀者所接受的作品內容和信息需要通過多種不同的信號傳輸和呈現形式來實現,具體包括內容預告、暗示以及形式化的信號傳輸。通過不同形式的引導和激發,盡可能將讀者沉睡的閱讀記憶喚醒,同時引出作者具有相對固定性的情感態度。這是不斷引導作者的閱讀期待,并且促使其原始的閱讀期待在閱讀進程中不斷修正和完善的有效路徑[4]。
(三)文本召喚結構觀點
在接受美學背景下,文學作品中固定的語言文字在不同的時代會產生新的意義變化,這主要是依托文學作品語言意義的未定性和意義空白特征而言的。這一特征也充分體現出讀者在文學作品價值產生中的重要性,即文學作品的價值體現需要通過不同讀者的閱讀來激發和體現。這主要是由于不同讀者的理解力、想象力和創造力與文學作品本文自身的意義空白和未定性具有相關性和銜接性特征,這也為兩者之間的相互轉換提供了關鍵性條件。轉換形成的結構是文學作品的基礎結構,即召喚結構。從功能性的角度出發進行分析,文本所具備的召喚結構的主要功能點有二:一是促進讀者在閱讀進程的推進過程中對文本內容中的未定性空間形成一個具有確定性意義的理解,實現文本中空白部分意義的填補和完善[5]。二是保持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對作品本身內容的熱情和興趣。
三、接受美學與外國文學作品漢譯的關系簡析
(一)為外國文學的漢譯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外國文學作品漢譯工作的開展有了接受美學的支持,便于翻譯人員以審美價值和文本信息傳遞為翻譯工作開展的切入點,以一種中國讀者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語言文字表達和呈現形式對文學作品進行重現。對于翻譯人員來講,這也為文學作品的翻譯研究開辟了新的領域,提供了新的視角[6]。
(二)與中國讀者思維方式相匹配
不同地域或國家的讀者在閱讀文學作品時,由于自身長期受到所處文化、語言和思維方式的熏染,導致習俗和價值觀、語言結構和思維習慣、社交禮儀和生活習慣以及文學語言的架構截然不同。當翻譯人員依托接受美學視角開展作品翻譯時,可通過不同的翻譯策略的靈活運用盡可能為中國讀者呈現出一幅易于理解和接受的畫景,這是幫助中國讀者群體獲得更好的審美閱讀體驗。
四、基于接受美學的外國文學翻譯策略
(一)翻譯者應當發揮好信息傳達的橋梁作用
作為翻譯人員,應當在翻譯的過程中全方位調動自身的知識儲備,盡可能地還原原作者本身的信息傳達意圖[7]。對于外國文學作品的漢譯而言,追求最真實的翻譯效果是翻譯工作開展最基本層面的要求。從翻譯后的作品角度分析,翻譯者則又充當著文學作品的二次創作作者角色。到了這一階段,翻譯人員就需要從中國讀者的角度對其期待視野進行預估,并且重視通過翻譯過程的執行為引導讀者參與到翻譯的過程中創造條件。作為文學作品的翻譯人員,應當在翻譯中充分追求讀者的期待視野與原文文本結構和內涵的融合,并且同步考慮讀者對所閱讀作品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充當好信息傳達的橋梁作用。
(二)重點關注讀者在文學作品翻譯中的主體地位
不同時代的譯者會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以滿足目的語讀者的期待視野和審美情趣。這也毫無疑問地導致了同一文學作品在不同歷史時期擁有不同的翻譯版本。隨著國際交流的不斷深入,文學翻譯界普遍倡議的翻譯原則是盡量直譯以保持原文風味,忠實地傳達原文文化和審美信息,以滿足讀者求實求異的心理。因此,翻譯工作的開展中應當合理采用直譯和意譯兩種翻譯策略,使翻譯和外國文學作品的閱讀這種具有跨文化特征的交流活動更符合中國讀者群體的閱讀需求和精神思想引導需求,盡可能在中國讀者的期待視野邊界范圍內創造空白的意義空間。
(三)重視作品翻譯中的語句組織方法優化
1.注重詞匯的合理選擇
從基本的大原則角度出發,外國文學作品中的詞匯選擇應當重視翻譯效果的理解性以及共鳴性。在具體落實中,要求翻譯人員多使用中國讀者更加易于理解的詞匯融入翻譯文本中,這有利于降低中國讀者主觀上的閱讀困難感。另外,關于提升共鳴性方面,譯者的翻譯可為讀者提供更加生動的閱讀體驗。例如,在翻譯《Uncle Tom’s Cabin》這一兒童文學作品時,作品名的翻譯就有多個不同的版本。受所處的歷史文化背景對其翻譯產生的深刻影響,林紓將之翻譯為《黑奴呼吁天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譯者又將其翻譯成為《湯姆叔叔的小屋》。在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時代背景下,在中華民族危在旦夕之際,愛國人士林紓悲痛之心情可想而知。“豈獨傷心在黑奴。”當時讀者的感情和心聲可見一斑。譯者林紓與當時讀者擁有同樣的悲憤的感情,因此產生了強烈的感情共鳴。當時這種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決定了讀者在文學閱讀中的期待視野和審美情趣。讀者對文學的審美判斷和審美情趣還建立在仍占有主導地位的文言文基礎上。林紓在翻譯過程中,將他生活的時代帶給他的“悲”“憤”和“痛”與原文中所描述的“悲”“憤”和“痛”相聯系(即接受美學所說的“文本召喚”)并不遺余力地將它展現出來。
2.重視句式結構的適當簡化
從原著出發進行觀察,可知外文文學作品在原著內容中使用句式結構復雜性較高的長句、倒裝句以及被動句的頻率是相對較高的,而漢語句法關系主要靠詞序和語義關系表達,句子中成分與成分之間的關系比較內在化、隱含化、模糊化,往往并不追求形式的完整,而只求達意而已。因此翻譯人員就需要從作品的翻譯階段入手,充分分析和理解句式中包含的語法結構和特征,梳理好不同句式的主謂賓結構,并將其翻譯出來,如翻譯人員能力素質較高,還可適當嘗試在翻譯過程中融入一定的思想感情,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中包含的文字和情感風格。例如,在《愛麗絲漫游奇境記》中“Her bees and her crows and her wolves…but if she could only get hold of the Silver Shoes, they would…”句子的翻譯中,“but if she could only…they would give her more power than all the other things she had lost.”一句就屬于典型的復句結構。如果翻譯者不考慮讀者群體的學習理解能力,直接將其按照原始的長句結構翻譯,則可翻譯為“如果他們得到這些,他們就會獲得比以前失去的魔力更為強大的魔力”。這種詞匯的重復表達會給閱讀帶來一定的障礙,使讀者感覺到閱讀句子的冗長感。為了減低讀者的這種閱讀負面體驗感,翻譯人員就可以適當通過句子分解的方法,將一個復雜的句子分解為兩個簡單的句子。翻譯成為“他們給她強大的魔力,比她以前失去的魔力更強大”,就更便于讀者的理解。句子內涵的層次感也更加鮮明。
3.重視修辭手法的合理應用
修辭手法在文學作品翻譯中的應用,主要目的在于美化翻譯的效果,使得句子的呈現效果更加具有文采,這也是提升外國文學作品翻譯質量的有效措施。具體的修辭手法類型包括了比喻、排比、擬人等。合理地運用不同的修辭手法是取得良好翻譯效果的科學手段。例如,排比修辭手法在翻譯中的合理應用,就有利于增強文學作品翻譯內容的感染力,使得作者的情感表達效果體現得更為充分。例如,在《瘸腿小王子》這部作品中,“Winds blowing,water flowing, trees stirring, insects whirring,…cattle, bleating sheep, grunting…”一句就包含了多個排比元素。不同的景物、動物本身具備并列排比關系,而他們發出的聲音又同步形成了另一組具有排比關系的元素。聲音和景象的結合不僅使得文字表達的生動性得到了加強,也給讀者創造了更加充分的想象空間。例如,小羊咩咩的叫聲、小溪潺潺的流水聲、風兒呼啦啦吹動的聲音等,都是運用排比方式進行翻譯,提升翻譯效果生動性的表現。
五、結語
通過本文的分析可知,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有了接受美學視角的支撐,不僅促使翻譯手法和思路得到了創新,更體現出了翻譯工作開展中對譯入語讀者引起重視的重要性。翻譯工作者需要從自身的角度出發,在合理真實地通過翻譯表達出文學作品的內涵的同時,依托讀者中心、期待視野、文本召喚結構三方面基本內涵,通過對翻譯工作者提出要求、依托讀者本位思想以及合理運用語句組織方式方法的路徑提升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質量,為讀者創造更好的外國文學作品閱讀鑒賞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