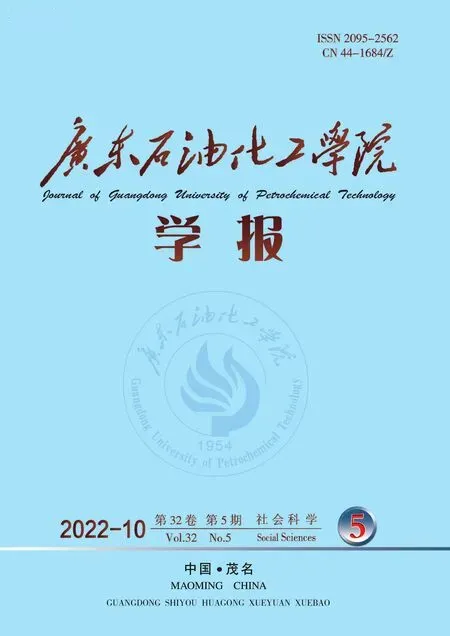概念隱喻理論下劉禹錫《竹枝詞》中的“人心”隱喻英譯研究
梁淑英
(1.韶關學院 外國語學院,廣東 韶關 512000;2.澳門大學 人文學院,中國 澳門 999078)
中國的傳統詩詞文化輸出有利于促進世界文學的蓬勃發展。中國的古詩詞的英譯是中國文化在世界傳播的重要力量。中國古詩源遠流長,其凝練的語言和蘊意豐富而鮮明的意象令學界著迷神往[1]。中唐詩人代表劉禹錫,系“著名文學家、思想家和政治家,被尊稱為‘詩豪’”[2]。顛沛流離的官宦生活,是滋養劉禹錫詩情的土壤,其以迥異于流俗的“骨干氣魄”而成為中唐時期獨樹一幟的詩人[3]。劉禹錫在夔州創作的《竹枝詞》組詩,景語清新、發人深省。劉禹錫借《竹枝詞》的民歌形式創作了多首膾炙人口的作品,本文選取《竹枝詞 其一》《竹枝詞(之六)》《竹枝詞(之七)》,以集中探討劉禹錫對人性“不可測”的慨嘆,以及其英譯本如何體現原詩中“景語”與“人心”的哲學思辨,尤其是如何向目的語讀者傳遞詩人的情緒。本文在概念隱喻理論的觀照下,對劉禹錫《竹枝詞》詩作的英譯展開深度研究,闡述其詩作符號意象的內涵和外延,以描繪其在跨文化交流過程中被翻譯和被解讀的改寫軌跡。
1 漢語古詩的隱喻英譯
漢語古詩中的詩性向來給翻譯帶來挑戰。漢語古詩中充滿了豐富的隱喻,其英譯對源文本中的隱喻詩性捕捉和再現,可借概念隱喻理論窺探一二。隱喻是想象理性,尤其在詩性隱喻中,新的概念隱喻通過語言媒介得以創造[4]。在詩詞翻譯中,譯者若想把隱喻調整安置在新的語境里,可以采取三種可能的手段,即提供與原隱喻的意義完全對等的隱,提供與原隱喻意義相似的隱喻式短語,在原隱喻無法被翻譯的情況下提供與其最相近的文學闡釋[5]。對隱喻的闡釋不僅跟說話者對編碼的詞條的恒定意義的語言知識相關,同時也跟文化背景所決定的知識世界的關聯意義相關[6]。隱喻的翻譯議題有三,分別是“轉換程序(transfer procedures)”“文本結構(text-typologies)”和“文化特性(cultural specificity)”[7]。古詩翻譯中,不能忽視其“英譯策略體系的層級性、關聯性和動態性”[8];同時,鑒于不同民族文學的文化特性的不可通約性,在翻譯實踐中很難完全實現原隱喻的具體意蘊。因此,翻譯時可采用替換法來重構目的語中的隱喻,以使目的語文本中新建的文本結構能最大限度再現原文本中隱喻的意蘊。
2 《竹枝詞 其一》中天氣的“人心”隱喻英譯
竹枝詞歷來以傳頌愛情的主題居多,原是四川一帶流行的民歌創作形式。劉禹錫這首《竹枝詞 其一》緊緊圍繞題眼“晴(情)”,采用白描的手法,以清新的風格,結合“實”的敘事與“虛”的類比,描述文本中隱含不見的主人公的情感體驗。
原文:竹枝詞 其一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9]90。
譯文:BAMBOO BRANCH SONG
Between the willows green the river flows along; My dear one in a boat is heard to sing a song. The west is veiled in rain; the east enjoys sunshine. My dear one is as deep in love as day is fine[9]91.
詩作的主人公并不明晰,但是主人公的視覺和聽覺所投射的對象清晰明了,即詩行的第二句中的“郞”,整首作品以“郎”為焦點輻射至文本的內涵范圍,例如,自然環境的季節提示和主人公的心理活動。詩作的第一句“楊柳青青”的爆青楊柳,直指當下季節為萬物復蘇的春季;此時主人公的春情萌動嵌入合適的文本語境之中,情感預設的框架已然搭好。“江水平”是與春季的代表性的“青楊柳”并舉,推動主人公的情感發展,蘊含更為豐富的環境渲染的感性厚度。江上緩緩行船,眼看兩岸楊柳青青,柔弱的柳枝隨風輕輕擺動,是與“郞”相對的主人公的觀景寫照。春情應可似春水江流澎湃滔滔;而在此情此景中,卻以自然節制、涓涓平流的方式呈現,給下文主人公的情感推高埋下伏筆。詩題“竹枝詞”采用直譯和意譯的翻譯策略,其中“竹枝”直譯為“Bamboo Branch”,而“詞”意譯為“Song”,傳遞給英語讀者的信息是這首詩是一首歌曲,營造“未成曲調先有情”的情感認知氛圍。縱觀該詩作的英譯本,“My dear one”的提示中,可見采用的視角是第一人稱。這個主人公“我”與原詩作中的主人公并非完全契合。詩作的主人公原型可分為兩類討論,即原詩作的主人公可以是詩人描述的客觀對象而作為一個被書寫的客體呈現在文本中,詩人采用全知全能的視角窺探主人公的內心世界;或者說,原詩作的主人公可以和詩人合為一體、不分彼此,即詩作英譯本的主人公設置模式。
詩作的第二句引入的“歌聲”似天籟之音,如主人公忽逢甘露,滋潤著自己期待愛情回應的干涸心靈。江上的蒼茫意境中,原本只有主人公一人與環境融為一體,展開綿密的互動交流。此時主人公內心活動投射的“郞”似先聲奪人。主人公為主體,環境為客體的二元對立環境中,引入了第三方“郞”——作為新的視野而成為主人公聽的對象和客體,詩作的心理情節發展進入螺旋式上升的質變階段。主人公從滿足于自然春景輸送的慰藉的第一層實在界,跨入自己情感猜測的第二層想象界。于此,主人公的視閾聽閾所囊括之物戛然而止,而主人公的情感重戲才拉開帷幕。前述中的“郞”譯作“My dear one”,使讀者期待有模糊性。原作中主人公與“郞”的關系不明,可能是兩情相悅,也可能是兩相思兩不知,也可能是主人公單相思。原詩中“聞郞歌聲”和“有晴無晴”在英譯本中統攝為“My dear one”以敘述發展情節,反復吟詠,符合“Song”曲子歌詠的特點要求。譯文把原詩的“青柳平江”和“東日西雨”處理成平行并列的兩道風景,格式工整,力圖把全詩的圖畫處理控制在同一時間維度。原詩作中的實在界和想象界的區分,在英譯策略的改寫中成為一統的實在界,詩意的連貫性更強。譯文末句的“as day is fine”更多偏向于前文的“the east enjoys sunshine”,可見譯文最后曲子的收尾是歌頌主人公與“郞”之間積極陽光的深厚情感,與原詩作中的曖昧不清有著明顯不同。
詩作的后半部分的兩句,看似跟前兩句關系不大,實則相互交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第三句和第四句的“日”“雨”“晴”是主人公想象界里心理起伏投射的自然幻景。東邊的“日”和西邊的“雨”形成陰陽分割的反立圖像,似光明與黑暗的對立,肯定與否定的力量較勁。第一句中描述的楊柳和江水,是構建和平畫景的雙元巨柱;第三句中提及的太陽和陰雨則是破壞前景平靜安寧的爆炸性顛覆力量。天地交合、陰陽合抱的傳統理式遭到前所未有的割裂,主人公的情感猶豫和猜忌在字里行間表露無疑。第二句中的“郞歌”乃大音希聲,讀者無從猜測歌的字面意義,只能通過主人公后續在第三句和第四句中,隱隱約約可猜出被抹去的情感印記。詩作第四句的“有晴”和“無晴”繼續建構分裂對比的圖式。“道”應是有聲思辨而作其述,于此是對主人公心中情感的隱秘窺見的無聲表白。“道”的主體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自然之語,二是主人公之感。自然之語,意為闡釋基于自然中天氣變幻的陰晴不定而引發的無奈之感;主人公之感,意為揭示與變幻天氣一樣難以捉摸和把握的人心,即主人公通過對“郎歌”的猜想而表露自己慌亂不安的心情。“晴”與“情”諧音,恰到好處地描繪了主人公對“郎”思念的嬌羞自然之態。整首詩作,內容樸質,手法清新,景語先行,情語水到渠成。第三句的“西邊雨”譯作“The west is veiled in rain”,使用被動語態“is veiled”,可見詩中的雨勢并不厲害,只是稍微蒙上了一層雨意。原詩作中的“東日西雨”指自然天氣的兩種極端現象的概念化的強烈對比,為后文的“有晴無晴”做鮮明的背景襯托。譯文 “The west is veiled in rain(雨蒙蒙的西邊)”和“the east enjoys sunshine(陽光充沛的東邊)”是用浪漫主義的情調側重強調“吾郞”情深義重的輕盈歡快之感,因此譯文的末句只有一元的表達,對原詩作中“無晴(情)”與“有晴(情)”的正面對立輕描淡寫,而著墨于原詩中的“卻”字,祛除了遮蔽的“無晴”,轉而全力敘述有情郎的有情事,因此第三句的“西邊雨”英譯的轉調處理,自有深意。
3 《竹枝詞(之六)》中磐石的“人心”隱喻英譯
《竹枝詞 其一》用變幻莫測的天氣襯托“人心”不可測,而《竹枝詞(之六)》采用自然中石頭的“不能摧”來反襯“人心”的反復無常。
原文:竹枝詞(之六)
城西門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惱人心不如石,少時東去復西來[10]40。
譯文:song of the bamboo branch No.6
out in front of the town’s western gate / the great rock stands in the middle of the river / powerful waves bash it year in and year out / but they cannot wash it away / it makes me sad the human heart / doesn’t rest as solid as this stone / the heart goes to the east for awhile / and then goes west a split second later[10]40
首句的視角焦點是“滟滪堆”,是個實實在在的存在物體。此“滟滪堆”被置于門前的地理位置,處在前景化之中,為下文的“物語”轉“情語”作鋪墊渲染。“滟滪堆”與第三句的“石”應是互相呼應的關系。城西門前有“滟滪堆”,其形象獨特,頗為引人注目。“城西門前”是公共空間,且是臨水而立,所以才會有第二句中“不能摧”的感慨。第二句的“年年波浪”被設置成“滟滪堆”的自然力量的宿敵。“水滴石穿”的世間常理在此并不適用,“波浪”的損毀之力根本于“滟滪堆”無用,反倒更強化了“滟滪堆”堅不可摧的物理特性,從而上升為人格化的品質特性。“滟滪堆”沒有自由選擇的權力,其處于被動的地位,但卻能如人所愿般迎向當頭的水浪而巋然不腐。該“滟滪堆”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命運,卻被擬化成勇敢地向摧殘自身命運的外部環境發起挑戰的形象。譯詩中,首先要看到譯文的第五句中的“me”是補充原文所沒有提示的敘事主語,那譯詩則以“我”之視角來借物抒情。“我”是因眼前的“滟滪堆”有感而發。在“我”的敘事視角的操縱下,原文中的“滟滪堆”的地理位置在譯文中顯得更為明確,有別于原文中的“滟滪堆”的地理位置的含糊。“滟滪堆”被譯作“the great rock(巨石)”,“in the middle of the river”標明其位置是河的正中央。前兩句的主要信息都圍繞“巨石”的地理位置展開。換言之,譯文通過改寫“滟滪堆”的地理位置,將其推到公共視域的中心。按譯文的行文來看,“powerful waves”若是承接“the river”,則該河是否也太不平靜了些?其從年末至年尾(year in and year out)一直在強烈地拍打處在正中央的“滟滪堆”,仿佛“滟滪堆”遭受波浪拍打的“凌遲”頓時有了別的深意。
至此,第三句的“人心不如石”,可見前兩句頗費周折地以“滟滪堆”為中心的畫面鋪陳,究其原因還是為了指向人格化敘事。“懊惱”可以是敘事對象的心理活動,也可以是敘事者的心理活動的直觀,暗示內心糾結不安。若此詩的敘事對象是本人“懊惱”,則“人心”則是非敘事者本人;若此時的敘事者是作為旁觀者,敘述對象是另有其人,則“人心”即為敘述對象心中的又一敘述對象。第四句的“少時”蘊含“反復無常”之意,而“東”“西”則是抽象意義上的橫向活動范圍閾限,如此,不斷移動的“人心”跟處于定點的“城西門前”的“滟滪堆”則形成一動一靜的鮮明對比。“人心不如石”的隱含意義則是對其在處理事務之中的游移不定、三心二意的描寫。若把“人心”直接具象化于“負心漢”,也可猜出詩中發出感慨的敘述者的心思。譯文遵循原文的構圖格式,上圖是目之所見的自然現象,下圖則是人心的有感而發。原文的“人心”包含解讀的多重性,而譯文中“the human heart”則有所特指而并非泛指。下文的“東去”“西來”的動作主體,指的是與“滟滪堆”相似的“人心”載體即人,而流水指的則是世事變幻中所反映的人的精神特質。以“我”之“懊惱”之情視角觀之,則應對“人心”有更清楚的態度判斷。 譯文的“sad”表達了“懊惱”的一面,但并非全部。原文中的“我”應對特指的“人心”還有不滿、憎恨的情緒,但在譯文中最終則回落至“我”的內指的情緒悲傷(sad)。譯文的“awhile”描述的時間跨度較長,而“a split second”則是瞬間的定格,描寫了“人心”在“東”的停留有一段時間,而忽然轉向“西”的方向則顯得猝不及防,行文故意制造突兀之感,以達到“我”之情轉向讀者的共情。這個“人心”的指向也就走向了虛無。可見,譯文若過度依賴直譯,則可能會罔顧詩意,消怠詩情。
4 《竹枝詞(之七)》中艱途的“人心”隱喻英譯
如果說《竹枝詞 其一》與《竹枝詞(之六)》都是以人們可以直觀感受和把握的自然之物來借以闡述人心不可測的特性,那么《竹枝詞(之七)》則是以更為抽象的“艱途”來進一步描述人心的不可測。
原文:竹枝詞(之七)
瞿塘嘈嘈十二灘,人言道路古來難。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閑平地起波瀾10[41]。
譯文:song of the bamboo branch No.7
the qutang gorge has twelve rapids / the river rushes the channel / with a long swish and a roar / people have said since the old days / it’s a hard way to go whatever you do / what a sorry business this is / how pitiful the human heart is / the rapids make wild waves in the gorges / but the trouble you make is shameful / when things run as smooth as open water10[41]
該詩作依舊采取“景語”聯動“情語”。景語中的“瞿塘”,自古以來以地勢險峻著稱,“十二灘”的湍流險急、交通不便的險惡環境如在眼前。“嘈嘈”系模仿猛浪若奔的水聲,視覺的呈現和聽覺的刺激雙管齊下,開篇題眼給讀者帶來“險”的真切感受。第二句采取側面描寫的手法,用旁觀者的第三視角給“瞿塘”的艱難險阻下個定義,即“道路難”。如此天險面前,人類欲征服自然的雄心壯志也難免碰壁、知難而退。詩作采用白描、正面的手法描寫自然險惡山水,從側面襯托其阻塞交通的地貌險勢。原文中形容湍流的擬聲詞“嘈嘈”二字經“厚譯”處理后譯為“with a long swish and a roar”。“swish”形容聲音帶有“嗖嗖”的特質,頗有風馳電掣之勢;“roar”則有熊吼虎咆的威猛之勢。原詩依然是“借景抒情”,若景語設置有偏差,則接下來的抒情也自然會移位。譯文的遣詞造句描述了瞿塘峽雄偉壯觀的自然觀景,而少了些應該突出的“艱險灘涂”的悲嘆。鑒于對應下文的景語的缺乏,譯文中的“it’s a hard way to go whatever you do(對譯“道路難”)”的轉承則顯突兀,因為此譯句中描述的“難”,較難在描述波瀾壯闊的風景之談的前文中找到關于描述情感上“難”的積淀對應。瞿塘峽在譯詩中只處于“被看”的位置,而非“被征服跨越”的位置。原詩中的“人言”是詩人基于瞿塘峽的自然環境險惡而發出的對人世間的道路坎坷的慨嘆,屬于描寫非自然的聲音。譯文把“長恨”譯為“what a sorry business this is”,把“人心不如水”譯為“how pitiful the human heart is”,難以從譯文中所描述的“人心”與瞿塘峽的奔涌澎湃的激流建立關系。此外,“it’s a hard way to go whatever you do”中增補的“you”的人稱主語按照原文的提示也只是泛指;而到 “but the trouble you make”的“you”則變成了特指,使得整首詩的指向性變得明確起來,好像是在針對特定的事件和人物發出的討檄。
“長恨人心不如水”的“人心究竟比水差到哪兒去”的討論,可落腳于水只有自高往下的流動中才有波瀾之勢,讓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如瞿塘峽的十二湍哪怕再艱險,也是可以讓人摸得透的。即人的肉眼可看出瞿塘峽的水急湍流,但卻難以看見彼此人心的波動起伏以及其背后的陰險算計。詩人苦于長期頗受人心難測之累感慨道,處于“不可說”的人心,其實比“可言說”的“道路難”難多了,表態不亞于對工于心計的“人心”的譴責,同時也表明了詩人的光明磊落。末句的“等閑平地起波瀾”再次說明“人心”的不可測性。水在“等閑平地”難起波瀾,但“人心”則會違反自然的常態而無事生非。從這意義出發,譯文將其譯作“the trouble you make is shameful”意義則顯得狹隘,而且“shameful”的增補也帶有強烈的偏向性,緊接著末句的“when things run as smooth”似把詩人本身也圈在某個特定敘事其中,把詩人與所譴責的“人心”的特指對象并置在同一畫面中,跟原詩的詩人看似超然的借景抒情的普遍意義有所不同。
總體而言,文化的異質性導致這幾首《竹枝詞》的概念隱喻的翻譯難以做到翻譯對等。通過仔細對比分析,以上三首《竹枝詞》的英譯中體現的層級性(“人心”概念隱喻翻譯中重建的語境內涵)、關聯性(“人心”概念隱喻翻譯重建的語義銜接)和動態性(“人心”概念隱喻翻譯中重建的詩學價值),與概念隱喻中所要求的轉換程序(transfer procedures)”“文本結構(text-typologies)”和“文化特性(cultural specificity)”均密不可分。
5 結語
概念隱喻的翻譯除了關注原作信息的翻譯傳遞,同時也需注意原作的美學價值的再現,詩詞翻譯尤為如此。劉禹錫創作的《竹枝詞》景語豐富,以兒女之情為基調,抒發了自身對人心的認識和感觸,詩中的隱喻意象生動。翻譯中,隱喻的闡釋與文化緊密相連,隱喻的翻譯尤為如此。“譯者帶著自己的先見與編輯和目標讀者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溝通,逐漸達成視域的融合”[11]。所選三首《竹枝詞》的景語的視覺化圖景在英譯文本中的再現,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替換和改寫。許淵沖的英譯本和王守義、約翰·諾弗爾的英譯本基本采取散文詩的形式改寫原作的詩體,以求生動再現詩韻。文章以劉禹錫的三首《竹枝詞》的翻譯討論為例,可見概念隱喻對討論中國古詩詞隱喻的翻譯有著一定的啟發,未來研究可對原作與譯作的隱喻轉換與文化特性的闡釋方面做深入探討。